潘卡吉·米什拉评《美好时代的背后》:争夺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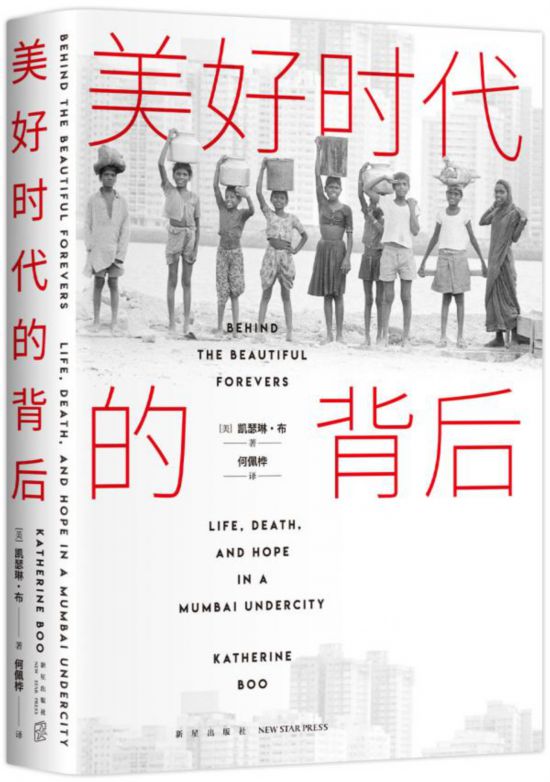
《美好时代的背后》,[美]凯瑟琳·布著,何佩桦译,新星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288页,69.00元
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普里莫·莱维讲述了一段经历,这段经历让他被关押在奥斯维辛的许多同伴都受到了致命打击。他写道,在进入集中营时,他曾希望“至少在不幸当中,同伴会团结一致”。然而,恰恰相反,那里只有“一千个封闭的个体,他们之间形成一个绝望的丛林,彼此不断争斗”。这就是莱维所说的“灰色地带”,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网不能简单归结为受害者和施害者这两大团体”,在这里“敌人在周围,也在内部”。
把在孟买机场边一个叫安纳瓦迪的贫民窟中自力更生的一群人,和莱维笔下在纳粹集中营挣扎求生的关押者相提并论,似乎很不合适。(安纳瓦迪是凯瑟琳·布处女作的创作背景,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废品回收者阿卜杜勒和他的朋友及家人在几个月内的生活。)毕竟,那些勇敢的“贫民窟居民”(slumdogs)可能是印度的下一位百万富翁(至少在最近的一部虚构作品中成为了百万富翁),是能够享受安纳瓦迪四周五星级酒店的幸运的百分之一。凯瑟琳·布现为《纽约客》专职作者,2000年任《华盛顿邮报》记者时曾获普利策公共服务奖。正如她所指出的那样,按照印度官方基准,他们不能被算作穷人,而属于“1991年以来摆脱贫穷的约一千万印度人口之列”,当时,中央政府“接受了经济改革”,他们便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史中最激励人心的成功故事之一”,在这类故事中,一个充满自驱力的经济体系已经准备好用财富奖励那些积极进取、随机应变的个体。
的确,在安纳瓦迪,“希望”是一种比丢弃的瓶装Eraz-ex(印度的修正液)更常见的麻醉剂,Eraz-ex是阿卜杜勒的拾荒朋友常常吸食的一种毒品。贫民窟居民“如今不时谈论起更美好的生活,仿佛命运之神是周日会来拜访的某个表亲,仿佛未来将和过去迥然不同”。然而,凯瑟琳补充了更多细节:“安纳瓦迪每两个逐步往上爬的人当中,便有一个陷入灾难。”
包括阿卜杜勒在内的许多贫民窟居民都是通过与更不幸的邻居比较后,才有了自己在向上走的感觉。那些邻居是“可怜人”,他们“必须诱捕老鼠和青蛙,油炸后当晚餐吃”,或者“吃污水湖畔的灌草丛”。从困境重重的农村逃到孟买的移民导致城市廉价劳动力过剩,所以被粉碎机切断手的男孩才会“任截断的手流着血”,反过来向老板保证,他不会报告这起事故。
一个两岁女孩可疑地溺死在水桶里,一个父亲把一锅煮沸的扁豆倒在他生病的孩子身上。凯瑟琳解释道:“身体不好的男孩女孩也会被处理掉,因为昂贵的医疗费用会让整个家庭破产。”她还写道:“贫民窟的女孩子不断地在各种可疑情况下死亡,只因为大多数贫民窟家庭都不像有钱人家负担得起超声波费用,能在女婴出生前堕胎。”
即便是成年人,也会像苍蝇一般殒命。阿卜杜勒的一个朋友死后眼睛被挖了出来;被撞伤的男人躺在通往机场的道路上流血致死,无人过问。还有凯瑟琳经常跟随采访的拾荒者,他们的疮口时常生蛆。“坏疽蚕食手指头;小腿肿成树干那样粗。阿卜杜勒和他的弟弟们时常打赌,谁是下一个死去的拾荒者。”
对于接连不断的死亡,安纳瓦迪的居民早就习以为常。阿卜杜勒和他的朋友们“大致接受了这个基本的事实:在日益繁荣的现代化城市里,他们令人难堪的生活最好局限在小小的空间内,他们的死根本无关紧要”。
死去的人甚至可能给生者带来麻烦。所以,阿卜杜勒脾气火爆的邻居“独腿婆子”法蒂玛引火自焚时,一小群人在一旁围观,却无一人伸出援手:“成年人三三两两回去吃晚饭,几个男孩子则等着看法蒂玛的脸皮会不会脱落。”把法蒂玛送去医院时,她的丈夫发现嘟嘟车司机因为担心烧伤“可能损害椅套”而拒载。
附近的警察在安纳瓦迪居民眼中完全是恐怖的代名词。他们会强奸无家可归的女孩,“会高高兴兴地把鼻涕擤在你的最后一块面包上”。警察甚至怂恿法蒂玛诬陷阿卜杜勒一家,好向他们一家索贿。一名政府官员还威胁说,不给钱的话,她就去找人做假证。
如果没有贱民阶层,印度虚有其表的民主制度和刻薄的新资本主义都是行不通的,无法减轻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残暴。安纳瓦迪根本不是无畏的希望、勇敢的人类品质或诸如此类事物的例证,相反,它成了一个灰色地带。这里的每一个居民都自成一体,用普里莫·莱维的话来说,除了“维护和巩固”他们“和毫无特权的人相比所拥有的既定特权”,他们什么都不想要。凯瑟琳笔下,甚至那些相对幸运的人,也会“在蚕食其他穷人生活机会的过程中改善自身命运”。
尽管描述了城市底层间的残酷争斗,《美好时代的背后》(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书名源自遮挡着安纳瓦迪的意大利瓷砖广告牌,上面写着Beautiful Forevers的广告语)并没有沦为一本暴行记录册——如果是,警觉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或许会视其为一份“下水道检查员报告”(1927年,美国历史学家凯瑟琳·马约[Katherine Mayo]出版作品《印度母亲》[Mother India],抨击印度的社会、宗教及文化,尤其是印度对女性和低种姓人群的态度。该作品引发许多印度独立运动人士的强烈反对,甘地批评其为“下水道检查员报告”),因而对此嗤之以鼻。这本书是甘愿冒险、让自己长期待在安纳瓦迪的成果,叙事围绕许多经过仔细调查后了解到的个人生活展开,夹杂着巧妙却又浅白的分析。文本蕴含的巨大文学力量来自凯瑟琳清醒而又优雅的行文,她偶尔会热情洋溢地使用新造的词汇(Glimmerglass Hyatt,意思是“玻璃闪耀的凯悦酒店”)和巧妙的比喻(每天晚上,他们扛着装满垃圾的麻袋,沿着贫民窟的街道归来,就像一群牙齿松动但一心想赚钱的圣诞老人)。

但《美好时代的背后》首先是一部道德追问之作,它承袭了奥斯卡·刘易斯和迈克尔·哈灵顿的伟大传统。正如凯瑟琳在后记中所解释的那样,孟买“极端和并列的不平等”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这个社会,什么是机会的基础结构?市场和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让哪些可能性如虎添翼,又让哪些可能性付诸流水?……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不平等的社会起来造反?”她目光敏锐,既能看到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关键事实,也能捕捉到亲密家庭关系中丑陋而又荒诞的现实:一个女大学生正在努力搞清《达洛维夫人》的情节,而她关系最好的朋友却被迫接受包办婚姻,最后吞下老鼠药自杀。(死前,医生还从她父母那儿敲诈了五千卢比,约一百美元。)
你会不时想起这本书的全知叙事者。凯瑟琳并没有出现在叙事中,这么做或许是明智的。有关一个美国白人记者如何打消采访对象的怀疑(以及应对警察直接的敌意),或者如何解决第一世界与第四世界密切接触时所产生的诸多伦理困境的故事,属于另一本书的内容。凯瑟琳不是在亚洲蛮荒之地游走的故作天真的解说者或无所畏惧的冒险者,相反,她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能力,并于无形之中将此前所遭遇的困苦、她付出的努力以及她对意识形态主张的质疑融入每一页文字之中。
西方常常称赞印度的民主制度,但凯瑟琳发现,民主在印度变成了一个权贵间互惠互利的内部网络:定期选举被纳入了一场“建构梦想的全国性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印度的许多老问题如贫穷、疾病、文盲、童工等,都得到积极解决”,虽然“腐败以及较不弱势者对弱势者的剥削等其余的老问题,[仍]在极少受到干预的情况下持续运作”。
凯瑟琳也能察觉到,为什么许多富裕的印度人对民主越来越不耐烦,甚至是越来越轻视,和世界各地其他有钱人一样,他们想削弱而不是加强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义务。她指出,这部分印度人“雇用私人保安,过滤城市的自来水,缴付私立学校的学费。多年来,这些选择发展成一项原则:最好的政府,是一个不干预的政府”。
近期,许多富裕的印度人支持一项半甘地式的抗议运动,提出许多关于印度腐败的平庸看法,凯瑟琳巧妙地避开了这些观点。她让我们看到,腐败绝不是一种恶性的外在增长,而是印度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她写道:“在有权有势的印度人当中,机会分配往往是内线交易”,而“在一个被腐败窃取了许多机会的国家,腐败对穷人而言,反倒是仍未消失的一个真正机会”。
《美好时代的背后》完全立足于印度混乱的当下,对相对而言不那么压抑的过去只是略微提及——在阿卜杜勒看来,那个“和平年代”听起来就像出自神话故事,那时,“穷人俯首听命于各自的神明,从而更友善地对待彼此”。这似乎是对东方宿命论过于浪漫的表述。不过,确实如此,几百年来——自从这座城市出现、被英国自由贸易者及其在本土的合作者建立以来——乡村地区的移民不断被吸引到孟买,却从未像现在这般悲惨不幸且手无寸铁。
这个城市最受欢迎的出口产品——电影和音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村移民试图在这个难以融入的大城市里重建他们所失去的社区传统。但和上一代移民不同,重返乡村生活、重建社区团结的美梦已经不属于安纳瓦迪的居民了。凯瑟琳在书中一处短暂的离题中点明了这一点:在印度西部一个农村地区,农民被迫脱离自给自足的经济,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在过去十年里,数以千计的农民因此自杀。
在这里,许多居民“不再相信政府会增加他们财富的承诺”,如凯瑟琳所解释的那样:“大规模企业和政府的种种现代化方案,摧毁了他们的土地和传统生计,于是他们协助革命分子持续了四十年的运动。这些游击队利用地雷、火箭筒、钉子炸弹和枪支,对抗资本主义及印度政府。他们的行动,如今遍布印度六百二十七个地区当中的三分之一。”
在“资本主义伟大的成功叙事”中,这些革命分子似乎是一种奇怪的、不合时宜的侵扰。但对他们来说,就像对那些剥夺印度农民的公司和政府来说,现代世界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零和游戏。不足为奇的是,阿卜杜勒的母亲也“让自己的儿子学会面对残酷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个时代,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他还小的时候,母亲就让他了解,他必须成功”。
然而,凯瑟琳以令人心痛的细节表明,阿卜杜勒受到的训练并不完整。在被诬陷谋杀邻居,而后进入一个“邪恶”的司法体系中后,阿卜杜勒开始明白“母亲并未让他做好独自失败的准备”。
近年来,印度表面上的“崛起”吸引了不少文学界和新闻界的投机者,定期进行选举、有许多热衷讲英语的人的印度更容易被纳入西方的进步叙事。因此,近期关于印度的书都不自觉地充满了关于这个时代的陈词滥调,谈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如何促进机会的全面爆发,从而在印度最贫困的人群中燃起希望。
而凯瑟琳描述的是:全球化时代下,机会在已经拥有特权的人身上不断累积,政府仍旧贪污腐败、无法有效运转,多数公民被困在财富与消费的幻想中,甚至希望也变得私人化,与任何有关共同富裕的信念割裂开来——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好时代的背后》不仅仅和印度虚幻的“希望”新文化有关。因为正如凯瑟琳所写的那样,“展现在孟买的事情,也展现在其他地方”,比如内罗毕和圣地亚哥、华盛顿和纽约。“在全球市场资本主义时代,期望和不满在个人心中狭隘地滋生,使人对共同的困境感到麻痹。穷人并未团结起来,反而为临时性的微薄收益彼此激烈竞争。”
她进一步解释:“穷人为政府的选择和市场而责备彼此,我们这些不是穷人的人,也同样动辄严厉地指责穷人。”同时,“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穷人间的争斗最多只掀起“微弱的涟漪”。因为在孟买这样的地方,“有钱人的大门……仍未被打破……穷人则干掉彼此。不平等的世界级大都市,在相对的和谐中继续向前迈进”。《美好时代的背后》以一种平静的方式打破了这种和谐,比许多言辞激烈的文章和理论都更加有效。近几十年来,一些观念的出现使得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的“灰色地带”成为“成功叙事”的一部分,而这本书超越了它的地理背景孟买,为这种观念鸦片提供了一剂有力的解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