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围攻美因茨》:由此证之


《围攻美因茨》德文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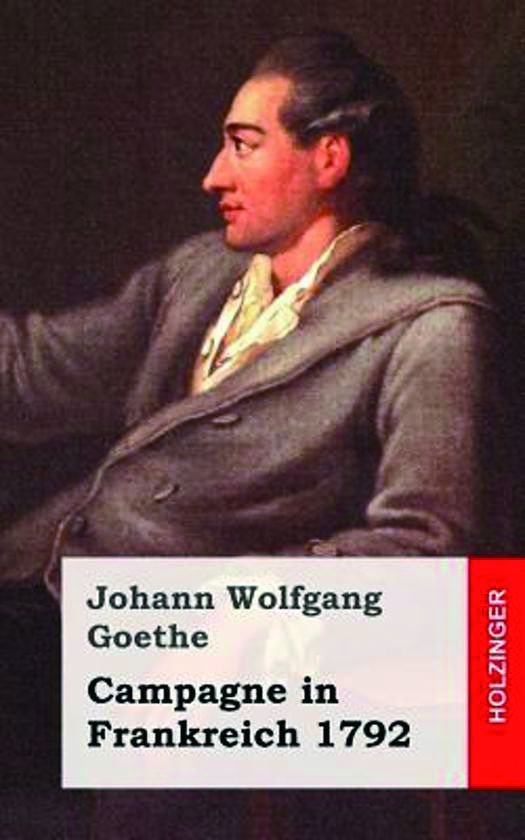
《进军法兰西》德文版封面
约200年前(1822年),歌德文库里的两部战争文学《进军法兰西》(Campagne in Frankreich)和《围攻美因茨》(Belagerung von Mainz)首次刊印。《围攻美因茨》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它有很大的回忆、自叙性成分,主要依据是歌德44岁那年的一次参战经历和日记,故而可以将书中的叙事者与作者歌德直接联系起来。那次战争是1793年春普奥联军对德国莱茵河畔城市美因茨发动的围攻之战,起因是1792年10月,法国军队反击普奥联军先前对法国的干涉,进军德国占领了美因茨,联合那里的革命党人于1793年3月成立了一个“美因茨共和国”,还计划要与法国合并。普鲁士和奥地利又立即组织起一支联军包围了美因茨,要恢复那里的封建秩序。歌德也参加了这场历史上的“围攻美因茨”之战。
歌德参战?匪夷所思。因为歌德自诩是“和平的孩子”,从来就是反对战争、反对暴力的。如法国爆发大革命时,歌德曾为此欢呼,但当雅各宾党暴力行为传到了他耳朵里,态度就发生了大转变:“说我不能做法国革命的朋友,这倒是真话,因为它的恐怖行动离我太近,每日每时都引起我的震惊。”又如1813年拿破仑军队入侵德国,德国人纷纷行动起来保卫家园,歌德却持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在把玩来自中国的玩意儿,在为他喜欢的女演员修改台词,得知自己儿子已自愿报名要去抵御法军,还使用了低下手段进行阻止。在歌德看来,战争彻头彻尾只是人类的祸害,不管以什么名义,即便是拿国家命运和民族存亡说事,也没理由让人们去遭受巨大牺牲。据托马斯·曼了解,歌德说过这样的话,“一家农户遭毁,才是一个真正的不幸和灾难,而‘祖国沦亡’,不过仅仅是一种说法上的而已。”真让人有些错愕。
这样一个极端和平主义立场的歌德怎么又去参加战争了呢?实际上,歌德是因为要陪伴他的君主卡尔·奥古斯特·冯·魏玛公爵,才去参加了围攻美因茨那场战争的。这个公爵带领他的军队加入了去围攻美因茨的普奥联军,歌德作为其枢密顾问还司管着军队事务,自然得跟随。美因茨离歌德故乡法兰克福不远,歌德青少年时期常去。1774年12月的一天,也就是在美因茨城内,歌德与当时还未亲政的卡尔·奥古斯特一席畅谈,决定了当时才20多岁的他的未来人生轨迹,歌德因此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普奥联军对美因茨的围攻发生在1793年的3月至7月。大约过了30年后,歌德才将当年参战经历整理出来,写成一个比纪实文学叙事上更为自由,所包蕴内容上也更为丰富的小说类作品发表。
那时的欧洲/德国,不断有大大小小的战争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应此情形召唤,有人在注目战争方略,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就在这个时期写了他的《战争论》(Über den Krieg),有人则在敲打被战争阴霾覆盖的人类社会进程。歌德属于后者。围攻美因茨之战给他留下了梦魇般记忆。近30年过去了,战争血痕虽然早已干涸,历史伤口并未因此愈合,记忆仍旧犹新。身为一个作家,歌德认为有必要记载下那场战争,既要清算战争之恶,也有要为自己倾吐之意。
与众不同的战争文学
此时歌德73岁,透过拉开了距离的时空,已把那场战争看得更加清楚。但在魏玛生活的特殊环境,已使歌德变得谨小慎微的中庸,温言软语的沉稳,如恩格斯对他的评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这个时候的歌德,文字避开机锋,不会去痛痛切切招惹当年发动战争的人和宫廷的不悦,但也不会放弃机会,找到适当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个背景下歌德书写《围攻美因茨》,用的是日记体文体,文本以“日期”分段保持了线性时间顺序,各段叙事长短不一,以叙事者经历、见闻、所思、所感连缀,接榫中隐含的整部作品构思,是人与战争时间的关系,或曰人在战争期间的所为。叙事叙述任达不拘,话里行间常埋藏有未直接言说出来的东西,对于熟悉那个时代的读者而言那些暗指或暗示又都不难领会。宏观和微观交融,行营生活和战争战事交替,选择一些历史人物、现场和情景,用“我”的视角连接事件与个人——歌德写下的这部作品故事是零散化的,无惯常战争小说那种情节波澜,曲折延绵。
此前在德国文学里,战争题材可谓就是金戈铁马弘扬圣武,为诸侯、领主等统治者所谓英雄雄才伟略写意造像、树碑立传的同义词。歌德的《围攻美因茨》则完全不在这种气象内。开篇时刻,书中的“我”借他人之口重复了他以前(即在歌德上一部战争文学《进军法兰西》里)说过的话,“此时此地,世界历史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你们可以说,我曾亲自在场”,给人一种似乎在跟着创造历史的激情自信、踌躇满志的感觉。但将作品一页页读下来,读者会发现,在数个月的战争里“我”记载了很多,唯独没有记载战争统领的气吞山河,也没有记载战争出英雄的粗犷大气。
歌德毫无英雄和英雄主义写作用意,笔下的“我”只是在以战争的历史线条和个人内心的双重角度记载着他的战争经历和日子。记载不论详略,所定格出来的图景显示出叙事在暗地里服膺于歌德的一种反对战争叙事学。如,“今天是6月8日,我在继续奋笔疾书我的《列那狐》;与最最尊贵的公爵一同骑马去了达姆施塔特营地,拜见了封地伯爵,这位仁慈大人一直对我亲切,见着他我满心愉悦。晚上,茨魏布吕肯的马克西米利安亲王,还有封·施泰因上校,也都到头领这里来了;几人交谈了一些事;最后说到即将开始的围城,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个记载就表面日常的叙述暗藏机锋,走笔恰到好处把歌德的军营生活和战争立场透露得淋漓尽致。它有两个层次,一是让人看到在军营里歌德念兹在兹的是他的文学,在用投入创作方式度过战争的日子,二是让人看到在歌德眼里那个下令围攻美因茨的普鲁士“头领”根本就不值得对他表示敬意,对他的名字予以一提。
以“毁灭”视角记叙战争
《列那狐》(Reinecke Fuchs)是歌德根据法国中世纪流传的动物故事创作的一部长诗。诗中假托动物世界和形象,讽刺了德国宫廷的专制、盲目、强暴和强盗主义政策,讽刺了教会及神职人员的腐朽变质,讽刺了法国移民者的贪婪,对一个已经运转了上千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被欧洲人自己的政治颓败、风气堕落所毁灭,发出了一声声叹息。同样,《围攻美因茨》与《列那狐》形成互文,背后隐逸的艺术智慧一是在用虚构的方式脱离现实,二是在用非虚构的方式讲述随军。即是说,歌德在《围攻美因茨》与《列那狐》之间设定了一种话语隐喻,既是在对战争时间和空间的超越,又使得对《列那狐》的提及充满了启示《围攻美因茨》作品意旨的可能性。即是说,《列那狐》和《围攻美因茨》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构性的,共同构成了歌德对普奥联军围攻美因茨之战的拒绝,共同指向这场战争在歌德眼里同样也是一片毁灭:邦国体制的毁灭,社会关系的毁灭,城市建筑的毁灭,个体生命的毁灭,古老文化的毁灭,悠久传统的毁灭,人伦关系的毁灭,生存环境的毁灭,简而言之是毁灭着一切的毁灭。
如对美因茨遭到的毁灭,歌德就记载哀叹道,“这个用了数百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个各地的财富都曾往这里汇集的城邑,这个曾经的扩展和巩固信徒们信仰的圣地,现在已是栋塌房坍,华屋丘墟,成了碎片和瓦砾。”历史上,普奥联军于1793年5月初完成了对美因茨的包围,从6月底起开始对这个城市实施重炮轰击。此前在1792年9月的法国马恩省瓦尔密村战役里,普奥联军曾被法军以重炮重创,不得不铩羽而归。现在普奥联军也使用这个战法,对歌德来说这是在用重炮自己焚毁自己的城市。以几个真实情形描述,歌德记载了炮火轰击下的美因茨:城里的标志性建筑或摇摇欲坠,或付之一炬,或面目全非,不仅民居住宅在遭殃及,就连花果树木也“无论怎样说都是遭遇了毁灭”。记载表明,面对战争这个人类未能避免的事实,歌德是在用“毁灭”视角筛选记忆,书写了围攻美因茨那场战争。
战争对人生命的毁灭,歌德也有记载:“枪战不久就停止了……夜间丢了性命的无套裤汉卧尸在地,状似侏儒,衣衫褴褛,与我们威武的骑兵形成怪怪的对比;死亡已将他们统统放倒,不加任何区别。我们的好上尉拉·维埃是第一批倒下中的一员,还有封·福斯上尉,卡尔克罗伊特伯爵的副官,被射穿了胸部,大家清楚他已是命不久矣。”生命就如同草芥般消逝了或就要消逝,歌德的记载只撬动冰山一角,并不深入战场写出它的鲜血淋漓,也不展开生存与死亡的形而上思考,只以“夜间丢了性命者卧尸在地”的言说表明在他眼里战争的最真实形态就是每个丢了性命者都毫无区别地被收割了生命的死亡。时间隔了近30年,战争造成一片尸体,把死亡突然摆在还活着的人面前的体验,对歌德来说仿佛仍在昨天。歌德这里唏嘘的“死亡已将他们统统放倒”中的“他们”,也包括普奥联军的人,即是说也包括人们通常说的“自己人”。对“自己人”的倒下也云淡风轻,没有哀恸,没有沉重,没有战争这一特定环境的爱与恨,只有为所有失去生命者感到的不值,显然,歌德虽在随军普奥联军,骨子里却是个保持距离的观察者,思想上并未站在发动围攻的普奥联军一边,而是将自己最坚决的立场放在了不选边站队的一侧。
特性独立的歌德
不仅如此,歌德实际上甚至超越了战争文学的阵营规定性,还有对法国人英勇的暗示之笔,对“自己人”的表现则笔触反讽,大喝倒彩:“河面上的响动吸引了我的注意:法国人的小船在奋力划向小岛,奥地利人的炮台在不停向他们射击。水面上跳弹纷飞,于我来说真是一出未曾见过的戏:首批炮弹射向河中,激起一些数尺高的水柱,尚未散落下来,已有第二批炮弹降临,又致新的水柱飞起,强度与前批一样,只是高度有些不同。然后是第三批、第四批,越往远处水柱激起越矮,直至最后到达法国人的船前,只是继续在对水面施加影响,偶然能对小船形成危险。对这出戏我怎么看也看不够,这可是一发接着一发炮弹,一柱接着一柱水柱,与此同时旧的水柱还没有消失的难得一见场面呀。”战争从来都是难以预料的例外状态,但战争是一出“戏”,一出奇观意义上的、儿戏意义上的、荒诞意义上的“戏”,这在德国战争文学中属于首次。
歌德这段言“戏”文字,有揶揄精神张扬,将冷眼看待战争如同在观看一出戏码的“游戏”观铺展到了极致。从美学层面看歌德这段话以形象跳荡语言把真枪真炮的战争调侃化为啼笑间作的滑稽,从思想层面看它是在挑战当时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对战争的思维模式。在普奥联军围攻美因茨那个时代,在歌德所在的生活区域,崇拜英雄,讴歌强者,诉诸武力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主流,是普遍的社会心理,是不容违逆的政治话语。歌德在其宫廷当臣的那个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歌德就形容他喜好军事“如同鱼对于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就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就在告诉人们战争似乎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即便不是在强化人们对战争的期待和膜拜,也是剥夺了人们对战争的思考和质疑。《围攻美因茨》则敞开了一个思想意识特立独行的歌德,打破当时普遍的战争认同,用“戏”、“好笑”、“有趣”、“怪怪的”等字眼描写普奥联军对美因茨的围攻,令人感觉兴味绵长,思路不羁。这不是歌德叙事语言上的俏皮,而是地地道道的颠覆和讽刺,表明在歌德眼里战争根本就是毫无意义。
因为战争除了毁灭生命和财产等外,它的巨大毁灭性还在于它使人的人性丧失,良知泯灭,社会的道德伦理全面崩溃。歌德清楚战争是人性的炼狱,《围攻美因茨》里“我”就议论说,“人就是这个样子,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对于不可避免的,他逆来顺受,对危险、紧急和烦恼间出现的空隙,他便以娱乐和寻欢来充填之。”说的是战争使得人的心理变得反常,行为变得乖戾,在死亡随时有可能降临头上的焦虑下一有机会就寻欢作乐,放纵自己,致使传统的规矩、约束、尺度等统统失去了说“不”的力量,致使人性上原来的“善”与“恶”平衡被打破,人性中的黑暗和残暴释放出来,人形同于兽。
在上一部战争文学《进军法兰西》中,歌德就记载了战争使得人性裂变之细末发梢的一件,在整个世界文学范围内都堪称是个经典:士兵收缴了牧羊人的羊,貌似付了钱,付给的却是以在法国大革命中已经掉了脑袋的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名义签押的代金券,实际上就是废纸。牧羊人无奈又无助,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的羊转眼间已被宰杀:“他们像孩子般呵护的羊被急着要吃烤肉的士兵就在他们的脚边破肚开膛了;我不得不承认,不曾有过比这还要残酷无情的残忍场面呈现在我的眼前,不曾有过比这还要更为痛楚至极的男人痛楚进入过我的心境。只有在看古希腊悲剧的时候曾让人感到过如此的浹髓沦肌,里外苍凉。”悲郁的笔调,既是在为牧羊人哭泣,也是在为人类悲剧写真。这部《围攻美因茨》里,歌德也记载了平民百姓的非人遭遇,读后同样令人黯然神伤:“6月24日。正如预料的那样,法国人和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人感到了日益严重的给养压力,便将老弱妇孺强行装上马车,往卡斯特尔方向驱赶。这些人来到城外,又被同样冷漠无情地驱赶了回去。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呐,被城内城外敌人驱来赶去的那个绝境,超出了所有的语言言表。”悲悯倾注的记载,再次表明在围攻美因茨战争中歌德只允许他扮演一个角色,那就是他自己,一个反对战争和反对暴力的人,一个不选边站队的战争观察者和一个人类悲剧的记载者。无论是对美因茨遭到毁坏的痛彻之情,还是对人性道德裂变感到的呜咽之悲,皆出自于此。
人道主义基础质地
套用福柯说过的一个意思,重要的不是历史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历史的年代,对先前的一段历史进行讲述的时间,一定层面上看比所讲述的那段历史还有其意义。战争过去了那么多年后歌德决定要写《围攻美因茨》,就有追求这个讲述时间意义之意,用意就在于要用这部作品写作来对抗有“战争热”的当前。1810年,歌德公开了要将当年随军经历书写出来的想法。他的秘书黎默尔记下了他给自己确立的如何书写的主导思想:“如同往昔用人道主义对付野蛮人那样,现在是用人道主义对付专制的时候了:要恰当描绘和这样描绘士兵生活,让士兵感觉到:不幸是作为命令下达给他的;当他独自处事时,他的行为必须是一个人。” 士兵必须接受命令参加战争,这是士兵无力改变的“不幸”,但士兵应当如何左右自己的行为,便是歌德的思考。
歌德思考的是让人道主义成为士兵思想的主导。《围攻美因茨》里歌德写“我”碰到一个带着孩子逃出美因茨逃难在外的中年人,中年人谈了要对美因茨革命党人实施报复的想法,“我”听后立即一脸严肃地告诫这个中年人一定要放弃他的这个念头,“能够回归和平,返还家园了,就不要再用新的内战、仇恨和报复之事来污染,否则不幸就将周而复始永远不止”。不能让褊狭成为合理,人道主义才应当是指导未来生活的思维。以此点睛之笔,歌德瞬间将小说叙事升华到了一个新境界。完成了“他的行为必须是一个人”的给予,歌德在有史以来的德国战争文学中首次写出了人道主义新意,给本身篇幅并不很大的《围攻美因茨》写出了大河般宏阔。
“我”不仅直接在宣告人道主义思想,还有对人道主义行为的敢为敢行。历史上,1793年7月22日,法国人宣布投降,于24日和25日分批离开,26日,普奥联军开进了美因茨城。歌德讲了进城后他做过的一件事。那是他看见一群人团团拦住骑在马上的一男一女,叫喊着要打死他们,便赶紧上前喝开人群,那一男一女趁机逃离。“他们的不幸和仇恨并不给予他们权力,在我这里绝不允许发生暴力”,这是歌德记载的行为动机。歌德的朋友戈雷听了这事后指责歌德的做法不妥,一是有可能让众人迁怒于他,给自己造成危险,二是那两个美因茨革命党人在法国人占领期间说不定犯下过罪行,不该让他们未受惩罚就走了。歌德不愿以人道主义自夸,找了个理由解释,但戈雷固执己见,没完没了。歌德受不了那喋喋不休了,“我不断以说笑的口吻指着房前场地上的清静给他解释,最终变得不耐烦,说:我宁可犯下不公正,也不愿忍受无规矩,这便是我的秉性。”显然,所谓“秉性”只不过是歌德找的一句话来堵住朋友的唠叨而已。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法国人将歌德这话剥离语境,翻译成法语句子“plutot une iniustice qu'un desordre”(“宁可不义,不愿无序”),用来作为抨击德国人就是个野蛮民族的证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智慧、知识、文化的最高代表歌德都说自己是个并不在乎公义之人,由此推知,整个德国人群体难道不都是宁可不公正,也不能被所谓无规则的野蛮性充斥。还有意思的是,法国人掐头去尾翻译的这句话又被德国人回译进了德语:“Lieber eine Ungerechtigkeit als eine Unordnung”(“宁可不公正,也不得乱秩序”),被一些不知原本上下文的德国人引用,成为他们批评德国人毛病的一件利器。殊不知,歌德这句话背后是战争语境下的人道主义境界彰显,经天纬地,叹为观止。
“卒章显其志”
读到歌德回忆他当年阻止私刑,读《围攻美因茨》已到其结尾部分。这里,歌德先是讲述他进入美因茨后看见战争造成的伤痕累累,然后颇有意味地说,还在围攻期间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却被人嘲笑他写这篇文章像个孩子和新手,而借嘲讽人之口表示了他对这篇文章的希望:希望人们对它发生兴趣,希望它能在德国生发作用,还说它“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有益的和有意义的”。这是一篇什么文章呢?能让歌德认为它如此重要,要对它进行如此铺垫,要在全书结尾处作为压轴将它提及,要如此“点拨”读者对它引起注意?这篇文章必当是深意存焉。
歌德道出了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要促使一件难做的和宏大的事得以完成,须得由不同的人组成的社会合作为之,每个人都从自己的方面共同参与。”深层的文字往往大于作家。歌德这句话清晰表达,根据歌德在书中设置的战后情景与语境,又有可从多个层面解读的可能性和开放性。驻足阅读,思索含义,层层递进,剥笋抽蕉,歌德这是在说:必须认可和促进社会是多元结构的,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社会的建设需要不同人的合力,需要每个人的贡献;又是在说:应当要摒弃纷争和仇恨,对即便是先前的“敌人”也要予以和解的精神;就是在说:要在认可不同之中求得文明共存发展,共建文化社会;即是在说,还在一场血与火的战争期间,歌德就在思考和提出了对战后人类社会应当如何修复和重建的问题。
所谓“卒章显其志”是也。《围攻美因茨》结尾处歌德这段话所涵的人道主义思想,在那个年代历史情境下是弥足珍贵的,说它代表着人类至善境界也不为过。从比较文化角度,歌德这个人道主义思想与我国“和而不同”思想有息息相通之处。作为歌德生活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我国儒家学说倡导的仁爱和以人类大同为崇高的思想,与欧洲思想家们倡导的理性主义、宽容精神和世界和谐理想有相互吻合之处;歌德阅读过大量的有关中国书籍,自叙曾“全身心地投入对中华帝国的钻研中”,被誉为是“魏玛的孔夫子”。当然,这里无意定将歌德的人道主义思维与我国的“和而不同”思想联系在一起,人道主义信念是歌德精神的一个本然存在。想说的是,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观念的歌德,有这样一个走在别人前面为人类情况担忧的歌德,有这样一个在其他人还持冷漠态度时就已在捕捉将要成为未来发展重大问题的歌德,即便是德国处于伶仟、虚弱、破碎、四分五裂时期,它在精神上依然是伟大的、富有的和坚强的。
历史似乎有这样一个特性:不断被人重复,直到教训被人理解为止。如何理解历史教训,《围攻美因茨》提供了一个启示。这部作品记载了战争造成的一片狼藉,也给我们记载了一个面对狼藉思考未来的歌德。人道主义是这部作品一个特别而重要的精神底色,造就这部作品的阅读回甘,是它能够抵抗时间侵蚀的思想精魂所在。正是因为有人道主义思想灌注,歌德成名二百多年来他的不少作品还是被人遗忘了,惟这部作品始终让人牢记着。二战后的1946年,包括美因茨在内的德国许多城市还是一片废墟,《围攻美因茨》被法国占领军军事管制委员会选中,编辑进一套“世界文学经典丛书”,就在美因茨出版,以期对此前追随了希特勒的德国人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之后这部作品又在德国接连再版了数次,最近一次是在2010年。歌德书籍再版史上这样情况不多,歌德这部卓然之书改写了歌德书籍再版史。德国媒体上的评论早已将它评价为是部德国文学标高之作和世界文学不朽著作。标高和不朽者必然会随着岁月流逝散发出历久弥新的芳香,永不耗尽它所传递的作者精神嘱托。作为外国人的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从中完全感受到歌德书写这部作品的出自心灵、为了心灵和创造心灵的文学高度,但应当是可以感受到歌德表达其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深度。深度在于歌德将他的文学不仅保存了人类灾难的真相,更在于指向修复灾难后的人类社会。再次回顾歌德为《围攻美因茨》确定的思想坐标:“现在是用人道主义对付专制的时候了”。说歌德将他的文学书写作为了一种社会责任、政治行动和人类道义担当,由此证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