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吉诃德》:阿拉贝拉出走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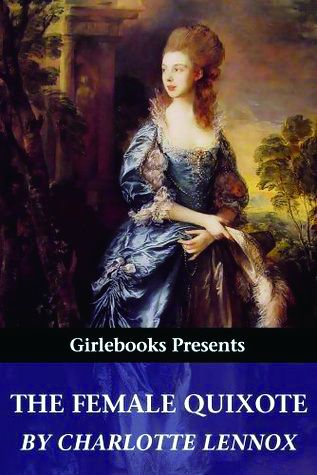
《女吉诃德》
《女吉诃德》,亦称《阿拉贝拉历险记》(The Female Quixote,Or The Adventures of Arabella),是18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特·伦诺克斯(Charlotte Lennox)的代表作。该小说是对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戏仿,1752年出版后受到文坛名家塞缪尔·理查森、亨利·菲尔丁和塞缪尔·约翰逊的一致赞誉,认为其思想性与艺术性几乎可以与同时期出版的《克拉丽莎》《汤姆·琼斯》和《兰登传》媲美。该书在后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简·奥斯汀《诺桑觉寺》以之为范本;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曾借鉴其人物形象;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则堪称“女吉诃德”的现代版——其悲剧精神可视为塞万提斯与伦诺克斯的合体。
正如堂吉诃德因沉迷骑士小说而陷于“疯狂”,小说女主阿拉贝拉阅读了过多的法国浪漫小说,结果“走火入魔”。堂吉诃德错将自己当成浪漫传奇中的骑士英雄,阿拉贝拉则错将自己当成浪漫故事中的恋爱少女(相信自己能用眼神“杀死”对方,并且坚信恋人有责任为之赴汤蹈火,同时又不得不备受煎熬)。当然,和唐吉诃德不同的是,阿拉贝拉不是与巨人风车搏斗,而是奋力反抗固化的社会观念。
阿拉贝拉生活在幽僻的英国城堡,由鳏居的父亲抚养成人。她自幼饱读母亲遗留的法国爱情小说——以斯居代里(Scudéry)夫人为代表,期待自己的生活也会同样轰轰烈烈,浪漫而美好。父亲在离世前宣称,如果阿拉贝拉不与堂兄格兰维尔爵士(Sir Charles Glanville)结婚,那么极有可能失去部分(甚至全部)财产。摆脱了父亲的威压,阿拉贝拉决定外出闯荡。当她初次涉足巴斯和伦敦的时尚社会时,仿佛童话中人物“乱入”现实生活,闹出了若干大笑话。在她看来,所有男人都心怀鬼胎、图谋不轨——格兰维尔接近她的目的只有一个:骗婚;他的竞争对手贝尔摩爵士(Sir George Bellmour)表面对她一味顺从,事实上只为满足他自己猎艳的虚荣心;甚至当格兰维尔的老父亲试图劝说这位“未来”的儿媳妇尽早完婚时,也被认为对她心存“非分之想”。于是她益发坚定“不婚”的信念。
最能体现阿拉贝拉荒唐念头的例子是园丁爱德华,他因为从城堡的池塘里偷盗鲤鱼而遭殴打,然后被驱逐——阿拉贝拉却坚信这是一位来自遥远国度的王子,他假扮仆人,忍受凌辱,只是为了带领她逃离是非之地。她的这一种执念,最初只是将到她府上做客的男青年身体抱恙误以为是为她害了相思病,后来则发展为处处“疑心生暗鬼”:晚上走在伦敦街头,她始终相信不远处马背上的男人尾随跟踪并试图诱拐她,于是鼓足勇气,跳入泰晤士河,差点断送性命。根据作者描述,当时她脑海中浮现的正是斯居代里夫人笔下的场景——她“将眼前的运河误作台伯河,向其全速奔跑,并纵身一跃,觉得自己就是克莱利亚(Clielia),并且也能像她一样游过去。”——小说中的克莱利亚投身台伯河,“以求保全自身,免受轻浮浪荡的塞克斯都(Sextus)的侵害”,正是阿拉贝拉意欲效仿的对象。获救之后,阿拉贝拉大病一场。医生(同时也是一位教会人士)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向她解释了社会现实和文学幻想之间的区别。阿拉贝拉如梦方醒:她“恢复了理智”,最终决定接受格兰维尔的求婚,从此过上安宁幸福的家庭生活。
尽管小说“大团圆”式的结局与主流社会价值观颇为契合,但小说人物展现出的“过激”言行,在保守人士看来无异于叛道离经,令人深感不安。尤其是阿拉贝拉面对一众男性,不但缺乏应有的敬畏,反而自恃美貌和才智,颐指气使,显然有悖于上流社会绅士淑女的传统道德观。作为父权制社会的代表和象征,阿拉贝拉的父亲首当其冲成为她反抗的对象。担心女儿沉溺于浪漫幻想不能自拔,她的父亲决定将此类“翻译得很糟糕”的外国小说悉数焚毁。目睹这一场面,阿拉贝拉为那些“将被投进无情的火焰”的浪漫骑士的命运感到悲哀,甚至一度悲观绝望想要自杀——在18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勇敢”的女性因生活打击而自杀,乃是寻常之事。熟读浪漫小说的阿拉贝拉对此心知肚明,自然也不缺乏这样的勇气;但她转念一想,觉得比自杀更好的报复手段无过于拒绝嫁给父亲中意的格兰维尔——如此一来,他老人家定当死不瞑目。
平心而论,格兰维尔出身名门,智勇双全,对阿拉贝拉也一见倾心,始终如一。阿拉贝拉却屡屡拒婚,颇有些无理取闹。倘若一定要找出搬得上台面的理由,只有一条,即格兰维尔没有做出“任何值得她去爱的事情”。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按照“浪漫的程式”来追求她。他的情感过于“炽热”,他的崇拜过于“亲密”,所以她要求他遵守骑士的爱情规则(rituals),与她保持恰当距离以示尊重。格兰维尔照此办理。但他既不像小说中的骑士“为爱憔悴”(反而日益增肥),也没有计划冒险远征,降妖除魔,然后在她的等待和期盼中凯旋归来。
为了证明自己的魅力,同时考验格兰维尔的“忠诚度”,阿拉贝拉曾下令,要格兰维尔杀死一名试图“跟踪并绑架”她的嫌犯,以此来展示他的“勇气”。当旁人提出此举可能涉嫌谋杀时,阿拉贝拉慨然回答:“英雄可以随便杀死坏人;爱杀多少杀多少。”——浪漫传奇中英雄人物从来不受人间律法的约束。她陶醉在浪漫小说编织的美妙世界,连衣着服饰,以及言谈举止都要一丝不苟地加以模仿。像堂吉诃德需要桑丘随行征战四方,阿拉贝拉也致力于找寻一名侍女,陪伴她开启冒险之旅。她在一所教堂遇到“迷人”的格罗夫斯小姐(Miss Groves),结果却发现,这位小姐15岁时便与家庭教师有染,后来又与一位已婚绅士产生婚外情(有两个私生子以及一段秘密婚姻)。这一类道德观念淡薄的女性往往为上流社会所唾弃,但阿拉贝拉对她却无端生出几分羡慕:根据描述,格罗夫斯小姐出身贫寒,打小“喜爱男性运动”——包括“翻越篱笆和横跨沟渠”,这些粗犷的运动使得她拥有了与其性别不符的强健身体,甚至“带有一丝阳刚之气”。与此同时,这位小姐复杂的人生阅历,更加坚定了阿拉贝拉闯荡历险的决心。
在经历了一连串喜忧参半的闹剧之后,阿拉贝拉遇到了年高德劭的伯爵夫人。当阿拉贝拉打算向伯爵夫人讲述她的“历险记”时,后者不容置疑地将她打断:“历险记,该词通常意味着自由和放荡,以至于人们很难恰当地把它运用于那些构成女性荣誉的历史性事件。”在她看来,一个女人出生,长大,遇到一个男人,出嫁,这就是故事(history)的结束。由此阿拉贝拉与伯爵夫人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伯爵夫人观点不同,阿拉贝拉认为道德善恶并无绝对标准,往往随历史背景而改变,因此固守道德教谕未必是明智之举。自始至终,这场对话实质上与男人无关;而是涉及道德、文学、历史等“严肃”话题——可谓是整个18世纪文学史中女性主导的最为有趣的谈话之一。虽然伯爵夫人意在纠正年轻女子阿拉贝拉的“疯狂想法”并试图改造阿拉贝拉:“历险一词用到女人身上会有失传统,因为好女人身上从来不会有故事发生……我从出生受洗,接受适当而实用的教育,直到得到我夫家的姓氏——这一切都是在我父母的建议下做的,我嫁给他也是得到父母的许可,自己心甘情愿的,而且因为我们生活得很和谐……这一切与跟我有着同样地位、同样理性、谨慎并有德行的女人没什么不同。”然而事实上,这一番循规蹈矩的“道德经”并未能说服阿拉贝拉,相反,倒是后者的“疯言疯语”占了上风。值得一提的是,伯爵夫人此后从小说中消失,直至终章也未能再次露面,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伦诺克斯安排这一角色,无非是借人物之口表达作家本人对社会习俗的不满和嘲讽。
这也正是作家伦诺克斯的高明之处:如同她笔下人物阿拉贝拉用浪漫小说为自己创造出“另一种现实”并退避其中——唯有在此间她的“疯狂”举动才有可能被接纳。换言之,正是这种“疯狂”给了她某种程度上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使得她能够从充满偏见的社会习俗中挣脱出来,展示出独立自我的女性形象。伦诺克斯也借助于阿拉贝拉这一形象,“重新定义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认为女性主体具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中心地位,而男性人物则在边缘地带打转。”起初,格兰维尔企图教导阿拉贝拉成为一名传统女性。但很快,角色便发生置换,老师变成了学生:阿拉贝拉时时教导格兰维尔如何行事。事实上,整部小说中,包括格兰维尔在内,没有一位男性能在智力上与阿拉贝拉并肩。查理先生时时被她驳得哑口无言,见多识广的历史学家塞文斯先生也不得不承认阿拉贝拉比他读过更多的历史书——承认她“阅读广泛”、“记忆超群”、能够“活学现用”且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如果她是一名男人,肯定能进下议院”——这既是对女性人物的美化,也寄寓了作家的社会理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评论家将阿拉贝拉背后的伦诺克斯誉为英国“最早的女权主义代表”(早于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权辩护》约半个世纪)。
作家的激进姿态不仅受到男性同行(和读者)的抨击,也受到女性作家——包括“蓝袜子”俱乐部成员——的质疑。蒙塔古夫人(Lady Montagu)是该俱乐部创始人,被誉为“蓝袜子女王”,伦诺克斯则为其中一员。以蒙塔古夫人为首的女才子尽管学识渊博,但在两性关系方面却恪守传统。她们指责伦诺克斯在书中的论断,即女性拥有对爱情的绝对主宰地位:“多一点点顺从和尊重,你的日子会变得更好过;你现在完全处于我的掌控之中”(阿拉贝拉语)。在她们眼里,这样的言辞对男性是极大的侮辱和冒犯,有“颠覆”现行社会秩序之嫌。伦诺克斯笔下的阿拉贝拉受她所读小说的影响,将当时所有社会机制看成是堕落的表征:高尚的英雄风范被遗弃,男男女女都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之上——访客、打牌、跳舞,一切都是娱乐和消遣;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人宴席的谈话,无不充斥着诽谤和恶意的流言;社会阶层固化:是出身和社会地位而不是道德品行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出人头地——尽管这些评论的确如实描述了18世纪中期英国社会生活的状况,但阿拉贝拉的控诉却普遍被当成一种“疯癫”,正如伦诺克斯本人被视为“一位煽动者”。
除了小说创作,伦诺克斯在诗歌和戏剧方面也卓有建树。1750年,她在《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上发表诗作《卖弄风情的艺术》(“The Art of Coquetry”),大获成功。1750年代中期,她对莎士比亚戏剧源头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刊载于《莎士比亚画报》(Shakespear Illustrated)第三卷的莎剧剧评中,伦诺克斯旁征博引,探讨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浪漫主义(古罗马、威尼斯)元素,开日后浪漫派莎评之先河。与此同时,她认为莎士比亚戏剧也存在明显缺点——剥夺了女性角色原有的威权,“褫夺了女性权力/力量(Power)和情感独立,而这些在他援引的文学经典中原本有所体现”。这一番不自量力挑战权威的言论,如同堂吉诃德挑战风车,给她本人招致了巨大的麻烦(尽管约翰逊博士为之题词背书)。她的戏剧《姐妹》(The Sister)——改编自她的小说《亨丽埃塔》(Henrietta)——首演之夜,若干“挺莎”的观众和戏剧爱好者联合起来,大喝倒彩,最终只得黯然收场。
伦诺克斯这位被称为“英国九大缪斯之一”的著名作家,晚年与丈夫分居后贫病交加,死后安葬于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附近一家无名公墓。正如18世纪诗人波尔维尔(Richard Polwhele)在名诗《无性的女性》(“The Unsex’d Females:A Poem”) 中预言的那样:特立独行的女作家往往被诬蔑成家庭和社会的“怪物”,不能见容于世。像她笔下的阿拉贝拉,从“让爱做主”到“美德有报”,历经磨难,终点却又回到起点,令人扼腕叹息。自小说《女吉诃德》面世至今已逾250余年,然而历史似乎始终走不出“阿拉贝拉走后怎样”这一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