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楸树 到紫花泡桐 ——斯特林堡笔下的植物景观及中国植物

斯特林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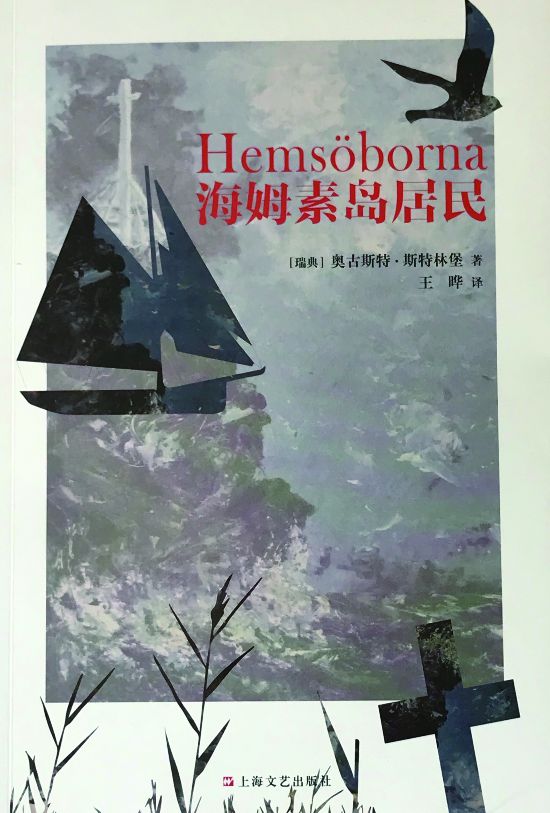
斯特林堡以博学著称,有些瑞典人甚至误以为他是汉学家,因为他对中国和汉字萌生过浓厚兴趣,书写过相关篇章。较之汉学,说斯特林堡具备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则毫不夸张,他谙熟上千种植物的拉丁文名称呢。
自然描写包括植物描写在斯特林堡作品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些描写只是点缀、烘托和背景吗?对斯特林堡来说绝非如此。
在林奈的精神的照耀下
斯特林堡对自然的描写如同很多瑞典作家乃至不少北欧作家一样,可以说都处于林奈的精神的照耀下。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游记、讲稿和信件显示出林奈对瑞典语及瑞典文学中的自然描写的推动作用。虽说有时也混杂了拉丁文,林奈还是将瑞典文推到了舞台中央。他的文本有原创性,简洁明了、富有活力、细节丰满,偶尔还活用方言,独立于同期盛行的拉丁文写作。本来,18世纪的瑞典文学很大程度上受法国模式影响,诗歌与学术散文的地位崇高,在瑞典史的“自由时代”里(1719年-1772年),英国小说和艺术的影响加大,面向大众的散文开始发展,丰富和捍卫本国语言的想法得到加强。古斯塔夫三世于1786年创立瑞典学院,更让这一想法得到最终的体现。林奈是自由时代最重要的散文作家,他依据亲身体历,在书写里呈现了植物介绍、农村故事和对自然的诗意描述,影响了同时代和后代的瑞典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影响了他们在文学里对自然的关注。
仿佛传承一种珍贵的文化基因,斯特林堡承继了对自然包括草木难以分割的一体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未刊稿里有言:“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若能打破时空的隔阂,斯特林堡一定会十分赞同王国维的这句话,因为斯特林堡描摹一草一木就显得十分忠实,这并不是说斯特林堡谙熟某种鸟语或草木之语,而是说他有投入的目光,有感同身受的共情之心,于是,一切景语皆情语,这样的情语不是浮泛之情,而是天然而醇厚,忠实于生命、从而映射出生命的。
在遥远的礁岛链上
斯特林堡以自然描写(含植物描写)而著称的作品首推以斯德哥尔摩附近多岛海为背景的小说《海姆素岛居民》及《在遥远的礁岛链上》。
在1887年问世的小说《海姆素岛居民》里,斯特林堡将农人们繁杂辛苦的割草劳作写出了喧腾中的诗意。斯特林堡绝不会粗略地涂抹,他写的是:“镰刀发出嗖嗖的声响,带着沾了露水的草一束束地落下。所有跑出森林和牧场冒险的夏天的花、一朵挨着一朵地倒下:牛眼雏菊和苦豌豆、剪秋罗和田紫草、蓬子菜和百里香、峨参、少女石竹、山罗花、野豌豆、蜂斗菜、三叶草,还有野地上各种各样的禾草与莎草,气息甜得像蜜和调味料”。其后是对蜜蜂、大黄蜂、草蛇、八哥等昆虫和动物的描绘。斯特林堡并非堆砌出一张植物表来,野草地上确实蔓生着各种各样的野草花,它们错落有序地迎来各自的满开时节,又不排斥短暂的百花齐放,而野草地的世界不只是植物的。这其中热闹而甜腻的气息好像要表明生命和生活都还年轻着,处于欣欣向荣的生长期。
描写得如此具体和详细固然和斯特林堡对自然主义表现手法的倾向性有关,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在文学表达上的野心和能力,他要尽力与环境接近,以接近让此地的自然熏陶了的海岛以及岛民的生活和特性。
割草是腰斩,可即便让镰刀砍倒了,野草和野花的根还在,同时,那被割下的草和花也在空气里抒发着青草味和无穷尽的生命的味道。大割草的日子是整本小说中最明媚的一段时光,对草的详细描写与其说是对大割草纯自然主义风格的再现,不如说带着浪漫的活跃,这景观里,一切都充满生的力量。那巨大的生命力中有全部的欲望和冲动。野草的倒下烘托出的不是哀愁,反而是热烈,让男男女女深受感染。接下来,出现了夜色里的酒宴和斗殴,调情和媾和,恰与白天野草地的景象对照,有互文效果。一切都尽其本能地为了生而活着,无论植物还是男男女女。体会和描摹植物也成了体会和描摹人的生命的有效途径。
善于用寥寥数语便凸显某种事物和景观的特征的斯特林堡,其文本又完全基于相关事实。在他强大的感受力下,大自然格外深情款款。
大割草之后,在《海姆素岛居民》里,斯特林堡还再现了一个7月末的早晨。是年轻人古斯腾出海散心。阳光耀眼,蓝白色的天空像脱脂牛奶。大大小小的岛屿和礁石柔和地融在水中。斯特林堡提及近处岛上的“云杉”和“桤木”,一座远处小岛上仅有“矮松”,另一处小岛上有一棵“花楸树”、一团蚊子在树冠的微风中浮动。古斯腾在一座多岩石的小岛靠岸,这座岛“只有几英亩,中间是个山谷。岩石间仅有光秃秃的一两棵花楸树,可壮丽的欧卫茅带着火红的浆果长在石缝里,山谷被厚厚的帚石楠、岩高兰和云莓覆盖,这会儿正在变黄。这里那里,刺柏铺展着,好像已给踩扁到石板上,它们拿指甲紧抠着,好不至于被吹跑”。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斯特林堡对植物进行了细致研究,但因当时资讯的限制,他还是会有认知上的疏漏。瑞典当代植物学家们认为,欧卫矛不能适应群岛贫瘠的土地,这里的欧卫矛更可能是荚蒾属植物。
《海姆素岛居民》写于斯特林堡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那些年,他对17岁时初次体验,继而终生眷恋的多岛海夏日天堂充满思念。在国外度过6年多之后,斯特林堡和家人返回瑞典。从1889年到1892年,在斯德哥尔摩多岛海的达拉岛等地消磨了四个夏天。不过,私人生活并不宁静,以烈焰般的浪漫而开始的第一次婚姻已走到缘分的尽头。
斯特林堡在海岛租屋,创作了又一部多岛海背景小说,他称之为“新伟大文艺复兴风格的雷霆之书”。讲述一个有着高度精神追求,职业为渔业监管员的孤独者,在陌生而平庸的环境中的坚强和脆弱、坚守和绝望,最终在肉体上被摧毁。创作时间从1889年5月到1890年6月。其中的自然描写独特而细致,主要涉及植物和鸟类。
这初来乍到的渔业监管员打开住处的窗户,看见一块块磨损得开裂的石板,裂缝里躺着沾满灰尘的飘雪,旁边盛开着细小的白色的黑麦花,“它们在地衣之床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那贫寒的后娘花,淡黄色像是因为挨饿,蓝紫色像是因为受冻,对着第一缕春阳,托举起它们贫瘠的土地的贫瘠的颜色”。有一天,监管员驾船去附近的小岛,就踏进了另一个植物世界。他看到“一些刺柏灌木地毯般延展开来,其下是一大群白色的、柔柔的森林之星即兴准备了自己的生长之地”,而在一块扁平的淡红色片麻石悬崖的避风侧,“站着一株百年花楸树,孤独、长满苔藓、多节。在它粗糙的枝干上,一只白鹡鸰在繁殖后代……那孤独的花楸树伫立在约一平米的草地上,看起来是那么孤独,却又因为缺少竞争者而显得不寻常的强大,良好地抗拒住了暴风、海盐及严寒,没有心怀嫉妒的同类为土屑争吵”,他感到 “被这孤独的老兵吸引,在短短的一瞬,他向往可以在枝干下支起一个窝棚……”
后来监管员在一座稍微大一些的岛上靠岸,看到那里有一排“黑醋栗”,较远处有一排小小的落叶树林,听到了他熟悉的“白杨”的沙沙声。接着,“他迅速避开一条在几块石头间水流一样往下游走的毒蛇,走近,便发现自己听对了。是小树林和野草地的颀长而可爱的白杨,正如北风和多石地,经漂冰和海盐的磨练形成自己的风格, 成了难以识别的变种。在对抗暴风雨及寒冷的搏斗中,顶端发灰而失去树冠,因此只有受着冻的新芽继续抽出、不懈地更新自己,而山羊已啃掉作为保护的树皮,让树汁流了出来。永远的青春在这灰胡子般没有枝条的树干上柔软而淡绿的树芽里,一个没有成年的老人,一个令人精神振奋的异常的人,因为它新,并且超越平凡”。
当他爬到顶端,“落叶树区域躺在他脚下,高原上已出现高山植物,山地形态的刺柏挨着真正的北欧云莓,云莓就在潮湿裂缝里的白苔藓上,这之间是小小的相当文明化了的瑞典草茱萸,也许是唯一的瑞典植物和多岛海植物。现在,他缓缓走下南坡,穿过越橘和熊果的枝叶,穿过发草和莎草、羊胡子草和摇摆的青苔,直到他突然站在一道峡谷边……在他的前边,在那些根部消失于野草地的垂直岩壁间,有一片展开的野草地毯,上边交错遍织着纯粹的花朵,品种比陆地上的更高雅、更茂盛。血红的天竺葵从山头走下来,在这底下寻找水分和温度;来自潮湿的莎草草甸的蜂蜜白色的梅花草与森林的蓝黄色山罗花相遭逢;还有那些来自南方的兰花,兴许是被风从葡萄种植地的哥特兰德带到了这里,已移居于此;类似风信子的‘亚当和夏娃’;灿烂的红门兰;华贵的头蕊兰;略带修饰的铃兰……”
还不仅仅是这些,“在远处的背景里,遮蔽了岩壁的白桦和桤木切实又害羞地在空中升起,没敢在风中抬头;这里那里地把自己种下而站在绿草地毯中的欧洲荚蒾,它们的白色雪球挂在那些和葡萄叶相似的叶片上;倾斜如同在棚架上攀援,深绿色的沙棘抵着悬崖生长,闪着光泽的叶子隐约让人想起被盛赞的橘,却更多汁,有更丰富的色调、更精巧的图形和更敏感的结构。”
《在遥远的礁岛链上》第十四章开头写到“帚石楠”和“岩高兰”,“刺柏”和“矮松”,“秋已缓缓向前滑行,可在礁岛上看不出夏已迁移,因为这里没有一棵叶子会发黄的落叶树,相反,崖石上的地衣变得格外奢华且因湿气而膨胀,帚石楠和岩高兰焕发出新绿,刺柏和矮松——北国永远的绿树,因为雨水而格外新鲜,并被掸去了尘埃。”松树在暴露的海岛上,在海风吹打和贫瘠的土壤中生长缓慢,往往很矮小,但也有“矮松”这样的树种。
不单树木和花卉,斯特林堡对地衣也不会笼统地概述,监管员这样对未婚妻介绍岛上的石头:“是的,这里有大理石,虽然表面是灰色的,其实并不灰。因为只要您仔细察看,就会发现这层地衣拥有无限变化的丰富色彩。好一个最美的色谱,从石耳衣的墨黑色,穿过煤渣衣的烟灰色、 梅衣的皮棕色、扁枝衣的舍勒绿、肺衣带斑点的铜绿色和石黄衣的蛋黄色。”
斯特林堡笔下的中国风植物
吐露芳香的花儿在斯特林堡笔下被赋予了一些微妙含义,如戏剧《朱莉小姐》里,朱莉小姐的手帕上洒了香堇菜(香堇菜因早年的误译,在中文里已约定俗成地称为紫罗兰)香水。除了香堇菜,有情色意味的花草还有丁香、金银花、风信子等,当然更不能缺了玫瑰。玫瑰被斯特林堡称为“我青年时期的花卉”,这份表达的字里行间飘动着年轻岁月那甜蜜和哀愁兼备的味道。有这么一盆花也叫玫瑰,在《疯人辩护词》里出现于家居环境中:“炫目的白色绣花桌布上摆着一盆在深绿的叶子中绽放着鲜红花朵的孟加拉玫瑰,看见它们和垂挂着的常春藤在一起,你会得到一种花宴的印象。”
这里的孟加拉玫瑰就是中国玫瑰也就是月季花。1789年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来到英国,才有了这么个被误会的名字。后来得以正名。比如比斯特林堡年轻约10岁的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尤斯塔·贝林的萨迦》里有这么一节,写一位寄居在别人家阁楼里的老姑娘玛丽小姐,她40岁,认为在情爱中只有悲惨,因而天天祈祷上帝别让她坠入情网。她从不给妈妈留下的玫瑰浇花,也不愿碰触吉他,可上帝却让她暗恋上一个暂时在此地停留的男子。这男子临别时,玛丽“穿着最好的衣服走下古老的阁楼的梯子。吉他用一根宽宽的绿色绸带吊在了脖子上,手里是一束中国月季——因为这一年,她母亲的那盆玫瑰树开花了”。她弹起吉他,为他歌唱,而后,把花儿插在他的铜纽扣眼里,直接吻上他的唇,又消失在阁楼的梯子上,仿佛一个古老的美丽幻影。爱让她成为人们的笑柄,“可她再没有抱怨过爱。她再没丢开吉他,再没忘记小心浇灌母亲的玫瑰树”。
和月季花相比,凤仙花说不上原产中国,比如非洲也有中国凤仙花的亲眷,但它实在是中国家居生活里常见的花,尤其在农历六月初六,女孩们喜爱拿凤仙花汁涂指甲。凤仙花在北欧也生存下来了,野生的有,更多的是室内盆栽。在《海姆素岛居民》的第一章,男主人公卡尔松刚抵达海姆素岛的那一晚,他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听得见外头的说话声,靴底的钉子踩在石头上的咔嚓声,在窗台上的盆栽凤仙花之间,卡尔松看见外头月光下两个肩头扛枪、背上驮了包裹的男子的轮廓。”
《在遥远的礁岛链上》,斯特林堡两次提及凤仙花,他先这么写,“似乎夏天的云就挂在凤仙花上”。后来,在男女主人公的最后一夜,“黄昏已降,残月只抛出一道黄绿色线条在地板上,剪出凤仙花似的阴影”。看来凤仙花在当时的海岛确实流行,在斯特林堡的眼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还有其他一些进入斯特林堡的视野、原产中国的植物,比如杏、荸荠、银杏、苎麻和紫花泡桐等。
17世纪传入欧洲的杏,斯特林堡是在短篇小说《受祝福者之岛》中提及的。
银杏于18世纪传入欧洲。斯特林堡有涉及天文学、生物学、化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神学等内容的随笔集《一本蓝色的书》。其中名为《植物谜语》的文章提到银杏。银杏也在另一本书里收录的《一些花卉的秘密》一文中出现,斯特林堡说,落叶松抽出新的针叶,唤起了他对银杏的联想。不过,在此文里,斯特林堡用的是拉丁Salisburia。
在一篇题为“中国——一些观点和阐释”的文章里,斯特林堡提及人参,他说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在满洲里北部发生了冲突,不是为了打猎,而是为人参根、海参以及可食用的海藻。
柏树也是在“中国——一些观点和阐释”一文里出现的。斯特林堡提到汉字的“第五类……大部分字符归于此类,这些字符一部分表音,另一部分表意。 所以,比如cypress(柏树)叫 Pe;然而,Pe也有白色的意思”。斯特林堡接着解释了木字旁,解释这个具有树的形象的合成图,提醒说,合成后,木失去了声音,而白丢掉了意思。
至于紫花泡桐,在充满自传色彩的小说《地狱》中,斯特林堡描述客居宾馆的“我”于窗前的桌边看到了不曾期待的愉悦风景。底下是一堵长着常春藤的围墙,看得见修道院、梧桐、泡桐、刺槐和小教堂的尖拱。后来,春天来了:“我”又看窗外,窗下蔓延着的眼泪和痛苦的山谷有了新绿,花朵重新绽放。绿色叶片覆盖地面,遮住了污垢,这片欣嫩谷(炼狱)变成了沙仑的山谷,不仅有百合花,还有丁香、刺槐和紫花泡桐。斯特林堡在这家宾馆换了三次客房,窗外景观略有变化,而这两处描写里都出现了紫花泡桐。
苎麻也叫中国荨麻,在《和法国农民在一起中》,斯特林堡和法国农民交谈,他听农民说起种苎麻,认识到“苎麻是一种中国荨麻,它的线比棉线更漂亮,比亚麻更结实,而且像丝绸一样闪亮”。
荸荠,瑞典文字面意思即为“水栗子”,斯特林堡在“瑞典与中国以及鞑靼诸国的关系”一文中列出此物。正是出现了荸荠的同一段植物列表里,斯特林堡也列出了竹子。
很可能,柏树、银杏等中国植物引发了斯特林堡对远在中国的住民的想象,而中国的住民不单是人。不难理解,斯特林堡的文学后辈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瑞 ·马丁松等人,都乐于将中国人置于竹林之下,以竹子指代那些具有竹林七贤一般洒脱气质的智慧的东方人。无论如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植物。植物仿佛是一种媒介、一根线索、一个局部。描绘植物,仿佛绕道而行、迂回地,以一种互文而几乎是物语的模式描绘人、人心和人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关注和描写植物便有不容小觑的意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前文里,我借王国维所言“忠实”二字,又寄予更厚重的使命,而试图声称,斯特林堡对植物的描写有一份巨大的忠实。
植物的秘密
斯特林堡和自然特别是和植物的缘分像冥冥之中的天注定。他的女儿格雷塔曾说,父亲自认是一棵脾气暴躁而孤独的欧刺柏。
斯德哥尔摩附近的较大岛屿早在17世纪即由瑞典贵族利用,在那里建造庄园和城堡。生于1849年的斯特林堡生活在瑞典的工业、技术和科学革命的发展期,当时社会的发展让城市居民重新发现未受人类破坏的自然。19世纪后期,斯德哥尔摩富裕阶层表达出了补偿生活中那失去了的自然的需求,在都市外围的多岛海度夏成为一种流行,而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家开始在海岛兴建别墅、树立身份。斯特林堡等相对贫困的作家和画家向农民和渔民租用小屋,也能在海岛亲近自然。
不过,多岛海风景对斯特林堡而言是突然的醒悟和终生的热爱。 他有个做船舶代理的父亲,一个出身卑微的母亲,母亲在他的自传体小说里被称为女仆。正是在《女仆的儿子》这本书里,斯特林堡描述了自己与多岛海自然的初次相逢,17岁,作为斯德哥尔摩人活着又一直不知身在何处的他,仿佛找到了一片在美丽梦境中看到、或在更早的存在中看到的土地,并确信,这是他的风景,是最符合自己天性的纯真环境。似乎少年跳出了让他感觉不适的家庭和日常环境,隐约感到一个更大的存在,而自然以一种少年人还不能完全听清和懂得的暗语絮叨着他的起源,一个更遥远的根本起源,暗示不可见的超出日常透视图的一切。来自自然的神秘启示,与一具小小肉身密切相关。
多岛海的天堂叙事在斯德哥尔摩变身现代都市的过程中形成,至今仍在延续,多数人恐怕只是在群岛寻找尘世和物理意义的天堂。据说“天堂”(paradise)一词源自古波斯语,意思是带围墙的花园。海岛可自我封闭,像天堂,也可成为自我放逐的地狱。这正是在遥远的礁岛链上自取灭亡的渔业监管员的结局。斯特林堡作为更纯粹意义上的现代人、现代作家和女仆的儿子,对失落的天堂有更深的向往和更矛盾的心情。而植物也是他发现的天堂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而言,传统的西方诗歌、散文多将植物描绘作为风景的一部分或人间故事的背景。植物作为人类情感的关联物反映人的心理状态。有关植物的描述便还是以人为中心,人终究难懂植物的神秘。然而植物不单是人心的隐喻,其本身也是客体而自在。斯特林堡的植物描述不能说全然站在了植物的立场上,但他以特别的敏感,强大的同理心和悲悯心作出了出色的尝试。更不能忽视的是斯特林堡的自然理念,他不单看植物、看自然,其实对植物和自然有更高期待,希望借助自然抵达某种境界,如此,抵达的可能是天堂、可能是起源,也可能是未来的去处。
斯特林堡的自然理念在他生命中那段著名的“地狱”危机时期(1894年-1896年)形成。他也并没有完全地处于悲观和绝望,而是以为通过自然,世界可以打开,灵魂能被接受。在无边的自然里,没有死亡,只有各种变化以及生命的周而复始。在这一段精神备受折磨的时期,斯特林堡中断了文学创作,将主要精力投入化学和炼金术实验及对自然的观察。他撰写了植物学、化学、炼金术等方面的大量文字。他琢磨地球生命从岩石到植物和动物,一直到人类的进化过程,甚至打算建立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也不排斥在这一过程中与上帝相遇。这样的思维模式和精神状态,确实同《在遥远的礁岛链上》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渔业监管员有很多重叠,而那个人正是常人眼里的疯子。这样的人的确不同寻常,执著而纯粹。
创作《在遥远的礁岛链上》时,斯特林堡回到他热爱的海岛风景里,似乎要在那里隐藏和抚慰自己。离婚处于进行时,他也曾试图吸引家人在海岛的夏日天堂团聚。1890至1891年,夫妻俩也曾在同一座岛上躲避世人的目光,却没住在一个地方。斯特林堡自白: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相爱,但不能共处一室;我们梦想重逢,非物质化,在一座绿岛上,那里只有我们俩或最多还有我们的孩子允许停留。我记得有那么半小时,我们三个真的手牵手、沿着绿岛的海滩散步,我感觉那就是天堂。然后午餐铃响,我们又回到了地球上, 紧接着陷入地狱。
如果说斯特林堡在《一个梦的戏剧》里清晰表明了对人间的态度,人间充满悲剧,人类值得同情;相对而言,自然就是他心中更理想之所在。于是,斯特林堡视线下的自然比之常人眼里的有更重大的价值,它们不只是草木和石头,而可能是和天堂有特殊连接的,是可以引领灵魂进入更纯粹的宇宙中的存在。人类以为自己从混沌走入了文明,可兴许也因此沉溺于世俗而失去了宇宙。所以,渔业监管员会羡慕岩石上一棵孤独的花楸树,能看见地衣的颜色和光泽——这不单因为知识,而是因为和自然相通、敬畏自然的心灵。
这位瑞典最著名的现代作家绝非典型的瑞典人,活跃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流行的文化氛围中的斯特林堡在根本上和潮流格格不入,他是一位实验作家。在提倡平衡和共识的瑞典风气中,他缺乏平衡乃至好斗。他处理现实的方式甚至被看作三岁孩子对待复杂玩具时的状态,特别不满、彻底崩溃,打烂玩具、试图搭建出自己的东西,一个他以为更有趣、更重要、更美好的东西。不少人认为,是对海岛的自然和风物的描写让斯特林堡在他自己的祖国更受欢迎。 如果说林奈是瑞典文学中自然描写的先行者,斯特林堡才是那个真正让这一写作蔚为大观的大作家。在他身后,塞尔玛·拉格洛夫,哈瑞· 马丁松,萨拉·里德曼,乃至特朗斯特罗姆、夏斯汀·埃克曼等都继续丰富了瑞典文学里的自然描写,而以马丁松和特朗斯特罗姆在与植物的交流上尤有心得。也许,对人类而言,最紧要的并非改造自然,而是理解自然包括理解植物那巨大的谜语,进而能在更大意义上理解人类自身的谜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