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忧伤的老虎》与形式主义小说:文艺青年无法治愈的情绪
拉美文学爆炸的核弹头之一的作品,即因凡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翻译成中文,译者最大的功绩,是把哈瓦那淫荡夜总会里狂乱而又无厘头的口语、俚语、俏皮话、谐音、戏仿、反讽、意识流的神韵翻译出来了。
这种登峰造极的形式主义小说到底叙述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只忧伤的老虎》掸去我布满灰尘的文学记忆史,再现那个时代的文学狂热、文学革命,躁动不安的主体,六神无主的叙事激情,四处突围的小说技术,一部又一部具有那个时代特有碎片式文学作品传世。四处移情的叙事荷尔蒙,滴落出存在主义的体液,疯狂而又手法独特。《三只忧伤的老虎》出生于世界文学的黄金时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童年,同时也是西方文学的青春期。
形式:登峰造极的无厘头文学结构
小说以一个儿童偷窥的色情故事开场,然后再以一个女童被强暴的色情故事收尾,开头具有戏谑性质的色情场景和结尾带有悲伤色彩的暴力色情故事,两者之间没有逻辑联系。是的,这是因凡特《三只忧伤的老虎》碎片化拼贴的风格。
其中,有一个精神病人气质的女性十一次独白,从头读到尾,不知道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这个独白和其他章节没有逻辑关系,人物之间没有交叉,十一个独白串起来单独成篇,从其他独白和无厘头对话以及意识流叙事调式来看,这个女性独白叙事风格和其他独白是不同的。拼贴在一篇小说里,不知所云;每一位小说人物独白都是单独的,既不是前因,同时不是后果。每一个独白都可以单独成篇,铺陈了大量的意识流。跳跃感极强,小说叙事风格不是靠事件来推动,而是通过意识流色彩的独白、无厘头的对话串联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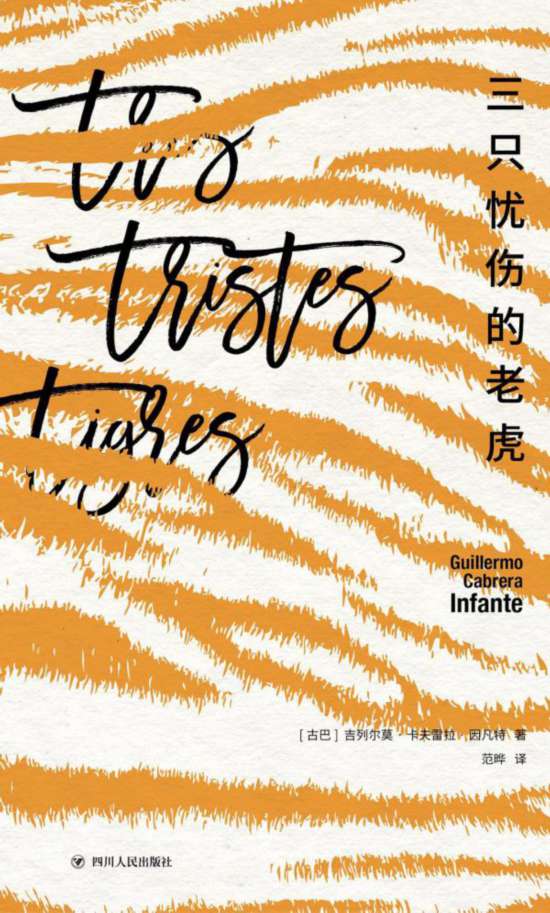
《三只忧伤的老虎》
最奇特的是,小说里出现了戏仿古巴作家写托洛茨基暗杀的情节,即《不同古巴作家笔下的托洛茨基之死,事发后—或事发前》,一共戏仿了7位作家。这7篇戏仿之作和其他独白没有联系。以前,很多搞文学理论的作家,如托洛茨基都转行搞革命了。现在,很多作家转行也转不了,无法理解为什么搞文学理论的转行去搞革命了。发论文,出名,挣外快,谈恋爱,搞投机,不香吗?托派就是怪物横行时期的怪物。因凡特戏仿7位作家写出了7篇刺杀托洛茨基的7个短篇,或长或短拼接在一起,每一篇都废话连篇,语焉不详。这7个奇特的短篇连在一起,碎片、废话、繁琐无趣的句子、莫名其妙的表达,我想,是在试图还原托洛茨基被暗杀前的巴洛克式的场景。
小说《游客》这一章出现了希区柯克悬念式的手杖,奇特在于,一共是四篇夫妻二人不同视角的重复叙述,除了地点外,这个章节和小说其他章节无关联性;小说中出现连续的文字留白空页;库埃被枪杀后,出现了无字的黑页;叙述中出现数字排列阵势;各种稀奇古怪的句式的排列;更为奇特的是,小说中出现整页的反体字,即书写一页文字,反过来阅读;用独白的形式说,“可以用两三个词做一本书而我知道他甚至用一个词写了一页,”戏仿音乐家,一首歌的歌词只有一个单词“blen”。
《三只忧伤的老虎》已经把语言游戏和叙事游戏推到了极致,小说极致的不正经,我认为是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标准。
文学存在内容的自由、形式的自由和语言的自由,但从古至今,作家很难达到三重自由写作。中国作家更难以企及,成功出版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了。乔伊斯没有达到,米勒没有达到,金斯堡也没有。垮掉一代、荒诞派和新小说都没有达到三重的自由,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的小说是《三只忧伤的老虎》。表达哈瓦那颓废青年的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创伤。但这不是一种吸毒嫖妓酗酒式的狂欢。
真正的作家的作品不需要读者,《三只忧伤的老虎》正如不需要发表、版税和名望一样,消费自我生产的写作激情。对于因凡特而言,《三只忧伤的老虎》是真正的游戏。布朗肖说,写作,就是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将召回的东西解放出来。
我相信,因凡特解放的是反抗精神,内容是一种反抗,形式是一种反抗,语言是一种反抗。我在阅读极致的游戏,也是一种精神反抗和文学起义。
狂乱:“随机文学”
在阅读《三只忧伤的老虎》时,我头脑里来回在切换小说家的形象,这种风格的小说,我以前大致读过。乔伊斯的,塞利纳的,米勒的,福克纳的……口语、俚语、俏皮话、谐音的,内容杂乱、异味、狂乱、颠覆、淫荡。形式上,很大一部分来自《尤利西斯》。把意识流叙述方式扶上正位并真正发扬光大的,是福克纳。
《三只忧伤的老虎》各个无关联的独白章节,组合在一起,主人公的独白和对话大多是无厘头的,不同章节之间没有明显的小说叙事的逻辑关系,对话是任意的,句子也是任意的,没有明确的叙事目的。
“随机文学”,同样也是西尔维斯特雷和库埃的无厘头对话的一句话,并且解释,所谓的随机文学不是某种比拟和隐喻,意思是掷出去的骰子。其大致是说,文学书写没有明确的定性,句子是无序的单词组合,叙事是无意义片段组合。
我曾经总结过现代派叙事技术,即拼贴、抹去时空、意识流,包括后来各种非传统叙事技术各种流派小说几乎都存在这三种模式。西方超现实主义兴起的时候,对传统小说进行了颠覆,嘲笑巴尔扎克的叙事彻底过时了。文本里人物模糊。出现过类似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这种随意性拼贴,把完全不相关的内容组合在一起;以及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的自动写作,取消小说人物刻画同时,取消了小说内核的故事性,甚至不再倡导小说的所谓社会意义。
任何文学作品的根基都是现实的,包括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风格,根据报纸文字来拼凑;贝克特并不知道《等待戈多》戈多等待什么;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古怪的对白来自英语学习教材。

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
因凡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把西方文学20世纪中期流行的自动写作、任意拼贴、意识流小说、荒诞派、超现实主义、新小说糅合一起,把小说形式结构发挥到极致。称之为随机文学,而且这种随机不是为了某个明确的目的比拟和隐喻。
《三只忧伤的老虎》表达的是大革命前古巴文艺青年内心无处安放的骚动的颓废、叛逆和绝望情绪,和当年的无政府倾向的达达主义一样,通过自动写作废除既往的审美传统,重建自由无序的审美秩序,相信破坏就是创造。
戏仿:“游戏发生语言学转向”
翻译成中文的《三只忧伤的老虎》,错别字惊人,“真阔怕,库埃说,对祖国缺乏信心的女人会生早产儿,”这种谐音的错别字从小说开头一直到小说结尾,不能说每一页都有,只要有对话,基本上都会出现大量的语言游戏式的谐音。译者把因凡特语言游戏性质的谐音翻译成中文,的确让阅读增添很多趣味,尽管这部小说读起来很枯燥,但语言游戏的特色是这部小说不可磨灭的印象。类似口每明威、徐要、估秘书、朋松、开森、哲噱家……比比皆是。
除了口语、俚语,小说出现大量的戏仿之语。“屁是肉体的叹息,叹息是灵魂的屁”戏仿的是达利的屁是肉体的叹息;“鸦片是人们的宗教,工作是人民的鸦片,电影是观众的鸦片,鸦片是盲人的电影”戏仿的是昆西《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性欲导致腐败,绝对的性欲导致绝对的腐败”戏仿英国政客阿克顿勋爵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类似这样的戏仿之作充斥在小说中,让小说充满了游戏之感,同时,因凡特小说中自主开发了大量游戏之语:没见过哪个女人那么耐看,现在值得看的只有海;离开祖国以后不要回去以及不要冲着太阳小便;禁止一切唯物主义者停车;海是性器官,另一个是阴道……
“免得让游戏发生语言学转向”,同样来自西尔维斯特雷和库埃的戏仿、无厘头对话的一句话。小说中“游戏发生语言学转向”这句话是对《三只忧伤的老虎》大量语言游戏的点睛总结。这种玩到极致的语言游戏对文学传统叙事方式的颠覆和厌烦,呈现哈瓦那文艺青年骚动着的荷尔蒙和颓废、无聊、叛逆的情绪混合在一起。
我不认为因凡特的语言缺乏锐利,为了语言游戏而游戏,为了戏仿而戏仿;相反,他的语言叙事的细节很讲究。
库埃,这个乡下穷小子,刚到大城市托关系找事做。“敲门前我看了看自己的手:每片指甲上都有一弯黑月牙。”特别形象,远比各种比喻修辞都具有煽动性。多年前读塞利纳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一句话至今还记得:天色漆黑一团,把胳膊一伸,过肩的部分便看不见了。滥用修辞,是全世界写稿人的臭毛病,永远改不了,包括我。
记得很久以前读小说,一上来就各种铺陈的修辞,空洞的华丽。作者就想表现一下语言的艺术,结果我一般翻了翻,就直接翻篇了。
情绪:继承了垮掉一代的心理基因
《三只忧伤的老虎》的人物模糊,个性相似,对话同质,通篇采用独白体,没有整块的情节,同时没有符合逻辑的叙事脉络。展现了古巴革命前夕一群文艺青年在哈瓦那夜总会醉生梦死的颓废、叛逆的文艺形象。
小说的情节晦涩,任意穿插意识流,如果不仔细分析,根本不知道独白的主人公是谁,搞不清楚独白中出现人物是干什么的。“书中人物虽基于真实原型,仍作为虚构出现”,小说第一句话就交代了人物背景,小说主要人物包括作家西尔维斯特雷,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是一家刊物的编辑。从文中时隐时现的情节来看,应该是以因凡特为原型的;演员阿塞尼奥.库埃,这也是小说中唯一一位具有完整经历的人,一个家境贫困的乡下穷小子来到大城市哈瓦那,是西尔维斯特雷高中同学。库埃也是小说中唯一具有小说故事情节的人物,即库埃被人枪杀的悬念,实际上虚惊一场,制作人用无子弹的枪,把库埃吓晕过去了,最终,库埃如愿以偿当上了主演,成为了男一号,完成了穷小子的逆袭之路;报社摄影记者柯哒,没有相关人物经历的描述;画家力波特,没有相关人物经历的描述;牾斯忒罗斐冬,小说中,这个人物没有独立的独白,是通过其他人物的独白出现的,没有相关人物经历的描述,应该是一位诗人。小说通过库埃、西尔维斯特雷、柯哒的独白合成的,或许是因凡特用这三个人暗指三只老虎。尤其是后半部,主要是西尔维斯特雷和库埃无聊、反讽、到处是戏仿的无厘头对话。
这些哈瓦那的文艺青年主要聚集的场所是夜总会和酒吧,他们从事着一个共同的事业:泡妞。他们具有一个相似气质:文艺范。从这些人物从事的职业来看,都是哈瓦那一群精神空虚、行为怪诞的文艺界精英。小说中出现的小说家、音乐家、电影的名字比比皆是,从小说开头一直到结尾,每一页码几乎都能读到一个文艺作品或者名字,总计估计得有1000个左右,这是我阅读中从没有见过的,大约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文艺小说。
因凡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完全继承了二战后迷惘一代、垮掉一代的心理基因,无聊独白、口语、俚语、俏皮话、谐音、戏仿、反讽、意识流糅合在一切,各种不相关的片段拼贴,叛逆是这部小说最为主要的气质。
“被露水和精液浸湿的婊子”、“他慵懒的睡意和我清醒的守望和永恒夏天上午肿胀的热气之间”……小说以自始至终散发荷尔蒙的腥气,但小说并不是为了写性而写性,小说甚至没有出现完整的性描写,性,只是表达叛逆的背景,无处不在的淫荡气息,展示的正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基因。叛逆,是文学性感的小背心。任何狂浪不羁、癫狂的叛逆文学作品,总是通过性背景来展现革命信息。
“上床和上菜都属于同样的拜物教”,西尔维斯特雷和库埃的无厘头对话的一句话,并不是说小说里遍布色情场景。这是一个时代文艺青年的情绪,更是文学表现现实的一个维度。
气质:“生存就是腐烂”
“精神病学,算术和文学都导致灾难”,小说中同样是西尔维斯特雷和库埃的无厘头对话的一句话,无意识还原了那个时期文学精神诉求:即没有明确诉求的颓废情绪。开车、性爱、咖啡、电台都会导致灾难,一切都会导致灾难。这是颓废之语,并不是说文学必然导致灾难,小说中库埃说,生活是糜烂的,我们进入生活,满怀年轻无暇的信念,相信生活中只有纯净和健康,但很快发现自己也是病人,被同样的东西污染,生存就是腐烂。柯哒在描述夜总会里的女歌手:用烟雾和空调的浊气和酒精毒害自己,把黑夜泡进一杯加冰的酒里,或者印在一张底片或者记忆里。
这是哈瓦那文艺青年无法治愈的忧伤,没有时间性,这也是全世界文学无法治愈的忧伤,这群文艺青年“被黑夜击败,在清晨衰老”、“抛下隐喻的街,穿过现实的街,想的是记忆的街”、文学妙语“只能自我欣赏像手淫一般私密”、“我不想喝咖啡因为我想继续醉着醉着走路醉着生活醉到睡醉到坠醉到毁”……
因凡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只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学摇滚其中一个曲目,文学作为遗产被继承,有一个残酷定律,珍贵的文学遗产,往往不表现美好,绝望才是文学第一生产力,痛苦是文学的永动机,颓废和叛逆恰恰是文学机床上两个非常固定的铆钉,悲剧是文学生产的基本调式,偷情和出轨的尺度越大文学展示空间反而越大。
革命前夕的哈瓦那,夜总会、性、颓废、迷惘、无聊。 一个男人在两个女人卧室里。裸体、乳房、化妆品……我很仔细,一字不落地读下去。絮絮叨叨零零碎碎不喘气的句子以及无法连贯的情节。实际上没有描述性。《三只忧伤的老虎》闪耀着非常典型的形式主义口红。
开始读第一页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自动跳出了格瓦纳和卡斯特罗。1959年之前的哈瓦那,没有这两个革命兄弟垫底,我都无法认知古巴。小说里淫荡的哈瓦那飘荡着1949年之前中统、军统、六十七号、地下党纠缠在一起的夜上海胭脂气。
《三只忧伤的老虎》是高仿版的尤利西斯式垮掉一代。喝完酒搂着妓女叼着烟在爵士乐中歪歪扭扭彻夜不眠,每一个句子我都听到在屋顶握着家伙的金斯堡嘶吼声。小说是记录时代糟糕生活的化石,形式和内容都在煽动革命的荷尔蒙。
情爱:“我猜是在找我的灵魂”
《三只忧伤的老虎》四处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但没有露骨的性描写。所以,我非常关注大量无厘头对话中的情愫。
小说从开头,一直到结尾,都有不同女性出现。但是小说中的不同女性都是不清晰的,具有相同的特质,即她们在小说中存在的意义是性对象,没有其他含义。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夜总会的玩物。她们和哈瓦那醉生梦死的文艺青年搞在一起。因凡特和全世界著名的作家一样,不善于描写女性,但大作家都善于描写妓女。
只有一个特例,因凡特模仿一个女人打电话的叙述,非常有质感。仔细分析文本,其实就是一个25岁姑娘和一个50多岁的大叔在一起,用我们的话来翻译,特别会装。大叔有好工作,有地位,特别黏人。这和社交媒体上策划的发嗲卖弄基本一模一样。古今中外,什么都可以改变,唯独人性没有发生位移。深谙人性,就知道作者再说什么。很多实力作家写不出来这个味道,要么在语言上晒遣词造句,要不在形式上玩深沉,要不在内容上玩点深刻。小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空间,空间感越大,文学的味道越浓。离小说越远,你就体会到小说在表达什么。
柯达非常爱最早从乡下来到哈瓦那的女模特“古巴”,但小说中没有两人交往的情节,同时没有两者的对话。
对于爱情,《三只忧伤的老虎》更多是用肉体来阐释。柯哒在独白中解释音乐的节奏说:“所有人都有节奏感就像所有人都有性欲,您们知道有不举的人,也有性冷淡的女人,但没人因为这些否定性的存在,没人能否定节奏感的存在,节奏感和性一样是天生的”。
因凡特戏仿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的剧名,用一个悖论来探寻女性肉体的欲望。西尔维斯特雷和一个满头漂亮金发的美女好上了,关键时刻,这个女人拒绝了他,他只好通过手淫方式解决。当西尔维斯特雷睡醒的时候,发现这个金发美女的假发脱落,是一个全秃的女人。因凡特用这种抽象的色情画面来注释女性肉体欲望:女人性欲是存在的,她们通过各种化妆,把真实的性欲包装起来,她们轻易不想让男人看清她们的真实面目。
“用舌头撬开我的嘴唇,咬我的嘴唇,外面和里面,在寻找什么,我猜是在找我的灵魂。”西尔维斯特雷和麦卡雷娜在接吻的细节,是对女性肉体欲望的发问,同时也是对性的发问,对爱情的灵魂发问。
“每个男演员的身上都藏着一个女演员”,这是《三只忧伤的老虎》一个令人沉思的爱恋话语。反过来说,每个女演员的身上都藏着一个男演员。你能演到什么样的级别,就能得到什么样的爱恋。
库埃问西尔维斯特雷,你真的爱过女人嘛?西尔维斯特雷的答案是肯定的,记忆爱过的女孩,有金黄的头发,丰满的嘴唇,苹果下巴和她长长的腿和穿凉鞋的脚和她走路的样子,在公园等她的时候回忆她的笑,微笑时露出完美的牙齿。
库埃回答,真的爱过,记不住嘴唇是宽还是厚,记不住头发额头眼睛嘴唇腿穿鞋的脚还有个公园,如果真的爱过就会奋力,拼了命记住她的声音,是声音。
每一个爱过恨过纠缠过痛不欲生过歇斯底里过的男男女女,或许和不同异性有过一时欢愉。但都有发自灵魂之爱体验,不仅仅肉体的交融。和那个秃头歌女的性欲悖论一样,不是她没有性欲,她把真实的面貌和性欲隐藏起来了,一旦她探寻到你的灵魂,就会把肉体和性欲公开赠送给你;库埃的答案不是终极的,或许真正爱过的人,正如库埃答案所说:拼了命记住她的声音,是声音。不是肉体。
结语:西方文学的青春期启迪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西方各种流派文学泥沙俱下,催生出一批先锋作家,至今还在文坛成为耀眼的文学明星。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则是西方文学的黄金时代,各种风格的文学喷涌而出,影响全世界几代作家的文学叙事。《三只忧伤的老虎》是那个是文学集大成者,所以,我才会说,《三只忧伤的老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童年时代,同时也是西方文学的青春期。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拉美文学爆炸”光晕似乎是随手转化成兴奋剂,最少意淫的对象足够接近。在国际化、一体化以及普遍价值流行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口红的确有释放光彩的时刻,2012年前后发生惊鸿一瞥,随即开始逐步暗淡,口红还是那款口红,不过已经色泽黯淡,诱惑力逐步消退,再次卷入狭隘的甬道内。这真不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才华缺陷导致门口罗雀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没有爆炸,不代表人才不够,潜力不够,炸药不够。市场足够庞大,一个蹩脚或者庸俗的作家,都会笼络到市场份额。由此可见,文学具有生产文化GDP的永恒价值。
时代不同了,不但是中国当代文学,西方当代文学同样走到了一个很难大爆炸的瓶颈期,除非世界的格局发生巨大的逆转。所以,《三只忧伤的老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迪在于,即唤起曾经的文学记忆,证明现在文学市场的号召力,昭示未来文学革命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