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周末》与真实的“唐顿庄园”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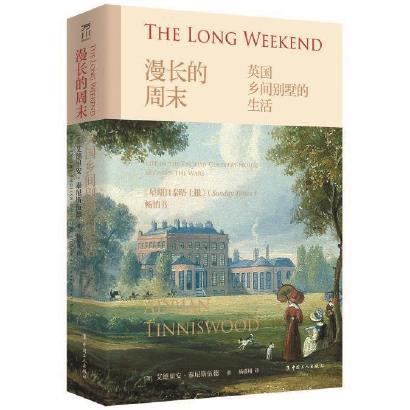
电影《傲慢与偏见》的片头,山岚氤氲、树影绰约,伊丽莎白捧着书,走出原野,穿过草甸,回到了坐落河畔的宅邸中。这幅徐徐展开的长轴画卷描绘了英国乡间别墅的传统生活,诉说着精致而节制的人生况味。
英剧《唐顿庄园》又再次向观众展现了英国乡间别墅的独特韵致。全剧宛似一首优雅、沉郁的英格兰叙事长诗,始于1912年,终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格兰瑟姆伯爵一家为代表,映见了贵族与仆人、主人与宾客的人世百态。
而《漫长的周末:英国乡间别墅的生活》一书问世不久便荣膺《每日电讯报》的年度推荐图书,跻身《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畅销榜单。作者艾德里安·泰尼斯伍德为写作《漫长的周末》,花费多年时间踏访和调研乡间别墅,查阅了近千份回忆录和无意发表的信函、日记,从银发的老伯爵、寡居的女继承人、见多识广的男管家那里获取证词,而后又化繁为简,对这些一手史料巧作剪裁,最终带给了读者“身处乡间别墅的图书馆里,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的阅读体验。兼顾学术旨趣和阅读意趣,主动为读者着想,这或许也是泰尼斯伍德的作品雅俗所共赏的原因之一。
乡间别墅是穿越时间的守望者
英国的乡间别墅,像英国的历史一样,表面波澜不惊,内里暗流澎湃,聚合了不变与变的双重因素。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乡间别墅作为一处历史场景、一个物理空间,为流逝的时间提供了锚定的坐标。
数百年来,英国上流社会始终保持着封建时代的传统,以拥有地产为荣,以坐拥别墅为傲。许多乡间别墅是真正的古迹,是英国历史的缩影。造反不成的怀亚特家族留下的阿灵顿城堡,如今周身布满青藤,风景如画;被砍了头的安妮·博林留下的赫弗城堡,依然被护城河环绕,阴魂不散;似乎每一座古堡里都藏有中世纪的彩绘十字架屏风和乔治王朝的胡桃木家具……那些事实上并不宜居的古代的残垣断瓦,恰恰构成了英国乡间别墅最具吸引力的特质——它有能力带给人们稳定和延续之感,有能力为人们提供庇护所,在文化和社会变革的漩涡里,扮演静止的中心。
诚然,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孕育了最早的现代都市和大机器制造业,可是真正的英国在乡下,真正的英国人是乡下人。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一定是热爱老宅子和田园牧歌的。安恬闲适的下午茶、紧张刺激的狩猎、衣着华贵的晚宴、灯火通明的舞会……英国贵族相信,这种典雅、正统、矫饰、有序的生活将永远不会落幕。
乡间别墅是时代更迭的见证者
然而,一切事与愿违。
自其变者而观之,20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日子,又是一个疾风骤雨的变革时代。乡间别墅以其在空间上的岿然不动,刚好见证了时间上的物换星移。
对外,渴望重铸世界秩序的德国,与老牌霸主英国久已势同水火。终于,1914年,一战爆发,枝头上歌唱的云雀被隆隆炮声赶去了天际。《漫长的周末》以斯托海德庄园的继承人哈利之死作为全书的开篇,他的阵亡是英国贵族慨然捐躯的真实写照。
对内,自19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以来,贵族的政治权力愈发萎缩。非但如此,遗产税法案的通过又令世家大族在经济上大伤元气,贵族子弟时而会因为高昂的遗产税,在继承祖宅时紧锁眉头。
战后,英国迎来了洗牌,这直观地反映在了乡间别墅的频频易主上,基林城堡的大议事厅拥有全英国最精巧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室内装潢,现在被卖给了美国富商。米德尔顿庄园迎来了新的女主人——在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中饰演失明卖花女,刚结束上一段短暂婚姻的好莱坞大明星切瑞尔。
一代新人换旧人,新的室内装潢、社交礼仪随同新人,被引入了古老的英国乡间别墅。电灯、电话、电报等电气化时代的新技术,也不可阻遏地闯入了乡间别墅。
社会史与公共史学的交融
社会史崛起为一门显学,始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的浪潮席卷欧美各国,更进一步促成了历史科学的“社会史转向”。这种治史的风气,对于泰尼斯伍德等成长于战后的新一代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社会史率先把社会的结构、进程、运动,列为历史研究的全新对象的话,那么公共史学则开创性地把社会大众纳入历史研究的服务对象,公然举起了“使公众受惠”的旗帜,前者拓展了传统史学的视域范围,后者扩大了传统史学的受众群体,二者异曲同工,分别为历史研究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如此,重视日常生活、贴近大众兴味的社会史研究,天然契合了公共史学的审美诉求,使得二者在未来的聚合变得越发引人期待。
从这一方向出发,《漫长的周末》由社会史领域的专家执笔,选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乡间别墅和别墅生活作为切入点,以微观折射宏观,从个体意识中照见集体心态,艺术地兼顾了社会史的学术性和公共史学的趣味性,这是历史学家回归公共领域的可贵尝试,也是当今历史学两大分支学科彼此合力的成功实验。研究社会和国民,为其而作,且为其所乐见,正是史学从业者的荣幸和使命。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