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伟《引路人》:人类在灾难面前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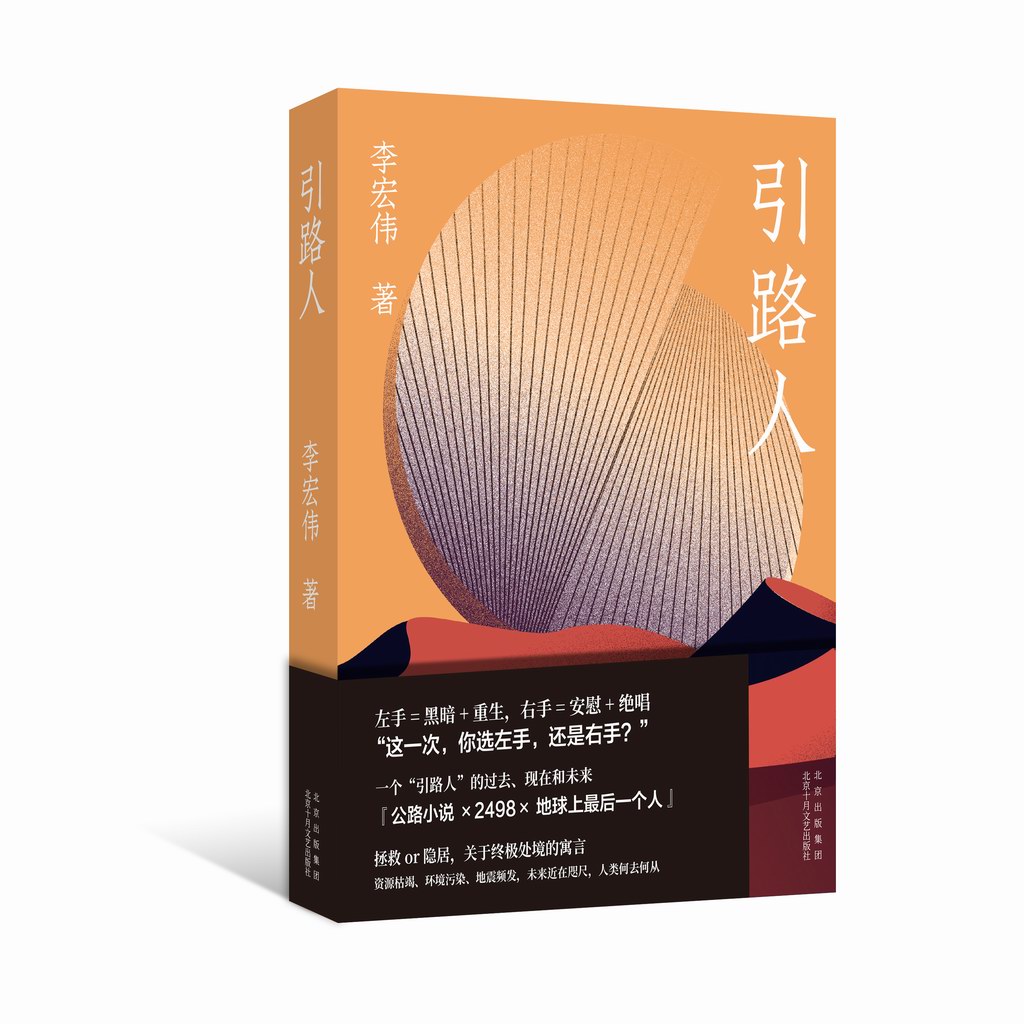
《引路人》带书腰书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作家李宏伟的《引路人》,这本书的背景设定在未来的“新文明时期”: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地震频发,地球被推到了极端化的处境。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案被实施,整个世界被区分为“丰裕社会”与“匮乏社会”。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月相沉积”“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月球隐士”。第一部分是现在时态,第二部分是过去时态,第三部分是未来时态。它们按次序分别呈现出核心人物的老年、青年和童年时期。
近日,《引路人》的一场新书分享会在线上举办。作家、评论家弋舟、张楚、季亚娅、肖江虹、黄德海、江汀与读者分享了《引路人》。
弋舟表示,《引路人》有一个宏大的架构,对未来有想象,主题直关人类命运,还有点悬疑小说的色彩。“如果硬要给这本小说下定义,科幻小说、类型小说、未来小说、末世小说,都难以去涵盖它。”张楚指出,“李宏伟关心的是将来的世界到底朝哪个方向走。他想讨论一些终极的问题,需要具像、表象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

李宏伟
选择的中间地带
这本书的责编江汀介绍说,第一部分在结尾抛出了整本书的核心问题——当人类在最大的灾难面前只有两条路,选择左手,会将人类带入非常困难的境地,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人会牺牲,但能够存留文明的种子和火焰;而选择右手,代表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所有人在一种温暖的团结当中全部去世,但也是一种很安慰的绝唱。“这一次,你选左手,还是右手?”,书中人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将与这个选择相关联。
季亚娅站在作者的立场分析,认为李宏伟既推出了左右手选择的有力命题,又同时表现出一种警惕。“比如他在里面一再嘲笑男人和女人的对立,还有底层和上层的对立。其实这是对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的思考。他说这种话语模式实际上是维系世界上大多仇恨和谎言以及冲突的根源。”因此她感到,“不要用左右手二元对立的方式禁锢你的头脑、去伤害你自己、去左右你的情绪、去愤怒。你所要做的是感受,发现这种逻辑结构背后的荒谬。我们到了不得不选择的时候,是尊重我们那一刻的本心、情感或者本能。但是你要反思它们从何而来,是不是已经被人塑造过的。”肖江虹也提出,除了左手和右手,还应该思考有没有第三种甚至更多种的可能。
黄德海说,在这些问题里,人们所有的选择都是“不得不”:“并不是说我们预想好了选择左手或者右手,而是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再不选择就面临瘫痪。”他指出,从《国王与抒情诗》到《引路人》,李宏伟的创作始终站在中间——只是引出情景,从来不做选择。“这个中间状态表面上看是犹豫,但其实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往下传递。大家所有的智慧在左手和右手的犹豫之间产生另外一个可能性,这也许是另外一代人的命运。”
而中间状态也是他认为《引路人》最出色的地方,“特里林说,立场之间才是唯一诚实之所。我们永恒地处于这个、那个甚至无数个可能之间。这本小说展现出了非常巨大的疑惑,对可能性的反思,对自己轻易站在某个立场上的质疑。”他还说,在这部小说中,所有难以抉择的问题,都被寄予了丰富、开阔和被反驳的空间,这非常重要。“如果想一步到位解决问题,其实我们不应该再扮演一个暴君的角色。在这些充分的可能里,甚至你在很多地方会看到一个男性揣摩女性心理时候的局限,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另外一个性别的人怎么想问题。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你会觉得文字的力量和自己能够理解的边界已经出现。”黄德海说。
江汀则引用罗杰·加洛蒂对卡夫卡作品的评论,来总结李宏伟的中间态度:“他既不是对世界原封不动的模仿,也不是乌托邦的幻想。他既不想解释世界,也不想改变世界。他暗示这个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
一切科幻写作都是写作当下
季亚娅表示,这本书的主题恰好跟她这两年做的两件事有关,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生态,这也确实是这两年非常受关注的两件事。
她认为李宏伟创作的原动力可能是现实焦虑:“当时最让我震惊的,就是他这个情节设计的核心:35岁没有找到对象的男性将会被流放到匮乏社会。网络上经常出现的一种集体的焦虑和无意识,就是关于两性性别话题的探讨,也是网络上特别流行的一个很主要的话题。很有意思的是他对爱情和两性关系的隐喻,中间有一个章节是樱桃园,那里面完全是一种诗意的叙述来探讨两性相处之间的各种可能性,有相爱,还有破坏,还有仇恨。最后达到的限度和可能性,以及最后那个状态,是两性合二为一的理想的人,没有性别的人。”季亚娅说,“引入性别视角,借这个女性曾经有对立的思考模式,借助她的眼睛,伴随故事的进程,去结构“之间”状态。我从来没有觉得性别是他一定要表示的内容,但这是很好的进入点。性别视角的意义绝不是用一种话语打倒另一种话语,而恰恰是这个视角维度的丰富。”
而生态则是指在文明和末世主题意义上的生态写作。她说,李宏伟对生态文学的理解,就是对自然的凝视中看清楚人类社会。“因为生态文学都有一个前提,就是灾难出现。有可能是环保灾难,有可能是自然灾难,比如这本书里写到的地震。也有可能是人和人之间的灾难。生态里面有一个词,废土意识。在这个废墟之上展开想象,恰恰是这个词汇和这种书写带给我们特别有启发性的地方。”
借用轻科幻、非现实的外衣和对未来文明的想象,能够更自由地讲述故事。“设置一个未来的末世场景,把所有想讲述的东西放入整个文明构架里面。比如这本书里放入的东西——有限的平等是什么,无限的平等是什么;有限的自由是什么,无限的自由是什么;工业污染和辐射之后的废土地带又是什么样子;人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管理自己渡过灾难。借用现实主义的故事,你没办法对背后直接的运行规则在前台表现,只能隐喻。但是在科幻题材或者末世题材里面,你可以把它呈现在前台,政治统治的模式、经济的模式,对人性伦理的探讨,都可以因为题材的弹性而拉扯到极限。”季亚娅说。
肖江虹认为,李宏伟的小说体现出哲学层面的稳定性,他完成了自我世界的构建。弋舟表示:“这个小说不仅仅给我们对未来人类世界的想象一些启发,所有的阅读都要对我们的当下起到某种抚慰。”
黄德海指出,无论是两性问题,还是生态文学问题,乃至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问题,都是我们思维的局限所造成的。“比如过去我们破坏自然的时候会认为是为了人类发展,但是忘记这个东西可能反噬人类自身,如果早意识到这点就不会出现这么恶劣的后果。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考虑这之间的状态,而不是果断地选择。不管是我们想维持田园牧歌式的未来还是狂飙突进式的未来,最终的方向,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
- 程德培:对视、对话以及热衷于拆解的对峙[2021-11-28]
- 炙饼·月光·行脚僧[2021-11-01]
- 李宏伟《引路人》:“现实顾问”与“附加题”[2021-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