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章文:翻译、花瓶与构建理想自我
11月21日,第十三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在上海揭晓,其中社科类获奖作品由章文翻译的《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以下简称《异域的考验》)摘得,颁奖词评价译作“精准地呈现了原作者精密而复杂的思考”,“还原度极高”。
傅雷翻译出版奖是我国法语翻译领域的重要奖项之一,奖励中国大陆译自法语的中文译作,《异域的考验》是第一部获奖的关于翻译理论本身的著作。严格来说,这部著作不属于社科类,对此,译者章文和澎湃新闻分享:“在法语表述中,这类关于思想传递的著作可以归类为‘essai’,即‘尝试’,来自于蒙田‘试笔’的概念,我个人可以认为将之理解成‘试着用语言来传达一个思想’。”
《异域的考验》1984年在法国首次出版,1992年出英文版,作者是法国学者安托瓦纳·贝尔曼(1942-1991)。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由法国学者研究德国特定时期的著作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法国的边界,在北美的影响力不输其本土:2000年前后,在社会思潮的变迁和学界的阐释下,这部著作在北美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距离法语首版37年后推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即使在今天仍然魅力不减,不仅是翻译领域的奠基之作,字里行间的哲思对于当下社会更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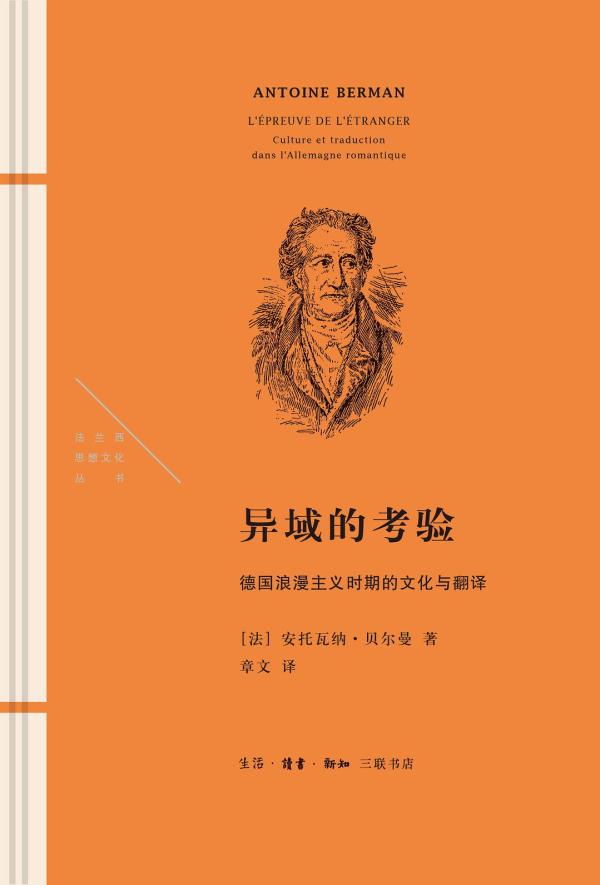
《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法】安托瓦纳·贝尔曼/著 章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之一,2021年1月版。安托瓦纳·贝尔曼,法国翻译理论家、德国哲学与拉美文学翻译家、当代西方翻译学的奠基人之一。翻译思想深受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本雅明等)的影响,摒弃法国式的种族中心主义翻译,强调尊重并接纳他者的“异”。《异域的考验》是最能体现其理论主张的翻译学及翻译史著作。
贝尔曼选取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聚焦于A. W. 施莱格尔、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并向上追溯到路德、赫尔德、歌德,向下延续至荷尔德林,系统地梳理了他们的翻译思考和实践。
这些浪漫主义者虽然看重翻译,但形成系统思考的却并不多。贝尔曼希望使隐形地罗织在这些人物的翻译实践中的理论与哲思显性地呈现出来,借这场梳理“揭示翻译理论在浪漫主义思想体系中曾扮演过的、却至今不为人知的角色”。译者章文称《异域的考验》令人想起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针对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观的一场考古”。
借由这本书,贝尔曼开启了翻译界“异化翻译”的理论分支,被誉为翻译界的重要奠基人。贝尔曼尤其重视“异”的翻译对民族文化的构建,正如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洪堡所说:“当语言意义扩张时,民族内涵亦会扩张。”
在贝尔曼看来,尊重他者的“异”,通过“异”对自我进行构建,是极其重要的:“构建必然会同翻译活动产生紧密联系:因为翻译就是一种从自身、从自我(也说是已知、日常或熟悉)出发,向着他者、异者(即未知、神话或不熟悉)前行的过程;随后,凭借着上述经验,翻译又会完成对自我的回归。”
即使不在翻译的范畴里,本书的思辨仍有丰富的文化意涵。如歌德所言:“与他者间的关系就是同自我的反面的一次相会,是同与我们对立的文化的一次交谈。”
我们采访了本书的译者章文,请她谈了贝尔曼的影响力和他开启的翻译流派、贝尔曼主张的以“异”的文化对自身的构建与中国过去及当下的关联,并从译者的翻译行为本身来看翻译处境题内和题外的理想与现实。

章文,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博士毕业于巴黎第三大学高等翻译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伦理及法国儿童文学的在华译介,教学之余从事翻译工作(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提供)
澎湃新闻:作为一部法国学者写的、关于德国特定历史时期翻译的著作,这本《异域的考验》在法国翻译史以及世界翻译史中有怎样的地位?
章文:我必须要说,虽然这本书是以法文来描述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实践,但是在西方的翻译学史上,而不仅仅是法国的翻译学史上,它是最为重要的奠基性著作之一。它的影响力在北美学界甚至超过了在法国学界。
因为我本人就是做翻译学的,我先概括一下翻译学简史。
翻译学最先从语言学中萌生,所以最古老的流派是后来所说的“语言学派”,纯粹地借由比较语际间的差别来比对译文和原文。后来出现了一些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翻译学研究,比如美国学者奈达(Eugene A. Nida,1914-2011)的理论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者开始跳脱语言的范畴,由此出现了后来常见的两个主要流派。一个是诞生于实践中的,强调交际行为的翻译流派,这些理论的创始人不约而同地强调翻译的交际性,比如法国的释意派,认为我们要翻译的并不是原文的语言,而是原文本中的意义,再比如德国的功能派,认为翻译既然是目标导向的行为,就要把原文本从它的语言中剥离出来,拿到译入语(目标语言)环境中实现交际目的。
翻译学的第二个主潮传统,则是由贝尔曼开创的,也被称为哲学流派。他真正地从历史学、精神分析学、哲学、神学的角度来看待翻译。一方面,他树立了翻译的正当性,要把翻译从“女仆化”的境地里解脱出来。在德国浪漫派的影响下,他认为,比起原著语言甚至所有原生态的东西,翻译可以处于一个更高的层次,是“超原著”、“超源语言”的。另一方面,他一次性地确立了“异化翻译”的合理地位。归化翻译的正当性是自不待言的,因为翻译要考虑读者,但是贝尔曼从相反的角度出发,认为异化翻译不仅是正当的,甚至是唯一正当的翻译策略。
贝尔曼的翻译主张被译成英文后在英美学界引发很大反响,因为这让他们发现了德国浪漫主义之后本雅明等人能为翻译学带来的突破。
所以,我认为从法语翻译学上来讲,贝尔曼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从世界翻译学来说,他不仅是一个奠基人,也是一个引荐者。在交际流派和哲学流派之后,翻译学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转向: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这两个转向联系紧密,很难区别,我们就泛泛地谈一下。比如多元系统理论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操纵学派”都是上述转向的早期代表,他们认为翻译其实是内嵌在译入语的语言文化系统中的,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来解释翻译。而广义上的“文化转向”的代表还有比如美国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或者一些支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学者比如雪莉·西蒙(Sherry Simon)。贝尔曼对这一转向,有着开创和启发的作用,一直到今天他的影响都非常大。韦努蒂他们一定是因为读到了贝尔曼关于德国浪漫主义的翻译理论的述评,才能发展出关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甚至关于少数族裔的翻译理论的主张。
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有一位我非常尊重的前辈学者说过,贝尔曼的作品是有神性的,他的很多话语其实是写给神的情书。他的语言里面十句话中有九句是写给人的,一句是写给神的,而所有的要旨都在写给神的这一句里面。换言之,虽然贝尔曼强调对他者的“异”的凸显,但是他是超脱于社会环境的一个人,他主张的并不是现世的“异”,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神、对至高精神的致意。可以说,韦努蒂、雪莉·西蒙以及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他们的主张是贝尔曼的现实性的版本。
韦努蒂把贝尔曼对“异”的尊重贯彻到了后殖民主义的场景中。他主张,把弱小的、被殖民国家的语言译成英文这种主流语言时,要采取相对忠实化的策略,才能让他们的文化身份在主流语境中得到充分“显现”,这是对他们的尊重,译者不应该隐身,译者应当是可见的(visible)。雪莉·西蒙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贝尔曼哲学思想进行继承,她认为在翻译时,要充分地为女性预留话语空间。斯皮瓦克是从北美社会的少数族裔角度出发,认为我们在对他们的东西进行翻译和书写的时候,要予以充分尊重。这几个版本虽然各有不同,但其实都是对“异”的尊重的尘世化的应用。
澎湃新闻:贝尔曼的“神性”或者说“对神的致意”具体指什么?
章文:德国的浪漫主义其实是较早或者说最早在欧洲形成广泛影响的浪漫主义流派,法国的浪漫主义已经是之后的一个产物了,是对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个误读。
德国的浪漫主义,说白了其实是对基督教传统的一种复归,它是中世纪文艺的一种复兴,它更强调的是我们怎么能够借由创作来回归神的国度,来复归于我们当时的一种基督教的最高的精神,所以它追求的其实是一种宗教的神秘和象征感,强调的是一种无限性。
贝尔曼深受本雅明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他似乎不在乎尘世间的自然语言限制,也不在乎我的翻译能不能够为译入语的读者所读,而是要接近巴别塔之前的神的语言。翻译难道单纯就是让我们这些尘世间的凡人交流吗?不是的。
这自然要说回本雅明的翻译观。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有一个著名的关于花瓶的表达。一部作品写的时候也没有考虑过能不能让作者读懂。我甚至觉得他的这篇《译者的任务》也是没有顾及到现实读者的,所以我不敢说自己的阐释是一定忠于他的精神的,只能概述一下。当然也可能因为描述得过于笼统,出现一些谬误。
在本雅明看来,大概可以把翻译当成对巴别塔诅咒的一个破除,在巴别塔的诅咒出现之前,上帝的语言可以被视为一个花瓶。巴别塔出现后,这个本来精美且完善的花瓶变成无数的碎片,撒到了世界各地。翻译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要忠实地翻译他者?因为我们在有自己的一片碎片的同时,也可以把他者的那一片复制过来,一旦我们把所有的碎片复制完成之后,就接近了上帝最开始说的最完美的语言,接近了“纯语言”。
贝尔曼也赞同本雅明的观点。我觉得,他一定在自己心中隐秘地认为,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需要沟通才有了翻译,而是因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要从现在的自然语言的经验性中挣脱出来,去接近神的超验性才需要翻译。所以,翻译不是给读者看的,翻译只对作品负责,它的最终目的是接近神的至高精神。

第十三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现场(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提供)
澎湃新闻:你刚提到翻译史的最初的语言学派,以及后来贝尔曼开启的第二条路径,反叛语言学的传统。那么贝尔曼的主张,在翻译学界是否产生了争议?
章文: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讲:贝尔曼的主张在理论上是无可取代的,但是在具体实践上,他的一些提法的确引起了很多争议。
贝尔曼对德国的浪漫主义的继承,是不是言之成理?这一点无可置疑。
释意派和贝尔曼的主张,在理论上应当是水火不容的。释意派认为,我们翻译的并不是原来的语言,而是原文的交际意图和内涵,所以传递到译入语时可以自由加工和改进——“自由”一词虽有点过,但译者有较大的诠释和改写的空间。贝尔曼则认为,翻译要忠实于原语言,让“异”的力量介入进来。
但是,所有人都会承认贝尔曼对异化翻译正当性的捍卫和理论贡献。《异域的考验》中,内容大部分是考古式的梳理,只是借由这个梳理以小见大,号召成立一门现代的翻译学,树立了几个颇为大的结论。
贝尔曼在树立了这些大的结论之后,又在《翻译与文字》(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一书里提出,翻译必须是反柏拉图主义的。柏拉图认为人的灵与肉可以脱离,为了更清楚地阐释,我想或许可以把“灵”对应理解为“意义”,“肉”对应理解为“文字”或“语言”。释意派对翻译的看法与柏拉图在理念上我认为是相通的,即“灵”和“肉”可以剥离;但是贝尔曼认为灵与肉不可以脱离,必须通过尊重肉才能尊重灵,或者干脆说“肉”和“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异域的考验》中他也主张翻译一定是对文字(肉)的最忠实的翻译。在这个层面上,贝尔曼的主张就有了可争议的地方,事实上,对于贝尔曼所有的争议几乎都是在这一个层面上的。如巴黎高翻的释意派创始人之一勒代雷(Lederer)教授所说:贝尔曼的翻译主张最大的风险在于,他试图给译入语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忠实的“异”,但是,对于“肉”的过度忠诚,一定会导致提供的是一个变形的他者,或者是一个已经被毁容了的他者。
但是,我听前辈老师讲过一个掌故:法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拉德米拉尔(Ladmiral)也是归化派翻译的信徒,与贝尔曼的理论主张完全不同,但是两人一辈子都是非常好的朋友。贝尔曼葬礼上的悼词就是拉德米拉尔致的。
澎湃新闻: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翻译《圣经》,部分地也借用希伯来文的圣经原本革新了德语,并在表达方式上参照了民众的语言,从而让德国的普通民众能够理解它,成为德国宗教改革的基石。贝尔曼评价:“路德所激烈排斥的,是作为罗马教廷官方媒介的拉丁语,更广泛地说,是书面的拉丁语。”路德的翻译开启了德语的翻译传统,翻译被视为对自我语言空间的构建,也成为了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的先声。之后,翻译有了“异”的力量进来,参与构建德国的文化。在中国,晚清民国时期的译介活动,以及白话文运动,是否有与之可类比之处?
章文:当然,我非常赞同你的类比。我个人认为,路德的翻译对德文来说,更多的是“建构”(Bildung,我深知这个词汇有“教育”、“教化”等多重意思,但我宁愿相信在路德《圣经》译本与德文的关系这里,它可以作“构建”讲),晚清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改革”和“现代化”。
据我所知,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翻译,尤其是直译,对现代汉语的形成和现代文学书写方式的习得,的的确确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词汇上、语法结构上、表达方式上,现代汉语极大地得益于直译。
我想到了一些知识点,当然还有待更新。比如傅斯年就主张汉字绝对地要用拼音文字来替代,钱玄同亦有同论,甚至还说过“汉字不死,中国必亡”。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说过,现在意义上的被动式在古汉语里是不存在的,“被”只能表示不如意或不被企望的事,如在古汉语里人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照顾”、“被邀请”等等,但是后来,得益于翻译,“西文里如意的事或企望的事也都可用被动式,于是凡西文能用的,中国人也跟着用(尤其是翻译)”。
我想提供一个个人的视角。我的确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法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对于我们的构建作用是明显且无可置疑的。我只想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翻译对于我国现代儿童观的构建,曾经造成过很大的影响。第二个是,法国儿童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影响了现代汉语文学空间里儿童文学的文体,此前我们没有童话、科幻小说和现代意义上的寓言。
第一点可以展开聊。“儿童观”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概念,不只是我国曾不把儿童当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个人,法国历史上也是如此。法国有一位著名学者曾说过,既然我们在好几个世纪都没有给儿童提供过合身的衣服,又怎么能指望提供给儿童真正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素材呢?
第一次儿童观的现代化,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伊拉斯谟、夸美纽斯等人。第二次儿童观的现代化则以卢梭为代表,而卢梭在中国的译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现代化。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说,应当把长者本位的道德改成幼者本位的道德。周作人曾说过,以前我们对儿童的教育很多是圣经贤传一股脑地灌下去,因为得益于西方对小儿的发现,我们才知道小儿和成人是不一样的。当然上述两位先生的思想源流颇为复杂,也不能全部归功于卢梭。胡适则说得更明显,新教育发明家卢梭有几句话说:“教儿童不要节省时间,要糟蹋时间。”坦白说,这句话的出处我未能在卢梭著作中找到完全对应的,但这种尊重童年长度的观点的确是卢梭惯持的论断。这一观点,还有更之前的先驱王国维关于儿童教育的论断,都能从卢梭的著作中找到明显的源流,与卢梭《爱弥儿》在我国的译介是共生共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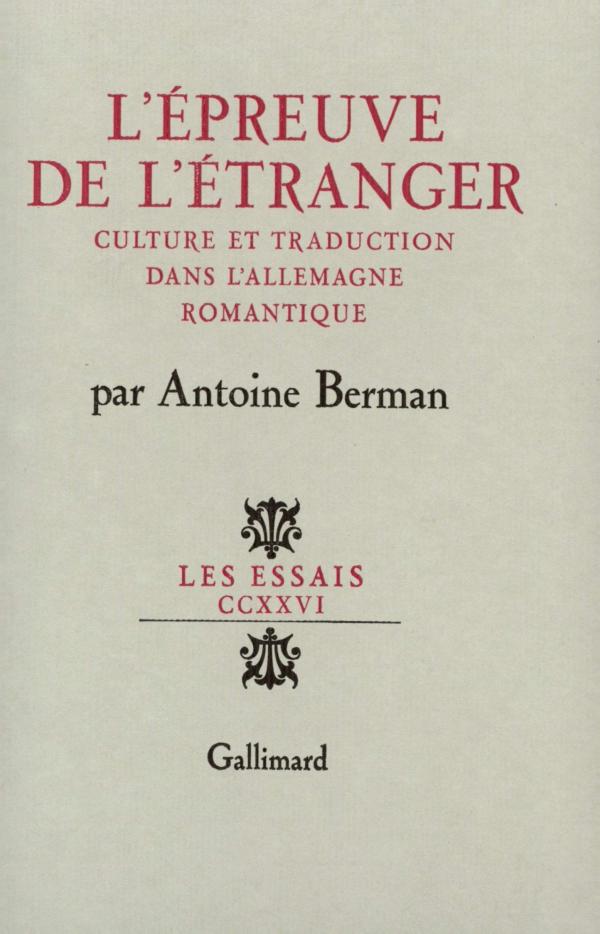
《异域的考验》法语版,1984年首版
澎湃新闻:《异域的考验》这本书法语版1984年出版,1992年被翻译到英语世界,2000年在韦努蒂的努力下,英美学界引发很大反响。时隔二十多年,这本书出版了中文版,却并未产生相应程度的影响力。您认为形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章文:虽然这本《异域的考验》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但贝尔曼的翻译主张在我国法语翻译领域早已为人所知。1998年,许钧和袁筱一两位老师出版的《当代法国翻译理论》中有很多内容介绍贝尔曼。
在语境上,北美社会复杂的族裔问题让他们对少数派或者弱势群体有天然的关注,所以更容易结合当代的社会现实引申出一些新的东西。在我们的语境里,不是有特别多的土壤能让贝尔曼的话语有现实性的意义。
还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在国内我们更多地会关注英美学界的理论,法语相对英语来说较小众。而英美学界对于贝尔曼理论的阐释和可能性的挖掘,我觉得几乎接近顶点了,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我们很难再阐扬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只停留在了解和引用上。
澎湃新闻:担任《异域的考验》这部翻译学奠基之作的译者,你是否有心理压力?
章文:心理压力是有的。翻译时有,翻译之后有,现在获了奖反而达到了压力的顶点,更感到羞愧和惶恐。再回到我刚刚引用过的那位很尊重的前辈老师的论断,贝尔曼写东西,有九句话是写给人的,但是有一句话是写给神的。所以我的第一重压力是担心自己不能够正确理解他。贝尔曼追求的是一种至高的精神,我虽然能够从语言上试图理解他,但我始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领会他的精神。第二重压力是表达上的,理解上的不完善让我很难确保用中文把他准确传递出来。翻译学中有一种说法,译者的翻译总是比原著的写作更加明晰,因为译者总是有一种惶恐,生怕自己译得不够清楚,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总是比原著看起来更加透明一点。我作为译者,虽然很明白这种倾向内部潜藏的风险,但是或多或少还是受到这种倾向的引诱,生怕读者以为我没有理解,所以遣词造句时总试图把我的话说得更明白甚至更浅显,我想在表达上我应该也无可避免地有和原文不同的地方,可能会破坏了原文本的神秘性和贝尔曼一直在追求的神性和晦涩性。
澎湃新闻:这部译作的理论性和思辨性都比较强,虽然作者是以你精通的法语写作,但其中有很多德语词汇,并且贝尔曼对这些德语词汇有自己的解释,把它翻译为中文的过程中,你觉得难度如何?
章文:难度很大。因为贝尔曼要用德国人的一些词句来展示自己的翻译主张,所以他的阐释可能比词句原意(即字典上或者大家对词句的普遍理解)有出入,这时我不知该采取哪一种方式,更多地选择尊重原作者贝尔曼,我想只有贝尔曼自己的阐释才是他最终真正想表达的翻译。事实上,虽然我自以为已经尽量忠实地翻译了贝尔曼,但成书后还是得到了来自各位方家的指正,明白自己对很多德语词的意义把控不够,相关的批评我也谨记在心,希望以后若有重印或再版的机会可以修正过来。
比如,贝尔曼的一个研究对象诺瓦利斯用了很多断片或者是断章(fragments)的表达方式。诺瓦利斯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表达一方面比较碎片,一方面比较形而上,他希望表达的是一种浪漫主义至高的精神。比如,我感觉他对无限是有追求的,可以说追逐“语言的语言、数学的数学、文本的文本”,我猜想即便用德文也是很难理解的,贝尔曼翻译过来的译文相对来说又多了一重障碍,所以我也只能试着直译。
翻译中的主要难点来自于贝尔曼本人。如前面谈到的,他是一个颇具神性的作者,他关注的并不是尘世间的翻译实践,因为他深受以本雅明为代表的德国神秘主义的影响,也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追求的是本雅明所说的一种“纯语言”:翻译带着我们超脱了自然的、经验的、语言的桎梏,让我们抵达一个更接近于巴别塔时态前的神性的语言状态。因此,他的大部分句子是相对清晰的,但是,我觉得总有一些句子中应该藏着他对翻译最深层的解读,也比较晦涩,即使法文的每一个词我都能看懂,连在一起,我也无法确切地肯定他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有哪个章节尤其难,一定是关于荷尔德林那一章。荷尔德林是一个很矛盾的作者,他在精神上也的确遇到过一些问题,最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他说翻译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们从古希腊人那里借来了天空之火的悲怆感,我们又有从古罗马时期流传下来的质朴感(用荷尔德林的话说,是“朱诺式的朴素”)。荷尔德林在翻译时,把朝向他者和朝向自我的两个面向融贯得特别好,但导致了文本的论述有一种极强的分裂感,对于我们这种长期受到逻辑式学术训练的人来说,很多地方难以把控。而且,荷尔德林的很多诗作我都难以译成中文,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体现这样一种双向运动的过程,非常痛苦。所以,我虽然很努力在模仿贝尔曼去尝试做直译,但很多地方只能做到意译,试图传达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澎湃新闻:翻译贝尔曼的这本《异域的考验》时,你倾向于认同贝尔曼的理论观点,“将他的文字在不妨害理解的前提下尽量忠实地还原出来”。另一方面,你又出自释意派的摇篮之一巴黎第三大学高等翻译学院,理念与贝尔曼是两个路径。那么在翻译中,你个人持什么样的翻译理念?
章文: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这样一种说法:一旦一个人在一个学科里待太久了,在这方面的想法就很有可塑性,就总是辩证的,很难去照着一个线条一直继续下去。对我个人来讲,在翻译贝尔曼的时候,我希望我是一个贝尔曼主义者,但是我在做口译或者更加应用性文本的翻译时,我还是摆脱不了巴黎高翻给我的影响,宁愿做一个释意派的信徒。
澎湃新闻:罗森茨威格说,翻译就是服侍两位主人,“外国的作品和语言、己方的受众及语言习惯”,所以翻译既需要双重的忠实,也承担这双重背叛的风险。贝尔曼希望摆脱翻译的“女仆化”处境,你认为这种摆脱可以实现吗?
章文:悲观地说,我认为一时无法摆脱。翻译低于原著,译者低于作者,这听起来很绝对,有很多值得待商榷的地方。但是,这种以二元论为基础底色,把东西对立化、等级化的方式,不管是思想上还是结构上,都是人们赖以建构世界的准则,特别符合我们的现代社会的运转方式。我真的不认为短时间内能有更多改变,只能说,理解这种现象并且试图反思,可能是改变的第一步。摆脱翻译的“女仆化”处境,需要更多人理解翻译的价值,思考翻译比原著值得歌颂的地方。
(感谢《异域的考验》责任编辑吴思博在联络采访中提供的帮助并提供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