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山庄》的“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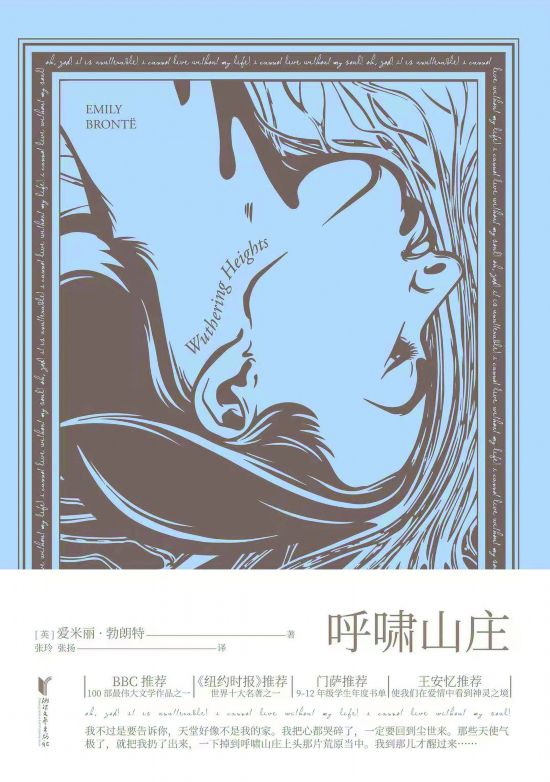
《呼啸山庄》被英国批评家称为“我们现代文学的斯芬克斯”——不仅作者艾米莉身世成谜,其创作素材也是长期未解之谜。在哈代之前,似乎没有哪位英国作家展现出如此深切的悲剧性(史文朋宣称其悲剧力量足以媲美《李尔王》)。小说描绘的梦幻激情和心灵感应超乎自然之上,并无任何现实基础,与另两位勃朗特姐妹(夏洛蒂和安妮)的题材风格也迥然有别。夏洛蒂在本书再版“序言”中强调“《呼啸山庄》是在一个野外的作坊里,用简陋的工具,对粗糙的材料进行加工凿成的……他用一把粗糙的凿子进行加工,他也没有模特儿,除了来自他的沉思的幻想”——几乎认定该书纯粹是大脑想象的产物,从而进一步“神化”了其创作过程。小说家梅·辛克莱(May Sinclair)由此断言,《呼啸山庄》源自“属灵的体验”,与作家所处环境及时代背景毫无关联。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本书问世百余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呼啸山庄》的创作起源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与夏洛蒂醉心于奢华的社交场景刻画不同,艾米莉对故乡霍沃斯的民间传说——中世纪的爱情罗曼司,古老的爱尔兰家族复仇,以及约克郡农庄佃户遭受领主残酷压迫的故事——情有独钟。这一种偏好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浪漫派文学影响:《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刊登的哥特式“黑暗”故事,广受读者青睐;拜伦诗作中雄奇的浪荡子形象风靡一时;德国浪漫派作家霍夫曼《古宅恩仇记》是她的心爱读物;柯尔律治《克丽斯特贝尔》中弱者变强者(并最终变为恶魔)的故事更被认为是“集拜伦式英雄与恶魔于一身”的希斯克利夫这一形象的直接来源。
根据批评家的一致看法,就整体风格而言,另一位浪漫派作家司各特对《呼啸山庄》的创作影响最大。书中对画眉山庄庭院屋舍的描摹,不禁令人联想起《威弗利》的开篇;而书中对于乡绅阶层家居场景的描写,如喧嚣纷争的恩肖一家,也神似《罗布·罗伊》中奥斯巴尔德斯通一家:比起与自己阶级相称的精神文化追求,他们似乎更愿意沉迷于赌博和美酒;甚至连书名中的形容词“呼啸”(wuthering)也是源自司各特的苏格兰歌谣——而非约克郡方言。
进入20世纪,夏洛蒂的一则日记引发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日记作于1844年7月30日,只有寥寥数语——“艾米莉,生日快乐。我只希望,你能留下更多的《贡代尔传奇》……它们必将流传于世。”无独有偶,安妮在一年之后的日记中也提及:“艾米莉在写诗。写什么不知道。”
传记作家温妮弗雷德·热兰(Winifred Gérin)对日记中语焉不详的《贡代尔传奇》作出了详细描述:“在新的一年里[1844],她(艾米莉)把自己的诗收集在两本谨慎保管的笔记本中,就好像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所写的东西是多么富有价值。再也没有什么装载伟大诗歌的东西比这两本笔记本更低调、更朴素:这些书背软软塌塌、线条模糊的酒红色笔记本好似洗衣妇的记录本。正是在这些本子上,她开始用一种晦涩难懂的自创书写方式抄录她的诗篇。”
遗憾的是,由于手稿韵文部分资料散失(散文全部遗失),历经二三十年搜集整理,《贡代尔传奇》才以《贡代尔诗篇》(1938)之名出版,由此艾米莉·勃朗特研究也步入一个崭新阶段。事实证明,无论是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还是场景刻画,两者都存在“诸多契合之处。从艺术样式来看,《呼啸山庄》堪称是《贡代尔传奇》的变体;就创作思想而言,《贡代尔传奇》无疑是《呼啸山庄》的先声。
据作者交待,贡代尔是“北太平洋的一个大岛”,但气候、习俗和景观与霍沃斯所在的约克郡极为相似。贡代尔国王朱利叶斯拥有两位情侣:一位是王后罗西娜,另一位是西多妮娅——后者为他生下女儿奥古丝塔(与拜伦同父异母之姊同名)。朱利叶斯心狠手辣,后来在一场宫廷内乱中惨遭暗杀,其王位由奥古丝塔继承。奥古丝塔生性风流,与多名贵族有染。她富于权谋,冷酷无情,将谋叛情人一一处死,最后自己也被推翻,在流放中抑郁而终。
贡代尔是不同于当时社会现实的假想世界,当地妇女不受任何传统道德约束。作为一部女权主义史诗,《贡代尔传奇》刻画出一位外表放荡不羁、内里机心深沉的女王形象——据说艾米莉的灵感来自维多利亚女王——女王登基的时间(1837年6月20日)比传奇中奥古丝塔的加冕仪式仅早一个月。更有意思的是,诗中居然安排年方十八(与艾米莉年龄相仿)的维多利亚女王应邀到访贡代尔,观摩奥古丝塔加冕——这也印证了夏洛蒂在日记中的看法:艾米莉时常沉溺于幻想,以致“想象和现实傻傻分不清”。
值得注意的是,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不同,艾米莉建构的贡代尔王国一切事务完全由女性主宰——在外寇入侵时,贡代尔妇女甚至上阵杀敌,犹如神话中亚马逊(Amazon)女武士。她们不像现实中的英国女性那样循规蹈矩(即所谓“家中的天使”),乐于充当平庸的家庭主妇和生儿育女的工具。恰恰相反,她们性格刚毅,思想活跃,对美好爱情充满渴望。这也是艾米莉与夏洛蒂大异其趣之处:在夏洛蒂笔下,爱情常常表现为单相思——女主会疯狂爱上男主(如简·爱之于罗切斯特),沦为爱情的奴隶,甘于自我牺牲。而在艾米莉笔下,女主往往表现得更为积极勇敢,更加渴望爱情中的平等(甚至凌驾于男性之上的)地位——于是,贡代尔传奇中的爱情故事不久便发展成为《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之间炽热而永恒的狂热恋情。
模仿史诗体裁(并参照拜伦《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样式),艾米莉在《贡代尔传奇》诗中插入若干叙事章节——大部分取材于想象中的王国编年史——以此展示男女主人公的种种欲望和痛苦,尤其是被放逐的女王奥古丝塔:她不仅失去王位,同时也失去家庭、财产以及人身自由。她被囚禁于地牢之中,受尽摧折凌辱(最终被迫遗弃亲生子女)——在政局动荡的年代,人人饱受磨难:上至女王,下至平民,谁也无法幸免。
这也是艾米莉对现实社会的影射。在标记为“作于1846年”的一篇诗作中,她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了贡代尔(英格兰)王国的一场内战:丰收的庄稼被马蹄肆意践踏,一旁则是食不果腹的饥民;被分裂的人民,为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和虚幻的宗教信仰,相互残杀,结果却发现从国王到女王,再到另一个新国王,人民承受的苦难一如从前。这一类诗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同时代(女)作家中可谓极不寻常,它们“间接反映出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至19世纪头50年间英国的社会动荡和阶级斗争”,而其中所蕴含的激情和愤怒,在《呼啸山庄》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据考证,希斯克利夫的原型是贡代尔传奇中出身寒微的国王朱利叶斯。在艾米莉笔下,他是强悍、意志和力量的化身,同时也是复仇神的化身。他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后,对政敌(及其支持者)进行疯狂报复,造成举国上下人人自危的局面——如传记作家克里斯蒂娜·亚历山大(Christine Alexander)在《勃朗特姐妹:玻璃城、安哥利亚和贡代尔传奇》中所说:“贡代尔到处弥漫着禁锢的气息:有的身体受禁锢,有的精神受禁锢……迫于统治者的淫威,谁也不敢发声。”
相对而言,奥古丝塔作为凯瑟琳的原型形象更为鲜明:她拥有一颗狂躁而孤独的灵魂,根本不了解自己无尽的欲望,更不愿轻易接受命运的安排。她反复无常,自私任性:一次又一次陷入疯狂的情爱,在爱焰消失后再将情人一一抛弃,在此过程中独自体味从天堂到地狱的大喜大悲——即便伤痕累累也毫无惧色。在“我的灵魂从不怯懦”一诗中,艾米莉以“自白体”的方式展示出女王孤傲而坚强的人格:她有意尝遍世间各种爱恨情仇,尽管偶尔也会对永恒逝去的时间感到遗憾和追悔,但“即便如此,我不敢听任灵魂枯死,/不敢迷恋于回忆的剧痛和狂喜”,而是在时间之流中无畏前行——恰如小说中凯瑟琳的爱情宣言:“若世上一切都灰飞烟灭,仅他独存,我会继续活下去。若是他消失不见,那这世界于我便将疏远如无物”。
众所周知,艾米莉对“囚禁”的意象极为钟爱,这一意象最早源自被伊丽莎白一世囚禁的苏格兰玛丽女王。通过仿写玛丽女王的悲惨人生,艾米莉“将猜忌、杀戮、情爱、囚禁和死亡等元素贯穿于整个贡代尔传奇”。同样,她把呼啸山庄比作一座封闭的城堡,用于囚禁男女主人公以及作者本人。正如夏洛蒂所说,艾米莉“习惯于把自己封闭在内心世界的城堡里——她的头脑是一座活跃而丰富的城堡”。由此可见,艾米莉在《呼啸山庄》写作过程中根本无力(也无意)从想象中的贡代尔王国解脱出来: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贡代尔传奇的延续”。
贡代尔王国中的人物经历监禁、流放、遗弃、绝望和自杀,最终完成传奇人生的不朽诗篇;同样的孤独感、寂寞感,以及背叛与复仇,在《呼啸山庄》人物身上也有明显体现。可见,她小说的素材并非源自天启,而是诗歌中融入的情感想象和生活经历。这些诗歌隐约形成一道轨迹,经过逐渐深化、提炼和完善,最后升华为她的创作思想和生命哲学。如批评家所言,贡代尔传奇旨在弘扬一种“精神存在”,它超越尘世一切,能够释放禁锢的灵魂,并能够将死生融为一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高度称赞艾米莉是“拜伦之后,无人能与之媲美的最杰出的诗人”,并认为贡代尔诗篇是她最有力的作品:她的强烈情感赋予诗篇内在的张力,而这种张力也体现在她创作的小说人物身上。因此,《呼啸山庄》最杰出的成就,就是“将混乱的激情置于日常生活的语境之中”,从而谱就一曲“人间情爱最宏伟的史诗”。
1845年10月至1846年6月,艾米莉完成《呼啸山庄》后,同时也终止了诗歌创作。她留下的最后几首诗主题都与死亡有关:同样包含囚禁、地牢以及人格面具(persona)等“贡代尔元素”。其实这也是她灵魂的真实写照。在最后一首诗中,艾米莉谴责这个专横暴力的世界“缺乏救赎”,同时她更骄傲地宣称自己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一个孤独的灵魂,“既不为家园而战,也不为上帝而战。”
感染肺炎后,艾米莉一直拒绝服药,也拒绝看医生。她觉得死亡并不可怕,它只是生命的延续和补充:死亡能使人的个性与自然元素相融合,是“与其他生物无声的交接和共情”。她经常不无遗憾地谈到天堂,但更愿意将地球作为自己永恒的安息之地,因为她的精神气质与自然早已形成“默契”。评论家认为,在完成杰作后,她已经耗尽了全部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生命本身,也自然迎来了死亡。
1848年底,艾米莉病逝于家乡霍沃斯。两年后,在她的遗作选集中,夏洛蒂加入一首未标注日期的诗篇,堪称是晚期艾米莉“性格和精神的最佳写照”:
我将前行,但不循往日英雄的足印,
——也不是那条荣耀的德行之路,
我也不会加入,如潮汹涌的人群,
那久远历史的身影,人脸已模糊。
我将前行,听凭自己天性的指引,
——另择向导只会徒增我的烦扰:
去往灰色羊群觅食的蕨丛山岭,
那里狂风阵阵,在山林间呼啸。
在这幅形象鲜明的自画像中,诗人/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的身份合二为一:《呼啸山庄》是它的亮色;《贡代尔诗篇》则是其“底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