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雀记》:作为性格悲剧的美学建构

苏童,1963年生,江苏苏州人。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为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著有中篇小说集《妻妾成群》《红粉》,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河岸》等。长篇小说《黄雀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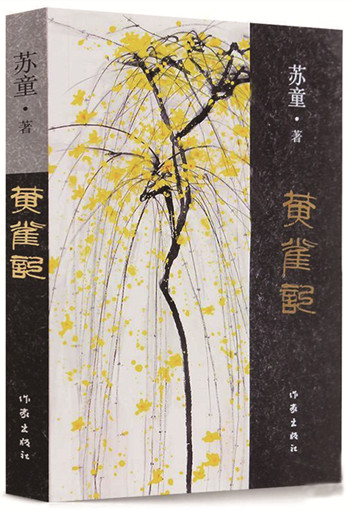
长篇小说《黄雀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苏童与悲剧美学的三种形态
《黄雀记》无论在苏童的创作史上,还是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都是一个带有现象意味的存在,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挖掘的美学标本。它融纳了多重思想元素,以其强大的个性印记和隐喻性挑战着阅读和研究界的审美习惯。从近年来评论界的反应来看,对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意象美学、成长叙述、女性悲剧、救赎主题等多种研究视角都有充分的关注和讨论,相关论文多达二百余篇。这一方面足见其强烈地激发了论者的阐释冲动,另一方面,这些讨论的多向性似乎也说明对于它的审美评价和价值定位尚存犹疑,莫衷一是,颇多浅尝辄止之论。
《黄雀记》特别值得挖掘的是其独具特质的悲剧美学意蕴。苏童近40年的小说创作所涉领域极为广泛,在女性题材、历史题材、成长题材、现实题材等方面,都有不少的精品杰作。尽管题材多样,故事各异,但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大多篇章基于作家对于“人的困境”的深度体验所带来的程度不同的悲剧美学色彩。
当我们把悲剧美学作为评论视角时,自然不能只是古老的悲剧理论对具体的文本泛泛而谈。就苏童的小说创作而言,总体上表现出三种基本的悲剧形态,即社会悲剧、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社会悲剧强调的是人与社会、时代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的悲剧,像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河岸》等,都存在着这样的冲突主线。社会悲剧作为一种基本形态,也可以表现为历史悲剧、英雄悲剧等。
苏童笔下的命运悲剧形态,有些类似于叔本华所说的“盲目命运”导致的悲剧。但是,正如大多数当代中国作家所表现的一样,苏童的命运悲剧不会刻意放大造成悲剧的神秘力量。另一方面,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苏童会突出作为悲剧根源的强大的文化力量。比如,《妻妾成群》的故事叙述就有意淡化历史与社会背景,颂莲无论怎样表现,都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桎梏,因此,它同时也是女性悲剧和文化悲剧。
在悲剧命运面前,颂莲们的被动性是第一位的,主体性、主动性难以起到改变命运的作用。性格上是否具有反抗性也不能影响悲剧的走向,甚至可以说,成群的妻妾谁的性格越刚强,谁越争强好胜,谁的命运往往越发悲惨。而在《黄雀记》中则完全不同,无论是保润、柳生,还是仙女,他们都有许许多多的自我选择的机会,都有向好的方向上改变人生的机遇和可能。换言之,他们不是被动地走向了悲剧,而是因性格的缺陷或者在主动的选择之下陷入了不可自拔的人生悲剧。由此,《黄雀记》建立起以性格悲剧为核心的美学形态。
性格悲剧与性格冲突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一方面以现实主义为主潮,另一方面先天远离宗教文化体系,因之,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在悲剧美学上表现出两个基本面相。其一是以“社会—历史”悲剧为主要形态;其二,即使产生了一些带有命运悲剧性质或者性格悲剧色彩的创作,也大多与前者纠结在一起,或者三种悲剧形态交互杂糅。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再到叔本华所分析的诸种悲剧类型,难以在中国找到一一对应的典型文本。苏童小说创作虽然也难以完全脱离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与审美心理,但相对而言,其悲剧创作在三种类型的纠缠中,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剥离意识与重构性。
悲剧美学的建构离不开悲剧冲突的设计。于《黄雀记》而言,尽管小说故事的跨度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世纪之交,香椿树街历经改革开放之初的春天到消费文化盛行的惶乱,但悲剧的主体冲突并不必然地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或者个体抗争与社会压抑的矛盾。主人公命运沉浮的轨迹,也不必然地取决于时代的变迁。当我们说苏童小说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大时代与小人物的关系时,应该主要限于他创作中的社会悲剧文本,同时也容易忽视时代之“大”与人物之“小”的相对性,甚至遮蔽掉小人物身上隐藏的主体世界和丰富的性格内涵。
在《黄雀记》中,悲剧冲突的本质则主要体现为性格的冲突,悲剧的走向也与复杂的性格冲突息息相关。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构成了小说悲剧结构的主线。祖父与母亲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性格矛盾与生活冲突。三位年轻主人公两两之间都发生了纠缠不清的性格冲突。与许多婚恋题材创作不同,保润与仙女的恩怨情仇,与贫富对立、地位差别等常见矛盾无多大关联。保润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仙女就被她身上那股“古里古怪的诗意”强烈吸引,无来由地喜欢上她,想方设法地接近她,但容貌姣好、骄横无礼的仙女并不掩饰对保润的嫌弃。少年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引发了敏感倔强、性格执拗的保润的攻击性和征服欲。在水塔的争吵中,情急之下,他以因照顾祖父练就的捆绑绝技将仙女拴在铁梯上,跑了出去。结果引来了强奸案的发生,也导致了保润的十年冤狱生涯。
二人之间的这种性格冲突直到保润出狱后再次相见时一如既往。保润找到变身白小姐的仙女要求“清账”时再次发生了争吵,白小姐不惮以恶言恶语刺激前者的自尊,她用“诚实的目光”,用实话实说的坦诚,直言“我实话告诉你,你以前很丑的,比现在还丑,又丑又抠门,柳生以前多帅啊,花钱大方,舞又跳得好,帅哥么,女孩子心里都喜欢的。”
小说结局阶段,保润突然放弃已经“清账”并原谅对方的承诺,在柳生的婚礼上捅死柳生,这似乎显得突兀的行为,一方面说明保润性格中有着被压抑至无意识层面的阴鸷暴力倾向,但另一方面,更为直接的根源则是因为即使因落魄寄居于保润家中以后,这位多年周旋于男人中间的风尘女子依然未改其自以为是、心高气傲的心性,未能顾及保润的感受,以一句脱口而出的“你爸爸的裤子,让柳生穿走了”让木讷而压抑的保润深感奇耻大辱,触发了他的过激反应机制。
与强大的外力作用导致的社会悲剧不同,也与惘惘之中被无情主宰的命运悲剧有异,性格悲剧往往发生于不经意的性格冲突,以始料未及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启人深思的悲剧结局。
性格的内在冲突及其美学意蕴
在《黄雀记》中,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冲突,尚只是悲剧冲突的外在冲突层面,它构成的是悲剧美学的表层结构;而发生于个体内部的自我内在冲突则具有更为深刻的审美价值,它体现着从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文化急剧转型时期人们内部心理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乃至分裂性。道德的变迁、人性的变异、动态的人心文化等尖锐复杂的问题都蕴藏在悲剧美学的深层结构之中。
从人物形象塑造来说,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三个悲剧主人公形象,都不是那种与典型时代环境中相对应的带有某一阶层思想或者身份意识的典型人物。但其性格又绝非那种概念化的扁平人物,或者表达作家某种理念的传声筒,而是鲜活的、丰满的,更重要的是始终处于动态的和矛盾性的内在张力之中。我们很难用某种固定的道德概念或价值判断来框定它们。
保润性格中既有盲目冲动、孤僻固执的底色,但同时也带有懵懂单纯、渴望被爱的一面。他胳膊上刻上“君子”“报仇”这样扎眼的刺青,无妄之灾让他的仇怨沉淀了几分,也让他成长了几分。而所谓复仇,也不过是要求回到水塔与仙女跳一曲小拉,事后就算“清账了”。保润对懵懂情愫的执念以及他性格中成长起来的理性意志,几乎让人看到了与生活和解的可能。自卑与自尊、复仇与和解、执念与放下、疯狂与理智,构成了保润性格中极其尖锐的一系列内在冲突,而且作为动态的矛盾张力推动着悲剧的走向。
常见到有论者评介《黄雀记》时,说它是用一种怪诞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被冤枉的少年,“如何在命运的裹挟下,一步步走向杀人深渊的故事”。类似这样的评价未免夸大了社会与命运的裹挟作用,而低估了主人公的性格冲突及其作用。性格决定命运,在苏童小说所建构的悲剧美学世界中,绝不只是展现大时代的滚滚车轮如何碾压小人物的命运,更要符合逻辑地展现小人物也有庞大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
侥幸逃脱惩罚的强奸犯柳生,其性格中则纠结了复杂的善与恶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油滑投机,痞性十足;但另一方面他又灵活大度,勇于忏悔,心存纯洁的一角。正如在庞先生别墅的露台上,白小姐问柳生是否做过祷告时,柳生所回的:“上帝和菩萨,我都无所谓。我就巴结财神爷,财神爷才是老大,你不信到庙里去看看,谁那儿的香火最旺?谁的香火旺,谁就是老大!”极为真实地道出了他唯利是图的一面。但这并非他性格的全部。
柳生多年“夹着尾巴”做人做事,长期代替保润照顾祖父,这不能不说是心甘情愿的向善之举。柳生心中的纯情与善念,还存系于那个当年的仙女。每当他想到当年那个仙女,骨子里就觉得没有其他女人比得上她。柳生善做生意,手上宽裕,也有过不少女人;但在他内心深处,“谁也不如仙女干净,谁也不如仙女刺激,谁也不如仙女性感。”即使面对落魄而归的白小姐的颐指气使,柳生也甘愿鞍前马后、赴汤蹈火。柳生性格内在的复杂冲突,显然不是简单的内疚或者还债心理能够解释的。
作为受害人与施害者的集合体,仙女身上的可怜与可恨之处都是那么突出。她以高傲洒脱的姿态掩盖孤独空虚之感,试图通过狂热追逐物质欲望改变弱者地位,滑向堕落的深渊却又不放弃对爱情的幻想。
变身白小姐后,她凭借颇为自信的姿色与智慧,几乎是以雌雄关系中身居优势的强大“母螳螂”一方自居,将男人视为自己的猎物,视为自己视野之内可控的“蝉”。然而,仅仅是一次在欧洲的浪漫之夜的忘我动情,她糊里糊涂地避孕失败。性格上的弱点强化了她人生的悲剧性。“为了报答一个夜晚的恩情,也许要付出一生的代价”。问题更在于,她忘了,这“恩情”难道是值得报答的么?“她发现自己的弱点像雨后春笋,任何一场雨下在任何一个角落,笋尖便会猝不及防地钻出地面,若要长成一棵竹子也好,可惜,弱点的春笋,最终都是被人割去食用的。”
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说,存在先于本质,一个人的选择可以重新定义自我的本质。但对于白小姐来说,我们惊讶地发现无论她怎样选择,都改变不了她的悲剧本质,也改变不了在堕落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的方向。怀上台商庞先生的孩子后,她先是选择去打胎,庞先生毕竟不是那种她离不开的年轻帅哥。临手术前,她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留下孩子并去找庞先生,她感觉庞先生似乎正是她黑暗里的光。可惜她太自负也太自恋了,见面一番试探和失望后的发作之下,两人反目成仇。
性格的内在悖论与人格的分裂,使仙女的自我成为自我的敌人,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他人,她都看不到真实。“白小姐的夏天”一开始有这样一句话:“她与我们这个城市之间,似乎有一个不公的约定,约定由命运书写,我们这个城市并不属于她,而她天生属于这个城市。她又回来了。一条鱼游来游去,最终逃不脱一张撒开的渔网。”这张渔网的确便是那逃不脱的人生悲剧,但白小姐只清醒地预见了真相的一半,另一半她也许永远参不透。那就是,这张渔网并非完全由外在的大手编织而成,她自己也是作茧自缚的编织者。
如果说黄雀无处不在,那么,每个个体都应该知道,你在作为螳螂去捕食蝉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自我制造着一只黄雀。《黄雀记》以隐喻的形式完成了性格悲剧的美学建构。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在《文艺报》所开设的“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2年2月21日第5版。)

相关文章:
- 河水与招魂:从《河岸》到《黄雀记》[2022-02-21]
- 培育中国当代文学新经典——茅盾文学奖40周年刍议[2022-01-26]
- “博物”美学与情感记忆的光泽[2022-01-24]
- 破局者:金宇澄和他的《繁花》[2022-01-24]
- 独家|茅盾文学奖得主、网络文学名家首度同台:所有的文学都来吧[2022-01-13]
- 英国“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举办苏童的《黄雀记》推介活动[2021-12-28]
- 塞尔维亚“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举办作家苏童读者见面会[2021-12-23]
- 如何讲好中国城乡故事[2021-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