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狐》:万物皆变 无一消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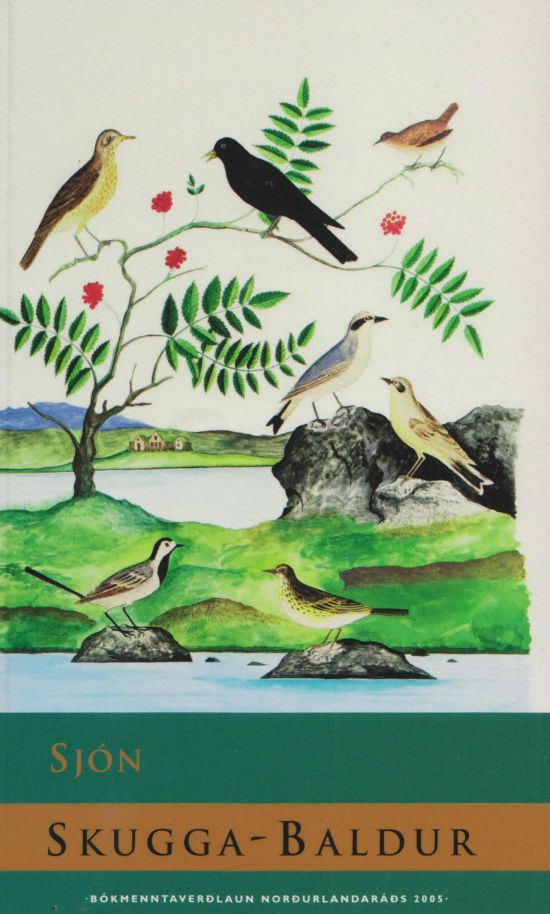
《蓝狐》冰岛语封面
当你的眼
停在球上
那挂于一颗星第三枝头的
你记得为何黑了,又为何正在变亮
地球(就像心脏那样)向后靠在它座位上
就这么它沿轨道行进
进入黑暗
天黑色的手掌里未抛光的珍珠
闪烁的太阳火焰
你记得
自己是个光明的使者
从别人那里收到了她的光热
这是松的几句诗。冰岛最受世界瞩目的当代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松(Sjón,1962),原名西格勇·比尔基·西格松。笔名是原名的缩写,有“视觉”的意思。16岁时用暑期打工的收入自费出版处女诗集。1987年的《钢之夜》是其小说处女作。他的第五部小说《蓝狐》于2005年荣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评委会赞扬这部作品巧妙地在诗歌和散文的边界建立了平衡,从冰岛民间传说、浪漫叙事艺术和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里编织所有的主题,其中凸显了当代伦理问题。此外,1980年代即活跃于冰岛乐坛的松是一位知名音乐人,他作词的作品在2001年获奥斯卡以及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提名。作为屡获世界殊荣的作家,他的小说已翻译至35种语言。
蓝狐的故事
《蓝狐》的情节不算复杂,事件主要发生于 1883年的冰岛乡间、寒冬一月那十天里,中间穿插有关此前的回忆,末尾缀上此后的补白。两条主叙事线交错着推进故事。
首先是猎人和一只雌性蓝狐。他要它的命,而它似乎并不打算真的逃脱。这场生死追杀缓急有序,阴冷中还出现了北极光姐妹的曼妙舞蹈,诗情画意唯美地演奏着一出惨烈复仇剧的序曲。小说家的笔下是诗人训练有素的凝练字符,他深知如何以寥寥数语将思想从一处带往另一处。有时一页只一行,这行字让空白围绕,就像猎人与蓝狐让静默无边的冰雪围绕。可有时,松又不惜笔墨地描摹细节,他对19世纪末的冰岛民俗等做过案头研究,把想象的或古老的场景琢磨得如同亲历、如在眼前。
另一条线是药草师和阿芭。药草师学过自然科学、大学肄业。他在药房当过助理,他喝进口茶、读法文书,更重要的是,他对唐氏综合症(旧称蒙古症)有科学认识,不似当时的广大民众那样,以为唐氏综合症患者是亚洲怪胎。 一只巨大的荷兰船在雷克雅未克附近搁浅,水手们不见了,船上扣留着的慰安妇阿芭似乎怀了身孕,她是唐氏综合症患者。不久,阿芭因为私埋婴儿将受审。本是短期回冰岛处理老屋的药草师遇到阿芭,搭手相救,阿芭从此在他监护下一起在乡村老屋里平安度日。
如果不是老牧师死了、新牧师来接任,药草师和阿芭不会和新牧师有任何交集。这新来的牧师禁止阿芭这样的“怪物”进教堂胡言乱语。会众迫于威权也一起排斥阿芭。本来,对阿芭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穿戴着礼拜日的漂亮服饰去教堂了。她还特别爱鸟,牧师的仆人、那善良的傻子非常爱她。
冷酷又贪婪的牧师在冰雪天追猎蓝狐,为了皮毛。出门前,他刚主持了阿芭的葬礼。身为唐氏综合症患者,在老屋居住16年后,阿芭活到约30岁,算正常死亡。不过,运到教堂的棺材里其实没有尸体,而是牛粪等。药草师以此反击冷漠的牧师和缺乏同情心的群众。他在自己和阿芭一起种出的树林里以泪和诗给了阿芭更有尊严的埋葬。
蓝狐应枪声倒下。雪崩,仿佛枪响的回音。让崩裂的雪冲到冰川洞里的牧师见一个女子走来又消失。而他塞在袋子里的蓝狐复活了,蓝狐抖掉身上的血,甩出胸膛里的子弹,和牧师展开一场关于电的争论,那时,电是个时兴又重要的议题。牧师伺机举刀刺死狐狸,把它的皮套在身上,将它的心送入嘴里,在死前的瞬间,牧师似乎成了一只蓝狐。
最后,药草师给友人的信成了一把解锁钥匙,披露牧师和阿芭的父女关系。多年前,阿芭的母亲死后,12岁的阿芭让生父以一杆枪和一袋子弹的价值给卖了。
松将牧师设计为猎人,并将他设计为阿芭的父亲,让两条线步步逼近。有着诗歌和散文肌理的《蓝狐》完全可以读作侦探和悬疑小说,因为这里有一场精心设计的谋杀,不然牧师不至于非要在暴风雪将至的日子出门打猎。药草师给前来拖运阿芭尸体的牧师仆人递过一封信,一再叮嘱须在葬礼结束后而不是开始前交给牧师。在那封信的末尾,有一行漫不经心的附言:昨晚梦见山谷里有一只蓝狐。这行字轻松勾动了惯于拿皮毛赚钱的牧师的贪心。
药草师甚至看到了牧师带枪出行的身影,转身进屋睡觉。牧师猎狐,也踏上了遭遇复仇的不归路。药草师对牧师的操控不限于一封信的引诱,他对迷幻剂也颇有心得。在牧师给延长了的死亡一刻里,蓝狐和牧师在冰洞里辩论,蓝狐说了个法语词汇,意思为“是吗”。这个词在小说里只出现了两次,另一次就是在药草师给友人的信里。
在现实主义的外或内
“蓝色山狐跟石头不可思议地相像。冬天,当它们卧在石头边时,想要把它们和石头分辨出来完全无望,真的,蓝狐比白狐狡猾多了,白狐不怎么能给看出来,可它们总在雪地投下阴影或在雪的映衬下看上去略微发黄。
一只蓝色雌狐紧靠在她的石头边,任一阵阵风袭过脊背。她拿屁股对着风、蜷起身子、鼻子埋进前腿下;垂下眼皮,只瞳孔还能感知。就这样她侦察着那男人,自打藏在飘挂的雪块边,他就纹丝不动,在这奥谢伊马山的最高坡待了约18个小时。风狂吹着,雪飞旋着朝他盖去,现在他很像残存的房基断片。
而那动物一定得小心,不能忘了他是猎人。”
《蓝狐》就是这样开了头,共四章,每一章先注明日期。在呈现了1月9至11日的猎狐场景后,切换到8至9日,谈阿芭的死去和埋葬,夹杂诸多回忆。继而回到11至17日冰雪地里子弹打出后猎人与蓝狐的对决。最后,以一封3月23日的信件结尾。按照松的说法,这是运用了舒伯特弦乐四重奏结构。的确,这一结构帮助作家不断打破线性叙事顺序,小说才有了持续的动感和张力,甚至有了得到反复的副歌。比如开头这一页文字在第一章近末尾处一字不漏地再次运用。可以说,松善于调配字眼的位置和信息量的浓度,在跳跃的文字里展示了资深音乐人的功夫,像专业音乐人把玩音调、音量和音长那样,他在文字的长短、轻重和起伏上匠心独运。
以音乐结构架构小说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就拿更早获得过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当代瑞典作家P·O·恩奎斯特来说,他那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1985年推出的《堕落的天使》是一则关于怪物、婚姻和爱的故事,采用奏鸣曲结构,也打破了线性时间,也有交错的两条主线推进故事,打散得破碎的一个个纸片要求读者快速组合,小说的语言也隽永如诗歌富有抒情性,就连篇幅也和《蓝狐》相差无几。可归根结底,恩奎斯特的《堕落的天使》和松的《蓝狐》有根本性的不同。谦虚地自认为其实是个深度报道记者而非小说家的恩奎斯特,在《堕落的天使》里的确拌入了很多神秘和奇谈,可他终究是个现实主义作家。松则可以说是一个从超现实主义的石头里蹦出的新世代作家。
松细数过影响自己文学创作的因素。阅读冰岛民间故事时不过7岁, 这个喜爱湖中怪物和山里巨人的孩子把自己读成了儿童百科全书,熟悉冰岛神话,也涉猎希腊和罗马神话。12岁时,他对占星术着迷。接着他又迷恋起科幻小说。后来,他受到冰岛作家居兹贝于尔·贝尔格松的现代派小说影响,还钟情于瑞典超现实主义诗人贡奈尔·埃凯洛夫的诗歌。不过他最大的偶像出现了,那就是大卫·鲍伊。这个相貌奇特的歌手的歌词让松看见了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门槛,由此深受启发,创作了处女作诗集。此外,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萨缪尔·贝克特,善于反映世界的混沌和文学的非现实感的博尔赫斯都成了松的文学精神导师,而神学教授之子、魔幻现实主义开山之作《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作者布尔加科夫让松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今不肯走出这一引力。还有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画家和小说家利奥诺拉·卡林顿等。不难想象,是从这一大群超现实主义者那里,松学到了以多种文学形式来创作的开放态度,带着这一态度试图堆起富有创造性的冰岛新火山。在《蓝狐》之前的小说里,松无一例外地依从了超现实主义传统,相比之下,《蓝狐》更紧凑而有力,也因此给松带去了突破性的成功。
超现实主义者排斥现实主义,不过近年来,松宣称自己书写的其实是现实主义小说, 因为一切皆基于人物经验,皆是尘世生活里的存在或人们头脑中体验的真实。很可能,他的书写不过是以奇幻、恐怖或夸张等形式去接触现实,以蜿蜒曲折的诉说在不同时间、在最具体和最虚幻的一切中穿梭。如果说博尔赫斯认为现实主义只是更大的文学史里的一个插曲, 松所欢迎的现实主义或许是可容纳传说和神话模式的超现实的现实主义,故事发生在过去,却非历史小说, 对于神怪,对于人的蜕变充满兴趣的松,将历史的余音翻新甚至逆转,和文学史上的重要遗产如传说、神话和史诗做对话和呼应恐怕才是他真正的文学野心。
和传说、神话及史诗的距离
《蓝狐》副题“一则民间故事”。书名原文“Skugga-Baldur”,“skugga”意思是“阴影”,“baldur”则为男子名,有勇敢的意味,更是北欧神话里的光明之神巴德尔,也就是主神奥丁和神后弗丽嘉的儿子。“skugga-baldur”是蓝狐的别称,在冰岛民间信仰里,蓝狐是公猫和母狐(亦说母狗)的后代,是会暴怒的家伙,是影子般鬼鬼祟祟、作邪恶之事的恶灵,子弹根本打不死它。曾有农人徒手搏杀它,死前它哭喊着求农人转述一句话,当晚,农人这么做了,话音未落,一只猫立刻扑起,咬住农人的喉咙,把他给咬死了。这样的传奇生物以及围绕它的鲜血之光构成了《蓝狐》的骨架。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给邪恶牧师设计的姓名是“Baldur Skuggasson”,暗示了巴德尔牧师和蓝狐的关联乃至一体性。
充满诗意的《蓝狐》的语言,有时也有粗粝之感,如冰岛的风雪,如维京人荡气回肠的诗歌,能传达出浓烈的生和死。牧师和狐狸的死生转换可能是出于玄幻的需要,也可能透露了在不少冰岛人看来相当可信也十分重要的看法:有些东西在某一纬度死后仍在其他层面存在,也会进入活着的人的梦境和思绪,就像这只蓝狐走入松的思绪,走在他笔下,而后由更多的人口口相传。
如果说缺乏神话和民间传说的日子在冰岛人看来绝无可能,缺乏神话和民间传说元素的小说在松的书写中也并不可能。神话和传说是往昔的民间诉说的提炼。松往往为自己的小说选一副神话或传说的骨架,他书写的过程成了往那副骨架上贴上一块块皮肉、吹上一口气的过程,好让一个生灵活起来。他承认,有时自己动用传说和神话的技术并不圆熟,比如在小说《月光石》里,作为作者未能全身而退。看来松重视变身就像巴德尔牧师披上蓝狐皮,但更重视进退的自如,以便在对神话和传说的现代化改造工程中,在它们及日常间进出自如,抖落一张皮就能回归日常。没有和当下的连接,神话与传说便没有意义,松的目的是进入神话又摆脱神话。
松认为,断片能推动故事发展,正如日子由一系列片段组成,读者完全有能力将断片自行整合并完成理解。或许是作为小说家的松有意识地要排除现实的整体画面,他把断片文字剪辑拼接,有大量留白。断片叙述一定程度上类似传说与神话在口口相传中时而受遮蔽、时而又获得发掘的过程。很难测算松的留白在多大比例上属有意为之,又在多大比例上属只能如此。总之超现实而刻意留白的写法是松的看家技术,这技术打破了读者想立刻获得全部真相和完整图景的传统习惯,松不给人具象全景,更愿给出带宏大寓意的暗示,给出时而细密、时而残缺的断章,好像神话那样的遥远的古代的信号时而清晰、时而消失。留白不是缩小而是拓宽了作品的疆域,增大了弹性和神秘感。
书写《蓝狐》时,松阅读了《奥德赛》,他认为自己也因此用荷马的眼睛看到了《蓝狐》里的文字。这简直是一种错误又正确的超现实主义说法,众所周知,传说里的荷马是一位盲诗人。《奥德赛》写一个男性英雄回乡复仇,那里有大冒险中奔放的想象力,有狂野的大海、塞壬的歌声、巨人的搏斗、家族的纠葛、人与人的连接。如果说《奥德赛》以大海为背景,《蓝狐》则是以雪山为背景。其中也有一个人的归来与复仇,不是男英雄,而是女人、普通人眼中的怪物和低能儿,名叫阿芭的唐氏综合症患者,她甚至已经死了。但死去的她借助松的想象,借传说里的生物“蓝狐”,借药草师、傻子仆人的共同力量,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复仇,也完成了和生身父亲的面对面。
虽说不断从史诗中汲取养分,松却鲜明地反对冰岛史诗故事的某些创作手法,在他看来,冰岛传统史诗作者会不惜笔墨地描述阿芭的山村生活 ,而他则刻意在类似于这样的地方停笔。
此外,松从历史中取材,但并不写历史小说,而往往以现代伦理剖析历史。在《蓝狐》里,松选择唐氏综合症女患者为标本,让一个父亲披上牧师袍,让父与女、宗教和世俗、金钱和感情,乃至男与女、聪明与愚笨、崇高和卑劣等统统摔打在冰川碎石上,如果有人能看到这一切撞击时的光泽,它或许有不亚于北极光的高冷和华美。一个现代化了的传说超越古老的报应、复仇、怜悯,旧传说在新目光审视下复活,像蓝狐的复活,古老的故事生出新启示。必须让古老的故事和现代人进行一番理论,不再是关于电,而是关于别的,比如人如何对待弱者和有缺陷者,如何对待异类,如何保有平等心,如何保障生的尊严和死的尊严。一只蓝狐有必要一次次地复活,站在人的对面,逼迫人面对一场严肃的问答。这是很可能复现的副歌,死去的蓝狐又开始说话。有人拿刀刺死它,披它的皮,吃它的心,成了一只蓝狐,踩进一则新传说。
一个女人,名叫阿芭
阿芭是小说中从未正面出现的角色,作家第一次提起她时,她就已经死了,却是个核心角色,围绕着她的有正义的和邪恶的,现代的和陈旧的。没有她,故事难成立,正如没有蓝狐故事也难成立。如果说蓝狐是头怪物,阿芭这个唐氏综合症患者也正是当时多数人眼中的怪物。
《蓝狐》可解读为冰岛现代化的故事,提醒人平等而尊重人之存在的现代伦理和价值观的可贵。昔日欧洲,唐氏综合症孩童因其智力不发达,往往刚出生即遭杀害或抛弃。因为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据说数十年后,不会再有新生唐氏综合症患儿,如果是这样,因唐氏综合症而产生的人间苦痛有望消除,然而对弱者乃至异类的尊重问题,依然悬在人类的头上。
唐氏综合症患者男女都有,松特意选一个女孩,让她遭到生父贱卖,后来沦为水手们的泄欲工具,这一选择发人深省。药草师认为阿芭值得拥有特别美好的一切。他以自己设计的复仇和一封揭晓真相的书信,赋予了阿芭有尊严的死,以及死亡后有尊严的重生——得到正名。小说里以雌性身份出现的角色,除了阿芭就是被追猎的蓝狐了。牧师在冰川洞里看到过一个女子的身影,这女子带着有流苏的帽子,流苏帽也正是阿芭喜欢的,上教堂时喜欢戴,她也戴着它躺在棺木里。阿芭死去,蓝狐出现,蓝狐和阿芭间有不曾点破的关联。
阿芭珍爱拼图,她死后,药草师将它们摆开,发现那里刻着一行拉丁文:“Omnia mutantur,nihil interit”(“万物皆变,无一消亡。”)奥维德《变形记》里的句子在阿芭的拼图上闪着光。
短篇或长篇,小说或散文
那一年,以书写短篇小说见长的加拿大作家艾丽斯·门罗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给不少短篇小说作家吹去一阵希望之风,也吹开不少人不写长篇小说便不敢自称作家的压力。在2005年那场北欧理事会文学奖评选活动中,松的《蓝狐》作为约120页的短篇,压倒一众候选人的作品,包括更具知名度的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一部长篇,不能不说显示了评委会的眼光独到以及松身为作家的自信。
在文字的力量日益受图像、影视、游戏等冲击的当下,作家不单困惑于文学流派、困惑于体裁,也困惑于走过诗歌等古老文学样式,此刻占据着文学体裁第一把交椅的小说,在未来会有怎样的命运。
松的短篇为主、偶见长篇,杂交物种般的小说创作成果或许指出了相对轻松而现实的尝试方向。万事皆变,而书写不变、形式和内容不拘。长篇或短篇,拥抱或抛弃现实主义,使用本民族语言或国际通行语言都不必纠结。在松的小说里,神话和现实,过去和当下,史诗、志怪或侦探,还有一些别的,都表现出肆意的融合,又力求避开彻底的交融。是在不断接近又保持距离的过程里,他要调配出独有的景观和色泽。
巴尔德的槲寄生枝条
松凭借《蓝狐》获得极大成功,赢得了世界性赞誉。不过《蓝狐》并非完美无缺。
比如第一章,1月9日至11日,记录过去年月里正进行的当下,行走中的猎人,被追猎的蓝狐。地点、日期、时间、天气、角色看起来颇为具体,但由于留白宽大,猎人和狐狸并不是具象化的,而是类型化和象征性的:一个是“男人”,一个是“狐狸精”,来自民间传说的蓝狐是作家要表达的象征意味所依附的一张皮,一块有光泽和质感的皮异常重要,直接影响象征意味的呈现效果。象征性可圈可点,而类型化会削减文学力量。又比如倒叙阿芭的漂泊遭遇以及药草师的救助情节时,接近现实主义叙述,这些文字看起来聚焦不够,并非因为历史太过遥远而难以聚焦,更像留白的手法难以掩盖一定的虚弱。里头当然有出彩的内容,阿芭稍纵即逝的笑就是一例,但整体而言有刻意构筑的痕迹。单凭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同情心,药草师就不顾世俗压力,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保释阿芭,定居冰岛,显得匆促,一笔带过的处理手法缺乏直面事物并让情节生根之力。又如药草师和阿芭的相遇纯属巧合。得知阿芭的身世源自巧合。牧师碰巧是阿芭的父亲。牧师碰巧给派到药草师老家的教堂继任。无巧不成书,然而更高级的文学需要非如此不可的、无处逃避的因果。过多凑巧的安排让文本少了说服力。这就像当下一些侦探剧,不乏炫目的悬疑,到了抖落包袱时,逻辑上不能严丝合缝,只用简单粗暴的巧合涂抹和弥合。不过《蓝狐》的弱点一定程度上是松的留白式超现实主义写作自带的,是优点里的弱点,就像光之神巴尔德,谁都杀不死他,除了那微不足道的槲寄生枝条。
结 语
《蓝狐》里跳跃着神秘的多重意识,于是猎人听到了一段距离之外蓝狐的心里话,而复活的蓝狐内心里潜伏了药草师的思绪,这一切不可说透,无需像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将字符敲死如板上钉钉。冰岛人喜欢生活中不可解的神秘,善于将日常带入神秘的旷野,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超自然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经过发掘和再利用的传说正在呼吸,逆转现在进行的时间和方向,让当下生活的气息在往昔的故事里流动,超越时空隔阂,松的文学体现了新时代冰岛文学家和历史中的文学以及外部文学的积极对话。和时代的祛魅特征相反,松的文字急于回流到尚未物质化、还富于很多神秘感的时空里。如同他们的名就在今日雷克雅未克的街头路牌上,众神必在拐弯处、在文学路径边,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时刻里冷不丁露出一只眼或一丝笑。值得一提的是,松对于民间传说的发掘不单是拿它们来做骨架,还在于他对民间所讲述的文学的珍视,因为它们不是官方文本,有一种靠口口相传也能延续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