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谈—— 重读《蛇与塔》:“女人何故属男人” ——读聂笔记之一
《蛇与塔》是聂绀弩1941年1月31日写下的一篇杂文,篇幅不长,仅八百余字。在这篇短杂文中,聂绀弩称赞《警世通言》版本的白蛇许仙故事,有着“一点淡淡的无名的悲哀,是中国短篇中的杰作”。和其余笔记小说或民间文学中的同一故事比较,《警世通言》的版本的确要简单朴素得多,尚未发生水漫金山的话语变动,也没有让“愚民百姓的代表”许仕林前去祭塔。聂绀弩认为用蛇来比喻女人,挂钩“纠缠”“毒”是“颇有些憎恶意思的”,但这种“憎恶”却在故事的传播中不断演化为人们对女人的“同情”,因为“中国没有大悲剧的故事,什么都让它大团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快人心……我们中国人于是非善恶之间,取舍极严,关心极大。”另一方面,象征镇压力量的雷峰塔也在二十世纪初期倒掉,“倒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人们偷砖”,用以卖钱、赏玩、辟邪等用。这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著名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的嘲讽,“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聂绀弩《蛇与塔》可与前文对读,其最后一句亦有春秋笔法,颇见杂文力量:“曰:要塔倒,要白蛇恢复自由。愚民百姓也自有愚民百姓的方法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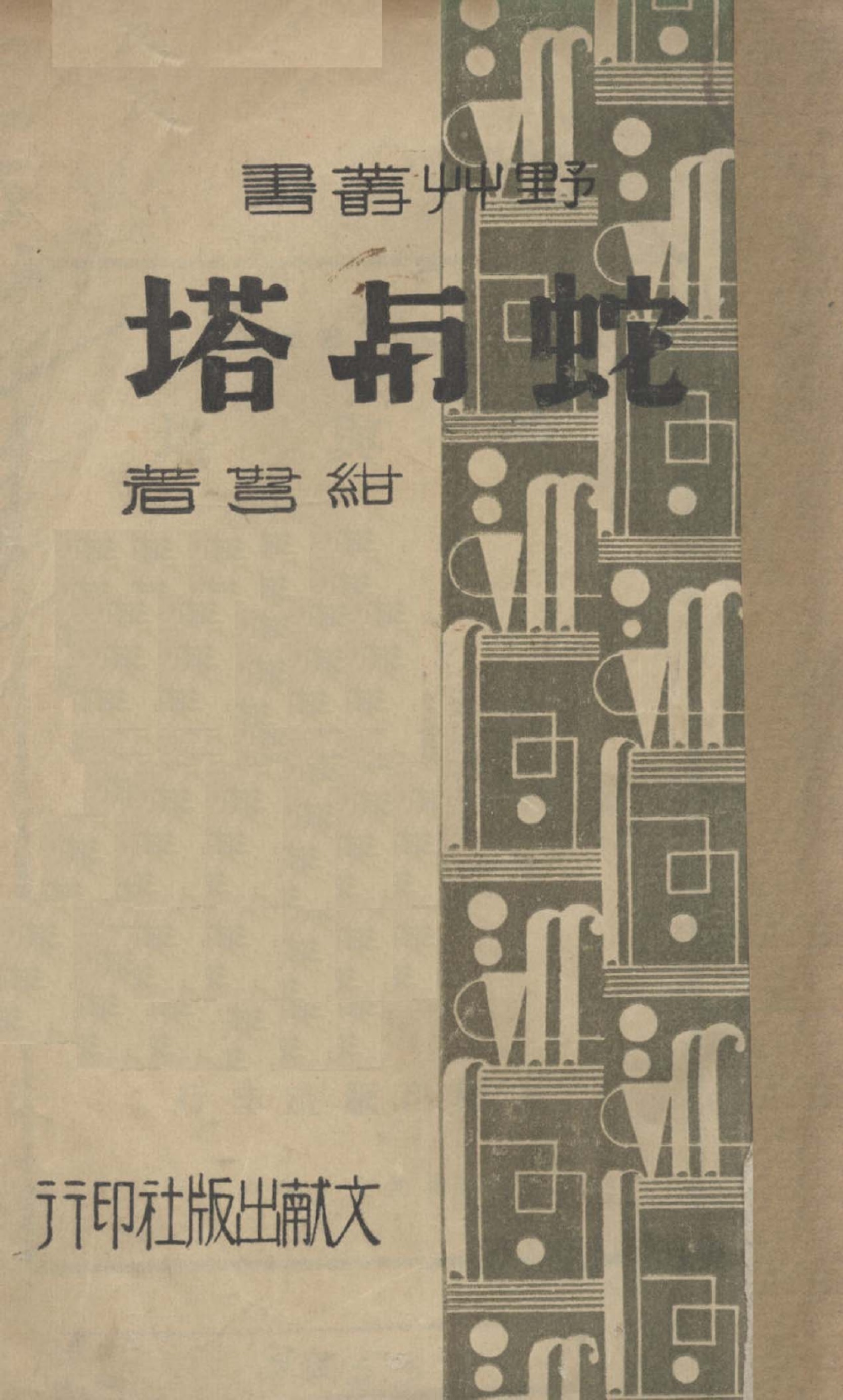
《蛇与塔》初版本(“野草丛书”之五),文献出版社(桂林),中华民国三十年八月(1941年8月)出版。
同年“三八”节,聂绀弩为同名杂文集《蛇与塔》写下“题记”,收拢自己过去几年间“关于妇女的文章”,并在数月后和他的另一本杂文集《历史的奥秘》一同列入“野草丛书”出版。初版收录13篇文章的《蛇与塔》一书可视为聂绀弩的杂文领域的代表作,尽显他关注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思想艺术特色,而其中最大的特点莫过于这本杂文集对女性问题的集中关注。这组关注女性、表明性别观的文章中最早的一篇,当属杂文《母亲们》(《母亲们》初刊1938年《七月》第7期,标记为散文,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聂绀弩全集》亦将此篇列入散文卷。但笔者认为,从内容上判断,包括《母亲们》在内的《蛇与塔》集中多篇“散文”仍应纳入杂文文体。另有《谈<娜拉>》一文作于1935年1月27日,载1935年2月5日《太白》第1卷第11期,署名为聂绀弩妻子“周颖”。该文初收初版《关于知识分子》,但此书1937年9月付排后因国难遭损未能复印,之后再次收入《蛇与塔》集)。《母亲们》是一篇全面抗战初期的反战控诉,从几位逃难母亲的交谈中描述战争的戕害,避免了空洞的呼号,有艺术性,很是巧妙。母亲们从叹息到交谈再到沉默,在逃亡的队伍中一点一点行进。“七七事变”后,聂绀弩请示周恩来去抗日战区工作,1938年1月7日写作《母亲们》时,他正在武汉待命,同月即与艾青、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田间等人一同前往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这篇杂文中已初见他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作为母亲的女性正经历丧子之痛,作为女性的母亲愤怒、挣扎、唾骂,她们的精神被残酷地粉碎着,“强盗的刀尖,或者会仁慈地插进她们的咽喉。在强盗面前,在野兽面前,女人,永远是无助的弱者!”次年杂文《圣母》中(《圣母》作于1939年“三八”节,结合1941年《<蛇与塔>题记》、1938年《心祭》、1950年《拥护爱人》等文章篇末都署日期“三八节”来看,聂绀弩在特定时间作文确不是巧合,而是有意为之),他对女性问题的思考逐渐深入。聂绀弩意识到女性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承担着一切苦痛与不幸中最悲惨的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两性的、民族的、人类的,甚至不限于“自然的”:“我们的女同胞不仅为了祖国的战斗而受难而死亡,同时也为了几千年来的一切两性的偏见,那从不合理的社会组织中产生出来的两性的偏见而受难而死亡;为了历史上的一切错误所造成的民族积弱而受难而死亡;……甚至于为了使女性由于生理的关系不能不变得较为柔弱的造物的偏私而受难而死亡!”从性别平等的角度认识女性特殊遭遇如聂绀弩这般深刻的男性作家,不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寥寥无几,放之今日也不甚多见。
言至此,就有必要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界一场有关女性主义的讨论稍加介绍,事实上,聂绀弩不仅是这场讨论的“正方辩手”,《蛇与塔》集中大部分文章的写作也与其有关。1940年10月1日的《战国策》上刊载署名从文的沈从文文章《谈家庭》,其中有关家庭中男性与女性应如何分工等问题的讨论为沈从文带去了麻烦。从诸如“一部分男性十足的女子,在生理上有点变态,在行为上只图模仿男子,当然不需要家”“她们之中大多数就并不明白自己在本性上需要的是什么”等字里行间可以很明显地暴露出沈从文这一阶段性别观念上的保守性。就连《沈从文全集》后附年表里都不讳言这一点,甚至专门单列一段,标出“《谈家庭》《男女平等》等,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聂绀弩等人认为沈从文的“妇女回家”论调是实打实的性别观倒退,对“沈从文们”发起关于女权问题的论战。聂绀弩亲自作文参战,并在次年将正反双方的文章合并结集出版为《女权论辩》,还特别再写《<女权论辩>题记》一文。“题记”中,聂绀弩称沈从文“把过去不平等的结果拿来作今后仍旧应该不平等的理由”;《妇女•家庭•政治》中,聂绀弩批判尹及,“女性要获得‘刹那间’的‘生物的平等’,除了从获得人的平等—社会的平等做起以外,没有另外的路。”上述观点着实很有洞见。这场论战发生前,聂绀弩与夏衍等人创办文学社团“野草社”并编辑杂志《野草》,有关女权论辩的相关文章包括《女权论辩》和《蛇与塔》两书“题记”以及《妇女•家庭•政治》《体貌篇》等后结集在《蛇与塔》一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发表于这一时期的《野草》上。但公正地看,论战中的沈从文并非完全主张一种性别上的不平等,或者说,他并非在刻意强调女性在家庭中应天然地对男性服从,《谈家庭》(及同月发表的《男女平等》)中也从侧面肯定了两性应转换思想观念,从对立走向合作。“聂绀弩们”与“沈从文们”之间的论战,表面上是针对性别观念或性别观念在言说方式上的激进、保守的分歧,实际则暗藏1940年前后“左翼”作家与“战国策派”的意识形态、话语舆论之争,从这一时期《野草》上聂绀弩《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偶语》等文章中即可略查一二。若对这一问题褫其华衮恐耗时过繁,考虑到其与《蛇与塔》在具体内容上关联相对有限,此处不作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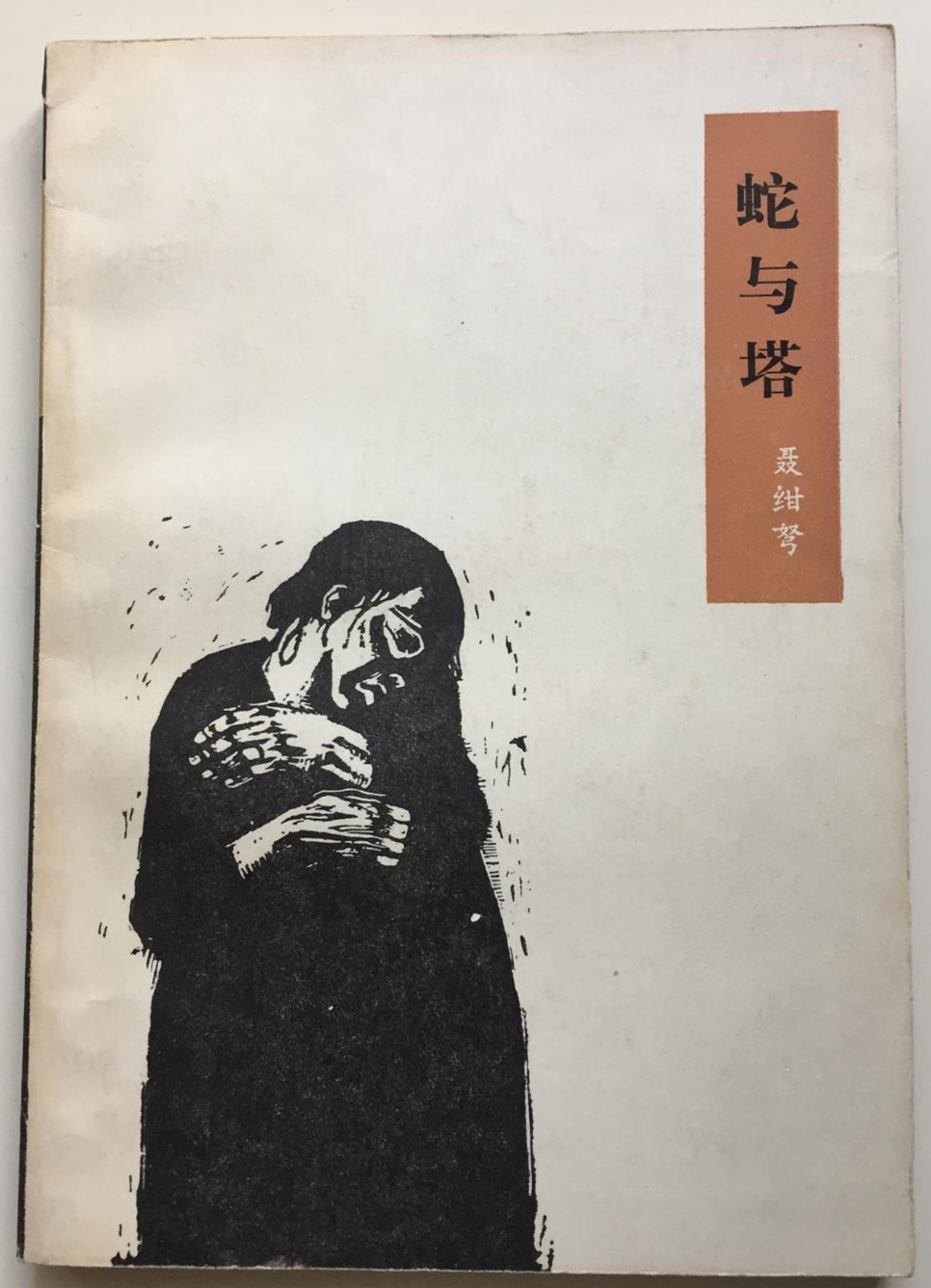
《蛇与塔》重编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6年2月出版。聂绀弩在生命最后一年写下《<蛇与塔>(重编本)自序》。
抛开更大的宏论暂时不谈,聂绀弩在这场女权论战中完成了后收录进《蛇与塔》集的大部分杂文,并通过写作梳理清晰了自己的性别观、女性观,形成了更犀利的杂文锋芒——这一点毋庸置疑。抗战时期,常见“乏嗣”男性登报广告,征求伴侣:“某君家道小康,生活独立,收入甚丰。因中年乏嗣,拟征十六岁至二十二岁品貌秀丽、肤白体健、性情温和、中学程度、未婚女性为伴侣。确系处女,小学亦可。”即便在对诸多怪相见怪不怪的今天,敲下这段文字都使人一阵反胃,可想而知八十余年前聂绀弩看到类似广告的心情。他在《“确系处女小学亦可”》中,将此等猥琐粗鄙的布告与封建礼教《杂事秘辛》《闲情偶寄》中载对女性身体的苛细检视以及“妻妾者人中之榻”的落后风化相提并论,但又心嗅蔷薇,试图以被战时的兽兵侮辱来体谅、关怀女性现实生存的不易。他更痛惜的是女性按男性的要求主动自我苛求。《体貌篇》中,聂绀弩悲怒言于表地戳破部分貌似“天性爱美”者的谎言:“完全忘记是为取悦男性,甚至于处于男性的希求之外苛求自己的体貌,在自己的体貌上想出种种花样,争妍斗巧,炫世骇俗。”我们与聂绀弩的时代相距甚远,但现实又何其相似。然而,今天徜徉在摩登都市中的新中产阶层和以女权主义自居者们极少能意识到,“人与非人之争,人权的大小多少高低之争,才是女权问题的症结之一部。”而在《阮玲玉的短见》一文中,聂绀弩沿着鲁迅先生在评价同一事(《论“人言可畏”》)时有关言论的尺度与责任这一观点继续出发,深化到反思封建道德伦理观的反扑与三四十年代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上,并指出:“但娜拉的时代虽然过去,新时代的女性应该同时负有作为反封建的娜拉的任务,也只有通过新女性的努力,娜拉的愿望才能彻底实现。”聂笔下的“新时代”与我们目前的时代社会环境具备修辞学意义上的同一,不过,关于“新女性”的想象恐怕不尽相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聂对未来有着光明的畅想(这种畅想从他的青年时代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在1949年的长诗作品《山呼》中仍清晰可见),他坚信“人类的愚昧不会是永久的”,“未来的女性将不再柔弱,我们的女同胞的受难与死亡也许是最后一次”,并在这种对未来光明想象的基础上将现实中罹难的女性进行文本再造,以绝对的神圣化达成了浪漫主义的自我实现(或瓦解):
假如因为她们的受难与死亡,以后的人类,以后的女性,不再有同样的受难与死亡;假如一切人类,一切女性的最不幸,最痛苦的命运,都是今天正在受难与死亡的我们的女同胞担受了;那末这些女同胞的受难与死亡是何等伟大,何等无我,何等慈悲,又何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我恍惚看见那些躺倒了的尸体一齐站立起来,汇合,融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新人。那新人美丽,庄严,崇高而和悦,周身射出着灿烂的金光,天风为她梳着披散的长发,太阳照着她挂在脸上的微笑;她昂着头,挺着胸,大踏步地走向祖国的明天,人类的明天!
她的名字叫做:圣母。
类似这样高度抒情化的表达在整个现代文学时期并不罕见,品尝了漫长的近代史苦果之后,人民有理由呼唤一方类似席勒笔下的欢乐颂圣土,“只要在你温柔的羽翼之下,一切的人们都成为兄弟。”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聂绀弩类似的畅想,就好比安徒生笔下的小女孩一瞬间擦亮手中全部的火柴:脱离实际、耽于想象即是思想局限的暴露。性别平等之路在日后仍无比艰难,面对肉体和精神上的铁索连环,鲁迅先生“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的忠告犹在耳畔。
除上述文章外,《蛇与塔》中集中讨论“母亲”“母性”的杂文也不容忽视,其中或埋藏着聂绀弩女性主义意识生成的“源头密码”。《<蛇与塔>题记》中聂也袒露了自己对“妇女问题”由来已久的关注——“怀在心里,差不多二十年了”。据《聂绀弩全集》第十卷后附王存诚、毛大风编年表,二十年前即1921年,当时18岁的聂绀弩迎来了他人生中的转折时刻,在师友帮助下,聂绀弩得以脱离原生家庭的束缚,途经武汉至上海,并初次接触到胡适的思想与“文学革命”。当然,从文人交往、聂氏自道、左联关系、文学史描述等各方面来看,聂绀弩日后在精神上与“文学革命”一代贤人中最亲近者莫过鲁迅,二者在相关话题上的文章题目都有因袭,如聂绀弩的《怎样做母亲》和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可谓一以贯之。(也有论者就习焉不察的鲁聂师从关系展开细致辩驳,认为需更谨慎地描述杂文家聂绀弩的文学史形象,注意“以鲁解聂”或“以聂注鲁”的局限。详见刘军《革命的游卒:聂绀弩论》)从“题记”不多的自述文字中,大抵能确定聂绀弩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起源于一种“怨母”心态。“……我对于我的母亲很少敬意。不但对于自己的母亲,对于天下人的母亲,我都不高兴,尤其是常被人说得天花乱坠的所谓‘母教’。”《怎样做母亲》《母性与女权》《贤妻良母论》几篇杂文中,涉及聂母的部分也几乎从不愉快:他“饱有”向母亲下跪、目瞪口呆的经验;母亲打他从不“哑打”;他认为“父严倒不要紧,母严才是一件倒霉的事”……“鸡毛帚教育”之下,聂绀弩对母亲的一句话记忆犹新,“将来你长大了,一定什么好处都不记得,只记得打你的事情”。聂母是否曾有过如此的表述,我们无从判断,但在学理层面不难发现聂绀弩尚不算过分隐秘的“自卑与超越”。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在其闻名于世的理论中,细数了冷落在童年经历中的影响、自卑情结以及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对儿童心理的作用。阿德勒说,
母亲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孩子体验到最初的对他人的依赖感。然后,她还必须把这种信任感加深扩大,直到这种情感延伸到孩子周围的所有事物。如果母亲的第一项工作没能完成——让孩子对事物发生兴趣、培养情感及合作观念——那么这个孩子将来就很难形成对社会的关注,很难培养出一种与周围人群建立伙伴关系的观念。……某些方面受到冷落而在其他方面一如常人的孩子。简而言之,有充足的证据显示,被人冷落的孩子从未真正找到值得信赖的“其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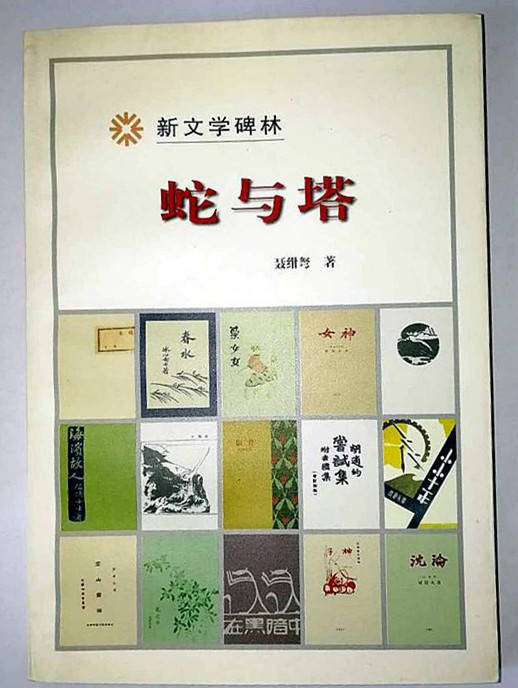
《蛇与塔》(“新文学碑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该版本是根据1941年文献出版社初版的重排再版。
这和聂绀弩无法释怀的精神创伤何其一致——
鸡毛帚教育的另一结果,是我无论对于什么人都缺乏热情,也缺乏对于热情的感受力。早年,我对人生抱着强烈的悲观,感到人与人之间,总是冷酷的,连母亲对于儿子也只有一根鸡毛帚,何况别人。……此外,鸡毛帚教育的结果,是我的怯懦,畏缩,自我否定。从小我就觉得人生天地之间,不过是一个罪犯,随时都会有惩戒落在头上。
对于聂绀弩来说,他从自卑中寻求超越的模式与女权主义有关。“母性是伟大的,但不能用于反对女权的理由。”因为“妇女也应该向更远更大的事业发展,不被限或自限于贤妻良母的狭小范围之内”。聂绀弩从“怨母”心态出发,为女性需要走出窄狭的家庭天地,获得更广的眼光和器量找到了现实依据,而当这种“怨母”心态的反传统性、女性主义的反专制观念与当时处于主流的启蒙话语相互融合、不分彼此时,他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自我情绪纾解的合法化路径——“首先她们应该是社会的人”,“只有这样……她们才能理解丈夫的事业,真有所助……作为母教施教者的时候,才能洞烛到儿子的将来而真有所教”。如此,女性走出家门,抛弃贤妻良母式的身份认同,这对于聂绀弩来说的确有着潜在的别样意义。
1941年,《蛇与塔》由桂林文献出版社初版后,聂绀弩并未放弃他的女性主义价值追求,关于女性问题的思考与写作贯彻在他生命中的各个阶段,仅名作就有杂文《女子教育一文献》(1946)、《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1946-1947)、《论怕老婆》(1948),语言文字论《拥护爱人》(1950),古典小说论《侠女•十三妹•水冰心》(1982)、红楼梦《小红论》(1984)等等。正像他《<蛇与塔>题记》中所说的那样,女性主义“岂止概括这本小小的书,它简直可以概括天下。”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聂绀弩的旧诗与呼唤男女平等的杂文是其两大贡献,而新时期后,他旧诗创作的声名日隆同时反向说明着女性主义实践在当下还任重道远。难道他的旧诗中就没有女性观的表达?“急人之急女朱家”“化杨枝水活枯花”(《赠静芳大姐之并州》,约1976)是他对山西高院女法官朱静芳勇气与义气的称赞(详见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人果无魂抑有魂,女人何故属男人?生前一饭方无地,死后双夫各半身!”(《小说三人物•祥林嫂》,1981)则充分可见他对祥林嫂的同情与对吃人伦理的痛斥……1986年2月,直到聂绀弩逝世前的一个月,他还在就女性问题发声,还为重编本《蛇与塔》撰写自序,而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重编本《蛇与塔》,也成为他辞世前看到的自己的最后一本书。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