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龙彦《虚舟》:荒怪的叙事与禁忌的消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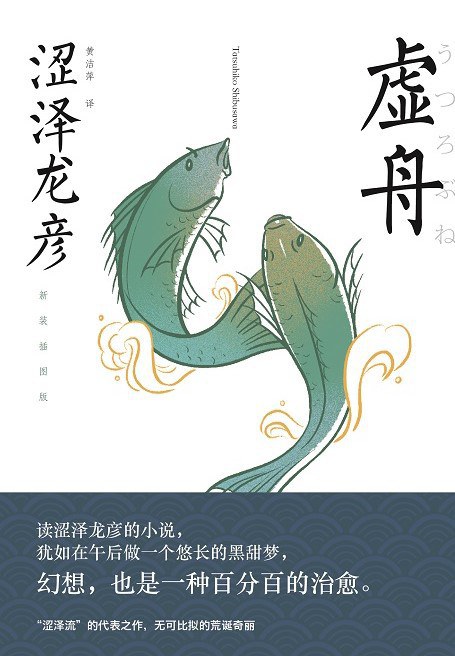
“如果这个人不在了,那么日本将变成怎样一个无趣的国家啊!”三岛由纪夫所说的“这个人”便是涩泽龙彦。他究竟是谁,又何以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呢?他是法国文学的研究家,是萨德、巴塔耶等法国异端书写的译介者,是因翻译萨德而引发“萨德大审判”却以游戏的态度面对审判庭的狂人,也是日本异色恐怖文学的始祖,更是引导日本文坛“暗黑”风潮的暗黑美学大师……读他的作品,你会感觉他更像是一个阴阳师,手摇巫铃,一点一点蛊惑你走入他编织的异境:开膛整腹、移头换面、挖坟掘墓、骷髅杯酒、人兽异形。他将这些异境大都设置在了历史、民俗与传说之中,使其更多出几分出人意料的色彩。他的出人意料也并不是由故事情节的剧烈变化所引起的跨幅,而是对常识的反转与撕裂,但他似乎丝毫不以此自得,甚至时常用“笔者认为”之类的话来出言警醒你,告诉你莫要沉溺于他的故事之中,让你知道,他想说的,除了那些荒怪和异端的故事之外,还有很多。
涩泽龙彦笔下,人就如同动物一般赤裸裸地呼喊着欲望,呼喊着欲望的即时实现,因而涩泽为其兑现欲望的方式也显得异常直观而骇人听闻。《护法童子》中的彦七因生性愚痴而被护法童子开肚整肠,变得聪敏颖悟之后,因不满于妻子的容貌而请求护法童子为其移头换面。在《骷髅杯》中,高野兰亭因小座头与自己不合而对他栽赃陷害令他愤然投井,因想制作骷髅酒杯而挖坟掘墓盗取名将头颅,纵然遇到天狗飞石示警也在所不惜,却终究在幻梦中被天狗拖入井底,肉身也离奇而死。对于人几近动物一般赤裸的欲念,涩泽龙彦非但不压抑它、掩饰它,更将它无限放大,又让它催动着那些不受社会理法与道德伦常制约的肆无忌惮,而在肆无忌惮之后却又堕入了无尽的空虚,最后都归结到了佛教的善恶偿报。
涩泽龙彦用一种日本古典文学所特有的幽微含蕴的笔调,不断地触碰着人们禁忌的边界,然而这一个个触碰禁忌的故事却并不会让人产生极端的恐惧感,或许是因为触摸极限的震颤本就不是涩泽龙彦写作的目的所在。他描写惊悚可怖的情节并不是为了激发读者的恐惧,描绘情色浪荡的场面也不是为了勾引读者的欲念。相反,他在极力地淡化着语言本身可能引起的刺激,许多细节被他写得淡而又淡。当然这本身就显得无比吊诡,这正是他区别于一般的恐怖小说的根底。在恐怖之外,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理智地站在这非理智的故事之外的慨叹:天命难违的悲哀,善恶偿报的轮回,无穷无尽的欲念之后的无穷无尽的虚空,更有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深广的悲悯与同情。
作为一个以奇绝的幻想著称的作家,他的作品中当然少不了纯粹的幻想。这本集子中的《鱼鳞记》与《鬼剃头》便是如此。《鱼鳞记》是涩泽以江户时代长崎的一位荷兰翻译的女儿由良离奇横死的事件推演而成的,谜一般出现而又消失的少年,谜一般死去而又魂魄流连的少女,以及奇谭中常常出现的砌进了秘密的墙壁。如果非要说作者要透过这些扑朔迷离表现什么,那大概就是驱动着故事进展的扑朔迷离本身了,是读完故事之后还盘旋在读者脑中的疑念,是对作者最纯粹的幻想的拍案叫绝。《鬼剃头》则是借由江户时期民间盛传的剪发妖的传说而生的幻想。女子的头发似乎向来都缠绕着一丝旖旎的情味,尤其是一个武艺高超、英姿飒爽的武士之女,佩刀的冷硬和发丝的柔软,不解情事的坚直与心头微微漾起的波澜……将“鬼剃头”的传说安置在这样一个女子身上,也可称得上是绮丽的恐怖与幻想了。
而《工匠》所叙说的,大约就是虚无了,用真实的历史人物编织的煞有介事的虚无,在华美的造梦之后将其毁灭殆尽的巨大虚无。华丽的大船是源实朝的梦,源实朝是绣帐美人的梦,这些又何尝不是涩泽龙彦为读者设造的迷梦呢?源实朝会乘大船去往他渴望的育王山,绣帐美人会等到她的将军。可事实上,大船半沉腐朽,源实朝早已身死,美人最终也被蟹钳剪碎,剩下的只有一艘残破的大船和爬来爬去的螃蟹。一切都是虚空,渴望是虚空,等待是虚空,美是虚空,梦也是虚空,就连故事中造梦亦毁梦的工匠、做梦的源实朝,也分不清到底是螃蟹幻化成了他们还是他们幻化成了螃蟹。在这里,无论是美人绣图、鹦鹉、螃蟹、寄身蝴蝶的源实朝的魂魄,还是人,交流起来都全无隔碍。他们之间不同的也只是形体,甚至就连形体也可以相互幻化。涩泽龙彦就是这样以漫不经心的语调颠覆着你的常识,却又用佛教的平等观和无常观统御着让你出其不意的一切:原来都不要紧啊!不管是人是物,是死是活,都不要紧,因为最终都将归于虚无。
读《虚舟》一篇,你会不由感慨,涩泽龙彦真是个揣摩人心的高手。人啊,总是因美而生欲,因谜而生惧,又因内心的恐惧而用语言妖魔化了美丽,再加上一些望而却步的不甘,便催生了一个个漾曳着艳冶情味的恐怖传说。在作品中,时间是断裂的,空间是可以跳转的,享和年间、两百年以后以及很久以前的古代,常陆国的神秘舟船、飞往欧洲的国际航班以及印度。唯一贯穿始终的是那一段“诸行无常”的经文,由虚舟中西洋女子的小便唱出,由飞机上的冲水马桶唱出,由比叡山僧厕所里的水流唱出。涩泽龙彦让恶浊的排泄物唱出圣洁的经文,再让它蛊惑着听见经文的人达到极端欢欣的精神高潮,这无疑是以佛法对巴塔耶所划分的动物性与圣性的链接。巴塔耶将世界分为动物世界、世俗世界与圣性世界三个层面。动物的世界是一种连续性的浑然无知的状态,不辨善恶,不分美丑,对死亡不解不知,对自我无意无识,没有道德牵制,不受理法约束,只要求欲望的即时兑现。而这一切都是人在产生自我意识从而进入世俗世界之后所要极力否定与撇清的禁忌。只有在文学中,才可达到对这些受世俗世界压制的动物性的回返,亦即巴塔耶所说的“恶——一种尖锐形式的恶——是文学的表达”。而巴塔耶所说的“恶”,并不是对“善”加以简单否定的“非善”,而是潜藏于世俗世界之后的最本初的人性,是人的动物性。显然,以“恶”为文学表达的观念也延续在了涩泽龙彦的小说中,形成了他异端与恐怖的根源。
然而,涩泽龙彦绝不仅仅如萨德、巴塔耶的异端书写一般将“恶”视作“至尊的价值”,在他的思想构造里,有佛教思想的渗透,有中国古典的熏染。他以欲望的实现与实现后的虚空验证着善恶的偿报,以小便声唱出经文的复沓消弥着恶与善之间的界线,以梦的造设与毁灭诠释着世间的虚无与世事的无常。同时,他在他荒怪故事里,也糅杂着中国古典志怪的情趣与信手拈来的引诗用典。可终究,他还是日本的、是“物哀”的。如果说萨德与巴塔耶对禁忌的书写是在挑衅性地扩展着文学的边界,最后终究化约成了语言的雄辩、思想的拗折以及观念化的恶,那么涩泽龙彦的禁忌书写则是在佛教的因果、轮回以及无常之中劝诫着恶、消解着恶,同时又以“物哀”的悲悯情怀哀怜着恶,及其它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