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关系》:法国大革命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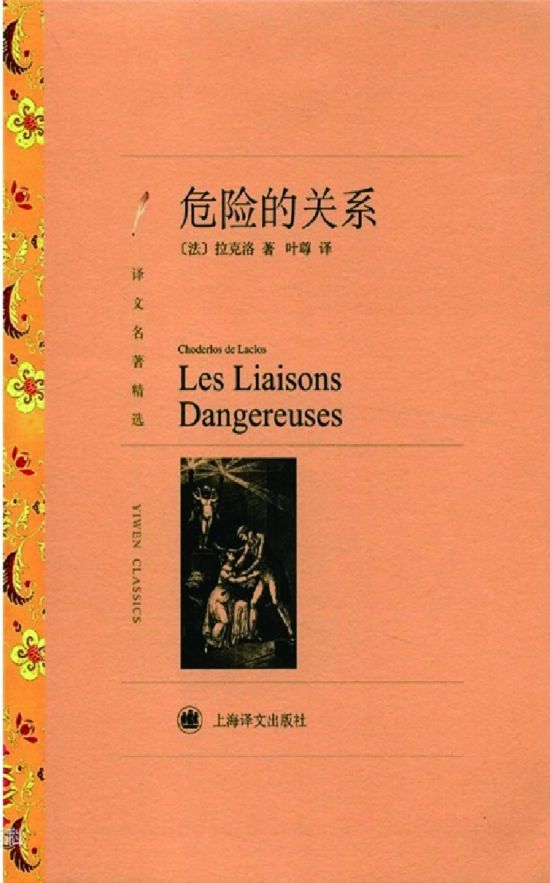
2013年“巴士底纪念日”(Bastille Day)当天,法国媒体评选出文学史上与法国大革命主题相关的十大杰作:狄更斯《双城记》排名第二,荣登榜首的是拉克洛《危险的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危险的关系》(1782)是法国文学史上一部“奇书”,也是作者肖代洛·德·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1741-1803)平生唯一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创作素材,据曾在拿破仑军队担任军需副官的文学家司汤达考证,主要源自行伍出身的拉克洛所部驻扎在法国东南部小镇格勒诺布尔的一段生活经历——当地的“年轻人时常从他们富有的情妇那里接受馈赠。他们用这一笔收入为自己添置华丽的服饰,并有余力包养另外一些较为贫困的情妇”。因此,拉克洛才有机会对上流社会的婚姻情感生活进行近距离的深入观察。不仅如此,小说中描绘的男女逐爱的种种攻防计策,多半也和小说家本人的军事专业息息相关——1792年,法国大革命领导人丹东任命拉克洛为行政委员,负责改组共和国炮兵部队(青年拿破仑为其麾下一员)。该部在与“反法同盟”首次较量的决定性战役——瓦尔密(Valmy)战役中表现勇猛,成功击溃普奥联军,拉克洛一战成名。
返回巴黎后,受贵族友人引荐,拉克洛出任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私人秘书,后者号称思想开明,赞同革命,是波旁王室的“另类”。在此期间,拉克洛不仅对宫廷权谋及贵族生活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同时也有机会结识米拉波、塔列朗等政治领袖——可惜他本人作为奥尔良公爵“代言人”提出的改革方案无一被采纳。大革命期间,拉克洛两度被捕入狱。第一次是1793年,他被诬告“里通外国”,极有可能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幸而此时前线战事吃紧,需要用到他不久前发明的一种威力无比的空心炮弹,于是他被释放,去军中充当教官,“戴罪立功”。然而大约半年后,他再度被捕,因为塔列朗等贵族流亡美国之前,成功说服奥尔良公爵之子路易·菲利普(后继位查理十世,加冕为法国国王)一同前往。如此一来,为奥尔良公爵家族出谋划策的拉克洛自然难脱干系——后得丹东援手,才侥幸逃过一劫。大革命期间,拉克洛前后共被关押13个月。出狱后,他第一时间向公安委员会提交《论战争与和平》的备忘录,主张收复法国失地,无果。此后,拉克洛心灰意冷,退出政坛,直到拿破仑称帝,他才得以东山再起。他被提拔为准将,率部加入意大利军团,于1803年不幸染疾身亡。
从表面来看,《危险的关系》与作者跌宕起伏的人生阅历似乎并无直接关联。小说以书信体形式,刻画路易十五时代末期上流社会的一桩惊天丑闻,或更准确地说,是由两桩阴谋交织勾连所造成的一出人间悲剧:巴黎名媛梅尔特伊侯爵夫人意欲报复喜新厌旧的热尔库尔伯爵,写信请求老情人瓦尔蒙子爵出手相助——后者正企图勾引年轻貌美的修道院院长夫人都尔维尔。一方面,热尔库尔伯爵抛弃侯爵夫人后,有意迎娶富家女塞西尔。塞西尔对年长的伯爵无感,但对风流倜傥的当瑟尼骑士一见倾心——在侯爵夫人暗中撮合之下,两位年轻人悄然展开地下恋情。而另一方面,院长夫人无力抵挡瓦尔蒙的连环计,屈身成为他的情妇,但不久便察觉这位浪荡子并非出于真爱而只是习惯性玩弄与淫狎——伤心之下,她遁入修道院,抑郁而亡。故事结尾,瓦尔蒙至侯爵夫人处,欲与之重续前缘,却意外发现其卧榻已由当瑟尼骑士捷足先登。在随之而来的一场决斗中,瓦尔蒙被刺,临终前将与侯爵夫人共同阴谋策划的往来书信悉数公之于众。侯爵夫人身败名裂,被上流社会永久驱逐。
书信体是18世纪流行的小说样式。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和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在文学市场大获成功,同时也吸引了更多读者的关注。此外,拉克洛在本书卷首所引用卢梭的《新爱洛伊斯》,以及书中院长夫人的枕边读物——英国伤感小说鼻祖塞缪尔·理查森的《克拉丽莎》也同样采用书信体裁。相对而言,后两本书——尤其是《克拉丽莎》——对拉克洛无疑影响更大。小说同名女主克拉丽莎性格忠贞,但终究未能抵御浪荡子的诱惑,同意与其私奔,结果却无端遭遇强暴,伤心绝望而死。理查森以描画人物心理见长,但论及小说的谋篇布局及叙事手法,拉克洛明显要胜出一筹。
《危险的关系》全书由12位大小人物总共175封书信构成,正如拉克洛手中的一副纸牌——上流社会的纸牌游戏(card game)的确是书中反复出现的场景——他缜密计算各色人等在每一局交锋中的得分失分,并以此决定他们的出场顺序及篇幅长短。比如他笔下的男主瓦尔蒙戏份最足:这位青年贵族既是花花公子,又是剑术高超的武士,他相信勾引是一门“战争”的艺术,因此仅仅占有肉体毫无乐趣可言——他的目标是要将对方从意志到精神彻底摧垮,让她彻底沦为自己的玩偶。以他的标准,被勾引者越是不甘顺服,越能激发他的斗志,而美貌贞洁的院长夫人恰好便成为他的理想猎物。值得注意的是,拉克洛对待小说人物,既不像卢梭那样雄辩理性——试图通过道德说教感化读者,也不像理查森那样伤感滥情——通过描写不幸身世打动人心。相反,他不动声色,仿佛一名冷酷无情的训练官操演他的士兵。作为一名精通军事防御工事营造的炮兵将军,同时也是深谙宫廷政治斗争技巧的资深政客,这样的排布和演练对小说家而言可谓毫不费力,只要保持他一贯漠然置之的“本色”即可。日后波德莱尔评价《危险的关系》时断言:“这本书要是能燃烧,只能像冰一样燃烧”——正表明诗人对拉克洛这位“不可靠叙述者”客观中立态度的认同和欣赏。
或许正是作者这样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激起了道德人士对本书的强烈愤慨。本书不仅有色情小说常见的“露骨”描画(仅此一项便足以将它查封),而且颇具无神论色彩——宗教与道德紧密相连,而本书通篇没有哪一位人物具备道德责任感。更要命的是,本书外表描画男女私情,其实是影射宫廷政治——作者本人是大革命前期臭名昭著的“阴谋家”,惯于造谣生事,四处煽风点火,与活跃政坛的其他一些小册子作家(如米拉波)一样居心叵测。
对于任何一部意图难以界定的文学作品,最简单粗暴的方法便是将它打上“色情”标签而后封禁销毁。与拉克洛同时代的萨德侯爵(年龄相差一岁)几乎每一部作品都难逃厄运——这些“色情”小说大多在监狱中完成,作家本人最后也老死于巴士底狱。对拉克洛极为仰慕的19世纪文学大师司汤达的《红与黑》以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同样长期遭到封杀。与上述文学名著命运相似,出版不久,《危险的关系》在巴黎被查封,罪名是“违背公德”“伤风败俗”。尽管时至今日,本书已取代卢梭《新爱洛伊斯》堂而皇之步入法国文学经典,其印数也远超《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茶花女》以及《追忆似水年华》等名著,但在近200年时间内,这部一度畅销(首印2000册两周内售罄,在当时堪称现象级事件)的文学经典却始终与读者“缘悭一面”,令人不胜唏嘘。
平心而论,尽管书中不乏性爱描写——比如侯爵夫人设计诱惑巴黎一名风流骑士,待他黑夜闯入闺房后又控告他非礼,甚至还有同性之爱——比如侯爵夫人与纯情少女塞西尔互生情愫,但总体而言,作者并未像色情作家那样大肆渲染,而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既体现出小说家驾驭题材的能力,更反映出他的文学品位。举个例子,侯爵夫人在致瓦尔蒙信中透露:与骑士共浴爱河之前,她需要通过阅读色情小说提升“性趣”——而她所读的并非坊间流传的萨德,而是另一位小说名家小克雷比永(Crébillon fils)的色情政治讽喻(erotic political satire)作品《索法》(Le Sopha)——小说家本人曾因著文嘲讽当朝大臣红衣主教罗昂(Cardinal de Rohan)而被判监禁。从这个角度看,正如评论家所说,与其说拉克洛近于萨德,不如说他更近于卢梭。
米兰·昆德拉在关于“小说的艺术”讲座中曾指出,《危险的关系》一书中人物别无所求,“唯有寻欢作乐”——或许这也是本书被指为“道德感缺失”的一个主要原因。以声名狼藉的侯爵夫人(波德莱尔称之为“撒旦式的夏娃”)为例,她生活放荡,人格卑劣,其人生信条为“爱情只是寻欢作乐的一个借口——即淫荡的代名词”。她善于操控他人(男女通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堪称贵族阶层道德败坏之典型。拉克洛通过这一人物形象展现贵族的腐朽没落和荒淫无耻,用他自己在本书“序言”中的话说,“揭穿道德败坏者用来腐化有德者的伎俩,这是为社会风尚的纯洁净化立了一功”。换言之,他的本意是要像先贤塞万提斯一样,做一篇警世的教育小说——可惜世人误会了他的良苦用心。
此处便涉及本书题旨之争的核心问题,即这部小说更大的问题“不在其淫,而在其诲淫”。在批评家看来,拉克洛刻意将侯爵夫人描画成“女唐璜”的形象——在中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学传统中,唐璜是始乱终弃、战无不胜的浪荡子原型,而侯爵夫人的一大“爱好”恰好也是先让男人拜倒在石榴裙下,而后再将他一脚踢开,从中获取绝对征服的快感。与唐璜津津乐道的爱情冒险(罗曼司)相比,侯爵夫人的“玩火”行径不仅践踏男性尊严,而且也是对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彻底“颠覆”——这样的指控,显然要比“有伤风化”的罪名严重得多。
似乎对“含沙射影”“诲淫诲盗”之类攻讦之词早有预判,拉克洛在“序言”中明明白白作出交代,并告诫读者请勿对号入座——本书中“有好些人道德品质如此败坏,很难想象他们曾在我们这个世纪中生活过。我们这个世纪是哲学的世纪,智慧的光芒普照每个角落,众所周知,我们所有的男人都是循规蹈矩、彬彬有礼的,我们的女人个个都是雍容持重、端庄娴静的……我们的意见是,如果这部作品里叙述的事件是真实的,那么这些事件只能发生在别的地方,别的时代。”如果说作者卷首引用卢梭的“正风俗论”——“我目睹了当代的习俗风尚”——仅仅是掩人耳目,则此处的告白无异于宣告此地无银。
正如历史教科书所言,大革命的爆发与法国的社会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作为权贵的第一等级(教士僧侣,如书中修道院院长)和第二等级(贵族领主,如书中瓦尔蒙子爵以及当瑟尼骑士)属于特权阶层,他们拥有世袭的爵位(通常附带城堡或庄园等大块地产,以及大笔年金),并在其领地上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凭借特权,他们总能从法律中找出漏洞,合理“避税”,从而得以尽享优渥生活,肆意挥霍浪费。相反,整个法兰西王国的财政收入都只能依靠对第三等级(如书中受瓦尔蒙救助的农夫,以及女仆)的剥削和压榨。贵族无所事事,华服盛装出席贵妇名媛的晚宴或许是他一天当中最紧要的事务——如何体面优雅地打发一天(或一生)的时间可能是他全部的生活目标。而第三等级的平民大众终日劳碌却食不果腹,并且时时有遭遇权贵凌辱的危险(如《双城记》中的马内特医生),因此贵族与平民的仇恨愈演愈烈,阶级矛盾也日益加深,大革命一触即发。
这也是《危险的关系》最重要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危险的”不仅是男女关系,更是等级关系。作为大革命前后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拉克洛不可能真正超然物外,对迫在眉睫的“危险”熟视无睹。他的友人米拉波在报刊发表雄文《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矛头直指臭名昭著的“国王密札”(即空白逮捕令),向王权绝对专制发出挑战。拉克洛身在体制内,无法像挚友一样直抒胸臆,而他更欣赏的是同时代另一位著名文人莫夫尔·安杰维勒(Mouffle d'Angerville,或译当热维尔)的反讽笔法——后者著《路易十五的私生活》(Vie privée de Louis XV),以史家的纪实手法将君主(及情妇)和廷臣的腐败、国家财政的挥霍、以及民众的深重苦难一同展现在世人面前。与之相似,拉克洛也以“纪实”的笔法,揭露宫廷贵族的生活糜烂和道德沦丧。
对封建王权及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拥护者而言,这显然属于别有用心的颠覆和解构。正如作家本人在书信中所说,大革命前夕,“宫廷”一词不再像路易十四时代那样令人肃然起敬、望而生畏:经过小册子作家的大肆渲染,生性暗弱的国王路易十六及纵情享乐的王后安托瓦内特双双沦为笑柄——尤其是关涉王后与罗昂红衣主教的“钻石项链事件”之后,民众对于沿袭数百年的法国君主制可谓好感全无,封建王权已呈摇摇欲坠之势。照拉克洛的看法,18世纪中期之前,法国朝野上下仅有少数人具备革新思想,期待一场革命风暴,而18世纪80年代前后,由于各类启蒙思想读物及地下宣传手册的散播(奥尔良公爵府邸四周的咖啡馆乃信息中心),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而正是这一思想观念的变迁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由此,波德莱尔作出如下研判,没有什么能比这类“有伤风化”的小说“更能说明和解释法国大革命”。从这个角度看,拉克洛《危险的关系》堪称是当之无愧的“法国大革命序曲(prelu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