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彦:编全集,是向以往版本和自身境界发起挑战

黄玮 摄影 图/广东人民出版社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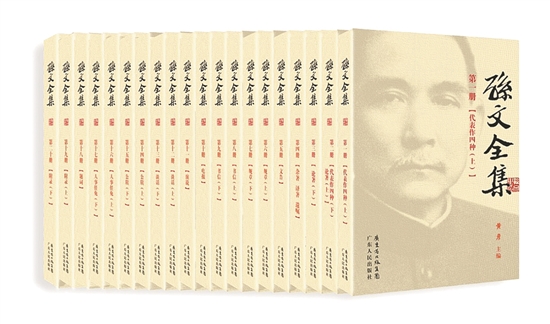
《孙文全集》 图/广东人民出版社提供
新出版的《孙文全集》主编、89岁高龄的黄彦老先生,在广州天河北省社科院大院里的朴素居所内,一字一句为我们审正了这篇文稿。之前,他也是这样一丝不苟地,一段一篇为我们提供参考资料,一问一答接受采访……
于今面世的这部煌煌1400万字、20大册的《孙文全集》,亦是这样经他审视、思忖,历二十七个寒暑,与来自广东、北京、香港、日本的孙中山研究同道者们,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数代出版人,一起编纂而成。
自从1925年孙文先生逝世以来,为他编辑出版的全集、选集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著作集不可胜数,但辑录数量和编辑质量能特别引起社会高度重视的却寥寥无几。即使晚出的佼佼者如上世纪80年代北京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台北1989年版《国父全集》增订本等,在收集资料方面依然存在着很大空间。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长期为革命颠沛流离,到过亚、美、欧各洲不少国家,又担任过国家元首和军事统帅,备受国内外媒体和各国政府的关注,许多中外文报刊都有关于他各种著述的报道,一些国家的公私档案机构也收藏有他的著作资料。这些资料数量庞大而又分散各地,联系渠道也未必通畅,所以往往不容易被发掘出来。正因如此,从1995年夏天起,广东人民出版社开始了编纂《孙文全集》的新一轮努力。
黄彦是国内孙中山研究和史料收集的权威专家,这套《孙文全集》从立项到出版历经近三十年时间,上下求索,查漏补缺,他及整个编纂出版团队倾注了无数心血。这背后的故事,不仅是一部迄今文献收集最齐全、考订最严密的孙中山全集成书的历史,也蕴含着数代岭南学人孜孜以求的文化初心。
这是篇幅最大、考释最完备的孙中山文集
羊城晚报:由您主编的这一套《孙文全集》有什么主要特点?
黄彦:这套全集是历来编纂的孙中山文集中篇幅最大、字数最多、考释最完备的。我们在文献底本的选择和内容校勘、标题的拟定、著述时间的订正等方面着力尤其多,同时也大幅度增收了孙中山的中外文献,特别是外文资料。我们以原文影印或者录入排版的形式收录了一批新增加的外文文献,包括英文、法文、俄文、日文等。
羊城晚报:本次编辑出版的《孙文全集》历时多年,这个千头万绪的过程是怎样的?
黄彦:本次编集是受广东人民出版社之托,始于1995年夏季,集合众人之力而成。那时正当我从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离任,本来想离任之后找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来做,比如看看小说等,没想到又接了这么个任务,更没想到一接就这么长时间。
我从当时研究所的人员中挑选研究水平较高,在孙中山研究领域内有成果、质量好的一些人组成班底,同时也对外招贤,从外文、文献等方面补足短板,构成一个班子。一开始我就抓紧书中的各个编辑环节,使大家统一思想,贯彻始终,要求尽量做到规范化。要求对相关资料必须甄别真伪,剔除各种牵强附会。特别是研究者应经常亲自寻访第一手资料,并确保其科学性、严谨性。
羊城晚报:编这么大规模的《孙文全集》,搜寻的过程一定克服了很多困难?
黄彦:由于我已退休,比别人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多年来得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搜集资料的工作中。我和工作伙伴多次赴港澳台及国外发掘资料,或者函请国内外学者、友人帮忙。这样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收获颇丰,终于可在本套全集中较大幅度地增收孙中山的中外文著述。
谈到在海外的收集,有一位旅美的建筑工程师黄俊威先生,他说自己周末有些空闲,而且对孙中山先生很崇敬,可以帮助收集美国这边的材料。我一听不禁大喜,就请他来帮忙,这一帮就是好几年,经过长期寻访而影印了数百篇英文原始报刊资料,非常珍贵。美国所有的州他都去找,搜集报纸,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比如说有一个州,在某个时段,就是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那一段,几个月内竟有二三十种报纸刊载过相关的内容!我们剔除了重复,经过考证、遴选,挑出好的底本收入全集。
羊城晚报:这些来自海外的新材料,带来什么新的认识?
黄彦:在新发掘出来的孙中山著述资料中,有些思想观点是前所未闻的。如1912年3月孙中山曾撰一文载于《旧金山呼声报半月刊》上,其中写道:“中国人对史诗一无所知,中国文学中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戏剧性诗歌……我们的戏剧反映人生,但并不关注人的心理状态,也不去刻画作品中的角色。俄国和法国文学在心理刻画方面优于其他国家,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我们要吸收西方艺术中精华的精华,以此来启迪我们的天分。”(沈洁 译)显然,这些论述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孙中山原有的形象。全集版本增补这类著述资料,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认真”二字,是个价值观问题
羊城晚报:那么作为研究者,您能否举例说说本次编辑出版的《孙文全集》投入了哪些精力?
黄彦:编书时我有一个重要发现,可以在此交代一下:孙中山在专著《实业计画》中举出的许多地名其实在当时并不存在,而现今中国各省区的地图中也无从找到这些地名。我花费了大约半年时间穷其究竟,发现是由于民国最初两年曾进行全国性行政区域改革,1912年在部分省区试行,1913年1月由北京临时政府在全国颁行,但孙中山写作时却无新的地理工具书可用,所以此书中的铁路、海港等起迄地点大量沿用了清代的旧地名。
所以我在编纂时,对凡能查到且经多种资料核实的地名,便分别注出当时的实际名称及今名,情况较为特殊的还另作了说明。这一来,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大大提高了《实业计画》这部名著的使用价值。这么一来,就把孙中山这个著作用活了。
羊城晚报:在这个搜寻和编纂过程中,您秉持的是什么态度?
黄彦:史料考证一是要认真,一是要动脑筋,多想办法。“认真”二字说来轻巧,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不是所有人都肯脚踏实地做学问,这是一个价值观问题,我只希望跟我一道编集的同人都要有一份责任心,勇于向以往全集版本的编者挑战,也向自己的思想境界挑战。从技术上说,充分利用电脑检索和向专家学者请教,就是两种效果不错的方法,常可使一些自己原先不懂或疑难问题找到答案。
入了孙中山研究这个领域,我就做到底
羊城晚报:您被学界称为“中国研究孙中山的第一人”,那您个人进入孙中山研究的契机是怎样的?
黄彦:这“第一人”之说,原是史学界前辈章开沅、金冲及等在2008年在武汉一次聚会上的谬赞。孙中山的研究范围很广,我能有所建树,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说到“契机”,我认为用发表于《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的《介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一文比较合适。因为在此之前,我参与编辑孙中山全集、选集已小有名气,故在编中华版孙集时被合作者推举起草凡例。而当介绍中华版第一卷发表时,著名史学家、《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先生甚为高兴,将我引荐给出席研讨会的外国学者,并说:“这本书编得比过去的全集都要好很多,这就是黄彦的贡献。”这篇很长的文章纠正了之前台版《国父全集》在处理史料上的一些讹误,因此在台湾影响尤大。
羊城晚报:无论是编孙中山文集、选集还是全集,都是收集史料的最基础工作。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黄彦:我深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学术研究的风气、趋向以及评判学术价值高低的标准各不相同,习惯于微观考察的历史学者自然会对史料的鉴别和考证更感兴趣。不过我也从中得到一点感悟,干史料活也并非毫无用处。
做任何历史课题的第一步功夫,就是要充分占有和认真分析史料,否则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只能是一堆远离客观历史事实的空话。所以我想,既然已经进入孙中山研究这个领域,就做到底吧。
高水平成果离不开深刻的理论分析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广东学术界在孙中山研究领域的状况?
黄彦:中山大学历史系陈锡祺教授培养了一批研究孙中山的力量,最早成立了孙中山研究室,并担任室主任,在中大提倡此项研究。同时,段云章、林家有、李吉奎、邱捷、桑兵等教授也是研究孙中山的中坚力量。广东省社科院的孙中山研究也有传统与优势,尤其是张磊研究员更为突出。此外,中山故居也利用馆藏资料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值得注意。
羊城晚报:您对今后的孙中山研究有怎样的期许?
黄彦:对于孙中山研究而言,高水平的成果必须建立在深刻而周全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坦率地说,本来我应把自己的素养和理论思维方法用在这项研究上,但是我没有下足功夫,这是我一直很感遗憾的事情。
【受访者简介:黄彦,1933年生,广东普宁人。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该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等职。长期从事孙中山史料的蒐集、整理、考释和编纂工作。曾参与编撰《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主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校订《孙中山选集》第二版(1981年版)等。曾编注“孙中山著作丛书”十二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2012年版)、主编《孙文全集》二十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 邹诗鹏:提升学术研究主体性、原创性[2022-06-08]
- 当下文学很需要一场“启蒙”[2022-05-06]
- 当好学术研究的把关人和引领者[2022-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