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的与幽邃的——再谈徐则臣小说

徐则臣,1978年生,江苏东海人。199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5年毕业后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2006年加入中国作协。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王城如海》,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北京西郊故事集》等。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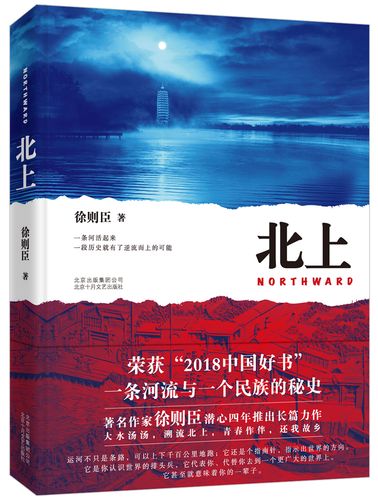
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我一直觉得好奇,徐则臣的小说,写小人物、写底层生活、写伤痕及微观的反抗,却总有一个宏大的对象世界在,辽远宏阔而触手可及的历史、抽象模糊但始终遥望的世界,以及那个许多人身处其间又仿佛若即若离的现代城市。如是构成了徐则臣小说中非常分明的精神岩层,时而堆叠得显而易见,不时又掩蔽而难以察觉,人心人性如此,时代历史亦如是。关键在于,通过宏大的历史、世界以及城市,徐则臣小说将幽邃的灵魂引向何方?与此同时,辩证的双向或多向之间如何共处又如何交互,是协调、追逐,还是对抗、分裂,又或是以此锻造新的可能?这构成了一代人,同时也是一时代的文化命题。
不仅如此,这样对立而统一于小说的叙事形态,在文本内部构成了对话的场域,当然这里边并不是多声部之间的协和,也往往鲜有众声喧哗的平等,徐则臣更多传递出来的是种种差异性的存在。而正是其中截然的分化,形成了阶层的与情感的共同体,也就是说,身份的一致性不断引导着命运的走向,微弱的人群、衰颓的命运、人世的幽眇,与他们所畅望和身处的宏大想象之间,多有撕裂和惶惑。在这种境况下,如何真正形成有效的交互及回音,人物主体与形而上的历史、世界以及城市之间的深巨落差,其背后是否能够传递进阶及流动的可能,以至于无论是宏大的抑或幽邃的所在,都不至于遥不可及,而是相互紧扣,可攀缘、可逆转,或可分割、可回撤,在此基础上构筑必要的情感机制、文化形态和社会机制。
从这个意义而言,徐则臣的小说既是保存式的呈现,也是批判中的呼唤,更重要的,写作者试图在小说中创生一种容纳并传导声音的场域,无论是横向的共时性空间,还是纵向的历时性流动,都试图珍重那些幽微的人性与幽邃的生命;与此相对的是,徐则臣小说总有一种性情的坚韧与心绪的气力,紧紧拽住宏硕得仿佛高不可攀的愿景或事物,见证个体的、底层的、世俗的力量,他们似乎自生自灭,却又自处与自洽,因而,小说在表面上呈现出迥异的标高,却得以展开深层的对话,构成灵魂的回响。
长篇小说《北上》就故事时间而言,从1900年的庚子事变牵引至2014年的运河成功申遗,将一个多世纪的运河故事讲得机巧生动。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宏阔悠长的运河及其久远邈杳的历史中,却挑选一段横截面,流布近现代中国/世界里不同个体的细碎情绪,其中是否有所扦格而显得空疏?徐则臣自述曾开展写作教学,他对那些陈腐的理论不感兴趣,更想让学生知道的,是“从具体而细微处看见一部小说是如何生成的”。《北上》从义和拳运动说起,世纪末与世纪初的冲回再造,都在人物漫长的行旅中进行探询。人的命运曲折蜿蜒,在流动中沉浮,不断浮现于背景之上,质言之,置于壮阔景象中的是人物的悲喜、死生,在绵延不尽的爱恨情仇中变得壮阔,从而与小说宏大悠远的叙事依托相符契。幽邃的人心在时间的流脉中脱落、显型,小说实现了自身的纵深与开阔。运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运河是古老的,也流衍当下;再者,运河那里有人心人性,更代表着家国与历史。此外,对于小说本身而言,叙事结构严谨整饬,而枝枝丫丫却四下伸展出来,从20世纪的开端到21世纪初,费德尔·迪马克的信被意外发现,那是形而下的“考古”,也开启了历史的再现与重探;而保罗·迪马克寻觅失踪的弟弟,无疑也是一个探寻/考古的过程。在这里,遗落的文化与失踪的人物,都是待“考”之古/人。而古老帝国旧邦维新,在现代发轫及开新中,沉浮跌宕,几度摇荡,于是,国与族、史与人融汇抱合。再宕开一处说,小说里,运河依旧在,且成功申遗,而细数开来,逝者已不可追,这又是一层落差。不仅如此,除去人物沉浮起落、存亡死生,小说一边是中国大江大河般的现代进化史,一边是运河边上无处不在的贩夫走卒、船上人家、兵匪盗贼、知识阶层……后者不再人微言轻、不见声响,而是在运河之滨簇拥洋洒,参与宏阔的历史激荡,生气勃勃、繁躁喧闹,于时间深邃的黑洞发出鼎沸之人声,虽不至振聋发聩,却雁过留声,不可抹除。
在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答谢词中,徐则臣提到:“以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它的辽阔与复杂,它的坚硬的偶然性和我们无力追根溯源的变异,早已经凶悍地溢出我们既有的逻辑框架。当我们以为一个光滑、有秩序的故事足以揭示万物真相的时候,被我们拒于小说门外的无数不可知的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东西,正从容地排列组合成一个更为广大和真实的世界,它们同时也在构成我们丰富复杂、不曾被逻辑照亮的那部分情感与内心。”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世界”既是人们无处不在的神圣想象,又是日常生活中虚无式的调侃与不时念怀的地方,“人听见车声站住了,扭回头看他们。是铜钱。这个游魂,一大早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初平阳想,他要到世界去呢。”对初平阳们而言,“世界”是形而上的,同时又具体而微,以至于他在所见所闻所感以及所言所行之中,都怀抱此念,即便经历了生命的危机,依旧记取有那么一个“世界”,尽管那常常是难以企及的幻象。小说表面上是关于花街的边缘叙事,却透析着当代中国的革新与开放,以及由此衍生的人物的心理异变。小说里,那些小人物身处断层的边缘,而初平阳却始终不忘心里的耶路撒冷,那里是“一个抽象的、有着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寓所”。没有差异和分裂,没有“宗教和派别”,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这与《如果大雪封城》中的理解相互协和,徐则臣描述雪后的北京城:“将是均贫富等贵贱,将是高楼不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积得厚薄不同而已。”而这样的北京,便如童话般,“清洁、安宁、饱满、祥和”,小说似乎在诉诸一个均等公平的乌托邦世界,然而在我看来,徐则臣试图将一个理想的世界带至每个人的面前,在那里,世界并非难以企及,恰恰相反,就在触手可碰之处,容得下一切的拼搏或挣扎、失落或遐思、成王与败寇。换言之,真正的“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徐则臣的小说而言,在历史、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偌大的北京城。但他小说的人物对北京的情感却极为复杂而暧昧,他们寄身于斯,却游走于边缘,四处碰壁成为了显明的艰困。他们对宏大之城遥遥相望,落差之中,时有分裂。小说《摩洛哥王子》里,“我们”正在经历一次荒诞的演出,“把扫帚支在椅背上当立式的麦克风,王枫抱着吉他站在麦克风后面,边弹边唱”。然而,这样的草根音乐,“让我们的生活有了一点别样的滋味,想一想,我都觉得我的神经衰弱的脑血管也跳得有了让人心怡的节奏”。《耶路撒冷》里,初平阳自况为“小民”,弱势、卑微,逆来顺受,经受不住冲击和伤害,在时代大潮面前,他们更多不是对抗关系,而是保求安稳;但有一点,对于那个庞大的城市以及那些略显空洞的前景,他们常常不服气,要四处闯一闯,到处拼一拼,试一试种种可能与不可能。《成人礼》中,叶姐想要通过勤勉奋斗,“实实在在地生活”,而行健则企图“在北京扎下根来”。《看不见的城市》里,建筑工地里的泥水匠天岫不幸去世,然而他在现实中却是如此地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想要描绘在北京生活与工作的人生蓝图。在城市与乡土、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的二项对立中,徐则臣写下的人物往往投射着背负与承担的勇毅,显现出当代中国及当代人的精神境况。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徐则臣小说中,自我的认知及其实践尽管不无倔强,失败后亦不无精神的支撑,但这样的经验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存在着一个足以容纳错误和灰色的空间,在多元的层次中探讨生活与生命的可能。更为关键的是,那些宏大的与幽邃的差异性参数,是否能够换算出想象的空间,并通过充分的辩证形成阶梯与径路。这是徐则臣小说提出的历史命题,人物主体在面对历史、世界与现实的生存场域时,如果处于莫大的鸿沟中,一代人或者说一种当代化的主体,有没有未来想象的可能性?《耶路撒冷》故事收尾时,易长安入狱,初平阳和杨杰陷入回忆和畅想,而齐苏红、吕冬和秦福小则最终处置他们的家事和情事,无有牵挂,各自归心。何去何从,何以为继,变得迷茫和无措。终了,初平阳与秦福小等人在火车站送别被押解的易长安,尔后小聚,福小领养的孩子天送睡着了,梦中呓语道:“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面对历史政治的、想象世界的以及现代意义的追寻,文学提供了一种多元价值认同的情感结构,掉到地上的要捡拾,失踪了的要觅寻,截断与分裂的试图填充,于是形成了补给的与救赎的诗学,以照亮那些过分幽邃的暗影。
总而言之,徐则臣小说中隐含着宏大的与幽邃的两重叙事结构,投射出一种深刻而内在的精神辩证,意识形态的宏大巨影中,投射着人的灵魂,并以此探询故事的深广度,如徐则臣所言:“的确,我几乎是不厌其烦地深入到他们的皮肤、眼睛和内心,我想把他们的困惑、疑问、疼痛和发现说清楚,起码是努力说清楚。”事实上,徐则臣所述写的人物并不甘愿下坠,而时时桀骜不驯、固执刚强,执拗于生活和感情,成为此一时代不易发觉的精神潜流,在他们那里,代表着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尊严,其在失衡的辩证中,追索自身内外的真切对位,在无比宏硕的旷野中,获致微弱无常却不至于被湮没的回响。
最后,我突然想起,初平阳曾对舒袖说:“我们都缺少对某种看不见的、空虚的、虚无之物的想象和坚持,所以我们都停下了。”对于徐则臣而言,那些宏大而虚空的现实存在,不是简单的推离与对抗,相反,是试图去“想象”和“坚持”,无论是历史的挤压,还是世界的空无,又或者是城市的放逐,都不足以指向无望的抛掷。确切地说,或者追逐进取,又或回炉再造,只是不要“停下来”,最起码践行尝试,一笔一画勾勒和描画,再不济便施以涂改,从头再来。当然,徐则臣的小说远不是励志的修辞,更在于开凿精神的空间及可能,勾连那些宏大的期望与幽邃的灵魂,使之不至于过分开裂而难以企及。于是乎,行健们要努力一把,初平阳们想奋力一搏,戴山川们欲一探究竟……然而退一步说,不是谁都要削尖脑袋,钻破藩篱与限定,小说《屋顶上》里,宝来身负重伤,从北京黯然回到花街,而“我”最终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创伤返回故乡。历史的、世界的与城市的宏大镜像固然辐射广大,而那些幽邃的内心亦丰富而多义,这其中并无贵贱高低,公平来去无有阻隔,彼此交连或断开,或是施展抱负与雄心,最起码留存生命之印记。在这个过程中,徐则臣小说展开了不同的心理与经验路径,四下发散,终而归拢于精神的总体,那是壮阔时代中声色俱在的质朴灵魂。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在《文艺报》所开设的“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2年7月18日第5版。)

相关文章:
- 徐则臣的“乌托邦”与小说的可能性[2022-07-18]
- 叶立文:“茅奖”杂忆[2022-06-23]
- 李洱的文学观与《应物兄》的接受[2022-06-20]
- 李洱小说中的“费边幽灵”[2022-06-20]
- 曾镇南:我所看见和亲历过的“茅奖”[2022-06-16]
- 徐则臣:“回到故乡”是另一种意义的“到世界去”[2022-06-10]
- 傅小平 徐则臣:在文化和历史的场中[2022-05-27]
- 徐则臣:今天怎样做小说家[2022-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