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上海影人剧团: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剧团:它的存在仅仅只有一年时间,但却是抗战初期大批戏剧团体入川的第一支队伍。为此它经历了后来者所不曾经历的苦难,遭受了后来者所不曾遭受的屈辱;它以自己的顽强和努力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发展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基础,这便是上海影人剧团。
然而,它的历史却成为了碎片,需要将其拾起,需要将其缀合。

影人剧团十姊妹,前右路曦,二排右一白杨,左二吴茵

上海影人剧团出发前
告别上海 为防止女演员被潜规则 拟定不得单独外出的《生活守则》
“八一三”沪战爆发之后,聚集于上海的戏剧工作者按照党的指示,组成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与敌后,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演出。然而,与他们堪称姊妹的另一支队伍——电影从业人员,却一时显得群龙无首。日寇的炮火使得电影公司关门停产,影人们陷入了失业的困境。首先想到这批进退无据人群的是蔡楚生,他决定组织一个剧团,就像那13支救亡演剧队一样,让这些失业而不失志的电影人,改用话剧的形式为抗日救亡服务。
他从华联、明星、艺华、新华四大影片公司中动员来了34人——女士12名,男士22名,其中不乏早已家喻户晓的老牌明星,更有一大批热情奔放、积极上进的年轻人。唯有陈白尘,不属于“影人”行列,蔡楚生找到他,只为邀请他担任剧团的编剧,更希望他能够代替自己率队出征,其本人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离沪。于是,一个为特定人物所设计的特定方案,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1937年9月23日,上海影人剧团在由陈白尘、沈浮、孟君谋三人组成的常务理事会的率领下,跟随着夏云瑚上路了。
一路的担惊受怕,一路的死里逃生,目的地终于日渐临近了。但是在几位领导者的心中,却开始不安与沉重起来:等待剧团的将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此时国民党的势力虽然已伸进夔门,但仅仅在重庆设立了一个蒋介石的行辕而已,整个四川基本还处于封建军阀的割据之中。从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的上海,来到这典型的半封建的四川,其凶险是难以预料的。
白杨曾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当轮船即将到达重庆时,夏云瑚面对12名女团员说:‘四川的军阀官僚横行霸道,专门玩弄女性,请各位衣着朴素,结伴而行,以防万一!’当时只有17岁的我,心中惴惴不安,由我主演的《十字街头》等影片已经入川放映过,他们会不会……?吴茵看到我的脸色不对,赶忙走到我身边,亲切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是姐妹,出门就像一家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集体行动,谁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请大家报一下年龄,让我们结成十二姐妹!’当时吴茵29岁,排行老大,大家就叫她大姐;我排行第九,大家就叫我九妹。”
三位理事则集体商议,拟出了一个以保护每位团员安全为宗旨的《生活守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除集体行动外,任何人不得单独参加任何社交活动。”

演员魏鹤龄

演员谢添
抵达重庆 以《生活守则》为武器,回绝心怀叵测的“邀请”
1937年10月15日,上海影人剧团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重庆。在夏云瑚的安排下,全团下榻在苍坪街一处半地下室里。未等洗净征尘,一场声势空前的欢迎活动便开始了。
这毕竟是头牌影星第一次光临四川,更何况人数又是如此之多,山城重庆有如掀起了一场狂澜。每日的报纸上报道与花絮不断,苍坪街住地的来访者与宴请者更是络绎不绝。在10月18日上海电影公司及国泰电影院举行的招待会上,陈白尘不得不以负责人的身份请求大众:“望四川同胞勿将我们的团员当明星看,应在剧情里求内容。”全团亦于该日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因要求团员签名者过多,从今日起,每求签一名字,捐法币一元,交抗敌后援会。”10月19日,剧团不得已又在《新蜀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入川从事救亡演剧以来,辱承各界人士或宠予招待,或设宴欢迎,即日起加紧排练,对各界招待容有方命之处,请予原宥。”
在这一片欢迎与颂扬声中,重庆的土皇帝们也登台露面了。市长李宏坤派人送来一张名片,传呼白杨到其府中赴宴。这无异于旧社会召唤歌舞女的“条子”,全团无不为之气愤难平。
白杨不会忘记的是:“这时吴茵大姐站了出来,对来人说:‘我们剧团有条纪律,演员不得单独外出,只能集体行动!’弄得那个市长骑虎难下。”
陈白尘则更为详细地写下了这一经过:“李宏坤不死心,当天晚上又派了一名身穿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的科长径直来找剧团负责人。他一声不响地从袖管里抽出12份大红请柬,摊在桌子上,每位的名字之下均是‘女士’二字,无一‘先生’。陈白尘怒不可遏,再次以《生活守则》为武器,回绝了这一心怀叵测的“邀请”。这位科长满面怒容,抄起请柬咕哝了一句:“不识抬举!”扬长而去。
恼羞成怒的李宏坤,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是夏云瑚亲自出面,才使对方改变了方式——邀请全体团员出席。那天大家被带进了一间客厅,赏了一桌饭菜后,李宏坤提出要请所有人去跳舞——狡猾成性的他终于“图穷匕首见”了。
陈白尘在文章中回忆:“众人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报告市长:我们都不会跳舞!’管理剧务的胡瑛女士霍地站起身来,抢先作了回答。我也忍耐不住,率领大家毅然离席:‘今晚我们要排戏,就此告辞!’李宏坤勃然变色,望着远去的我们跳脚大骂。最终只得把一家歌舞团的女演员们喊来,充当了替身。”
10月27日,影人剧团终于正式公演了,剧场即为夏云瑚经营的国泰大戏院。首场演出的是陈白尘的三幕剧《卢沟桥之战》和独幕剧《沈阳之夜》。其中“慰劳座”的票款收入,提取25%作为捐款,支援前线。
重庆不少市民是第一次观看话剧,更何况又有如此之多的明星作为号召,“国泰”的门前每天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场内的气氛更是热烈,每当台上演员喊出“我们为民族而战”时,台下则掌声雷动,呼声四起。
11月2日,又轮换演出了陈凝秋(塞克)的《流民三千万》,以及屡演不衰的《放下你的鞭子》;一周后再次推出了陈白尘的新作《汉奸》。
影人剧团终于为重庆的剧坛播下了抗敌的火种,拉开了大后方抗战戏剧的序幕。11月7日,《国民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全民文化”谈到影人剧团的演出》的长文,作者姜公伟对剧团的努力作出很高的评价。在此期间,关心影人剧团的朋友委实不少,有人提出应该再降低一些票价,以争取更多的观众;有人建议应该到农村和部队中去演出,以扩大宣传的范围。对于这些意见,常务理事们非常重视,但囿于没有经济实权,又与夏云瑚签有合同,而难以成行。他们找来夏云瑚商量,最后的决定是:转移码头,另辟战场——向成都进发,去川西坝子里再点燃一把抗战戏剧的烈火。
11月30日,影人剧团动身上路了,他们在《新蜀报》和《国民公报》上连登启事三天,鸣谢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关怀。他们告别了这座难忘的山城,也同时告别了第一阶段的战斗。

理事孟君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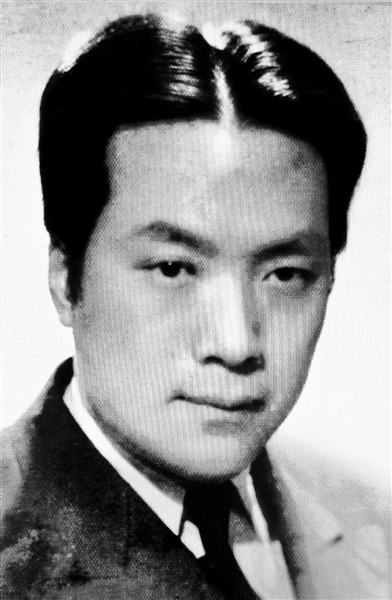
理事陈白尘
转战成都 剧团和演员们都被迫更名
12月2日,影人剧团一行风尘仆仆地来到成都,各界人士的欢迎不亚于重庆。演出剧场选在智育电影院,在夏云瑚的帮助下,将舞台进行了一番改造与扩建。十天之后公演正式开始,剧目仍选用在重庆演出过的《卢沟桥之战》《沈阳之夜》和《流民三千万》,演出效果同样轰动了蓉城。
吴茵说,她最难忘记的是:“成都观众都疯了,不但戏院门前像集市一样热闹,就连住地附近也是川流不息的人群。看化妆,认演员,加之采访与会谈,天天都是应接不暇,有时甚至影响到开幕,不得不婉言谢绝。”
然而,成都是一个军阀统治更加根深蒂固的地区,其土皇帝们的威势也更高重庆一筹。在剧团呈请租园演出的呈文上,成都市政府主任委员稽祖佑的批示竟是这样:“应与警局切商监视办法,并遴选监视人员。因时代不同,本市情形近来尤为复杂,须特别注意,万勿照平时手续,是为至要。”
警备司令严啸虎更是不可一世,他三番五次地“下条子”,“邀请”白杨陪他喝咖啡。
那一天让所有人都不会忘记——屡屡遭到拒绝的严啸虎不甘失败,他派出当地的川剧名角“四川胡蝶”径直到后台来,说是亲自陪同白杨一同前往,结果同样碰了一个大钉子。这个恶魔大发雷霆,就在剧团上演《流民三千万》时,他闯进剧场,指着天幕上冉冉升起的象征着光明前途的红日,一口咬定是日本国旗,是在为敌寇作宣传。紧接着命令下达了:立即停演,限三日出境。
一出反映抗日的话剧,一个从事救亡宣传的剧团,竟被如此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成为千古奇冤!
影人剧团所遭受的迫害,引起了强烈民愤。文艺界、新闻界、教育界,以及广大青年学生们纷纷前来声援。他们责问当局抗日宣传何罪之有,如果要将白杨等人拿办,大家便陪同剧团一道坐牢。严啸虎赶到某中学操场训话,愤怒的同学根本不予理睬,他们一遍遍呼喊着白杨的名字,以此表示强烈抗议。
专横跋扈的严啸虎不得不让步,但为了下台,又提出了两个极为苛刻的条件:一、剧团必须更换名称,否则不许在成都地区演出;二、所有演职员一律改名易姓,否则不允许刊登广告。
为了能够继续宣传抗日、报答成都的观众,大家只得忍气吞声,咬牙应允。从此,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上海影人剧团”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成都剧社”;观众所熟悉的演员们不见了,代之而出现的是一些闻所未闻的名字。
谢添是个乐天派,面对愁眉不展的众人,他动起了脑筋:“严啸虎不是一口咬定你是日本人吗?”他对白杨说,“那么我建议你索性改个日本名字——‘西门樱’,谁让咱们的剧团住在成都的西门呢!”大家无不拍手称绝。紧接着什么“西门辣斐”(谢添)啦,什么“温慈”(吴茵)啦,一大堆古里古怪的名字相继出现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知是由于剧团的名声大振呢,还是严啸虎又作了什么手脚,事隔不久,一批成都的地头蛇纷纷来到剧团,以月薪200元的高价为诱饵,进行拉拢收买。
自从入川以来,剧团的演出虽说一直很卖座,但收入的大部分都捐给了前方,每人每月只能领到10元的零用费。面对如此诱人的薪酬,原上海明星公司的那批老牌明星们抵挡不住了,王献斋、徐莘园、龚稼农等人纷纷动摇,或是去了沙利文剧场,或是去了春熙大舞台,剧团的原班人马一分为三了。
这似乎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每个人的立场与态度都在经受着考验。留下来的人虽说仅有十余个,但是成都剧社的旗帜没有倒下。他们是白杨、吴茵、杨露茜(路曦)、谢天(谢添)、施超、燕群、刘莉影、严皇、高步霄、董湘萍、沈浮、孟君谋和陈白尘。此外还有灯光师程默、木工师王元元,以及两位新加入的当地青年。大家同仇敌忾,甘苦与共,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排演出大型话剧《日出》和《雷雨》。
由于演员不敷分配,演《日出》时所有人都上场了。导演沈浮自己饰演潘经理,负责行政的孟君谋也上台扮演了黑三这一角色。
排练《雷雨》时又走了一批,人力就更加紧张了。没有布景师,找来一个学美术的大学生,边学边干竟也搭起了一台颇具气氛的公馆布景;后台人手不够,大家便身兼多职——上场是演员,下场管效果。
吴茵经常会回忆起那段日子:“做效果是很忙的,响雷要抖铁皮,闷雷要推木滚,下雨则用竹匾滚黄豆,还得准确地配合着台上的表演。人手少,演员下了场就得帮忙,还得一边听着台上的对话,轮到自己上场了,连忙丢下手里的活儿,跑步上台,既紧张又有趣。大伙为了争口气,忙死也心甘情愿。”
成都剧社胜利了,它经受住了重重磨难与考验。对于上海影人剧团来说,这是它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最为艰难的阶段。
搬兵武汉 阳翰笙拍板,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两团合并
夏云瑚虽说不是剧人,但是却有着戏剧活动家与组织者的敏锐与果断。就在影人剧团离开重庆抵达成都的当日,他找来陈白尘作了一番秘密长谈。
“剧团有分裂的可能!”他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的焦虑。入川后那批原上海明星公司的老牌明星们一直令夏云瑚头疼,不是动辄摆出明星的架子,提出种种过分要求,就是无端地同剧团负责人争吵,理由是偏袒年青演员。至于说某些人的恶习更是极大地损害了剧团的声誉。“看来,同他们是难以继续合作了。”夏云瑚不能不作出决定:“为了挽救剧团,只有搬请救兵!”
夏云瑚的担心,后来果然不幸而言中。但在当时,他却提前萌发了这样一个大胆的计划——此时由上海出发的救亡演剧队已大部分到了汉口,其中原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的人马都是昔日的战友;他希望陈白尘能够亲自去一趟武汉,邀请他们入川合作。
陈白尘二话不说,次日清晨便悄悄上路了。然而,抵达武汉后方知,此时的救亡演剧队已大多解散;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人员所组成的三队、四队也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去了前线,一部分人恢复了左翼剧联时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名称,在汉口作营业性的演出。
万般无奈的陈白尘想到了阳翰笙——此时的他正遵循周恩来的指示,为筹建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忙碌。影人剧团的命运深深牵动了他的心,特别是严啸虎一手策划的“成都风波”更是让他焦虑万分。他当即拍板:两团立即合并。
1938年元月,陈白尘兴高采烈地陪同着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同仁们登船起航了。这是一支人才济济的队伍,既有电影明星,又有话剧新秀;既有著名编剧,又有杰出导演。沈西苓、赵丹、魏鹤龄、陈鲤庭、陶金、章曼萍、朱今明、钱千里、英茵……一共20余人,这样的演剧团体就是在后来——大后方进入话剧运动的高潮时期,也是不多见的。
4月中旬,业余剧人协会终于抵达成都。它的到来,不仅使成都剧社转危为安,更让白杨等人的真实姓名重见了天日。由于两支队伍在人数上存在明显差异,业余剧人协会坚持袭用他们的名称。至此,上海影人剧团进入了他们的第三阶段——合并与易名后的新阶段。新的理事会成立了,除了影人剧团原有的三位常务理事陈白尘、沈浮、孟君谋外,又加上了“业余”的陈鲤庭、赵丹、陶金和刘郁民四人。
自4月25日起,业余剧人协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公演,10余台优秀的剧目令成都观众耳目一新。除了有原“业余”演出过的《民族万岁》《故乡》《夜光杯》《自由魂》,以及原成都剧社演出过的《雷雨》《日出》外,又排演了田汉根据鲁迅先生原著改编的《阿Q正传》、曹禺的《原野》、吴祖光的《凤凰城》、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及新作《群魔乱舞》等等。公演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如此盛况,无论是在以前的影人剧团,还是在以前的业余剧人协会,都是不曾有过的。
燕群作为原影人剧团的一员,最令她难以忘怀的是与魏鹤龄同台演出《原野》:“魏鹤龄扮演仇虎,我扮演金子。魏鹤龄为自己的人物造型设置得很特别:上齿是突出的假牙,腿是一瘸一拐的,脸上有一道刀疤,显示出在监狱里受过的酷刑。他尺寸的拿捏非常到位,将仇虎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活灵活现,而我也被他渐渐地带入了角色。”
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帮国民党士兵听说《日出》演得挺红火,死乞白赖地非让剧团给他们的弟兄们演一场。恰巧那天演陈白露的白杨病了,剧团向这帮大兵们作解释,可他们蛮横不讲理:“人不齐也得演,今天是非看不可了!”
被称为“中国的卓别林”的谢添,回忆起来有声有色——
“这帮家伙可不好惹,闹下去我们就得吃亏。可是没有陈白露,《日出》怎么演呀?好在这个戏我们也都熟了,陈白露的好多台词,别人也能记住一点儿,到时就看我们几个老爷们在台上怎么折腾了——“逢到有陈白露上场的地方,别人就替代着说:‘白露刚才说啦,怎么着……怎么着……’说了一堆陈白露的台词。”
“电话一响,‘喂!找陈白露呀,告诉你,她不在,有事儿就跟我说吧!……’又讲了一段陈白露的事儿。”
“就这样,我们演了一场没有陈白露的《日出》,本来是三个钟头的戏,我们只用半个小时就演完了。”
这里虽说讲出了他们的机智多谋,却也体现了他们的高超演技。
易名后的业余剧人协会在成都掀起了演剧的高潮。陈白尘与陈鲤庭在一心一意地忙于剧团的发展与建设——为了摆脱剧场老板的控制与剥削,他俩四处奔波,找到一处名叫“沙利文”的小剧场,地点虽偏,租金却很低廉,于是在长期租赁的合同上签了字,兴致勃勃地计划着以《茶花女》作为1939年元旦新剧场开张的开锣戏。
哪知就在此时,业余剧人协会于一夜之间彻底瓦解了!团内的大批人员被国民党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暗中拉走,剩下的人员溃不成军。
然而,它毕竟生存了一年,战斗了一年,为大后方戏剧运动所作出的贡献亦不可磨灭。它留下的诸多“碎片”,将被一一拾起,缀合成一串串闪光的珍珠。
(孟树英、谢平等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