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回忆文学讲习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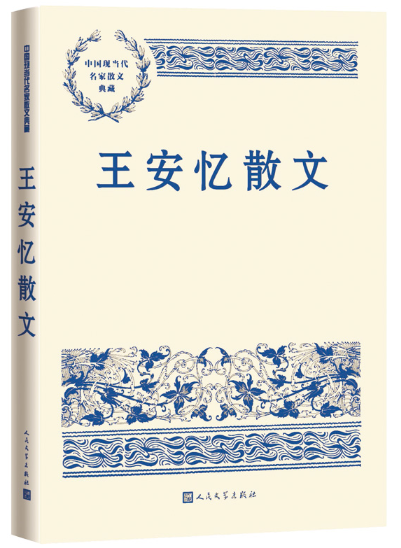
原文选自《王安忆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
我们那时候,鲁迅文学院是叫“文学讲习所”,没有自己的校舍,临时设在朝阳区委党校里面。党校周围空落得很,出了院门,走一段,才可抵到一个勉强可称为“街”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烟杂食品店,小是不小,可里面也是空落落的。因是早春乍暖还寒的天气,商店门口挂着一幅厚重的棉帘子,粗蓝布,绗着线,就像一床农家用的被子。路对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邮局。边上呢,是十八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就这些,也够了。生活起居就是这样简单。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党校周围的草木绿了起来。不是像江南地方的葱茏的绿,因为地方大,气候又干燥。但树身是高大的,枝叶错乱着伸展得很开,草呢?七高八低地冒了出来,就有了一种庞大和杂芜的春意。吃过晚饭,我们成群结伙,在党校后边散步。记忆中,那里有一二幢住宅楼,兀立于空地上的大树,一道丘陵般起伏的土岗子,岗上有杂树林。但要我进一步地描述出位置、方向和具体的环境特征,就做不到了。它的面积似乎相当大,并且,漫无秩序。并且,终究有些单调,没有特别的景物做参照。我们散步过了,回到党校,各自用功去了。
宿舍是四个人一间,我们仅有的五个女生,住走廊尽头的一大间。原先班上只有三个女生,这样不是要浪费一个名额了?校方又从地域出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仅只有竹林一个学员似乎委屈了,便委托上海少儿出版社,再推荐一名女生。恰巧,我正开始写作儿童文学,又不像其他几名候选人,比如王小鹰那样,在大学本科就读。于是,就这样,我乘虚而入,进了讲习所。在我来了之后,北京却又将一名男学员换成了女学员刘淑华。所以,老师们有时会和我开玩笑:要是刘淑华先来,你就来不了了。这真是万分幸运的事,想起来都有些后怕。我将进讲习所看得很重大,我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的。不是有人不来吗?先是贾平凹,后是母国政,最后才换上刘淑华。可这也影响不了,讲习所是我生活的转折点。
我们才来不久,就搬了一次家,从走廊那端的四人间搬到这端的五人间。后窗正对着后院,院里有一个浴室,每周六烧锅炉供热水。先是女生洗,再是男生洗。浴室很小,不晓得出于什么样的原理,它就像一个共鸣箱,将声音放得很大,然后从顶上的小气窗送了出来。所以,坐在我们的房间里,哪怕关着窗,浴室里的声音也清晰入耳。并且,很奇怪地,他们男生进了浴室,都喜欢唱歌。像贾大山这样,平时缄默的人,也放开嗓子唱起来。唱的是他们那地方的戏曲吧?很高亢的声腔。等洗澡的喧哗过去,后院便静了下来。
课堂是兼作饭厅的。前面是讲台和黑板,后边的角落里,有一扇玻璃窗,到开饭时,便拉开来,卖饭卖菜。里面就是厨房。所以上课时饭和馒头的蒸汽,炒菜的油烟,还有鱼香肉香,便飘忽出来,弥漫在课堂上,刺激着我们的食欲。一九八〇年的北京,吃,还是一个问题。饭票是分作面票和米票的,十斤全国粮票,只能换四斤米票,其余六斤是面票。到现在还记得米票的样子,是一分钱纸币的大小,牛皮纸的颜色,用黑色的墨印着“米票”的字样,四两为一张。这样比例的米票,对于吃惯面食的北方人来说,正够调剂口味;而南方人,可就苦了。那时候,油粮都是定量供给,一个人一个月的地方粮票,要搭上一人一月的油票,才可换三十斤全国粮票。我要是多向家中要全国粮票,就等于克扣家中的吃油了。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花费超出定量的饭票。越是这样米票紧张,越是能吃米。四两一满碗的米饭,眨眼就吃下去了。与此同时,是对面食不恰当的厌恶,以至到了后期,闻到蒸馒头的酵粉的微酸的蒸汽,就要作呕了。可是,没有办法,还是要吃。别人似乎多少有些办法,在北京有一些关系,可多得几张米票。他们也会匀给我几张,虽然有限,但聊胜于无。有一回,我在卖饭的窗口,与里面商量,能不能用面票当米票用,只此一次。那食堂工作人员很和气,却很坚决地,不肯通融。排在我后面的,吉林作家王世美,目睹了这一情景,二话不说,从兜里拔出一捆米票,刷,刷,刷,抽出一堆米票在我面前。
不开课,也不开饭的时候,我们会到这里来写东西。东一个,西一个,散得很开,各自埋头苦作。遇到不会写的字了,就转过身去问:“陈世旭,‘兔崽子’的‘崽’怎么写?”越过几排桌椅,远处的莫伸则插嘴道:“安忆也要用这样粗鲁的字吗?”有一些小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环境是杂一些,可心都是静的。我更喜欢在院子一侧的,另一座平房里的,小会议室写东西。小会议室很小,中间一张拼起的长桌,周围一圈椅子。我们就围着桌子,各写各的。这里空间小一些,也隐蔽一些,就比敞开的大饭厅里更有一种静谧的空气。中间进来一个人,将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放,发出咯的一声。于是,都从草稿本上抬起头来,去看新进的人。日光灯下,低头低得久了,猛抬起来,看出去的人脸都有些发黄,而且恍惚。复再低下头去,纸面上就有了一圈圈的光影,过一会儿,才散去。小会议室外的甬道边,有一棵,还是一行大树,是不是槐树?我不认树,记忆也模糊了,只知道枝条很粗,叶片很大,一层层的。月光将影子铺在地上,晚上,收拾了纸笔,从树底下,深深浅浅的影子上面,走回宿舍去。北方的月亮也是很大的。
写作总是在晚上,因为白天课排得很紧。老师对我们说:不要错过听课,写作的日子长呢!还许诺给我们,在学习期末一定安排写作的时间。一周六天,上午下午都排了课时。古典,西方,现当代,基础类的,思潮性的,理论的,实践的——这是请著名的作家来作创作的经验谈,我们听了多少课啊!有一位北大的老师,来讲俄国文学,讲《安娜·卡列尼娜》,说贵族的社交场,主要是举办舞会。他走到讲台前边,离我们很近地,用手罩着嘴加了一句:就像我们的开会!他讲得很好,上午讲完了,我们要求他下午再接着讲。老师真的将他留了下来,吃了一份客饭,睡了一个午觉,又讲了一个半天。吴组缃先生讲《红楼梦》,也是这样。讲了一次,不够,再让老师去请来讲第二次。因此,在规定好的课程外,又有些即兴的,多加出来的课。
吴组缃先生讲《红楼梦》,至今还在眼前。他微侧了身子,坐在讲桌后面,摆开长谈的架势,谈兴很浓。说到激动的地方,就隔了讲桌欠过身子,眼睛很亮地盯着前排的学员,好像要问他:你说是不是?他讲他的一个瑞典还是哪里的外国留学生,跟他学了三年的《红楼梦》,临毕业时,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大意是从地形上看,怡红院和潇湘馆实是不远,他们为何不能同居,抑或是出走?吴先生说,听了他的问题,便感到这三年是白教了,因他不懂得中国的社会,所以就不懂得宝黛的悲剧。你们知道吗?黛玉为什么老是和宝玉吵?吴先生问大家。黛玉为什么这么别扭?老要试探宝玉,而宝玉一旦表露心迹,她又要说宝玉欺负她?然后,吴先生便说到男女大防。在婚前,不能有一点点有涉的;否则,即便像宝玉与她这样的两情相知,都难免会小视她。他们就必须借别的一些事,来谈情。在他们感情史上决定性的一次交流,是宝玉挨贾政的棒子。黛玉去探望,说道:“你从此可就改了吧!”宝玉回答说:“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吴先生认为这是大有深意的,其实是宝玉向黛玉的彻心交代,而黛玉也听懂了。所以,在此之后,黛玉再没同宝玉闹过小性子。可是,吴先生不禁愤怒起来,越剧《红楼梦》竟然将情节顺序颠倒了,将黛玉在怡红院吃闭门羹,与宝玉生隙这一场,放到了宝玉挨打之后。宝玉已经向她说了: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里的“这些人”,就是黛玉啊!黛玉怎么会再对他生疑?这是个大大的错误!吴先生感情十分投入地认为,“金玉良缘”是个阴谋,书中有许多迹象,证明薛宝钗对贾宝玉窥觑已久。比如,薛家进京,说是送宝钗宫选,可是为什么后来就不提了,再没有下文了呢?吴先生从讲桌后面欠过身子问我们大家。还有,不是说宝钗“不爱花儿粉儿”,装束简朴,可为什么偏要时时戴个项圈?吴先生讲《红楼梦》,真是好听,就像在与你辨析一段世事,其中深谙着许多缘故端底。
听课以外,还举办过几次课堂讨论。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假期过后的一次,讨论小说形式的创新。贾大山很认真地准备了一份书面发言,逐字逐句地念了下来。方才说过,他是一个缄默的人,但也可能是在公众场合,私底下,他或者是相当善言的。那时候,我们班上的学员也是一拨一拨的,由于年龄、经历,还有地域的差别,他不是我们这一拨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矜持的贾大山,就只是表面。即便是从表面上,也还是可以看出他的活泼与俏皮。在他无限恳切的表情之下,隐忍着一丝明察秋毫的笑意,就是这,使他虽然沉默寡言,却绝不是乏味的了。这一天,他在讨论会上宣读了他的这份假期作业,专门谈意识流。这时节,意识流是个新概念,它给我们保守了多年的小说带来了一个新的契机,已经有意识超前的作家在使用它了。尽管还并不完全了解它内部的、心理学和语法学背景下的含义,但仅止是表面上,它的那种将叙述切碎了,又将某种细节夸张了的方式,就足够我们见识的了。这时节,刚刚走出封闭,世界一百年的思潮向我们扑面而来,都来不及地听、看、汲取。贾大山发言中说,他在假期里,也写了一篇意识流的习作,现在,他就将这篇习作念给大家听。他的小说是写收割的,记得最清楚的,是关于田野里草帽的描述,大致是:草帽,草帽,草帽,大的草帽,小的草帽,起伏的草帽,旋转的草帽,阳光烁烁的草帽,草帽,草帽,草帽……大家早已笑得前仰后合,而他始终不笑,坚持将小说读到底。他以农民式的狡黠表达了对这些半生不熟的现代小说观念的怀疑,其中是有一些保守,可是也包含着坚守的态度,坚守他一贯遵守的经典叙述原则。那种以创造人物与故事为最终审美的叙述原则,其实是困难的,对作者的想象力,生活经验以及语言能力都是永不歇止的挑战。不是吗?贾大山的“草帽,草帽,草帽”不是很简单,很方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小说技法掩盖在另辟蹊径之下的是叙述的软弱。直到他终年,他都没有向叙述的严格性妥协过,他不多的那些小说,无一不是遵循着经典的原则。
我忘不了,有一次在水池边洗衣服,遇到贾大山,他对我说:你发在《河北文艺》上的《平原上》,写得不错,我和张庆田——就是《河北文艺》主编说,这孩子会有出息。《平原上》是我的第一篇小说,还是由我妈妈送到《河北文艺》去发表的,多少带有些“后门”的性质。一篇三千来字,排在很后面的小稿,谁能看见呢?可贾大山看见了,还断定我会有出息,真是莫大的鼓舞啊!而我相信贾大山的眼光,也相信他的诚实天性,他不会是因为我妈妈的缘故恭维我。
当时,在讲习所,我可实在是没本钱,倘若不是前面说的那个偶然因素,我是进不来讲习所的。周围的同学们,我只在杂志上读到他们的名字,都是我羡慕和崇拜的人。然而,大家都对我很好,并且,我也能看出,这里边并不全是因为我妈妈的缘故,我得到了许多真诚的关爱。同学中,有不少在当地主持刊物的工作,他们竟也来向我约稿,这其实是很冒险的。由于讲习所集中了这么一大批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分子,编辑就络绎不绝地前来约稿,可是没有人向我约稿。再是自谦,也是不自在的。逢到这时候,我便知趣地走开去。我也忘不了东北作家王宗汉,他约我为他主编的《江城》写一篇小说,我如期写完,交给他。他看了之后却说:这篇给《江城》可惜了,我替你给了中青社的《小说季刊》。这篇小说就是《小院琐记》。还有蒋子龙,约我给《新港》写的《命运》,当他在饭厅里和我谈修改意见时,我激动得气都急了。我觉得他们都很像我的兄长,一点不嫌弃我,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携了我。
大约是在讲习所学习的后半期,不知如何开的头,我们兴起了舞会。周末晚上,吃过晚饭,将桌椅推到墙边,再拎来一架录音机,音乐就放响了。先是一对两对比较会跳和勇敢的,渐渐地,大家都下了海。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不大会跳,而且,跳舞这事情也显得有些不寻常。所以,跳起来,表情都很肃穆。要罗曼蒂克地,一边闲聊一边走舞步,那是想也别想。在刚开放的年头里,每一件新起的事物,无论是比较重大的,比如“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还是比较不那么重大,跳舞这样的娱乐消遣,都有着启蒙的意思,人们都是带着股韧劲去做的。记得那年的“五一”节,讲习所放假,张抗抗挑头,我,陈世旭、艾克拜尔,还有叶辛,一行五人去八大处玩。在一处空着的偏殿里,传出节奏激烈的音乐,大家争相拥去,将偏殿围得水泄不通,偏殿里有七八个男女在跳摇摆舞,地上放着架录音机,音乐就是从那里面发出的。他们穿着喇叭裤,女孩子穿着男式领角的衬衫,衬衫下摆束在裤腰里,十分摩登。看上去,他们也算不得多少会跳,胯和腰的扭动有些生硬,也并不都能踩在点子上。可他们顽强地扭动着腰胯,一曲结束,便有人立即过去,将磁带翻个面,再续上一曲,接着往下
讲习所舞会开张,党校食堂里的那几个年轻人也来参加,他们带来了录音机、磁带,还有舞伴。他们都比我们会跳,可做我们的老师。再后来,有些杂志社的编辑也来赴我们的舞会。后来,我们安排到北戴河度假,也带着录音机和舞曲的磁带。晚上,我们走到海滩去跳舞,夜晚的北戴河,与白天很不一样,它显得相当荒凉。海和天都很黑,而且空阔。海水一层层地拍着岸,听起来没什么声响,可录音机里的乐曲却变得虚弱了,原来,它们是有着巨大的轰鸣。说实在的,舞兴也不怎么样。柔软的沙地裹着脚,走不开步子。可我们还是坚持跳着。不一会儿,四周就围上了一些当地的小孩子,站,或者蹲在暗夜里,默默地望着我们动来动去的身影。
那时候,生活是简朴的。讲习所里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可彩色还不如黑白的清楚。永远调不准频道似的,所有的图像都在不停地抖动和变形。偶尔碰巧了,出来一个盛装的女人,报幕还是歌唱,大家便惊异地问:这是谁?其中一个就回答:谁?妖精!又有人逗蒋子龙的小男孩,问:你家有吗?有!几个色?两个色!什么色?黑的和白的!小男孩反应特别敏捷,应对如流,一口的天津话,将“色”说成“塞”,发第三声。
常来讲习所玩的孩子,还有王宗汉的一儿一女。儿子王家男正处在少年的飞跃性发育阶段,身量很高,特别瘦削,脸呢,还是幼稚的孩子脸,异常的沉默。但即便在这种身心不平衡的成长时期,他依然是温顺与安静的,可见得他柔和的天性。后来看到他写的小说《乡恋》,一下子与他的少年形象联系起来了。女儿的名字起得很好,叫做“可心”,人也长得“可心”,那时才齐桌高。两年前,忽然接到一个女孩子的电话,声音特别清亮,代表东北某家报纸来约稿,自称是“王可心”。不由吃了一惊,有多少时间过去了呀!
校舍后面是一个操场,有篮球架,讲习所与党校举行过篮球友谊比赛。还有一张乒乓桌,但拍子和球似乎不太好找,偶尔凑齐一副,就打上一阵子,然后又没了。
还有就是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聊天。聊的呢,大多是文学。那时候真的很热衷谈文学,一点不是矫情,而是很认真,也很自然,谈自己的思想和构思。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还有《芙蓉镇》,就是在那时候讲给我们听的。听着就觉得好,不料,写出来,更好。也谈苦恼。河北作家申跃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写作了。那时,拘泥着写,还能写出来,现在,放开了,反而写不出了。他说,他就好像是一张网眼特别稀的网,打下去,东西都从网眼里漏了。
读书也占了许多时间。讲习所有一个小小的,只一间屋的图书馆,管理员叫小井。书不多,有一本新来的好书便永远地在人们手里周转,回不到书架上。那时候,有一本很抢手的苏联小说,叫做《白比姆·黑耳朵》,陈世旭看着,看着,就独自在房间里踱着步,大声朗读起来。人们走过他的房间,都朝里望一眼。
晚上,党校的学员走了,工作人员也走了,就剩讲习所的这些人,在各自的房间里,做着自己的事情。偶尔从开阖的房门里,传出一两句说话声。等大多数宿舍关了灯,走廊里会响起一阵脚步声,是最后一班十八路汽车将哪个人送回来了。也有来串门看朋友的人,也得赶十八路的末班车回去。
然后,讲习所就组织去北戴河了。很隆重地,出发之前,我和抗抗,还有叶辛,特地去了趟王府井,买旅行用品。买了太阳镜、遮阳帽,我没有买到合适的游泳衣,后来是小井将他妹妹的游泳衣借了给我。男式的游泳裤倒有,但叶辛又不想买了。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假如买了游泳裤,他就要去游泳,假如去游泳,就可能淹死。最后,在抗抗的连笑带骂之下,他不得不买了游泳裤。到了北戴河,他就穿了新买的游泳裤,站在齐膝的海水里,用手蘸了水往身上拍。脸上的表情多少有些愁苦,好像不是出自情愿,多少是由于某种压力。去海滨游玩的东西准备齐了,上路了。
到了北戴河,住下,所领导古鉴之立即召集开会,作一番讲话。大意不外是让大家好好休息,好好玩,注意安全,通过这机会,更进一步地互相了解——所以,不妨可以打破圈子,广泛地接触、交往,比如古鉴之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乔典运也可以和王安忆一起散散步,聊聊天嘛!大家便哄然大笑,大约是觉得乔典运与我太不相似了。
乔典运来自河南农村,是学员中最年长的一位,当年已是四十九岁。开学初,天还寒冷,他就穿一件对襟的黑布棉袄,理着一个发茬很低的平头,完全是一个田里的把式。但他有着相当沉着的气质,这是内心生活在起作用,这使他变得睿智。大家拿这话取笑了很久,老乔则很厚道又不失大方地说:“其实我和安忆经常聊天。”
北戴河,蓝天绿海。都是刚走出暗淡的生活不久,不相信好日子就这么轻易地来了。往后的日子其实越来越好,可是再好哪有刚开始的时候新鲜?有希望?
住的招待所面向大海,走过去只几百米。我们成日价泡在水里,也不管是会游泳,不会游泳。然后在沙滩上晒太阳。沙粒很细,滑润,均匀。早上,潮退去了,留下了贝壳,海星,花石子。拾一捧,看看,有更好的,就丢了,再拾一捧。太阳一点一点升高,绿海就变成金海。
北戴河有一家德国西餐厅,“起土林”。在当时看来,极其的豪华,价格也贵得惊人。那时候,花钱还很节制。人们大多是走过看看,真正进去吃的很少。所以,店堂里相当冷清。抗抗请我吃了一次色拉,艾克拜尔庆贺得子,又请我和陈世旭吃了一回圣代。陈世旭将他杯中的掼奶油都分给了我们俩他,说他是吃野菜的命,欣赏不来这洋玩意儿。
讲习所还向渔船上买过一回海螃蟹,请招待所的食堂煮了给大家尝鲜。可惜大部分北方同学吃不来,也不赏识,草草地嚼一遍,丢下一桌子蟹钳蟹脚,走了。
北戴河是讲习所生活的高潮,从北戴河回来,多少有些人意阑珊。
回来不几天便放假,一个月。等一个月以后,大家从各地家中纷纷返校。离别了一段,重聚一起,就又有了些重新开头的喜悦和振作。彼此看看,都有点变样,新理了头发,换了装束,身上脸上染了些家庭生活温暖又私密的气息。本来已经稔熟了的,这时候又生分了似的,不大好意思。散了一半的心这会儿又聚拢起来,但总归是向收尾上靠了。各人忙着写毕业作品,交上去,所方则四处联络刊物审阅与批用这些作品。学员们又提出,讲习所能否出面,向各人所在单位请一段时间的创作假,作为讲习所课程的延续。再有,举行一次答谢导师的宴会。
讲习所的前期是上大课,后期则效仿研究院的导师制。每三至五人,认一位导师,导师是由著名的作家担任。我,瞿小伟,郭玉道,因是写儿童文学,所以,就跟了金近老师。
瞿小伟是北京的青年,当时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小薇薇》,写一对小儿女跟了父母在干校里的遭遇。和描写那个时代的故事一样,结局是凄楚的,但是却流露出特别纯真和温暖的感情。里面还有一条忠实的大狗,就像所有天性善良的男孩,梦想中的伙伴,最后也伤心地死了。这篇小说后来和我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同获得了全国第二届少年文艺创作二等奖。颁奖正是在讲习所的学习期间举行,这使得默默无闻的我们俩,多少挣得了一点荣誉。他和我同是讲习所里唯有的共青团员,所以,开学的第一天,就由我们俩再加上打字员小林,组成了一个团小组,由共产党员、军人作家李占恒来领导我们。郭玉道来自青海,其实在那时候,他已经呈现出疾病的征兆,可谁也没有注意,他削瘦,面色萎黄,精神多少有些不济。他似乎不顶合群,也许只不过是性格羞怯,不惯于在人前说话。在他的宿舍里,还有我们共同去赴老师家上课的路上,他还是活跃的。
我们三个一同去金近老师家,路上需转两路或是三路汽车,再要走一段。我们到的时候,老师已经候在那里了。准备好了茶水,还有盛在菜碗里的半碗杏子。金近老师是江浙人,乡音很重的普通话。但决不会听不懂,于我来说,还很亲切。因在上海,多是听到这样的普通话,它比字正腔圆的北方话,要家常得多,也温婉得多。因是夏季,他多是穿着汗背心,手上持一把蒲扇,和我们说话。他看上去,就像是个乡下小老头,可这“乡下小老头”,却有着骨子里的优雅:安静,温和,从容不迫。他显然不善言谈,甚至于还有些不安,不知该对我们说什么。他很努力地想着,想一句,就说一句。而他又没有一丝一毫应付我们的意思。他特别愿意同我们多说一些,把写作的秘诀教给我们。可是,写作有什么秘诀呢?像老师这样一个诚实的人,是连一句虚浮的话也说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他家,就坐不长,大约一小时左右,便告辞了。可是,我们每一次都定好下周的上课时间。到时间一准去,老师也已在等着我们了。
谢师宴会是在朝阳区委党校的饭厅里举行。党校的伙房很有些军队应变作战的素质。平常日子里,玉米面饼,大楂子粥,米饭一碗碗蒸着,菜是大锅炖煮,大勺子当当地舀到一溜排开的搪瓷盆里,然后,打铃开饭。可到了要紧时刻,它八冷盘,八热炒,大菜甜食,说上就上。办事情的杯盘碗盏也都拿出来了,虽不是细瓷描花的,可却齐齐整整。饭厅里一下子布满了餐桌,一圈冷盘中间,立着酒水瓶子。五时许,导师们陆续到了,由各自的学生陪着,参观讲习所驻地,又到院子里树底下照相。金近老师也来了,穿一件白衬衫,手里提一个人造革的黑拎包。导师自然是和学生坐一桌,桌边放的都是长凳和方凳。我们中的谁就到宿舍里搬来一张靠背椅,要老师移坐到椅上去。金近老师一定不肯,说这样就蛮好,觉得我们实在多此一举。我们则一定要他坐椅子,瞿小伟还站起来,从金近老师的身后,双手扶住他的肋下,要将他强持到椅上。瘦小的老师在高大的学生身下,滑稽地挣着手,就是不从,都快要生气了。我们到底强不过老师,只得作罢。晚宴开始时,还矜持着,等喝了酒,气氛就松弛了。那时候,吃喝的事情还不太经常,大家都兴奋得很。说话的声音也大了,酒呢,敬来敬去的,都有三分醉了。金近老师看来是不惯于这种喧哗的,但他不扫人兴,等到有人陆续离了席,他才说要走了。然后,我们三个人送他去搭乘十八路车。走在通往汽车站的,黑漆漆的土路上,师生四人都放松下来,说着闲话。走一截,有了路灯,将我们几长几短的身影,投在地上。车暗着灯,敞着门等在终点站,老师同我们一个个告别,就转身上车。瞿小伟又伸出手,扶住老师的肋下,托他上了车。车门关上,车灯亮起,驶离了站。我们三个,再荡啊荡地,荡回讲习所。已是秋初,风很凉爽,月亮升起来了。
离开讲习所以后,是多少日子?三年,还是五年?传来了郭玉道患癌疾逝世的消息,他是我们中间第一个早逝的同学。接下去,就有乔典运、贾大山,相继而去。他们都是贫瘠地区的农人,艰苦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身体,繁重的思想劳动又雪上加霜。
金近老师也离开了我们。讲习所过后,老师寄给我一本童话书,名叫《爱听故事的仙鹤》。这一篇中,写了一个作家,六十多岁,灰白头发,瘦瘦的,人们都管他叫“乡下爷爷”。这其实就是老师自己吧。现在,他也像文中的“乡下爷爷”,在对我们说:“我要讲的童话,还没有讲完哩。”
讲习所结束之前,我们还举行了一场舞会。大家期待着,再热闹一次,可已是曲终人散的气氛了。有人在打行李,宿舍里散乱着书籍纸张。有人忙于和北京的亲友告别,在房间里待客,或者出门去了来跳舞的就也心不定,过来坐一时,再走开一时。倒是一些外来的编辑,或是党校工作人员,和他们的熟人,在场子里舞着。
然后,一个一个走了,房间一个一个空了下来。卸下蚊帐,一下子露出了前后的窗户。窗外是北方的杨树,叶子茂密,在秋日的阳光下,翻着亮片,闪闪烁烁。真是满窗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