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我从未放弃过找到奶酪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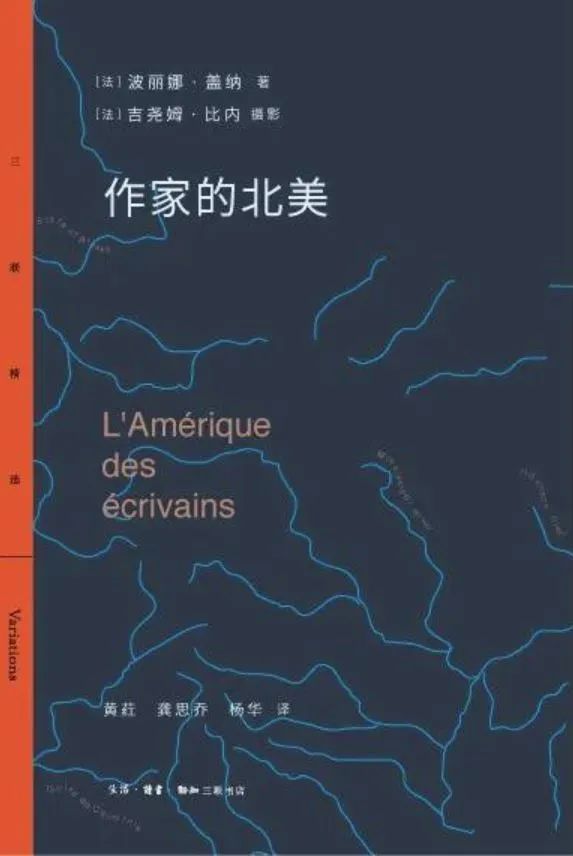
在安尼科斯【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居住区,毗邻多伦多大学】东边坐落着一座美丽的红砖房:宽敞的厨房,柜台上摆放着旅游指南和鸟类指南,花瓶中插着怒放的鲜花。靠近窗户的位置摆放着一盆兰花,整个房间都浸润在苍白的冬日阳光里。我们瞥见站在花园一隅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裹在厚厚的红色长款羽绒服里,正在穿一双大大的徒步鞋,准备带我们去喝咖啡。半路上,她指给我看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房子正面被独具特色的鱼形瓦片覆盖,有着黑色的尖屋顶,还有稍矮的房子,窗户更大——这是一种随着技术发展而变革的建筑:中央制暖的出现让炉子退伍了,室内供暖更容易了,即使开更大的窗户也不会影响屋内的温度……玛格丽特从八十年代起就住在这栋房子里,但她从六十年代起就生活在这个街区了。那时候,这些房子是按一个个房间短期分租出去的,还只是一个穷人区。而今天,有名望的银行家和知识分子正在对房子进行持续的翻新和美化。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在法国卢尔马兰的吕贝隆小镇生活过一年,加缪的遗孀卡特琳娜至今仍住在那里。
波丽娜·盖纳:
做一个加拿大作家意味着什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所有人都与他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关。法国有个有趣的现象,这片不算大的土地上存在着巨大的地理差异,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可能从一种风景过渡到另一种,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而在加拿大,如果要从一种风景过渡到另一种则需要穿过很长一段距离,我们永远都无法忽视加拿大的广袤无垠。从哈利法克斯到伦敦的距离不算什么,从哈利法克斯到温哥华的距离才叫远呢。我的家族在美洲大陆上生活的历史悠久,在那里,有在十七世纪被赶出去的美国清教徒、法国胡格诺派。他们中一部分人去了美国,一部分人去了爱尔兰或柏林,还有一部分去了新苏格兰。应该就是我这一支……
波丽娜·盖纳:
您的作品中有哪些主题是典型的加拿大主题呢?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她突然开始用法语说话。)有很多。我在一九六二年写了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里面涵盖了所有相关内容。(她换回用英语说话。)虽然后来情况有了一些不同,但并没有完全改变。我建议您去看看一九七二年发行的那版里关于印第安人的那章,再和约瑟夫·博伊登聊聊。那个时候还没有他的书。虽然已经有几个人开始写自传了,但那就是全部了。其他相关的作品都是之后才有的。
波丽娜·盖纳:
居住地对您的影响大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当然,我在附近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她笑。)在加拿大,没有我没去过的地方,甚至几乎没有我没生活过的地方。虽然我没在曼尼托巴生活过,但我在阿尔伯塔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在魁北克都生活过。在我小时候,一年被分为冬季和其他季节。每年,我们在渥太华过冬,在森林里度过余下的时间。我们一开始住在魁北克北部,后来去了苏必利尔湖北部。我的父亲是森林昆虫学家。因为他研究昆虫,所以需要住在森林里。但是昆虫在冬天什么也做不了,它们都被冻僵了。所以我们回到城市,在那里,父亲把他的研究写下来。十二岁以前我从来没有在学校读完过一个完整的学年,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学校外度过的时间越来越短。十二岁那年我上了高中——我跳了几级……那是我在学校上的第一个完整的学年。而往常,学期初或学期末我都是缺席的,甚至前后都缺席,只有在一学期的中间部分才去上课。在那时,对学校而言,这并不是个问题,但可能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母亲将学校发的课本领回家,带到森林里。只要我们每天完成了课本中计划要看的那几页书,就能出去玩耍了。所以我们一般都能比较快速地完成……在学校,我们必须等所有人都完成才行,简直太没劲了……(她笑。)就像您料想的那样,我接触书籍的时间比一般人早,毕竟在树林里没有其他别的事情可以做了,没有任何其他的娱乐方式,没有电影院,没有电影,没有图书馆,但是有很多的书……我的母亲发现安静的孩子往往都很充实。“读你想读的……”所以没有什么书是我读不到或被禁止读的,我也因此比今天的孩子提早很多获准读了不少侦探小说。家里这类书很多,我父亲喜欢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我们家也有一些和生物学相关的书籍,以及连环画,这些我也读。所有我能找到的我都会去读……
波丽娜·盖纳:
您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写作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我在七岁的时候写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关于一只蚂蚁的故事,透过情节的发展,我得到的感悟颇多。因为在蚂蚁一生中的前三个阶段,它们几乎什么也没做:首先是一个卵,之后变成了幼虫,再然后是它们的幼年时期,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对一个七岁大的小孩来说,这已经是一段很长的插画故事了,但是这段故事直到结束了也没有任何情节。(她笑。)不该这样开始啊!所以我写了这个之后就停止写作,开始投入到绘画中。我涂涂画画,直到高中才开始一种肤浅的写作。十六岁时我才开始认真对待写作这件事。
波丽娜·盖纳:
怎样?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我宣布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这可把大家给吓坏了。“什么!”那是在五十年代的加拿大,见不到什么作家。加拿大那时当然是有作家的,但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不过我得到了一位高中老师的鼓励。虽然另一方面,我上学年的老师曾说过:“在我的班上,她没表现出任何特殊的天赋。”通常情况下,老师们是不会说实话的,他们会说“是的,他有一些天赋”,而她,她却说出了真相。我在我们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天赋。直到下一年,在另一位老师的班上,事情才有所改变。我们在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十七岁的我们要成熟得多。虽然中间只隔了两年,但却是关键的两年。我觉得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只是在玩乐。那时候高中是五年制,第五年决定了我们是否能继续上大学。这个体制跟今天法国的体制更像。而在这里,这项体制如今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当时,众所周知,高中的最后一年是很难读的,学年结束后所有人要挤在一间没有空调的体育馆内进行毕业考试。我们需要用功备考。
波丽娜·盖纳:
《道德困境》这部小说可以算是您的回忆录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除了主人公不是作家本人之外基本全是根据我的回忆写的。而书中英语老师的原型就是当年给予我鼓励的那位老师。
波丽娜·盖纳:
就是那位拥有一双美腿,穿着漂亮鞋子的女老师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就是她。因为她已经去世多年,我甚至在书中使用了她的真实姓名。当时老师们就是这样教我们英语的,对一些文章进行详细的讲解。这同时也是当时教授文学的方法。学习一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弄明白每一个单词的意思。
波丽娜·盖纳:
也就是说,是在那个时候,您表达了想要成为作家的愿望?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是的,是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最近对我说:“你那时候太勇敢了!你在午餐时间向餐桌上的每一个人宣布你将要成为一名作家,这是一件特别需要勇气的事。”
波丽娜·盖纳:
那对您本人来说这是个充满勇气的举动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一点也不。我过去并不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长期生活在森林里,我都不知道这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我最初的想法——在《与死者协商》的第一章里提到过——是当一名记者。我的父母都很紧张,他们找遍了整个家族(我们有一堆堂兄弟表姐妹)才终于找到一位干记者这行的,这位记者对我说:“如果你为一份报纸写稿,由于你是女性的缘故,你将只能负责那些专门给女人看的以及刊登讣告的版面。”好吧,我对自己说我可不能去干这个。当然,时代改变了,现在有无数女性活跃在要闻版块,而在那个年代,女记者被限制在和女性时尚以及死亡相关的页面。我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两大主题……(她笑。)因此,我想我只能进入大学教书,然后利用暑假的时间来写作了。我就这么进入了大学,而在大学里很快我就发现最棒的事莫过于逃到伦敦或巴黎,在那里,我可以更认真地创作我的作品。我有几位演员朋友去了伦敦,其中一位就是唐纳德·萨瑟兰,在同一时期,他和我一样也在大学。因为他比我大几岁,我看过他演的最初几部戏剧。他过去一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当时还有大卫·柯南伯格,但我那时还不认识他。我们这一代是有点奇怪的一代……之后我告诉自己必须逃离,逃到欧洲去做一个流浪汉,在当时,这比在纽约做一个流浪汉要容易:作为加拿大人,在英国入境对我来说要比在美国入境更容易。直到后来我的一位老师推荐我申请奖学金。当时正处在婴儿潮之后,大学教师不久后就要供不应求了,所以学校给我提供了奖学金让我去念硕士。
波丽娜·盖纳:
那时您就开始写作了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啊,是的!是的,亲爱的!十六岁起我就开始在一些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了。
波丽娜·盖纳:
一些短篇小说和诗歌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我们得还原一下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极少有出版社愿意冒发表加拿大作家作品的风险,他们更愿意找美国作家和英国作家,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家英美出版社一起分担成本。他们常说两句自相矛盾的话,一方面他们抱怨作品“没有加拿大特色”,另一方面又说“您的小说加拿大味太浓了!”。所以对加拿大作家来说,诗歌是最容易的。当时是咖啡馆的黄金时代,起源于旧金山的咖啡馆开始普及,在多伦多也有一家咖啡馆开张了,叫流浪者大使馆。很多人真的把它当成了大使馆,寄信过去申请签证!(她笑。)但实际上这只是一家咖啡店。上楼我们就到了一个四壁砖墙的房间,所有的家具都被刷成了黑色,桌上铺着桌布,放着一个插着蜡烛的瓶子,还有一台咖啡机,我们从未见过这玩意儿,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看它……每周四晚这里都会举办一场晚会,供大家朗诵诗歌,放爵士乐。一些最伟大的爵士乐手曾在这儿为我们表演过。
波丽娜·盖纳:
听起来棒极了。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有谁意识到了呢?我们那时都太年轻了,没意识到那究竟有多棒。我们只是想着:“啊,今天是周四了,有人要唱歌了。”在那个年纪,我们把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首先,我们认为这很正常,之后,又以为那样的时光会永远延续。但其实那只是短短的一刻,画着眼线,穿着黑套衫的“朱丽叶·格雷科【朱丽叶·格雷科(1927— ),法国歌手,演员】一刻”,属于存在主义的一刻。我们读萨特、加缪、波伏娃。太可怕了。(她从嗓子里发出愉快而讽刺的笑,谈话不得不暂停一会儿。)一切都沉浸在这种气氛里,那时正好处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之间。我当众朗诵我写的诗歌——或者不如说,我当众朗诵我那“灾难般”的诗歌。我还在一些小型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它们。一共只有五六首,有一首是写给流浪者大使馆咖啡馆的。那时候我们连电脑都还没有呢!嘘……我们都用铅字印刷机和油印机印刷作品,然后再把它们钉起来。就这样,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用亚麻油毡版画做的封面。
波丽娜·盖纳:
作为一名女性,在文学圈子里混是不是很难?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有点难。在加拿大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我觉得在美国才是真的很难,在那里,女作家完全被当作另类。那时,战争刚刚结束,写作完全是男人们的领域。诺曼·梅勒、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这些都是当时鼎鼎有名的大作家。战前有一些像卡森·麦卡勒斯这样的女作家,但到了那个时候,她们要么已经上了年纪,要么已经不在人世了。在美国,当一名年轻女作家被认为是很大胆的事情。我们被看作追星族,或是颓废派的小女朋友。但在加拿大,由于文学圈子很小而且独特,所以作家们都很团结。如果您是一名诗人,您就加入诗人圈,而不是别的……不过,我们偶尔还是会听到有人说“女人是不能写作的”,但这往往是上了年纪的男人的想法。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与之相反,我们互相帮助,组成一些编辑小组。阿南西出版社,如今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了,就是我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在一九六六年创办的。我们每人领一份政府发的微薄补贴,然后把这些钱放到一起创办了一家出版社。一共大概花了六百美元。我们当时也是迫于无奈,因为根本找不到任何其他出路。我们的出版社就这么发展起来了。后来因为小出版社的政策问题,我在一九七二年离开了:椅子越小,为得到它而进行的争斗就越激烈。最后,是我朋友格拉汉姆·吉布森的前妻当上了出版社的头,她想方设法把我们都挤走了!(她笑。)另一位创始人和我一起上了大学,后来,他在儿童文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波丽娜·盖纳:
请您跟我讲讲您第一部小说的出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可以吃的女人》?这是我一九六四年写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考试手册上的作品,当时每天早上八点半,我在那儿给工程师教语法,在一幢二战时期的农业建筑里,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当时很有意思。我在一张桥牌桌上写作,然后用手动打字机打出来——那时我还没有电动打字机。
波丽娜·盖纳:
您的作品《可以吃的女人》大获成功了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要说成功的话,那就是雅克把这本书卖到了英国和美国,对于一个二十九岁、没什么名气的作家写的处女作而言,这大概可以算某种成功吧。
波丽娜·盖纳:
那您认为哪本书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呢?是《使女的故事》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确切地说,成功指的是什么呢?它们都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毕竟成功是可以有多重含义的。很奇怪,《使女的故事》并没有一炮打红,它的际遇和《秧鸡与羚羊》《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类似。比如说销量都没有《盲刺客》多,可能因为这几本书比较另类。在英国,《使女的故事》卖得很少,后来就干脆停止销售了,但它获奖之后,又重新上架了,而且再也没下架过。在加拿大,也可以说是小获成功,因为之后也再没下架过。
波丽娜·盖纳:
而这本书可是一九八五年发表的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各国读者的反映都不一样,加拿大人说:“在我们国家不可能发生这种事!”美国人说:“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现在,书中描写的场景大多都已经在上演了。这本书已经被改编成芭蕾舞剧和歌剧,在丹麦、英国、加拿大等国已经上映了。您可以和约瑟夫·博伊登讨论这些——他也写过芭蕾舞剧——这本书跟美洲印第安人的寄宿学校有关,这些十九世纪出现的寄宿学校主要是为了同化印第安人,这使得这部剧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很快还会出一部绘本,也是从《使女的故事》这里得到灵感的,一部典型的法国连环画……我很喜欢《阿斯特里克斯和奥贝利克斯》,还有克莱尔·布勒特谢尔的《阿格里皮娜》。
波丽娜·盖纳:
您是怎么喜欢上连环画还有科幻小说这些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我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我们那代人都很喜欢连环画和科幻小说。四十年代,漫画铺天盖地,孩子们都很爱看漫画,那时候电视也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早上的时候会放电影,但没法去,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森林里。我哥哥收集漫画,如果您去蒙特利尔,那里有家叫“德罗恩&考特利”的很不错的商店,它同时也是一家连环画出版社,您可以去看看他们的网站。至于科幻小说,您想想,五十年代正是雷·布莱伯利经典作品发表的时期,约翰·温德姆,还有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我们有威尔斯的作品全集,我爸爸很迷他。同时还看一些讽刺作品,比如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企鹅岛》。我们还有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那时候我还太小了,以至于把它当成了维尼熊之类的作品……哎呀,好奇怪。我十一二岁的时候,《1984》的口袋本出来了,于是我就读了这个封面很丑的版本。这些书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还看了一些别的类型的书,比方说亚瑟·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实际上,这是历史类的书,但我却把它当科幻小说来读,因为我对俄国不太了解。后来我还重温过……所以说,我什么书都读。中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个阅读俱乐部,注册之后可以每个月借一本书。还有现在每天晚上都能在电视上看到的B系列,那个时候会在电影院上映。您随便说一部,我当年应该都看过,有的十分有趣,有的不如说有点恐怖。那是俄国文化来势汹汹的年代。
波丽娜·盖纳:
但这跟您写的东西完全是两回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是的,我不擅长写这种题材。但是在《盲刺客》里,我书中写的就是这种故事,那是三十年代流行的文学。
波丽娜·盖纳:
而且故事很棒。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那个年代,没有人真的关注这些作品,它们属于副文化,但是我挺感兴趣的。我认为文学总是随着时代发展的,崭露头角的新文学形式大都经过了从大众文学进入到正统文学的过程。即使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古典戏剧,如果没有古希腊神话,也就是那些脍炙人口的传说作为基础的话,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有个老师是诺思洛普·弗莱,如果您去看他的文学理论的话,您会看到他说作品的主题并不是区分流行文学和其他文学的标准,故事周围的那些因素才是,因为情节大同小异。我尤其对形式感兴趣,我在哈佛一直没写完的论文,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不过是讲十九世纪的。您可以随便问我任意一本您曾听说过的十九世纪的奇怪的小说……您看,您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对儒勒·凡尔纳了解这么多了吧!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儒勒·凡尔纳是当代这类文学的两个分支,儒勒·凡尔纳写的都是些可能会发生会实现的事,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是全新的创造。有一天,儒勒·凡尔纳愤怒地喊道:“他那是瞎编乱造!”而他自己谈论的是氢气球和潜水艇,都是些正在酝酿发明的东西。
波丽娜·盖纳:
在叙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无非是人物、情节、故事的铺垫。
波丽娜·盖纳:
您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当然是从一些废纸上没有意义的涂鸦开始的。
波丽娜·盖纳:
您写提纲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不写。我尝试写过一次,真是太失败了,后来再也没写过。
波丽娜·盖纳:
那是哪本书?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是一本我从没写完的书。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那是一部糟糕透顶的作品。我想表现得有条理一些,因此我写了一些小卡片,有八个人物,共五个部分,每个人物在每个部分里有一小节内容,所以一共有四十个小节,我对每个人物都了如指掌,他们穿的什么鞋子,早餐吃的什么,他们受的教育,他们的父母,这大概就写了有两百多页吧,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有点像我写的那本跟蚂蚁有关的小说。(我们都大笑起来。)就像我跟我的学生们说过的那样:“在一部侦探小说里,一开始就要死人,不然的话,你就会失去你的读者。”对于一起神秘谋杀案而言,一定要尽快安排一场谋杀,或者至少要有一个诸如此类的开场:“克莱尔不知道自己今天会遇害。”
波丽娜·盖纳:
您写作的程式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套路?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没有,理论上说,我是应该有一个。其实我也很希望有,但事实上我并没有。
波丽娜·盖纳:
从来都没有过?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从来没有,不过生活一直在改变……可能我会去尝试吧。
波丽娜·盖纳:
当您开始写一部小说,大概需要多久能写完?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这说不准,《使女的故事》大概写了七个月,《盲刺客》写了好几年,我开了几次头,又把它扔了。
波丽娜·盖纳:
为什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亲爱的,因为写不下去了啊。
波丽娜·盖纳:
您是怎么知道就行不通了?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噢,会知道,知道或许哪条路都行不通。声音不对,总找不着合适的人来讲故事。
波丽娜·盖纳:
您一开始是从哪个角色开始下笔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我一直都知道这会是一位老妇人的回忆。我想把上世纪最本质的东西梳理梳理。我希望这个老妇人是我母亲或者祖母那一代人。我对她们十分了解,她们的衣橱(她笑),她们的经历。我刚开始是从这个已经去世的老妇人的一个年轻的亲戚开始写的,这个年轻的女孩发现了一个装满信的盒子。很老套的桥段。然后我对自己说:“太没劲了。”于是我放弃了,又重新开始。这次呢,这个老妇人还活着,有两个年轻人对劳拉的事情存疑并且展开了调查,这次不是从一个盒子,而是从一个行李箱开始的。但这次里面放的不是信,而是一本相册……我继续写下去。不幸的是,这两个年轻的记者相爱了,并且打算私奔,然而男方已经结婚了,并且才有了一对双胞胎。这离故事主线已经太远了,我都不知道该拿这对双胞胎怎么办才好了!于是我又重头再来,这次我让我的老妇人自己讲故事了,相册的情节我保留了一点。
波丽娜·盖纳:
您想用这个故事表达什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受好奇心的驱使,您走进一个故事。您想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先您并不知道您自己将要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才能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没办法写提纲。不过我如果写侦探小说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埃德加·爱伦·坡说得很有道理:侦探小说是倒过来写的。您需要知道是谁做的,不然的话就不能一直布下线索,以便在读者找到正确答案之前,引他们误入歧途。
波丽娜·盖纳:
为了写《盲刺客》,您对世纪初的多伦多做过很多调查研究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大部分的事情我原本就知道,但我一般写完后都会再去验证一下。如果您在写作前做太多的调查会很容易陷进去。我都是从我知道的开始写起,然后再去验证。我做了最多研究的书是《别名格蕾丝》,因为我要知道谁是托马斯·金奈尔,比方说我得知道他多大年纪,我找到了两个托马斯·金奈尔,一个四十多岁,一个已经七十二岁了……这肯定不可能是同一个故事。我又去苏格兰找相关的信息,还拜托了别人帮我去搜寻文件,最后在教养所找到了一些案件报告……我的原则就是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我就没有权利去修改它。幸运的是,大家对这件事都不太了解,就跟对辛普森杀妻事件一样迷惑。他们对格蕾丝·马可【作品女主角,十六岁时被判终身监禁】的发色都不能确定。
波丽娜·盖纳:
那些地点呢?比方说《盲刺客》中的提康德罗加港,是真实存在的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这是三个不同城市的拼凑,一个是安大略港,另外一个是一座有险滩的城市,而采石场来自第三座城市。也就是说,在安大略南部画一个圈的话,这三所城市您都能找到。
波丽娜·盖纳:
您觉得词语的读音重要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极其重要。
波丽娜·盖纳:
您会大声读文章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会,在英语里面,人们一般想避免的是s这个发音:Sary sells sea shelves by the sea shore,she’s sad……然而英语里面总有大量的s,写作时就必须得当心,因为人们一般不喜欢一个句子里有大量的叠韵。
波丽娜·盖纳:
谁是您的第一个读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这得根据书来。我更希望有一些纯粹的读者,也就是不属于文学圈里的。当我把书寄给我的编辑时,他总是说棒极了——他也不能说别的,这毕竟是他的工作嘛。但我还是更希望有人跟我说:“这书写得不怎么样。”
波丽娜·盖纳:
您做大量的修改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是的,我会大量修改。
波丽娜·盖纳:
您会去读那些评论文章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我对于批评的态度是:如果非要读的话,就在作品巡回活动结束后再读。这样的话,当有人问起:“您对这篇糟糕的评论怎么看?”你就可以直接说:“啊?我没读过。”特别有用,事情就了了。回应批评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批评只是个人观点。你也不能跟别人说:“您的观点糟糕透了。”如果事情真的是弄错了,那另当别论。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回应就是解释你自己的书,这不是作者该做的。书是写给读者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阅读感受。同样,每个演奏者都会对同一首奏鸣曲有不同的诠释。有很糟糕的小提琴手……而且就算都是优秀的音乐家,诠释的方式还是会有所不同。
波丽娜·盖纳:
是否有过一篇评论文章完全改变了您的某部作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那都为时已晚,不是吗?
波丽娜·盖纳:
但是这会不会导致您对自己的作品产生质疑呢?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不会,我觉得不会。文学批评一直都是个人见解。您看双人花样滑冰吗?为什么在评分时总会产生如此多的分歧?假设两个人中有一个摔倒了,毫无疑问,大家都看见了,这是个明显的失误,但要是没人摔倒呢?所有参赛选手都完整地演绎了他们艺术编排的内容,完成了规定动作,甚至连三周半跳都做到了,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服装,自己的特色,但是他们的分数不一样,为什么呢?什么才是“好”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主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艺术很有趣的原因了。在田径赛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看出谁赢了,但是服装和风格就是两码事了。您是更喜欢巴洛克风格呢,还是古典主义风格呢?
波丽娜·盖纳:
您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作吗?这种内在的需求是什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您对梅维斯·迦兰有所了解吗?她是位了不起的加拿大女作家,她目前的情况不太好。[就在这次访谈结束几天后,小说家梅维斯·迦兰在巴黎去世。]她对“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太晚了,已经停不下来了。”(她笑。)萨缪尔·贝克特说:“我只会写作……”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成为歌手或者经纪人的原因,因为现在要开始已经太迟了,而且也没有那方面的天赋。为什么我会坚持写作呢?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它很有趣,如果有一天我对它不感兴趣了,我就不写了。
波丽娜·盖纳:
您能够想象没有写作的生活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啊,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原因让一位作家放弃写作,那就是当我们感到快要失去它的时候。
波丽娜·盖纳:
您曾经遭遇过写作危机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像一只迷宫里的小老鼠一样,你觉得总有某个地方会有奶酪。你从这个隧道出来,没找到奶酪。你回到出口,重新进入另外一个隧道,还是没有奶酪。尽管如此,你也知道里面一定有奶酪,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找到它的希望。你继续找,找遍另外一条隧道,依旧什么也没有,你继续走着,找着,一遍又一遍。所以说,是的,我也有过一些停滞不前的经历,就像我之前跟您提到过的,我重写《别名格蕾丝》的过程。我是在法国写的,那时候正值学校放假,我准备去巴黎看看,火车上全是大吵大闹的小孩子,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刚写完的一百多页毫无意义,我得把它们扔了。这时候,我的偏头痛犯了,哎呀呀!(她笑。)所以必须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办。我们需要重新开始并且去寻找解决办法。现在我正在写一个故事,大概写了五十页吧,三天前,我意识到真正适合它们的地方是垃圾桶。但我知道奶酪就在那里,只是需要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而已。
波丽娜·盖纳:
您从未放弃过找到奶酪的希望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是的,从未放弃过。虽然我最终放弃了一些书,而当时我已经写了两百多页了。实在是行不通。这两本里面,有一本我只保留了其中的一个句子,另外一本,我把里面两个片段变成了两篇短篇小说。第一本就是人物过多,而且是在我热衷于写“小卡片”的时期写的,这种方法不适合我。第二本的故事发生在太多不同的时期。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是在英国写的,在夏天租给度假者的一个小屋里,而当时是冬天。地是石头铺的,有一个壁炉,但我生不了火,一个电炉我不知道怎么用。之前的房客留了一堆通俗小说。于是我开始看书。大多数都是关于苏格兰王后玛丽的。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些书比对我正在写的小说更感兴趣……于是马上我就出发去了柏林,我在那里写了《使女的故事》。有时候,要懂得割舍。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次练习,或消磨时间。不过写作就是这样,该放手的时候该懂得放手。
波丽娜·盖纳:
您一直教书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断断续续,类似客座的。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教人阅读作品开头的几段。各种开头。
波丽娜·盖纳:
在结冰的人行道上小步往回走的时候,我们谈论生态,她最关心的主题之一。路上铺满了前一场暴风雪打落的树枝。孩子们和我们会合,他们从渥太华皇家博物馆出来,突然对物种的灭绝变得敏感了。在宽敞的屋子里,晚饭的餐桌已经摆好。玛格丽特的女儿,一位迷人的画家,正和作家的助手闲聊,后者说话就跟机关枪一样。摄影是在一间紫色的客厅里进行,等待的当儿,我们随手翻翻《奥斯特利克斯和奥贝利克斯历险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