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福楼拜的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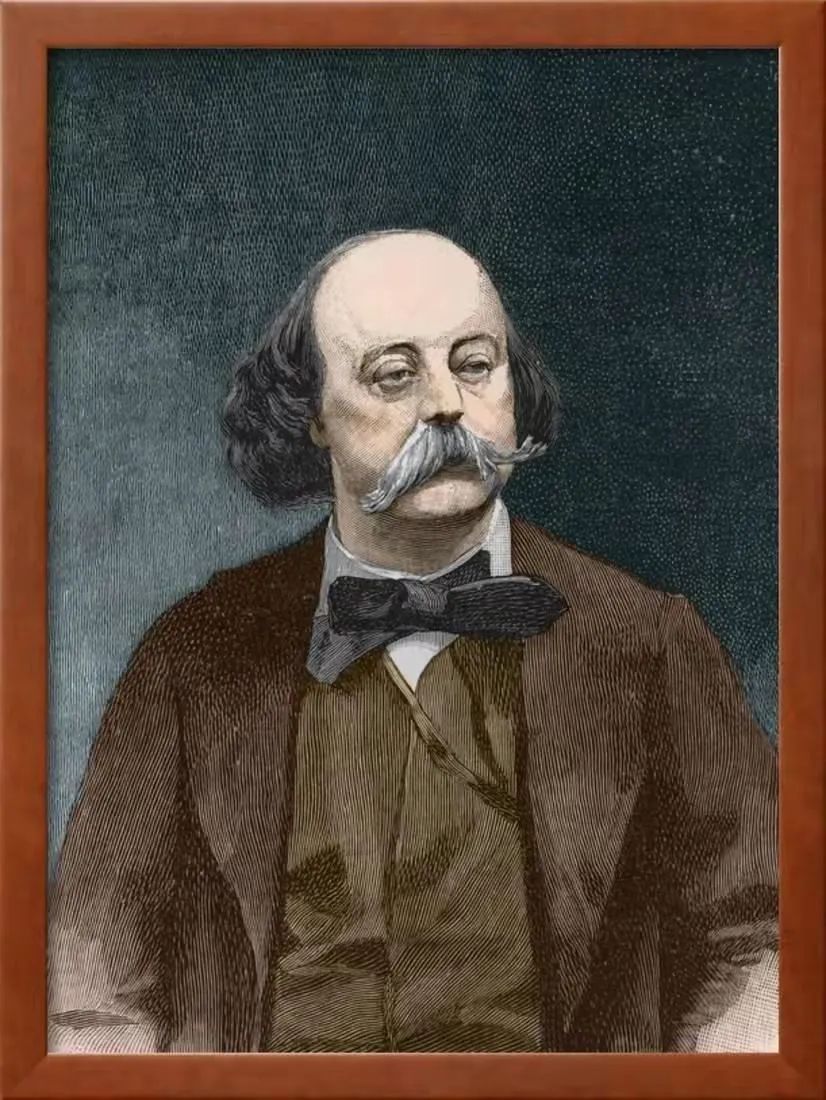
一
福楼拜是公认的文体家。说是“公认”,是鲜有例外的意思。有名的例外,普鲁斯特算一个,他说,“福楼拜不是文体家”。对此,蒂博岱评述道,普鲁斯特所谓文体,是语法意义上的,这牵扯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场争论,此处不赘。何谓文体家?汉语词典上一般不列为词条,但大多数谈文学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所谓文体家,就是注重和讲究文章风格的人,所以有“文学家不尽是文体家,文体家是文学家最高的荣誉”的说法流行于世。福楼拜无疑是一个注重和讲究文章风格的人,他不是一般地注重和讲究,而是苦吟,是纠缠,是摸爬滚打,是呕心沥血,是宗教般地追求词句之美的人。他的风格是自然流畅,真实客观,不容冗词赘语,起承转合,了无痕迹,通篇澄清无滓。这种风格是连贯的,袅娜多姿的,“珠子再多,也不成项链,关键在串珠子的丝线”,而这丝线就是句子,是连接整篇文章或整部作品成为一个整体的一个个句子。福楼拜是造句的大师。他的弟子莫泊桑对乃师了解得既深且透,他说得好:“他有这种绝对的信仰;就是表现一切事物只有一种样式,一个字说,一个形容词形容,一个动词激发,所以不辞超人的劳苦,他为句子来发现这个字,这个形容词,这个动词。因为他相信一种表现的神秘的谐和,一个正确的字他要是觉得声音有一点不调和,他会用一种极端的忍耐再去寻找一个,明白他手边不是那真实的,唯一的。”李健吾先生在《福楼拜评传》中引用了莫泊桑说的话,并总结道:“创作是他的生活,字句是他的悲欢离合,而艺术是他整个的生命。”这是对福楼拜一生的概括,精准而贴切,一语中的。字句,在别人,是生命的装饰,在他,是生命的存在。义足为句,一个句子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一个段落,一篇文章,一部作品,全赖这种独立的句子组成,它像一根丝线串连成一整幅图画。句子的作用可谓大矣!
二
一个好的句子值得福楼拜一生的努力。什么样的句子是好的句子?1844年6月7日,在给路易·科姆南的信中,福楼拜说:“我喜欢的是刚劲有力的句子,是内涵丰富、明白易懂的句子,这种句子仿佛筋肉突出,有茶褐色的皮肤。我喜爱雄性的句子,而不喜爱雌性的句子,比如,常见的拉马丁的诗句,和更低级些的,维尔曼的句子。”他在《包法利夫人》中写道,爱玛“由着自己滑入拉马丁的蜿蜒细流,谛听湖上的竖琴、天鹅死时的哀鸣、落叶的种种响声、升天的贞女和在溪谷布道的天父的声音,拉马丁的“蜿蜒细流”说的是他的一些忧伤绝望的一唱三叹之作,是典型的“雌性的句子”,他不喜欢。八年之后,即1852年6月13日,在给路易丝·科莱的信中,他用不同的形象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我喜欢清晰的句子,这种句子站得直直的,连跑的时候都直立着。这几乎不可能做到。散文的理想已达到闻所未闻的困难程度;必须摆脱古体摆脱普通词汇,必须具有当代的思想却不应有当代的错误用语,还必须像伏尔泰的东西一样明快,像蒙田的东西一样芜杂,像德·拉布吕埃尔的东西一样刚劲有力,而且永远色彩纷呈。”他用人体比喻句子,血肉丰沛,动作灵活,在任何情况下都腰挺背直,活脱脱一副健美的模样。刚劲,有力,清晰,明快,芜杂,雄赳赳,气昂昂,并且色彩纷呈,洋溢着阳刚之气,这是福楼拜对句子的要求。所以,他喜欢的句子绝不是表面光鲜而内容空洞的所谓金句或警句之类,而是内容丰盈而形式完美的、并与其他的句子形成和谐整体的句子。
福楼拜要求“分句和复合句的和谐”,不无骄傲地说:“耗尽毕生的精力斟酌字词,整日价辛辛苦苦修饰各个分句以求形式完美的复合句,这是怎样滑稽的怪癖!”他不允许他的句子有“不和谐或重复”的部分,他说:
“人在写关于自己的东西时,一气呵成的句子可以是精彩的句子(抒情性顺着天然的倾向很容易产生效果),然而却缺乏总体的协调。重复比比皆是,还有大量的重述、陈词滥调、平庸的词组。相反,人们在写想象的事物时,一切都必须来自构思,哪怕一个小逗点都取决于总的提纲,作者的注意力便自动转向。即不能失去广阔的视野,同时又要观照自己的脚下。写细节最是酷刑,尤其在大家像我一样喜欢写细节的时候。珍珠组成项链,但穿成项链的是线。然而,用线穿项链又不丢一颗珠子,另一只手还要一直拿稳线,那可得使出全部的解数。”
既要整体的和谐,又要细节的正确,难矣!然而福楼拜做到了,不仅单个的句子要和谐,句子与句子之间要和谐,整部作品与具体的细节要和谐,人物与人物、与周围的环境也要和谐。李健吾先生说他这样描写“一位多感的少妇,听见了晚钟,对着晚钟抑扬之中的暮景,心中兜起无可奈何的愁怅”:
正当四月初旬,樱草开花,一阵煦风吹过新掘的花畦,花园如同妇女,着意修饰,迎接夏季的节日。人从花棚的空当望出,就见河水曲曲折折,漫不经心,流过草原。黄昏的雾气,在枯落的白杨中间浮过,仿佛细纱挂在树枝,却比细纱还要发白,还要透明,鸿蒙一片,把白杨的轮廓勾成了堇色。远处有牲畜走动,听不见脚步响,也听不见叫唤。钟总在响,安安静静,哀号似的,在空中一直响个不停。
人与周围的环境和谐无间,加上词句的轻柔恬静,好一幅惆怅而略感忧伤的图景!“福楼拜用词类(例如动词、接续词等等)复兴了法国文学的生命”,普鲁斯特如是说。
福楼拜要求文句如音乐般和谐,声音如天籁般纯洁,他说:“在我眼里,世界上只有美妙的诗句,只有组织得精彩又和谐、又富于歌唱性的句子,绚丽的日落,月光,色彩丰富的画卷,古代的大理石雕像,雄浑有力的头像。”英国作家毛姆如此评论福楼拜:“他尽量不使自己(像乔治·穆尔在后期著作中那样)被韵律束缚住,而是尽量使韵律多样化。他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能在用词的同时考虑到语音的效果,能使他写出来的句子给人以快速或者缓慢、倦怠或者紧张的感觉。事实上,他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表达出任何情绪状态。”在词句上,犹如在音乐上,“最美而且最珍贵的,是声音的纯洁”,他不能容忍的,是用词的逼仄,不清爽,有毛刺。辉煌的日落,清幽的月光,如此感觉上的对比显示出不同的句子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李健吾先生指出:“一本书对于他就是像一个宏大的合奏曲,错综然而自然,繁复然而单纯。一本书如此,一章如此,一段或者一句也如此;单独来看是一幅画,例如《包法利夫人》里面的农产品改进竞赛会,然而前后来看,忽正忽反,忽雅忽俗,忽而喧嚣,忽而唼喋,上下起伏,正是一片音乐。”他在1876年4月3日给乔治·桑的一封信中说:“是不是一本书,离开它的内容,能够产生同一的效果?在组合的准确里,成分的珍贵里,浮面的光滑里,全盘的谐和里,难道就没有一种内在的品质,一种神奇的力量,原理一样永久的一种东西(我像伯拉图说话?)那么介乎正确的字和音乐的字之间,为什么会一种必然的关联?为什么人一紧缩思想,总可以写出诗来。难道音节的法则统制着情感和意象,而所谓外在也就是内在?”正确的字和音乐的字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这是福楼拜毕生坚持的观念。
福楼拜1857年7月13日写信给夏尔·波德莱尔,对《恶之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盛赞它的“句子满蕴着思想”。十年前的1846年9月18日,他给路易丝·科莱写的信中,就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对我来说,在一定的句子里,只要没有给我把形式和实质分离开来,我都会坚持认为这两个词是毫无意义的。没有美的形式就没有美的思想,反之亦然。”一个月之后(1847年10月),他又说:“我时刻挂在心上的文笔问题使我极度不安。我对自己十分气恼,而且忧心如焚。有几天我为此而生病,夜里还发过烧。我越写下去,越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表达思想。”他对句子的挑剔,源于他对表达思想的苛求。然而,思想不能强加于句子,也就是说,美的句子自然包含着美的思想,美的思想自然蕴含在美的句子中。思想,并不是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对某一事物的看法,而是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是大自然的真实,所谓“天地不言,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他在小说创作中提出了客观性,排除自我,不流露感情,不发表议论,不让一字一句显露出作者的观点和意图。“激情成不了诗,……你对某一事物感受越少,你越有能力把它照原样(照它一贯的样子,本身的样子,它的一般状态,即摆脱了一切昙花一现的偶然成分的状态)表达出来”,这就是他眼中的句子和思想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信中说:“我认为精彩的,我愿意写的,是一本不谈任何问题的书,一本无任何外在捆缚物的书,这本好书只靠文笔的内在力量支撑,犹如没有支撑物的地球悬在空中。这本是几乎没有主题,或者说,如果可能,至少它的主题几乎看不出来。最成功的作品是素材最少的作品;表达愈接近思想,文字愈胶合其上并隐没其间,作品就愈精彩。”所谓“不谈任何问题”,“几乎没有主题”,“素材最少”,说的是没有宏大的事物,作品只谈平常生活中的平常事,这样的作品才是精彩的作品。平常的句子,平常的思想,二者的结合才能焕发出不平常的光彩。
综上所述,福楼拜的心目中,好的句子应该是:具有阳刚之美的句子,整体与细节之间的和谐的句子,准确的字与音乐的字之间相互关联的句子,句子与思想相互依存的句子。
三
福楼拜在1852年6月26日给马克西姆·迪康的信中说:“我宁肯像狗一样死去,也不肯提前一秒钟写完还没有成熟的句子。”他的创作实践证实了他的誓言:《包法利夫人》写了五年,《情感教育》从初稿到定稿相距二十四年,《圣安东尼的诱惑》三易其稿,历时二十五载,《萨朗波》写了五年,短篇小说集《三故事》译成中文七万字,却整整花了他一年半的时间,1874年开始写作《布瓦尔与佩库歇》,直到1880年去世,遗憾地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杰作,他的确是把作品写到了尽善尽美、无可挑剔的程度,其中字斟句酌、安排位置占了很大的成分,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他意识到一个完美的句子是一件作品的开始,它像一个自然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支撑,只是艺术家看待事物的独特的方式。他说:
依我之见,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最困难之处)既非令人发笑或哭泣,也非让人动情或发怒,而是像大自然那样行事,即引起思索。因此一切杰作都具有这个品质。它们看上去很客观,但却颇费琢磨。在写作手法上,它们像峭壁一般巍然屹立,像海洋一般波涛汹涌;它们像树木一样叶满枝头、苍翠欲滴、喃喃细语,像沙漠一样苍凉,像天空一样湛蓝。我感觉荷马、拉伯雷、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歌德似乎显得冷酷无情。那是无底的、多边的、多重的。从小孔可以窥见悬崖,崖底漆黑,令人晕眩。与此同时,却有某种异常清淡柔和的东西超然笼罩着总体!那是辉煌的光彩,是太阳的微笑,那是宁静!是宁静!
这一段话透露出他的浪漫主义情怀一直存在到中年,支配着他对法国散文的认识:“散文是一种非物质的艺术(它对感官影响不大,它缺少引起快感的一切因素),它需要塞满东西而别人还发现不了。”散文要塞满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一个个的句子;这一个个的句子要塞满的东西,正是峭壁、海洋、树木、沙漠、天空、悬崖、光彩、太阳等等,人们看不见却需要艺术家接不上气也要追求的东西。这就是福楼拜毕生狂热而始终不渝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得到了他所追求的东西了吗?他被称为文体家,“堪称世上最诚实和最值得敬仰的艺术家”(瓦莱里语),看来他是得到了。他是如何得到的呢?换句话说,他是如何处理他的句子呢?
四
首先是构思,构思的有无和精粗,决定着句子的成败。福楼拜在1852年1月31日写道:“自己脑子里还很模糊,怎能表达得很清晰。起草,划掉,趔趄,摸索。现在或许有点头绪。”1852年9月13日,他说:“在下笔之前,你应该思考再思考。一切取决于构思。伟大的歌德的这句至理名言是最简单、最令人叹服的概括,而是一切可以接受的艺术作品的箴言。”一年以后,他又明确地说:“假如你拼命地寻求某个句子结构或某个表达方式而不得,那是因为你没有构思。形象,或者脑子里非常明确的观念,必定会把字句带到你的纸上。后者产生于前者。构思周全的东西,等等。”清晰的思想产生于周全的构思,正如布瓦洛在《诗艺》中所说:“构思周全的东西陈述也明确。”程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句子的手艺》,文中说:“句子的构成事关思维的构成,事关你观察世界及其关系的独特角度。一个作家之所以写不好句子,是因为他的思维不够清晰,还没有学会如何以他自己的角度观察世界以及世界万物之间无形的关系。”诚哉斯言!不过,我还要加上一句,句子事关表达他的感情的细腻还是粗糙之程度,因为福楼拜曾经说过:“情感的衔接使我痛苦万分,而这本书的一切都取决于此;因为我主张既可以同各种思想玩游戏,也可以同各种事实玩游戏,但要做到这点,必须是一种思想引出另一种思想,如同一个瀑布流到另一个瀑布,还必须让那些思想如此这般把读者引到句子的震颤当中,引到隐喻的激奋情调里。”“句子的震颤”,他又说到句子,可见,句子的作用不可小觑,决不是简单还是复杂、委婉还是直接、朴素还是华美那样简单与直观。
向古典作家学习,经常阅读他们的作品,以至于烂熟于心。福楼拜提到的、他经常阅读的古典作家的名字有荷马、拉伯雷、蒙田、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歌德、雨果等,他说:“必须背熟大师们的东西,狂热崇拜他们,尽量像他们那样思想,然后永远同他们分开。”敬仰的心思要有,但是不能成为任何人的奴隶,要保持独立的品性。因此他又说:“我在这里冒险提出一个我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不敢说的主张,那就是伟人们的东西往往写得很糟糕。——对他们来说,这更好。不应该从他们那里,而必须从二流作家(贺拉斯,拉布吕埃尔等)那里寻找形式的艺术。”他的这种说法的确有些“冒险”,我们不是要从大师们手上学习一切东西吗?为什么要从二流作家那里学习“形式的艺术”,即“句子”的艺术呢?我们看一看他的另外一番话就豁然开朗了:
还有什么比拉伯雷、塞万提斯、莫里哀、雨果的许多作品架构得更差劲的东西?然而,那是怎样骤然打来的拳头!单单一个词就有怎样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把许多小石头一个一个垒成自己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也顶不了他们的百分之一,而他们的金字塔却是用整块的石头建造的。但想模仿这些人的创作方法,那会使自己迷失方向。他们之所以伟大,反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方法。
大师着眼的地方都是广大宏阔的星辰大海,具体的操作则是二流作家的看家本领,所以个人的操守和行动的做法,要到不同的人那里去寻找。福楼拜说:
就我个人消磨时间而言,我喜爱的是给人的感觉不那么愉快的天才,这种天才对人民显得更倨傲,更与世隔绝,他们的举止更加豪迈,趣味更加高尚,或者说唯一的一个可以替代其他所有人的人,我的老师莎士比亚……我一读莎士比亚的书就会感到自己变得更高尚、更聪明、更纯洁。每当我攀登上他作品的高峰时,我仿佛登上了一座高山。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出现了。人已经不再是人,他成了眼睛。全新的地平线突然冒了出来,远景伸展开去,无边无际;人再也想不出自己曾在那些几乎辨认不出的简陋小屋里生活过,想不出自己曾喝过那些看上去比小溪更小的河流里的水,曾在那些密密麻麻、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辗转、焦虑,而且是他们中的一员。
因阅读大师而净化了心灵,开扩了胸怀,提高了境界,这种快乐促使他写下了美好的句子:“有时,我觉得那些诗句激起我的热情仿佛使我成了与诗人同等的人,使我升华到了他们的水平。”
福楼拜不是那种文思泉涌的天才,他拥有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文体家,完全是靠呕心沥血的艰苦努力,“靠耐心和苦功,才去掉肥肉,长点筋骨”。他的《包法利夫人》写的很慢,很苦,他在信中说到他的写作:“《包法利夫人》进展不快,一个星期写了两页”;“四天写了五页”;“这一个星期写了三页”;“六个星期写了二十五页”,等等。他写《包法利夫人》,仿佛“在一片没完没了的烂泥地里行走,烂泥不断增加,我得不断清扫”。他写得慢,其重要原因在于他要修改他的句子。他坚信“头发越梳越亮。文笔也如此,修改可以使其有声有色”。他写信给路易丝·科莱,劝她修改她的小说:“我恳求你,修改它们。别放过任何东西。修改本身就是件作品。你还记得沃维纳格那句名言吗:‘修改是大师们的釉彩’。”福楼拜所说的修改绝不是修修补补,将句子弄得光鲜漂亮,而是“努力寻找表达他们思想的准确词组”。他有时因为“写得太精细,抄了又抄,变了又变,东改西改,眼睛都发花了”,例如,1853年9月30日,他写信说:“今晚,我又根据一个新提纲写我那该死的一页——折纸彩色灯笼——了,为这一页我已经写了四遍。”为什么要写四遍,那是因为要反复地修改,一直到眼睛发花。他要为完成体过去时、未完成体过去时、现在分词、过去分词、代词、前置词、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分句、复合句等做出完全新的、个人的运用,甚至改变了法国语言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福楼拜的修改导致了法语句法的某些改变,他不愧为文体家、“作家中的作家”。
李健吾先生在《福楼拜评传》中,引用《龚古尔日记》中高地耶的话评论道:“我们抓不住福楼拜的文笔,这有时太为他自己一个人了,因为一本书不是写来预备高声念的,而他朗诵自己的书给自己听。在他朗诵的句子里面,有些他觉得谐和,然而这必须像他那样念法,才能得到他朗诵的效果。”福楼拜不但把自己的作品朗诵给自己听,还给他的朋友听,例如路易·布耶。他在信中说:“这二十五页写得真艰苦呀。明天,我要读给布耶听。”布耶的意见,将决定这二十五页的命运。我国唐代诗人杜甫有句曰“新诗改罢自长吟”,说的是锤炼字句,反复修改,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以求作品和谐流畅,顺嘴顺耳,能感动人。古今中外,皆是一理,然而,福楼拜不仅读给自己听,还要读给别人听,听取别人的意见;不仅用普通的音调,还要高声诵读。他的朗诵要求分句与复合句衔接得自然,避免字句的重复以及含义的肤浅,等等,他在1876年3月10日给乔治·桑写信,说:“你指责我追求外在的美,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方法。当我在我的句子中发现不和谐或重复时,我就知道我肯定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亨利·特罗亚在《不朽作家福楼拜》中写道:
为了保证情节的顺利进展,福楼拜的写作方式是做严密准备。写出文本之前,先用电报式文字记下大纲。各部分在更具体的概要里加以发展。有了概要,就起草稿,顺着文思,放任写去。草稿出来后,再去芜存菁,平衡内容,筛选也很艰巨。存精存下的草稿,再逐字推敲,精雕细琢,不厌其烦,到一天结束,能抢救出几句好句子,便感到不胜欣慰。这些句子,他在寂静的书房里,用洪声大嗓来回诵读,经得起“狮吼龙吟”的,才算写定。不然,就发狠锤锻,直改到铿锵顿挫,音节谐和。这文字杂技耍得筋疲力尽之后,散文的奇迹出现了,读来觉得既自然又清通。
这段文字,如若加上“在寂静的书房里还有路易·布耶在”,那就更加完整了。福楼拜给自己、给友人诵读自己的作品,检查其不完美,的确是他独有的方法。
构思,求教,修改,诵读,是福楼拜获得他心目中的好句的四门功课。
五
对句子的尊崇,实现这种尊崇的方法,最终的目的乃是“写得恰如其分”,正如福楼拜在1853年3月31日的一封信中所言:
我们为路易十四时代那些老人感到惊奇,但他们并不是了不起的天才。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你并没有那种惊叹不已的感觉,没有!他们只让你相信他们身上有一种超人的气质,就像你阅读荷马、拉伯雷,尤其是莎士比亚一样。但他们有怎样的良心!他们在当时怎样努力寻找表达他们思想的准确词组!他们在怎样工作!做了什么样的涂改!他们相互间作过多少咨询。他们多么擅长拉丁文!他们阅读多么慢!因此,他们的全部思想都在他们的文章里,这个载体之充实和丰满,真到了要炸开的程度。但,那里没有程度之分:好的就是好的。
他们慢慢地阅读,努力寻找准确的词组,修改句子,相互咨询,等等,只是为了“好好地想”,“好好地写”。李健吾先生说的好:“必须好好地写,正因为文笔的造型性不像整个观念那样广大。语言没有那样复杂,那样飘忽,那样难以抓住,那样柔顺可人……我们有过多的事物,过少的形体。所有艺术家的磨难,都在寻求‘恰到好处’的形体。”“单字的追逐”,“和字奋斗”,“在词句面前断气”等等,说的都是福楼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写得“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好好地想,好好地写,乃是福楼拜毕生的追求。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年第5期,“重读”专栏,责任编辑萧莎,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