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2022年度“文学之星”获奖名单
自中国作家网原创平台开通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可以让原创作者自由成长、积极交流与充分展示的平台。2022年3月22日至5月22日,继2021年成功举办小说征文大赛之后,再次举办原创频道征文(散文)大赛;同月,为了进一步打通作者、互联网平台与文学刊物间的交流通道,实现优质资源共享,中国作家网与《天津文学》《诗选刊》《散文选刊》《梵净山》《大江文艺》等多家刊物陆续开展合作,定期向刊物推介原创频道的优秀作品。
这些举措收获了许多读者的认可,中国作家网原创平台的规模也在逐步平稳扩大,2022年平台新增原创注册用户1万6千余人,共收到投稿12万余件。通过优选这些海量作品,我们一共推出了49期“本周之星”,作为原创平台的品牌栏目,我们希望“本周之星”能鼓舞广大写作者更加积极踊跃地参与原创写作中。为此,我们从2022年总共49期“本周之星”中,评选出17位中国作家网2022年度“文学之星”,分别授予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并颁发获奖证书。
中国作家网2022年度“文学之星”获奖名单
| 作品名称 | 作者 | 体裁 | |
| 一等奖 | 寒葱河 | 陈华 | 小说 |
| 二等奖 | 临水而居 | 叶青才 | 散文 |
| 大地是铺展开来的唐卡(组诗节选) | 惠永臣 | 诗歌 | |
| 阿黑离家以后 | 《群岛》 | 小说 | |
| 三等奖 | 诗十首 | 阿未 | 诗歌 |
| 从长安出发·甘南行记 | 释一尘 | 散文 | |
| 虫子的忧伤 | 钱金利 | 散文 | |
| 柿子树下 | 卢仁强 | 小说 | |
| 糖 | 路嘉 | 小说 | |
| 优秀奖 | 拍甲鱼 | 许起 | 小说 |
| 宗角禄康(外一首) | 嘎代才让 | 诗歌 | |
| 盐湖笔记 | 陈登 | 诗歌 | |
| 月光的疼痛(组诗) | 弋吾 | 诗歌 | |
| 虫儿飞 | 李汀 | 散文 | |
| 花花鸟儿绿翅膀 | 刘玉红 | 散文 | |
| 慢慢灌浆的生活 | 蒋康政 | 散文 | |
| 指尖上的红 | 陈伟芳 | 散文 | |
获奖者介绍:
一等奖

陈华
陈国华,笔名陈华,1971年9月10日出生。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目前工作在杭州。1997年开始在纯文学刊物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三百多篇,出版散文集《爹娘的客》、小说集《赶花人》、《逆流》获得奖励若干。2013年,2016年分别被保送黑龙江省萧红文学院研修班学习。2015年至今,担任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作协副主席,2016年至今,担任黑龙江省《远东文学》小说编辑,202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获奖作品:《寒葱河》
寒葱河像个弃妇,被孤零零地遗落在东北边境线上。
六十年前,我爹还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和我拉古叔,从山东和吉林两个地方奔向这里。
我爹在红松树下拾起饱满的松塔,取一颗松子在叶隙间的阳光里端详着。松子光滑饱满,散发着幽幽的松脂香。我爹叹:天公啊,还有这么神奇的果子!然后抛向空中,松子画了个弧,掉进嘴里。嘎嘣一声儿,一颗饱满的果仁儿就落在我爹的舌尖儿上。他肆无忌惮地咀嚼着,口舌生津。
松子油滋润了他干涸的肠胃,只一会儿,他贫瘠的肠道就润滑顺畅起来,一个臭屁在森林里炸响,吓坏了趴在松塔上午餐的松鼠,它满是条纹花儿的毛直立起来,睁圆了黄豆粒子样儿的眼睛,似乎想看清这直立行走的入侵者。当它看着无数双脚板踏过厚厚的针叶逼近它的时候,两只小爪子一抖,扔掉吃了一半的松塔,一跳,再一跳,窜了。
蒲扇样儿的灵芝,草丛里抖着复叶的野山参,紫莹莹的山葡萄,红艳艳的枸杞子,绿油油的灯笼果儿,榛蘑、冻蘑、鸡腿蘑、黑木耳、松茸,还有各种草药……它们从石缝儿中、草丛里、树底下,生机勃勃肆无忌惮地蓬勃招展,琳琅满目的红松,几搂粗的树干,枝头挂满的松塔把我爹的眼睛砸晕了。他惊羡的眼神随着笔直的树干直冲云霄。
那时,我年轻的爹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富饶的、仿佛永远也取之不竭的宝藏。他兴奋得像只野鹿,满山乱窜。脚下一绊,我爹一低头,一根干叉子(野鹿角)横在脚板下。后来我爹给老家爷爷奶奶的信里这样写道:棒槌鸟儿放山参,石头缝儿里长山珍,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砂锅里,娘啊,这不是瞎话,是真的……(点击阅读原文)
二等奖

叶青才
叶青才,安庆大别山科技学校(原岳西职教中心)讲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现为岳西县诗词学会会长、法人、《岳西诗词》主编。曾用笔名叶静、西溪等,已出版散文集《源头》《秋天里的单音节》《笔底天蓝》等,诗词集《逗雨庐诗钞》。曾获第三届安徽省政府文学奖、首届安徽省张恨水文学奖、中国散文奖等,作品被选入多家国内外选本。
获奖作品:《临水而居》
我再次与水磨合出一片切肤之亲,是在离开家乡五年之后。这是一条不大的河,河水不急不慢地流向下一个山峡,流向大别山的出口,一直到长江。此时,婉曲的老鸭涧钻出霜染的红枫林,在堆满稻草垛的那块场地的西角突然转了个弯,然后扬开岔口,如一弯新月,灿亮且忸怩着向我的小屋踅来。
这栋小屋是一颗不太显眼的纽扣,缀在这个小镇不够对称的衣襟上,而潜水河暴涨时,不啻一条引人注目的红色领带,就从我的小屋披挂下来。
我不止一次临水而居,先是在一条只能叫做“溪”的河边住了三十几年。我后来把它叫做西溪,因为东面还有一条干沟,夏季山洪暴发的时候,干沟里同样有水,有冲突的轰鸣声,有送上堤岸的浪渣浮滓。由于我天天直面这条溪的缘故,它似乎已经深深地植根在我的记忆中了。西溪的水也只有水桶那般粗细,却从没有断流过,附近几户人家的饮用和洗涮,全靠了它。冬天,白冰封死了河道,水流在冰层下汩汩地发声,只有一个潭一直冒着热气,四周长着绿的青苔,红的浮藻,里面游动着数不清的米虾。潭其实是被大半圈山岩抱着的,避风,低凹,阳光却能早早地照临。黑褐色的岩石,在冷光下泛着清幽,毫无遮拦的,是晒衣被晾冬菜的好去处。潭子以下便转了一个弯,西溪就一直流向村外。我不知道河流为什么总在有人居住的地方拐个弯,而略显深澈的河潭也大多分布在弯子里。事实上,它的选择一定比我们人类智慧,它破坏了人们的既定设置又让人们重新来筑起拦水坝,它掠走了放在河边的什物又再次将人们一回回引向河潭,它干得要死了却在三伏天里使人听见淙淙的水声……(点击阅读原文)

惠永臣
惠永臣,男,1970年9月出生,甘肃镇原人,中国作协会员,甘肃“诗歌八骏” 成员。先后有1000多篇(首)诗歌、散文、小说发表于《诗刊》《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中国校园文学》《飞天》《星星诗刊》等多家刊物,出版诗集《时光里的阴影》《春风引》,先后获第五届、第六届“黄河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多种选本。
获奖作品:《大地是铺展开来的唐卡(组诗节选)》
山坡上
山坡上,那么多的牛羊低头吃草
那么多的石头
都放弃了言说,它们却都是见证者:
草木绿了又黄
黄了又绿;牛羊一批批长大
又一批批被运到山外
牧人从来舍不得让皮鞭
打在牛羊的身上
挤奶的女人,从来都会给羔犊子
留一口奶水
当你站在山坡上
甚至站在它们中间
你就会感动的流泪
——它们一抬头
世界就会马上温柔起来
……(点击阅读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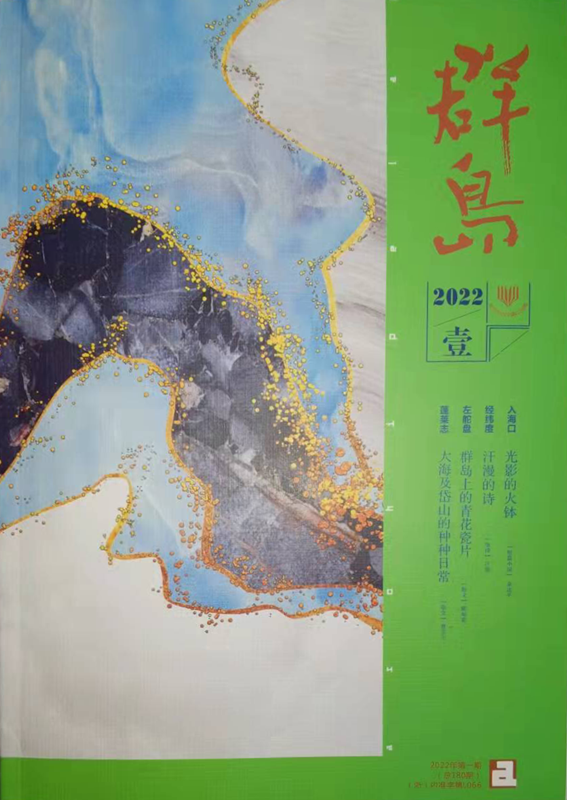
《群岛》
《群岛》创立于上世纪80年代,由浙江省岱山县作家协会主办。《群岛》以海纳百川的姿态,保持“独立、开放、海洋、新锐”的办刊理念,致力打造一份优秀的海洋文学实验文本。《群岛》为文学季刊,每期114个页码,累计总出版期数已达181期。
《群岛》栏目设置有“入海口”“大潮汛”“经纬度”“左舵盘”“蓬莱志”“山海经”等,使之清晰贴上海洋和海岛的地域标签,海洋精神的灼灼其辉可见一斑,形成建构地域文学空间的重要力量。
《群岛》除少量邀约稿,大量选用全国各地自然来稿。同时,还编有《群岛小小说》季刊、《群岛诗年卷》等。
获奖作品:《阿黑离家以后》
从中午起,李静静一直在找她家的阿黑狗。她不叫阿黑的名字,只是脚步不停地在白花花的大太阳下到处搜寻着,碰上了人也没问,她认定别人不会在意她的阿黑。
这是暑假的第一天,整个上午李静静都在水库边洗衣服,两条腿都蹲麻了。本来,她是打算去水井洗的。当她把一大堆脏衣服都收起来,放进大塑料盆里,正要去找水桶时,忽然听到“嘭”的一声,爸爸把那只红色的塑料桶一脚踹过来,桶摔在院子墙角的石头上,裂开的缝像一道长长的泪痕。妈妈在屋内尖叫着,又哭又嚎。
李静静站在院子中央,沉默着,太阳渐渐大起来,晒得她后颈有点疼。阿黑跑过来,用脑袋蹭着她花裙子下的腿。她蹲下来,和它抱了一会儿,就端起塑料大盆,往水库走去。盆里的衣服有些酸臭,妈妈和爸爸吵架,已有三天没洗衣服了。
当爸爸午睡后醒来,拖着懒散的脚步往村头奶奶家走去时,李静静感到这一天似乎可以提前轻松了。其实午饭后看到爸爸没有急着要出去的意思,李静静半悬的心已经有些落下来了。只要爸爸不去那里,妈妈的脸色就能好看些,家里的气氛也能缓和不少。
李静静把村里所有的弄堂旮旯寻了个遍,始终没见到阿黑的影子。她来到村里唯一贴着紫色墙面砖的三层小楼前,轻轻地推开虚掩的院门,看到一条胖胖的黄狗正露着肚皮在水泥地上睡着。那狗听到有动静,张开眼,看到李静静,又懒懒地闭上眼,继续睡去。平时它经常去招引阿黑,对李静静也很熟了。
“静静!”有人在上面叫。抬头看到夏雪儿俯在二楼阳台上,那裙子的大圆领像小孩子嚎哭时的嘴,张得大大的,使里面两个白生生的小馒头展露无遗。李静静带着几分心悸,几分嫌恶,刷地转过了头……(点击阅读原文)
三等奖

阿未
阿未,本名魏连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作家》《诗刊》《青年文学》等刊发表作品,有诗作入选《中国诗歌精选》《中国最佳诗歌》等选本。诗集《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获中国作协重点作品项目扶持,曾获吉林文学奖,中国年度诗歌奖等奖项,吉林省作协首届签约作家。
获奖作品:《诗十首》
三月
最后的冰是羞愧的,它们对水的劫持
终究以自己也成为水
而终结了一个寒冷又僵硬的季节
三月在水的喧哗中,实现了
它的颠覆性,并就此开始了一场瓦解
和暖风入怀的春梦,多美啊
曾经封冻的土地,有了更多
湿漉漉的细节,有了重建花红柳绿的
底气,那些深埋于冻土的草木之心
正在复苏,轻风拂过之后
就有无数伸展的骨骼嘎吱作响,仿佛
故人归来,在三月冰消雪融的云水间
轻声唤我……
……(点击阅读原文)

释一尘
释一尘,原名刘忠涛,陕西旬阳人,陕西国画院理论家、陕西画院联盟执行秘书长,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现挂职于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长期从事中国画创作与美术史论研究工作。陕西省人文社科类重大学术研究项目:陕西美术考察研究系列丛书•长安风格《唐•王维研究》《北宋•范宽研究》《华山研究》《大写意研究》等书籍执行编著。
获奖作品:《从长安出发·甘南行记》
火车从关中平原驶出,过秦岭,频频在隧道里穿梭,一路渭水相伴,与我的家乡陕南地貌类似。只是流经陕南的汉水清澈如明镜,而渭水浊黄似泥浆。想起唐代诗人贾岛的两句诗:“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从诗句中可以揣度,那时,即便是秋天,渭水水位也是很高的,水流量更不会小,不然无从得来“秋风吹渭水”的意境。但如今,我们只能看到空旷的河床,仿佛一位有着无限往事却什么也记不起来的临终老人。
陡然一片绿洲,树木葱茏,花草明媚,便到了甘肃最为富庶的天水地区,天水不同陕南的温婉沉静,也有别于陕北的粗犷豪放,独具韵味。关于天水命名有两种说法,都跟汉武帝有关:一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上)曰:“五城相连,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在汉武帝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二是源于“天河注水”的美丽传说:相传秦末汉初,邽县遭逢大旱,民不聊生,突然一天夜里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干涸的土地上裂出一条大缝,天上河水倾泻而下注入缝中,形成了“天水湖”。后来这个传说被汉武帝知道了,他就在元鼎三年下令把新设的郡建在邽县北城的湖边,命名“天水郡”,天水便从此得名……(点击阅读原文)

钱金利
钱金利,笔名半文。杭州人。业余作文。曾在《散文》《散文海外版》《散文百家》《星火》等发表习作,有作品被《散文选刊》《读者》等选载,有作品收入《中国散文年选》《新散文百人百篇》等。
获奖作品:《虫子的忧伤》
须夏夜,须乡下,须天黑如墨,须紫微、天璇、瑶光、天狼、牛郎、织女……星辰棋布,镶缀其上。夜空如一个硕大的盖头。我站立在星空之下,伸手,摘一颗闪闪发亮的星,装入小药瓶。再伸手,又摘一颗,又装入。夏夜的萤火虫,和星星一样闪亮,在夜空划出一条美妙的弧度。我在弧度的尽头,伸手托举,像一颗流星坠入大地。萤火虫飞得不快,亦不重,伸手可摘,举手可托。我从夜空中摘下一只一只萤火虫,装在褐色的小药瓶,挂于帐顶。于是,帐似穹庐,整夜闪闪烁烁,像在星空下入眠。梦里,漫天飞翔的流星。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夜里,梦里,有人唱着儿时的歌谣。萤火虫提着心爱的灯笼,踽踽而飞。孤独,从容,带一点淡淡的忧伤。我喜欢这样一种简单而美丽的忧伤。虫虫有虫虫的忧伤,人类有人类的忧愁。各自忧各自的伤各自的愁,互相映照,互不侵犯……(点击阅读原文)

卢仁强
卢仁强,男,汉族,贵州普定人,贵州省作协会员,有作品散见于《岁月》《辽河》《三峡文学》《天池小小说》《读者》《微型小说选刊》《贵州作家》等文学期刊。小小说《打工》入选《2008中国微型小说年选》(花城出版社)《一条鱼的狂奔》。
获奖作品:《柿子树下》
她躺在棺材里,身上穿着手工缝制的长衬,四件棉衣,四件单衣。人去到那个世界,要把春夏秋冬的衣服带齐。
她想,我死了吗?恐惧犹如一张黑网,裹挟着她的身躯,吊在半天云上,摇来晃去。她想哭,又哭不出声气,死人怎么能哭出声音呢?她努力让自己静下来,就望见了儿女们个个披麻戴孝,站满了堂屋,仿佛下过大雪的院子,四周洁白的积雪,围着中间的棺材。那是她喜欢的棺材,霞光亮崭,好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四周皑皑白雪。
她没有死。死人怎么还有意识呢?她心中一阵窃喜,或许自己是在梦里。这样的场景,她看得太多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关于死亡,她一直想着一口好棺材,那口棺材,仿佛她一生的追求。可是,她太忙了,屋外的田地,屋内的厨房,这些都离不了她的双手。往往脑海里才闪过棺材的模样,身体已被繁重的农活淹没了。
村人用长长的龙杆,抬着她和棺材,出了村口,向着田坝里走去。田坝是生长粮食的地方,也许村人也如种庄稼一般,把她埋进田地里,生根发芽。她觉得有点好笑,自己长不成一株庄稼,但能生成一棵狗尾巴草。她转瞬又伤感起来,疯长的野草自生自灭,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坟茔地处何方……(点击阅读原文)

路嘉
路嘉,女,汉族,1999年10月生,甘肃省作协会员。作品见《飞天》《延河》《山西文学》《美文》《北方作家》《骏马》《中国青年作家报》《文汇报》等报刊,散文《从前慢》入选《爱在狭路孤行》一书。
获奖作品:《糖》
“爱或死亡会令我变成花朵。”眼镜框下沿播放这句歌词,习惯送餐时听歌,听点儿激昂的,听点儿死气沉沉的,逼近临界的旋律带来亢奋情绪,让他重新对赚钱斗志昂扬。
飘一场雪,寒意撕扯秋衣仓促赶来,车轮碾磨落叶,揉捏人民币的声音。踩住刹车,冯天伟从后备箱抱出一摞塑料盒,走路大跨步的他会在这时缩成小碎步,热的粉和冷空气撞出白茫茫的吻。
发送今天第一条朋友圈:“终于再一次实现定存七位数。”
十分钟,朋友圈下多了一句,“哄老板娘开心一下,你们也信?”
闪婚的第五个年头,相识到结婚仅仅十二天,甚至现在过年一家人坐满桌,孙子孙女缠着要红包,他父母也会有没回过神的感慨。大宝到三宝,不敢懈怠一天,拉下卷闸门,晚上十一点,返回车里,犹豫一会儿,还是拿出白天送餐间隙在学校商店买的烟,婚后戒了烟,太久不抽烟的冯天伟如同在干坏事,一根烟几乎让他从脖子红到脑门,后视镜中看到烟雾在自己唇齿间穿针引线,缝合欲言又止的嘴。朝北开,和家相反,花费十分钟去郊区看鹅,站在湖边,垂落一片影子下去,任由影子接近大鹅,穿梭在它们拨动的脚掌间。
插口袋站在湖边的他更想做个影子……(点击阅读原文)
优秀奖

许起
许起,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有散文发于《新华日报》《苏州日志》等。出版长篇小说《飘云下的绿色流水》和《援越青春》两部。
获奖作品:《拍甲鱼》
二凤结交的几个小姐妹,都住在附近三条弄堂里。她和她们都很要好,自小至大从未红过脸。尤其和隔壁东边弄堂里的菱花,亲密程度好似亲姐妹。菱花的最大特点是嘴巴紧,不喜欢多说一句,更不对别人评头论足。二凤是个有话就要说,有气就要出的人,但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不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别人,免得流言蜚语满天飞。她对菱花例外。菱花老实,从不把二凤讲给她的秘密漏一点出去。一天二凤把和阿二的关系告诉了菱花,要菱花保密,因为她和阿二的定亲仪式要到年底举行。
“我不会说的。”菱花嘴上答应,心中一个咯噔,很不痛快,表面上却没有明显的反应。其实她心中也有阿二,只是没有说,一直闷在心里。她以前也知道二凤喜欢阿二,粘着阿二,使她无法进一步靠近。菱花比二凤小一岁,身体比较单簿;打也打不过二凤,骂也骂不过二凤,何况二凤一直待她不薄,和她反目成仇不妥。更主要不知道阿二的心思:究竟有她还是有二凤?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她不想说,也无法说,说了没有用,就像在白墙头上刷石灰水。对二凤后来说的话她没有全听进去,敷衍两句走了。
二凤看到菱花异常的神态,一惊,自然而然起了警觉;菱花是不是对阿二也有心思?她马上过电影般把菱花以前的表现在脑海中展示一遍,找不到可疑之处,心也定了,笑自己多虑,菱花的异常许是有其他的心事……(点击阅读原文)

嘎代才让
嘎代才让,藏族。生于8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星星诗刊》《章恰尔》等发表大量的藏汉双语诗作,入选六十余种重要诗歌选集。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多种文字。荣获全国十大少数民族诗人、诗选刊•2005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 、滇池·80后十家诗人、首届安康诗歌奖、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一等奖、第六届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奖、《岗尖梅朵》文学奖、唐蕃古道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诗歌奖等。
获奖作品:《宗角禄康(外一首)》
一
一场沉缓的雨夜之后,拉萨林廓北路
提前伸展到刚刚起身的春天
转经路上的放生羊念念有词
一回眸,闻见了草的清香,一群鸟
像时间一样赶来
得以听见
被风阻拦的噪音,有云朵碰撞的惨叫
二
传说:禄康园林为基座
曾迎请墨竹赛钦和八龙供奉于北潭水中
像是一派葱绿极为保护的泉眼
像是信众执意保佑的佛龛
像是被认领的故居,年代久远;像熟睡的婴儿
面对每一张新面孔
又像绘制常年的唐卡,人们在它的怀抱中
拾柴,开灶,语笑喧阗
每个人如此朴素,踩着自己进进出出
……(点击阅读原文)

陈登
陈登,98年生人,云南省作协会员,古代文学研究生在读,现居兰州。作品见《散文》《草原》等刊。
获奖作品:《盐湖笔记》
夜入吴
热衷反复 不论
俯首请命或 扬眉折返
无数顿笔与墨点
涂抹肺腑的白纸
洇出暗色
便被拱手送还
寒雨连江
窗畔 虚拟的洛阳亲友将信对折
冰心玉壶 只是遗物
斩断慧根 一身雪白
方能趁夜入吴
酒唱哀弦 和楚山
平分秋色也
平分孤独
……(点击阅读原文)

弋吾
弋吾,本名王喜,甘肃会宁人,2016年习诗,倡导无意识写作,创作有长诗《流水集》《漂萍集》《炊烟》等15部,近五万行。有作品见《文艺报》等刊,出版诗集《在人间》。
获奖作品:《月光的疼痛(组诗)》
苦水河
跨过苦水河就算离开了家乡
苦水河就是——
隔开我们的那一场大雪,妈妈,你还好吗?
你活着的世界里
是不是也有一条苦水河
装满了你的眼睛
菡菠菜长疯了,遮住了眼睛
苦水河看不见人世
美好的变化,心上的苦依然淌着
你活着的世界里
妈妈,你能不能告诉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
跨过苦水河,那一场大雪能不能
压垮你,我不知道
苦水河一句话也不说,妈妈
人生为什么要有别离
你能不能告诉我,河水断流后,你会不会消失
……(点击阅读原文)

李汀
李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人民日报》《散文》《青年作家》《散文百家》《北京文学》《读者》《岁月》《滇池》《小说月刊》《短篇小说》《辽河》《鸭绿江》《福建文学》《四川文学》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作品数百篇,有作品被《青年文摘》《文学教育》杂志选载并评介,出版散文集《农谚里的村庄》《西藏,清水一样的光芒》《民间有味》。先后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第五届宝石文学奖、首届浩然文学奖、首届四川省散文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大赛三等奖。
获奖作品:《虫儿飞》
夏天热得人烦,山间的蝉儿还往死里叫,让人更烦。
好在山间,还有一山的绿树,在阳光下流光溢彩。一想,那么大的山,装着一山的安静,要是没有这一声声“知了知了”的蝉叫,树寂寞,人也寂寞。这么一想,再静心听蝉叫,就觉得蝉儿叫得有理由,叫得还真像是山间单纯且绵长的一首首歌谣。蝉鸣,山间的杜鹃花在风中摇曳,躲在树丛里的野百合开了,山间遗落的一间小庙,有人吱呀一声推开门,门口那口老井,落了一井蝉鸣。那人拿起井口的一个老葫芦瓢,舀了一瓢蝉鸣,仰头咕噜咕噜喝下了。“好爽。”水的凉爽和蝉儿的单纯都在肚里了。这时候,寂寞变得清澈起来。
再想,蝉鸣是什么颜色?五月,山花烂漫,红、黄、青、蓝、紫都有,蝉鸣隐藏在这些颜色当中。这个季节,颜色的丰富可想而知,大地所有的颜色汹涌而来,鼓乐齐鸣,树梢、花间、溪水、山坡,甚至天空的蔚蓝,都被蝉鸣一一摇醒,穿过颜色的隧道启程,坐上颜色的马车赶路。其实,蝉鸣是透明的,因为在众多颜色的簇拥下,天空变得异常亮堂起来……(点击阅读原文)

刘玉红
刘玉红,笔名东方,七十年代末出生于甘肃定西。十五岁初中毕业后在建筑工地打工十余年,自学考试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爱好阅读,有十余万字的散文诗词作品见于报刊杂志,出版随笔散文集《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
获奖作品:《花花鸟儿绿翅膀》
细心的父亲发现,祖母好长时间没有再唱过花花巧儿(方言中的鸟儿)绿翅膀了。不仅是祖母,母亲也是很长时间没再唱过,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怪事。
那会儿的祖母站在磨窑口,悠闲地哼着和河湟花儿差不多的调子,边哼边督促着黑驴拉磨。蒙着眼睛的小黑驴四蹄疾走,和着麸皮的小麦粉从两合石磨的唇齿间扑簌簌地落下,在半尺宽的磨台上堆成一大圈灰白相间的连麸面。
务(那)坡里骑大马的,
戴红花的,
可是额(我)的出家的人?
……
务(那)坡里坐破车的,
领细狗的,
可是额(我)的当家的人?
晚上挤进祖母的被窝里,我便缠着要祖母说说她那些古怪的调调哼的到底是什么。好几次祖母都是以太累了嘴都张不开而委婉地将我的小脑袋和好奇心一并严严实实地捂进被窝里。过了好多天,我早已忘了这件事了,祖母竟主动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两个晚上:某年某月,一个贫困的母亲将年幼的女儿灵儿送到地主张二爷家里做童养媳。灵儿在张家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受尽刁钻的婆婆和刻薄的小姑子的折磨虐待,一事不周就会遭到擀面杖捶打,甚至会被锥子猛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十五岁那年,灵儿和张二爷的儿子完婚。未满一个月,张公子赴陕西赶考,一走两年再无音信……(点击阅读原文)

蒋康政
蒋康政,1969年出生,江苏泰兴人,教师,江苏省作协会员。在《人民文学》《诗刊》《北京文学》《文学港》《中国诗人》《中国诗歌》《绿风》等发表过诗作,获得《诗刊》《华语诗刊》的征文奖,入选过中国诗歌网“每日好诗”和“中国好诗”栏目,江苏文学院首届高研班学员。
获奖作品:《慢慢灌浆的生活》
下午四点
下午四点,起身,我想出去看看它们。
没有风,阳光还正在火候上,天气正显现出少有的温情。经历了两场天寒地冻的彻骨寒之后,我来到了它们身旁,彼此依偎。萎缩。疲倦。暗淡。枯黄。沉寂。它们想必还心有余悸,往日不堪回首。阳光把它们暖在怀里,安安静静的,没有杂音,更没有喧嚣。经历得多了,自然会丰厚而深沉起来。
远远近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这样兜眼看了几圈。
香樟的伤最深:叶卷边瑟缩,枝静默无言,好在离残枝败叶似乎还有两三个冬天的距离,可是人间从来都只有一个冬天,一年。
海桐倒好,还是那个油光满面的嬉皮笑脸样,看来它们没心没肺的,从来不打算记住灾难。一只鸟“扑棱棱”飞起,原来我来到了它家门口。它这是向谁去通风报信呢?它有很多亲人散落在寒冬深处?
五只香橼缀在母体的最高处,它们的蒂此时是九头牛、两只虎住在里面……(点击阅读原文)

陈伟芳
陈伟芳,笔名绿艾、陈伟昉,山东省济宁市人,职业为保安。荣获第八届万松浦文学新人奖。
获奖作品:《指尖上的红》
晾干的被面,飘散着淡淡的皂粉味。我握这头,母亲拽那头,拉好架势,两人轻轻地松一弯,再一下拉直;一递一拉,拽过来,送过去,前倾后仰着身子,摇晃出扯大锯的样子,笑就憋不住地拱将出来。一笑,节奏大乱,手和胳膊软成了面条,脚底没了根,浑身轻飘飘。攥被面的手软得没了劲,哗地一下,一头挣脱了去,被面的小碎花瞬间烂漫一地。只好试意着用劲,不然,会被诓倒在地的。母亲似嗔似怪:绷住,别笑啦!越是故作严肃,越禁不住地爆笑开来。若是与妹妹拽被子,一会儿,脸红脖子粗地拔河,一会儿,像两只争抢一条蚯蚓的小鸡,一使坏,就指不定诓谁个屁股墩了。笑一下子炸了窝,云在笑,风在笑,鸟儿在笑,我们更笑得直不起腰,眼窝里的泪也不招自来地淌下来。抱蛋的母鸡受了感染,扑棱到我们脚后跟,咯咯地笑;猪在圈里哼唧着拾起剩笑。
被上的褶子在欢声笑语里绽开了。不知为什么,抻被里被面,是我一想就要笑的活计,灵验着呢,笑就藏在了这里,那样花枝乱颤地笑,笑得春光满院。人生不知怎么了,那样放肆的大笑,都跑到了梦里面……(点击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