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中国与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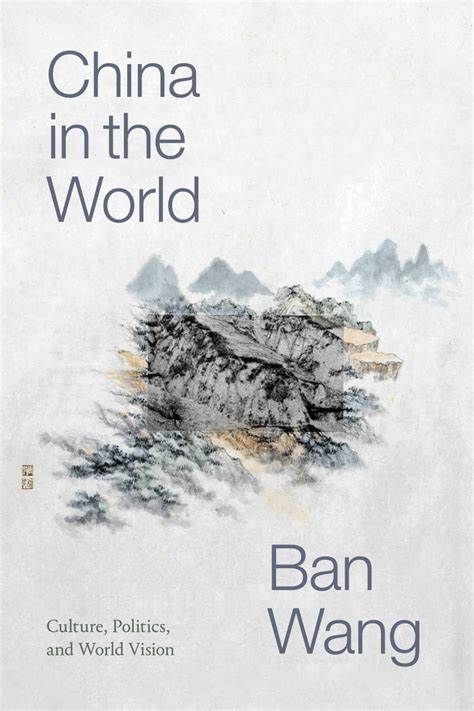
世界中的中国》英文版封面
叶玮玮:王老师好,您的著作《世界中的中国:文化、政治和世界观》(China in the World:Culture,Politics,and World Vision,2022)堪称是从世界看中国的扛鼎之作。在此著中,您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天下大同”“国家主义”观点进行了鞭辟入里、深入浅出的评述。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康、梁的“天下大同观”?
王 斑:康有为、梁启超生活在帝制转化为民族国家的时代,在政治活动和思考中,康、梁都意识到建立民族国家概念的重要性。康有为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持批评态度,视其为世界太平的祸害和根源,认为殖民列强乃“自私其国、夺人之国”,扩张权利掠取他人领土、市场、资源;倡导去国弭兵求大同。相较于康的思想,梁启超关于民族和国家的理解较为现实。
在梁启超看来,在当时的列强扩张时代,民族和国家能够很好地凝聚群体,确保同种、同宗、同俗之族群互为“同胞”,从而形成独立自治、组织民治的政府,为本国谋公益、抵御他族入侵。梁启超深谙西方民族国家的局限和弊病,在观摩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时,梁就提出,世界大同为时尚早,但国联的诉求却与天下观遥相呼应,并由此提出“世界主义国家”概念:国人要爱国,但不能只认本国不了解世界。世界主义国家力图发挥其成员的天赋才能,把国家作为人类全体进化的一个手段,“不是把自己国家变得富强便罢了,而是叫自己国家有功于全人类”。
叶玮玮:康、梁“世界大同”思想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层面扮演怎样角色?
王 斑:中国“一带一路”构想和实践,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可以说正在将梁的“世界主义国家”理想付诸实践。
叶玮玮:2017年,我在攻读博士学位之时,曾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接受联合培养;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文学研究能够被放置在“环境人文”这个“从地方到全球、从生态到万物”的跨学科新术语之下。我一度认为,中国学者追求纵深,西式学者偏向广博。您在新著《世界中的中国》第八章中,也呼吁西方的中国研究应从中国本土生态视域重申世界主义,进行更纵深、传统的研究。是否正是因为您意识到,单就康、梁“天下观”及“新型中国世界主义观”的理解,西方汉学界与中国本土学者就有分歧?您认为,中西学界跨界对话需注意什么问题?
王 斑:是的。西方主导论述对“天下”话语一般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天下观”是要重组世界格局。在西方话语界,康德“普世主义”有绝对话语权;若是中国人谈世界,则容易被扣上以特殊性冒充普遍性的帽子;中国本土评论家谈“走出去”,容易被说成想重焕昔日大同。但如赵汀阳所说,当今世界甚至不足称为“一个世界”,仍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之感。
在我看来,中西学界对话时应纵深、全面地理解“本土与世界”。关于“天下”,素有中国和西方学者忽略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认为,20世纪中国历经改革、战争、革命,继承中国传统中可与现代价值能接轨的遗产。从民族国家和天下观融合角度来看,中国早已在“世界主义国家”的征途上。
叶玮玮:王老师,您的研究堪称“全球地方性”(Glocalization)研究的代表。您是否遇到过关于“何为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学”类的基础问题?您如何看待“地方的即是全球的”这一说法?
王 斑:我会跟学生解释:生态批评是对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气候变迁的思考;其核心论题是强调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共存,反思“人类世”(Anthropocene),批评“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我素来对“人类世”持审慎态度:该概念忽略经济体制、生产方式对外在自然的索取,对内在自然即生产者的剥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对待内在自然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取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时三百余年,酿成了破坏自然的恶果。生态危机并非产自现代农耕,也不可归罪于低消费劳动阶级。“人类世”概念将气候危机归于人祸,笼统对所有人问责,掩盖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生态撕裂及阶级矛盾。我经常告诉学生,并不是人类整体造成了环境危机,而是某个历史时段的经济体制和资本集团肆意扩张的后果。“人类世”的说法,遮蔽了资本集团、金融权威和科技寡头生产方式的后果;它掩盖了一个事实:有钱人总有办法生存,至少可以多活几十年,甚至殖民外星球。所谓“人类的化石足迹”(human fossil footprint)更是大而无当的说法:它无视穷困族群被异化的现象;与那些开不起车、生活在窝棚、终身赤脚的人毫无关系。
叶玮玮:如此说来,曾经西方人文话题下的“世界文学”和“人类世”本质还是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语境延伸的话语,这样理解可以吗?
王 斑:没错。西方人文话题下的“世界文学”和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是孪生兄弟。大工业的兴起,资本积累在全球的扩张,世界贸易和市场的发达,让歌德开始倡导“世界文学”。马克思也说,资本主义大工业不用本国的原料而攫取别国原料,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也供世界各地消费。如此场域下的“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旨在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化为公共财产,地方文学也就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但是,资本世界远不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包容的世界;他有劳动分工、尊卑贵贱秩序,由资本金融统治奴役边缘,把世界分裂为统治和依附体系。强势国家从弱势地区攫取资源、剥夺劳力,破坏当地社群文化;这就是“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的议题。西方人文话题下的世界文学的想象固然美好,但这样的残酷不平的世界,如何能造就世界文学的共享平台?
叶玮玮:王老师,我明白了。您躬耕践行着中国学界常谈的“平等对话”,想让世界听到多元本土世界的声音。生态文学作为从环境公正视角审视生态与人性、民族发展与多样物种的书写,是否具有“走出去”的先天优势?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中国本土的生态文学就是“世界文学”;或者说,所有能被冠名为“生态”的文学,本身就有世界文学性?
王 斑:是的。我们谈“文学走出去”,所期待的是与世界接轨,是中国作品在世界文坛得到公平待遇,是确保国际读者能公正评价中国历史、社会和人心。上世纪30年代,上海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倡议“文学世界主义”,就有同样的诉求。但是,彼时的他们是在殖民租借地发出这种声音,根本没人理睬。走向世界愿望很好,但当时的现实很残酷。当时的世界权力结构、文化交流其实很大部分保留着殖民主义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中国文化虽然走出了国门,但远远没有进入到与人平等交流的平台,因为掌控话语平台之人不会轻易让你成为座上宾。
当下,文学“走出去”有时会隐含着一个迷思,即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跨文化对话蔚为大观,多元文化大门对所有人都敞开。但是,西方的“世界文学”,所依赖的是西方人文主义、启蒙传统。人文主义植根于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注重理性、主体和自觉;在艺术上,倡导独创、想象和真情。如何与过去神权主导世界观和前现代的封建宗法秩序群决裂,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这才是全球性思想的革命,是在世界传播的思想。人文主义近百年来的华丽转身,一跃好像成为跨文化、跨国界的思想先锋。但是,君不见西方人文主义包藏着狭隘、偏见、傲慢和霸权,欧洲中心论及放大的民族国家论,以及奴役自然、劳动者、妇女和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西方的经典小说常以个人成长的履历为重心,描写个人成长、家庭关系、社会和政治层面,着重谈及个人的自我及社会、历史的关联。比如,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完全嵌入早期维多利亚文化政治氛围内,描述那个时代的阶级和性别的作用,呈现大英帝国的风土人情。如此一来,西方的“自我”远没资格称“世界公民”,而是植根于某一地缘的表象。此“个体”更像是个四海漫游的异地探险家、经纪人、贸易商人、风险投资者。他足迹遍布天涯海角,掠取当地自然和人力资源;其身后是资本财团和殖民帝国的船坚炮利,而资本全球的扩张是自由个体形象的推手和后盾。
如此,我们如果想要赋予文学以真正世界性,就必须突破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西方经典人文主义视角就很狭隘,人类之外的天地万物,仿佛只有在人的狭隘视野中才有意义和价值;外在自然环境不过是社会环境和文明发展被压抑的背景。也正因如此,生态批评上穷碧落下黄泉,视角深入地球万物万类,重视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与生物系统,触及气候、空气、植物、山川及生灵万类互联议题,能够作为挖掘文学的世界性的重要工具。如此,生态文学作为建构共同体的一方空间,自然堪称是真正的世界文学。
(王斑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叶玮玮系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