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凌云:往事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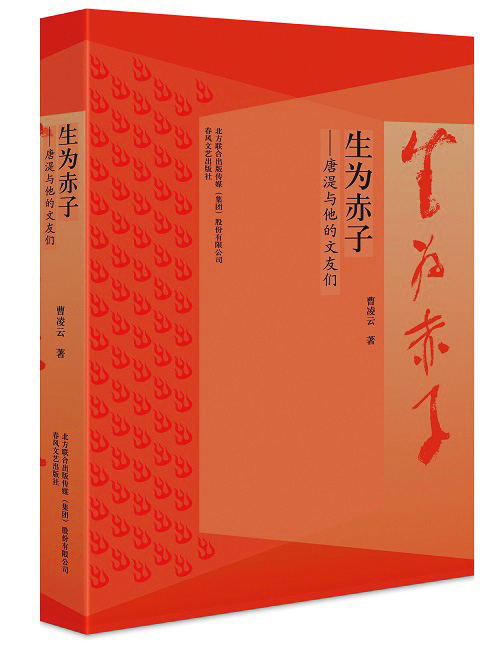
一
仍记得32年前的1990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唐湜先生。那时我还是学生,他应邀来我就读的温州市第十五中学做诗歌讲座。那时唐湜先生70岁,圆圆的脸庞,微胖的身材,深沉的态度,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讲座结束后,我们几个写作尖子与他近距离对话。我读过他的许多诗作,能讲出一些自己的想法来,自然成为对话的主角。他慈祥的目光、温和的语言和亲切的微笑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那天我们谈到夜色苍茫,才送唐湜回家。
我参加工作后,时常到温州花柳塘唐湜家里坐坐。他的居室50多平方米,陈设简陋,小小的客厅兼作书房,摆满了书籍和杂物。尽管唐湜是大诗人,我才刚刚学习写作,以他为师,但他的亲和力使我没有一点生疏和拘谨,在我们轻松自在的长谈中,充满着长者对晚辈的关怀和爱护。经过多次深谈后,我们成了忘年交。
我记不清我和唐湜有过多少次交谈,交谈中,他说话虽然有些含混不清,但思路很清晰,谈到一些往事时,都能详尽叙述。他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坦率直言文坛上的人与事。他喜欢谈胡风,喜欢谈陈敬容,当然也谈些自己的经历,几乎每一次都少不了这些话题。他谈起陈敬容时曾说:“陈敬容72岁时,心情凄凉,身心交瘁……偶然得了一次感冒,竟转为肺炎,昏迷了几天就去世了,没留下一句嘱咐的话。”
我还记得,在唐湜先生来十五中做讲座之前的1989年秋天,赵瑞蕻先生也来过十五中做讲座。
赵瑞蕻的讲座大概是学校老师宣传和组织得更好,慕名听讲座的师生太多,老师把原计划的讲座地点从阶梯教室改到大操场上。赵瑞蕻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却身材挺拔,声音洪亮,思路敏捷,还显得那么庄重、宽厚和慈祥。讲座后,赵瑞蕻与学校几个写作尖子座谈,他说:“祖国需要多少人才、多少知识分子、多少有着崇高奋斗目标的后代子孙,就可以看出文化教育、特别是中学生教育的艰巨任务了。”我聆听着他的每一句话,也一直仔细打量着他。赵瑞蕻回南京后不久,为我主编的校刊《龙腾》寄来题词。
记忆的闸门一打开,我又想起与金江先生交往的一些事儿。印象里,金江先生有着硬朗的身体、爽朗的声音、利落的动作。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温州龙湾区文联工作,请他到龙湾的一些学校里给学生讲寓言创作。他的讲课就像他的寓言作品,善用比喻、夸张、象征,讲得生动而幽默、风起而云涌,讲课的效果很好。他每讲一次课,便会让许多学生喜欢上寓言,有编辑校刊的老师告诉我:“金江老师的讲座之后,我收到大量同学们写的寓言习作。”
我还请金江参加龙湾的一些文化活动,他从来不摆谱,不推辞,更不自视清高或高人一等,一来龙湾就融入文艺工作者之中,谈天说地,畅所欲言。我们探讨文学的话题,沟通创作的计划,也闲聊生活琐事,甚至不回避一些八卦新闻。当然,谈得最多的是寓言、童话等儿童文学的写作,他对儿童文学的创作带着本色,保持了孩童的感觉,其作品常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关于莫洛先生的记忆,总是特别温暖。我认识莫洛先生,是我读初中时,从他的诗歌里;他认识我,是在一次温州作家采风的途中。那时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在温州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小文,可谓初出茅庐,受到温州作家协会的邀请,参加采风活动。记得那天一大早,参加采风的老中青作家代表在墨池坊集中上车,我坐到了大客车的最后排座位。路途中,有作家指着我问莫洛是否认识我,他回头一看,摇了摇头回答:“不认识。”那位作家便报出了我的姓名,他再次回头,脸上露出了笑容,高声地说:“嗬,大名鼎鼎呀。”顿时,全车人都笑了,氛围很轻松,我红起了脸,心里却是何等的受用与畅快。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老前辈,比我大52岁,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距离我出生人世还有33年,不料他也抽空阅读我稚嫩的作品,还记住我的名字。这是莫洛给我最初的鼓励。
有一年时间,我在《温州日报》的一个版面上开设专栏,文章不过千字,内容大多是针对某些社会现象的忧思。过年时我去看望莫洛,他告诉我这个专栏“每篇必看”,还拿起其中的一期报纸,指着我的文章《心灵的呼吁》说:“写得好呀,一个文化人的责任感,也是我的‘心灵的呼吁’。”莫洛的赞誉让我喜不自禁。我们谈过去、谈当下、谈创作、谈文坛,他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言简意赅,语重心长。他寄大希望于年轻人,希望年轻人对生活、对社会、对未来、对时代都要充满爱,让爱的薪火炽燃。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林斤澜先生,是在1991年秋天,林斤澜带着汪曾祺、唐达成、刘心武、邵燕祥等作家来永嘉楠溪江采风,寻山问水。我当时初学写作,凭着初生牛犊的勇气前往永嘉拜访他,他笑容可掬,与我聊了话,还给我题了字。最后一次与他相聚是在2004年夏天,林斤澜应邀参加由我牵头举办的张璁文化探源游座谈会,他年已耄耋,但红光满面,步履稳健,神采飞扬。这一次,我们就张璁文化、龙湾旅游、温州文学等话题谈了许多,可算是一次畅谈了。
二
2010年冬天,我调到温州市文联工作后,更加关注温州籍的文艺工作者,特别像唐湜、莫洛、金江、赵瑞蕻、林斤澜等“大师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得到读者的喜爱和信赖,经得住读者的评判、时间的洗礼和时代的考验。而此时,唐湜、赵瑞蕻、林斤澜三位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了,莫洛和金江先生不久也驾鹤西去了。
我在文联工作,有机会牵头编辑《唐湜全集》。我与唐湜的次子唐彦中开始整理、收集唐湜的作品。据我们估计,唐湜的诗歌、评论各有九十余万字,译作有五十万字左右,戏剧、散文各有三十余万字,还有数量不少的信件。我一边进行着《唐湜全集》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一边有感而发,开始陆陆续续写起关于唐湜的文章。
在写唐湜的人生和创作历程时,会写到他与莫洛、赵瑞蕻、金江、林斤澜等的交集,因为正如《生为赤子——唐湜与他的文友们》(下文简称《生为赤子》)开头所说的,“他们都出生在上世纪初的温州,他们是同学,是文友,是患难之交,是革命同志,他们从瓯江南岸起步,心怀赤诚,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于是,我又把笔触延伸到莫洛、赵瑞蕻、金江、林斤澜的身上。
在温州文化界,唐湜、莫洛、金江被尊称为“文坛三老”,他们是社会的尊者、育人的能者、心怀国家文学事业的大者。我有幸与“三老”都有过较为亲密的交往,唐湜是我的恩师,莫洛提携过我,金江可算老交情。我虽然与林斤澜交往不多,也就三五次光景,可是近十年来,由于工作原因,陆续通读了十卷本的《林斤澜文集》,他却成了我“接触”较多的老一辈温州籍作家。
我与赵瑞蕻交往最少,但我也阅读了他的多部作品集,了解了他的一些人生过往和创作经历。在写赵瑞蕻的过程中,我多次采访与赵瑞蕻交情甚笃的温州作家瞿光辉,向他询问一些细节,他也解答了我的一些疑问。我还多次与赵瑞蕻的长女赵苡微信联系。我说:“我想去南京拜访杨苡先生(赵瑞蕻夫人),想跟她聊聊赵先生,想表达对她和赵先生的崇敬。”赵苡说:“我母亲毕竟是100多岁的老者,不便打扰,但我会尽己所知回答你的问题。”
因此,在写作时我成竹在胸、运笔自如,如回忆般温暖,如江水般流畅。
在我写唐湜、莫洛、赵瑞蕻、金江、林斤澜的时候,我还时不时要写到两个人,就是胡景瑊和郑伯永,因为他们同为“同学、文友、患难之交、革命同志”,甚至胡景瑊和郑伯永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始终在第一线出生入死,百折不挠,是值得我们缅怀和尊敬的革命者、好干部,为温州的解放事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我没有与他们交往过,但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两人我也不得不写。
上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我们的祖国,山河破碎,无辜的百姓流离失所。身为温州中学学生的胡景瑊、赵瑞蕻、莫洛、唐湜、林斤澜、金江和郑伯永,他们不只是关注自己的学业和一己的悲欢,而是把深情的目光投向满目疮痍的祖国大地和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的中国人民。他们冒着随时被学校开除、被当局逮捕的危险,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
温州中学是进步思潮的大本营,他们和爱国、进步的同学一起,参加共产党暗中领导下的野火读书会、永嘉(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他们汇集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表达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他们通过出墙报、印传单、编画刊、办画展、设立书报阅览室、开展话剧公演、街头演讲等多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使得抗日救亡运动在温州蓬勃掀起,播下的爱国种子在瓯江两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此时的温州,还有一批追求理想、追求革命的年轻人,他们把目光投到了上海。多元文化并存的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左翼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和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地。中国革命“红色源头”城市上海光芒四射,备受人们瞩目。他们陆续来到了上海,在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领导者鲁迅先生的直接指导下,以刀笔为枪,奋战在民族救亡文艺运动第一线。他们就是温州版画家林夫、野夫、张明曹和王良俭等。
在鲁迅先生逝世、抗战爆发之后,他们毅然返回温州,在连天的战火中,积极投身于家乡的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他们以赤诚之心,筚路蓝缕,风雨兼程,行进在改天换地建立新中国的道路上,甘心奉献青春,直至奉献生命。他们与胡景瑊、莫洛、林斤澜、唐湜等是同道中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走到了一起来。
2021年8月,2021年浙江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项目申报开始,基于以上的写作与掌握的素材,我申报了长篇纪实文学《生为赤子》的创作选题。我思考再三,《生为赤子》以九叶派诗人唐湜为中心,讲述唐湜和他的文友莫洛、赵瑞蕻、胡景瑊、林夫、金江、林斤澜、郑伯永等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用断点式截取替代全局式概述,来反映浙南地区一批充满理想信念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激情,投身于革命事业,凭借巨大的精神力量,收获学业上的累累硕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创作《生为赤子》之前,我已为唐湜、莫洛、赵瑞蕻、胡景瑊、林夫、金江、林斤澜、郑伯永等写下了一定数量的文稿,我的主题设定是根据他们人生故事的文学张力而来的,是作品中的人物自身所携带和存在的问题意识而来的。
唐湜、胡景瑊、莫洛等的家族在温州属于名门望族,上辈族人基本上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但深重的国难让许多家族成员包括身边的亲人、爱人仰视红色人物,心中萌发和积聚了爱国之情,最终追求进步,投身革命,奔向了战火纷飞的第一线。比如唐湜的大弟唐文荣、大妹唐金金、小妹唐小玉、小姨王静香、表哥陈桂芳、表妹林翘翘,比如胡景瑊的母亲姚平子、三弟胡景濓、四弟胡景燊,比如莫洛的妻子林绵、林斤澜的妻子谷叶及赵瑞蕻的妻子杨苡等,他们也都投身到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中,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有属于他们的忠诚和英雄的故事。当然,他们在现实中有窘迫、压抑、痛苦、彷徨,甚至曾迷失自我和哀号呻吟,他们也有自己的亲情和爱情。
选择以唐湜为主线,自然离不开他在“九叶”中的八位诗友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郑敏、唐祈、袁可嘉和穆旦。这九位诗人都生长于家国离乱之际,受过良好的中西方文学教育和文化熏陶,深受外国诗歌的影响,学成后多有漂泊的经历,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一颗跳荡的诗心,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积极而勇敢地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上世纪40年代,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作,明显受到西方文学的熏染,常有多层次的构思与深层的心理探索,较多地接受了现实主义精神和中国艺术传统的风格,形成了他们的文学思想和艺术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国新诗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现在距离他们成名成家已经过去了70多年,而九位诗人和他们作品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反而发出更加迷人的光芒。《生为赤子》或多或少都给予记之。
三
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远去的背影,虽多为我早年的相识,但亲近如唐湜这样的恩师,也因时间久远,往事如烟,许多记忆被岁月冲刷得支离破碎,像被雨水沾湿的老照片般模糊不清。况且,他们的过往经历,我也没有全面、详细地掌握。全景式地写起来,确实困难重重。
为了追寻历史往事、精彩人生,获取更多的情节、细节,我开始系统阅读他们包括回忆录在内的文艺作品。故人往矣,而文字还留着温度,与我耳鬓厮磨,往日的情感由远而近,一点点回归,并日益深厚。
我又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赴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先后采访和请教了50多人,其中有唐湜的二儿子唐彦中、当时唯一健在的九叶诗人郑敏(已于2022年1月3日去世)、九叶诗人陈敬容的大女儿沙灵娜教授、屠岸的女儿章燕教授、九叶诗人辛笛的女儿王圣思教授、唐湜的学生沈克成、唐湜的好友瞿光辉、莫洛的次子马大康教授、作家渠川、王季思的长子王兆凯、赵瑞蕻的长女赵苡、赵瑞蕻的二女儿赵衡、胡景瑊的儿子胡济、金江的儿子金辉、郑伯永的儿子郑国惠、高级编辑潘虹、林夫纪念馆馆长林亦挺、林夫的孙子林秀敏等,从而捕捉到书中主要人物许多丰沛的情节和生动的细节,点点滴滴,汇聚精彩,他们的生平事迹也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
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寻访了书中主要人物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比如温州中学旧址、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旧址、春草池、籀园图书馆等,那里有他们青春的一部分,那里洋溢着温馨、和谐与诗意的生命,那里有遥远苍凉的历史烟云、有循着灯火去拓荒的坚实脚步声、有从斑驳旧影里响起的新曲……岁月迁流,世事繁变,抚今追昔,不禁百感交集。
在《生为赤子》的写作进入尾声的时候,我还走访了温州老城区“县前头135号”。这是一栋七间三层砖木混合洋式楼房,坐北朝南,北面临街,带西式装饰立面。这里是16岁的唐湜入党宣誓的地方。两年后的1938年,新四军在此设立驻温采购办事处,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以上海红十字会的名义也在此设立办事处,配合开展工作,将大批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军用紧缺物资输送到华中地区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静静地从一楼走到三楼,唐湜先生入党的痕迹已不可寻,早已消失在时间的深处,但我想,唐湜先生在这里抱定革命的决心,承担起所处时代赋予的使命,同时也让他的生命开始变得丰盈、多姿和壮美。我久久地站在二楼的窗台前,窗下是平整的柏油街面,午后的阳光把街上穿行的车辆照耀得明光灿亮,行人在街两边轻松行走,三两为伴地一起说说笑笑。
眼下正是人间四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