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亦假时假亦真 ——读科尔姆·托宾《魔术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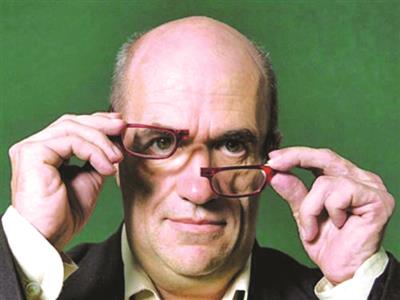
科尔姆·托宾
同《大师》相似,《魔术师》徐缓的叙事、克制的语调让我们的阅读仿若行踏在松软温润而令人舒适的泥土中——这泥土中弥漫着青草的幽香。但最令《魔术师》不同凡响之处在于,托宾通过书写托马斯·曼邀请我们去思考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如果写作的源泉与根芽是一个作家周遭世界里身边的人,甚至于压根就是他自己的话,那么托宾又为何要去书写托马斯·曼呢?
在当代文学的光谱中,虚构与真实的国界线逐渐溶化,形成了一块暧昧而模糊的地带。塞巴尔德利用来自于现实世界的照片为他建构的陆离的世界做注脚,赫塔·米勒的《心兽》携带着显而易见的自传色彩;进入21世纪后最负盛名的两个作家埃莱娜·费兰特与克瑙斯高,前者虽然刻意隐退至大众视线之外,但那不勒斯四部曲不断让万千读者们猜测这究竟是不是源自小说家本人的经历,而她的不露面容某种程度上更加强了这种揣度;后者继承了普鲁斯特的衣钵,《我的奋斗》以六部曲的煌煌巨作之姿态向我们展露着某种残酷的直白与坦诚,自传与小说的界限被砸个粉碎。在这片奇异的疆域中,托宾的《大师》与他的新作《魔术师》必然不容忽视地占据着一席之地。2004年,托宾创作了他迄今为止最动人的作品《大师》,以虚构的小说形式讲述了真实的作家亨利·詹姆斯1895至1899年的人生片段。17年后,托宾怀着莫大的勇气,以及与这勇气等量的野心,选择了同类型,但以另一个文学巨擘托马斯·曼为主角的传记小说,向他的最高峰发起了毅然而决绝的冲击。
有些惊喜又有点些微的失望,同《大师》相似,徐缓的叙事、克制的语调让我们的阅读仿若行踏在松软温润而令人舒适的泥土中——这泥土中弥漫着青草的幽香。虽然两本小说都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但托宾依然以高超的笔法深入两位文坛大师的内心世界,读者几乎是趴在他们的胸前聆听他们心跳的起伏变化。但与此并行的是,我们又明确无误地可以意识到这种贴近完全是作者的蓄意为之,这孕育出了一个有些诡异的悖论——我们越是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就越能了解他们的虚构成分。本质上,亨利·詹姆斯和托马斯·曼不是历史的人物,而是托宾的人物。同时,在这两本小说中,托宾都缝制出了一种绝妙的效果,他的主角虽然身负盛名,但描述他们传统意义上的缺点多于优点,我们明晰地洞察他们的懦弱、伪装以及身为作家的自私,尤其是他们在那个时代隐晦而不可告人的情欲。但托宾将这些与一种温柔的目光注视融汇在一起,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既不抱有过度饱和的同情,但也不会带上道德批判的墨镜,部分源于托宾塑造人物形象的细致、丰满与立体,而他的塑造方式是优雅而隐淡的,不推进磅礴而情绪化的排比,不插入灿烂如光华般的比喻,一切都在润物细无声中隐晦地行进——譬如,我们会发现托马斯·曼极少向我们投掷出格言式的句子,格言是一瞬间的爆破,格言震动着读者的心灵感受,但有时又会变成让人物的真实性消弭的危险暗流,托宾迂回地让他的妻子卡提娅去说出这些精妙通透的格言,通常在一段对话戏中最后一句吐出妙语的都是卡提娅。
《大师》中有一个极其值得玩味的暧昧之处,亨利·詹姆斯拥有着双重身份,既是观察者,同时也是被观察者,他在观察着别人的同时总是会发觉对方或者第三者也在观察着他,视点的摆锤在钟摆的垂线两端来回摇晃,人物的双重身份也与这本书读者的双重身份啮合,这是一抹细微的美妙,我们透过亨利·詹姆斯的眼睛观察书中的人物,同时又透过作者的视角审视亨利·詹姆斯。但《魔术师》中这样的双重身份的精微被缩减。而对比《大师》,托宾仅仅对焦在亨利·詹姆斯的四年时光同时又掺杂大量对过往的回溯,《魔术师》的时间的容量被大幅度拉长,闪回的技法几近绝迹,反而是在小说的前半段偶尔掠过一种预叙的闪光,其内容通常是现在的行为与话语将会在未来的时刻被咀嚼与回味。《魔术师》体现了托宾的某种转变,他在其中追求着更为宏大的命题,小说的语调静水流深但构架却是气势磅礴,他意图展现托马斯·曼是如何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托马斯·曼所经历的时代是世界最为混乱的时代,一战、二战、冷战接踵而至,他不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带有预言性色彩的作家(希利斯·米勒在《共同体的焚毁》中提出卡夫卡窥探到了集中营的出现),无论是战争或者纳粹,他都缺乏敏锐的先见之明,而是迟钝地抱着鸵鸟式的自欺欺人;他也不是奥威尔式带有批判性的战士作家,他带着虚弱的谨慎,在纳粹掌权之初努力避免着激进的发言,而在美国又因为政治原因不断地妥协。本质上在精神意志方面他是个普通人,只是被裹挟着一步步前进。他同样也是个属于旧世界的人,他眷恋着过去的年代,对新世界不满地评头论足。有些讽刺的是,托马斯·曼某种意义上其实变成了当年自己最讨厌的人,他的原生家庭与后来创造的家庭互为镜像,他对应着受人尊重的父亲,他的妻子对应着他富有生命力的母亲,而他的孩子则对应的是当年反抗父权专制的他本人,历史仿若轮回,就像战争的往复循环一样——历史与家族互为对照,正如小说中所述“德国分裂了,正如曼家兄弟也分裂了”。对于那个一直沉浸在旧世界的托马斯·曼而言,他是现实中的流亡者,也是精神上的流亡者。
自罗兰·巴特以降,作品与作者之前丝线的断裂已然成为了一个常识,作品自其从作者手中完成的一刻伊始,便脱离了作者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有机体,作品的诞生预示着“作者之死”,作品不再被视为作者的自我投射。托宾大胆而激进地站到了这个传统的对立面,与诸多描述真实存在作家的小说如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契诃夫的一生》和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的殊异之处在于,托宾近乎彻底摒弃了通过作者介入或人物之口对文本特征进行分析与阐述,托宾不断强调的是小说源自现实世界的叶脉,小说重心是托马斯·曼如何将现实世界拆分、重组、扭曲、幻化成小说朦胧的虚影,他不断沉溺于自己由现实世界吸收的素材所连锁产生的想象。不仅仅涉及小说与作者,托宾同样意图挑衅的还有小说与读者关系的地基,他从故旧的废纸篓中重新拾起了“理想读者”这个泛黄的古老概念,小说中,托马斯·曼对于跟随自己的作品一部部出世所匹配的受众的判断有着不断下滑的趋势,从一开始的广泛的大众不断收窄缩化,到之后他认为他的新作品只有卡提娅一人才能体会到其中蕴藏的真义,再后来他又自我想像出了一种理想的读者——“秘密的德国人,内心的流亡者,或者是未来的德国人,生活在一个从灰烬中重生的国家里”。直至他在人生结尾处创作的小说《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他觉得“无人猜得到他与菲利斯克·克鲁尔是多么气息相通”,最终通过读者,托宾指向了作家所必然面临的终极孤独——在文学的路径上,他依然是一个流亡者。
但《魔术师》不同凡响之处在于,托宾通过书写托马斯·曼邀请我们去思考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如果写作的源泉与根芽是一个作家周遭世界里身边的人甚至于压根就是他自己的话,那么托宾又为何要去书写托马斯·曼呢?托宾先是悄然退居到幕后,又以这样引人深思的方式杀回前台。作者渴望我们去了解他。小说最终止步在托马斯·曼的行就就木的晚年,而在现实中,托宾已经罹患了癌症,这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也意味着写作生命的终结,而《魔术师》或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之书,他是怀着极度浓烈的饥渴来书写这部已经曾经被他推迟了十多年的传记小说。这解释了小说为何在时间上彰显了一种史诗般的长度,又为何停留于生命即将枯萎的时刻。曾经托宾被问到是何种原因要选择书写托马斯·曼,他提到了亨利·詹姆斯,并声称“我没有第三个人选了”,他形容他们“像某些房间里的幽灵”,黏附在他们的身上,托宾本人也成为了小说暗影里的幽灵。《魔术师》是幽灵性的现实主义,尤其在托曼斯·曼的晚年,他死亡的大部分至亲变成了“不在场的在场”,他总是在想象一件事,如果他的亲人倘若还在世应该怎么看待,假如某人还活着的句式反反复复地磷火般飘荡着。小说的最后几章如此令人感动,托宾对人生的思考与托马斯·曼水乳交融,“人类是不可信任的,只要风向一转,他们的故事就会跟着转,他们的人生是一种持续的、渐衰的、滑稽的、让自身看似可信的努力。他觉得,人类纯粹的创造力就在其中,一切悲哀也在其中。”这个形容也同样适切于《魔术师》,这本书被那么炽热地创造、又蕴含了那么深沉的悲哀。在《大师》与《魔术师》中都有一个关于小说作用的隐含的主题——文学可以打捞那些如同沉船般被淹没与失去的亡灵,这是独属于作家的秘制魔术。《魔术师》奇迹般拯救了消逝的托马斯·曼,也同样拯救了即将消逝且必然消逝的科尔姆·托宾。
科尔姆·托宾致读者的信
亲爱的读者:
我在1996年为三部托马斯·曼的传记写了评论。我了解他的作品,但在读这些传记以及曼的日记之前,我对他的个人生活知之甚少。我发现他一直在思考一种他得不到的生活。托马斯·曼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最有名望的德国人,也是六个孩子的父亲。1912年《死于威尼斯》出版时,没有人想到它来自真实的欲望和真实的事件,那发生在前一年他和妻子的威尼斯之行时。
后来我读了曼的妻子卡提娅所写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是一个对丈夫了如指掌的人。她回忆了1911年旅居威尼斯期间,曼对酒店中一个客人的痴迷之情,她明确写道,她的丈夫“把他从这个迷人的男孩身上得来的愉悦感,转移给了阿申巴赫(小说主人公),并将之风格化为强烈的情感”。
正如曼把他的生活运用到小说中,我也把我所了解的威尼斯的地点运用到我笔下的曼夫妇之旅中。我把他们放在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中,观赏提香的《圣母升天图》,然后带他们去斯拉夫的圣乔治会堂,那里挂着卡尔帕乔的画。我让曼站在我站过的空间里。我用切实的回忆来支撑写作。
1911年托马斯和卡提娅行走于威尼斯时,不可能预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希特勒的崛起、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于威尼斯》似乎对未来一无所知,但字里行间我们能听到一种病弱而优美的音乐、一种渴望感、一种腐朽的气息,以及南北欧之间的鸿沟。这些要素都将在后来的悲剧中发挥作用,在这场悲剧中,世界以托马斯和卡提娅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