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为何用儿子之名命名他最负盛名的剧作?
1596年的一个夏日,住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的小姑娘朱迪丝发烧卧床,双胞胎哥哥哈姆奈特到处找人帮忙,却一无所获。他们的母亲在一英里外的地方侍弄药草和蜂巢,父亲远在伦敦;夫妻二人谁都不曾想到将有一子活不过本周……大约四年后,他们的父亲写出史上最伟大的悲剧《哈姆莱特》。
《哈姆奈特》是英国小说家玛姬·欧法洛的长篇历史小说,以莎翁之子哈姆奈特为原型创作,聚焦这个鲜为人知的男孩和始终神秘的莎翁一家。小说出版后,获女性小说奖、英国图书奖年度小说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爱尔兰多基文学奖年度小说奖等文学奖项。
在欧法洛笔下,伟大的的作家莎士比亚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是一辈子活在丧子之痛里的活生生的人,他选择离经叛道的婚姻,为寻觅生活的方向而苦闷,也自有办法让挚爱的孩子被后世口口传诵其名、拥有不朽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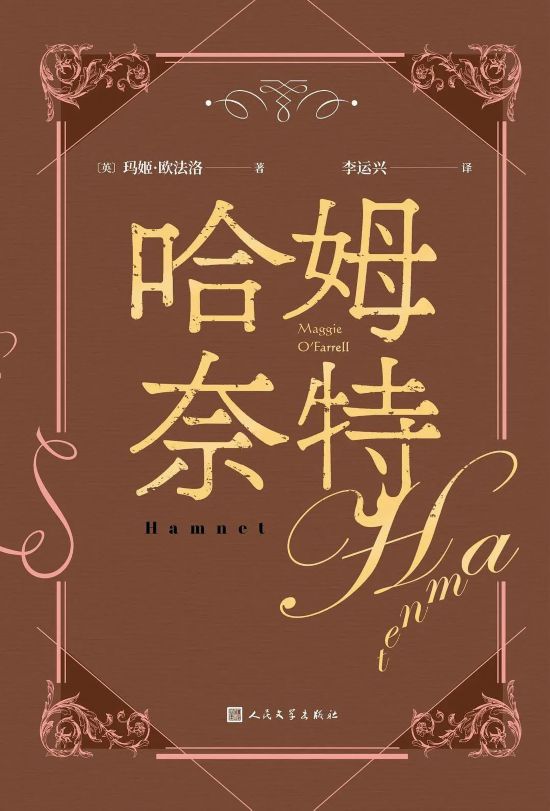
《哈姆奈特》作者:[英]玛姬·欧法洛 译者:李运兴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小说作品,创作灵感来自于1596年夏在沃里克郡斯特拉特福镇夭折的一个小男孩的短暂人生。我尽可能忠实于真实生活中哈姆奈特及其家庭的有限史料,但对一些细节——特别是人名——做了某些改动或替换。
许多人知道男孩的母亲叫“安妮”,但她在父亲理查德·海瑟薇的遗嘱里是被称为“艾格尼丝”的,我据此决定使用这个名字。有人认为琼·海瑟薇是艾格尼丝的母亲,其他一些人认为只是继母,支持和否定任何一种观点的证据均显不足。
哈姆奈特唯一一位存活下来的姑姑并不叫小说中的名字伊莱扎,而是叫琼(与先于这个姑姑去世的大姐同名);我冒昧地做此改动,是为了避免小说读者弄混,尽管在当时的教区档案中使用重名是司空见惯的。
玛姬·欧法洛
莎士比亚出生地基金会的导游曾告诉我,哈姆奈特、朱迪丝和苏珊娜是在亨利大街祖父母的房子里长大的;而其他人却很有把握地说,孩子们住的是相邻的一座较小的房子。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两座房子应该是紧紧相邻的,我在小说里采用了后一种说法。
最后,哈姆奈特·莎士比亚究竟因何而死,我们不得而知:他的葬礼史料有所记载,但没提及死因。黑死病,或按十六世纪晚期说法叫“瘟疫”,莎士比亚在任何一部剧或任何一首诗中都没提到过。为什么从未提及,这其中又可能有何深意,对此,我一直有所思考;这部小说是我个人遐思迩想的成果。
史料
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一对夫妇曾生活在斯特拉特福镇的亨利大街上。他们有三个孩子:长女苏珊娜以及双胞兄妹哈姆奈特和朱迪丝。哈姆奈特死于1596年,时年十一岁。大约四年后,他的父亲创作出悲剧《哈姆莱特》。
哈姆奈特和哈姆莱特实际上是同一个名字,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斯特拉特福镇地方志中是完全可以互换的。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哈姆奈特之死与〈哈姆莱特〉之生》
节选
男孩走下一段楼梯。
楼梯过道很窄,还向后折回。他一步步沿着板壁慢慢走下来,靴子踩在阶梯上发出咚咚的声响。
快到楼梯口了,他停了停,回头看看来路,然后一定神,习惯性地大步跳下最后三级台阶。落地时一个踉跄,跪在了石板地上。
这是夏末一个闷热无风的日子,楼下的房间被一道道长长的光线分割着。阳光照在他身上,嵌在墙壁里的花格窗被阳光染成一个个金黄的小格子。
他站起身,揉揉腿,朝楼梯上看看,又看看前面,不知往哪边走才好。
房间空空的,壁炉里的火慢慢烧着,橘红色的火苗暖暖的,冒出一圈圈青烟。他受伤的膝盖随着心跳一阵阵地刺痛。他站在那儿,一只手扶着通向楼梯的门闩。脚上磨秃了皮头的靴子,一只已经抬了起来,准备要起飞的样子。那遮在前额上差不多是金黄色的浅色柔发,一绺绺地向上扬起。
一个人也没有。
今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哈姆奈特》改编为舞台剧,
图为演出剧照,下同
他叹口气,吸了一口暖乎乎又充满灰尘的空气,穿过房间,出了前门,来到街上。外面,手推车、马匹、小贩,一片嘈杂,人们互相喊叫着,一个人从上面一层的窗口嗖地扔下一个袋子,不过这些哈姆奈特都没理会。他沿着房子的前脸一直走到相邻的大房子的门口。
他祖父母家一向是这种气味,有烧木头的烟气,还有上光剂、皮革、羊毛的混合味道。比起毗邻的他与母亲及姐妹们居住的两室住宅(那是祖父在大房子旁边一块狭长的空地上盖起来的),既相似,又有着说不出的不同。有时候,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这两所房子毕竟只是一篱笆墙之隔,但两处的空气可是截然不同,不同的气味,不同的温度。
房子里小风呼呼吹着,打着旋,祖父的作坊里又敲又打,叮叮咚咚,售货窗口上顾客们敲着窗玻璃,叫唤着,后院里也是嘈嘈杂杂,一堆堆的杂物,几个叔叔你来我往忙个不停。
不过,今天可不是这样。男孩站在过道里,真想听到点人们活动的声响。但他看到,右边的作坊是空的,工作台前的凳子上没人,台子上的工具静静地躺着,托盘上放着丢弃的手套,像按的手印似的,一目了然。售货窗口锁得紧紧的。左边饭堂里空空如也。长桌上放着一沓餐巾,一支没点着的蜡烛,一堆羽毛。别的就没什么了。
他喊了一声,是问候,也是发问。一声,两声,他叫着。然后他仰起头,听有没有人回答。
没有。只有一条条横梁在太阳下晒得发胀,吱吱作响;风在门底下、房屋间叹着气,亚麻布帘被刮得沙沙响,壁炉里火烧得毕毕剥剥;是空荡荡的大房子里那种说不出来的嘈杂之声。
他的手指紧紧抓在铁制的门把手上。白日的热气,尽管时间已晚,还是叫他额头、后颈都是汗。双膝的疼痛再次袭来,一阵阵的,然后又消失了。
男孩张开嘴,呼叫着一个个的名字,所有住在这里的人他都喊。祖母。女佣。叔叔。阿姨。学徒。还有祖父。他一个个地呼唤着。有那么一瞬间,他真想叫父亲的名字,呼唤他,可是父亲是在百英里之外的伦敦啊,要走几天几小时呢,他还从来没去过。
但是,他确实想知道母亲、姐姐、祖母和叔叔都去哪儿了。女佣呢?祖父呢?那老人家白天是从不离开的,常常见他待在作坊里,要么吆喝着徒弟们干活,要么就是埋头在账本里算计着赚了多少。人都去哪儿了?怎么两座房子都空无一人?
他沿着过道走着。在作坊门口,他停住了。他回头扫了一眼,确信没人,这才走进去。
祖父的手套作坊,一般不让他进去,连在门口站一下都不行。祖父会大吼,别没事在那杵着。人家在这踏踏实实干活,就非得来个人傻乎乎地盯着看吗?闲得没事干,在那儿抓苍蝇哪?
哈姆奈特脑子快:老师讲的他一听就懂。教什么都能心领神会,过目不忘。动词、语法、时态、修辞,加上数字和计算,样样记得清、不费力,有时还真惹得其他男孩嫉妒不已。不过,这个小脑瓜也挺容易走神。正上着希腊语课,一辆马车从街上走过,他的心立马就会被吸引出去,琢磨着这车是往哪儿去,拉的什么货,还想起叔叔曾让他和姐姐、妹妹坐在拉干草的车上,那可是太爽了,刚切过的干草闻着挺香,摸着扎手,疲惫不堪的母马蹄声嗒嗒,车轮随之有节奏地向前滚动。这几周,就是因为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不止两次挨了老师的鞭子。(他祖母说了,下不为例,只要再犯,就一定告诉他父亲。)老师们搞不懂是为什么,哈姆奈特学得很快,能记善背,就是心思不集中。
天上有鸟叫,哪怕是正说着话,他也会戛然而止,就好像老天爷一下子把他打成了哑巴。有人走进来,哪怕只是用眼角瞥见,他也会立即停止正在做的事情,不管是在吃饭、看书,还是抄写作业,然后死盯着人家看,好像那人独独给他带来了什么重要消息似的。他有一种倾向:思绪总是溜出身边有形的现实世界,进入另一个天地。人坐在屋子里,可心早到了别处,成了另一个人,待在一个只有他自己才了解的地方。醒醒啊,孩子!他祖母这么叫着,向他打着响指。又走神啦,姐姐苏珊娜向他发出嘘声,用手弹他耳朵。集中精力,老师们高声叫道。你上哪儿去啦?妹妹朱迪丝悄声问他。此时,哈姆奈特已回到现实世界,心神收回来了,他环顾四周,知道已经回来了,在自己的房子里,坐在自家桌前,周围是自己的亲人。母亲上下打量着他,似笑非笑,就像知道他刚才去过什么地方似的。
现在,情况有些类似。走进手套作坊这块禁地,哈姆奈特记不得是来干什么的了。他又暂时脱离了现实,忘了是朱迪丝不舒服,得找个人关照一下,而他就是来找母亲、祖母或其他什么人,看看该怎么办的。
一个架子上挂着各种兽皮。哈姆奈特可知道不少,认得出那锈红色带斑点的是鹿皮,又嫩又软的是小山羊皮,松鼠皮要小一点,而野猪皮则又粗又硬。当他走近的时候,这一张张兽皮开始在架子上唰唰地抖动起来,就好像还残留着某种生命力,就那么一点点,但足以让它们听见他的脚步声。哈姆奈特伸出一个指头,触了触山羊皮,怎么那么柔软,就像夏天在河里游泳水草滑在腿上。山羊皮轻轻摆动着,四腿分开,展得平平的,要飞起来,像鸟,像传说中的食尸鬼。
哈姆奈特转过身,看着工作台边的两个座位:一个有皮垫,已被祖父的马裤磨得发亮,另一个硬硬的木凳是徒弟内德的。工作台上方墙壁的钩子上挂着各式工具。他能分得出哪些是切割或拉伸用的,哪些又是用来固定和缝合的。他看到有个稍小一些的手套撑子——用来做女式手套的——没放回钩子上,而是丢在了内德的工作台上。这个小学徒,干起活来低着头,弓着肩,十个手指又灵巧又麻利。哈姆奈特知道,他祖父对徒弟可是沾火就着,大呼大叫,有时还更过分。于是他拿起那个撑子,掂了掂,暖乎乎、沉甸甸的,顺手把它挂回钩子上。
他正要拉开装着线团和一盒盒扣子的抽屉——轻轻地,轻轻地,因为他知道会吱吱响,这时一种什么东西被人拉动或摩擦的细小声音,传进他耳朵。
眨眼间,哈姆奈特就穿过过道冲到院子里。他又记起他来这儿的目的了。可现在自己在干些什么呢?在作坊里闲逛吗?妹妹不舒服,他是来找人帮忙的。
他一间一间砰砰地推开房门,厨房、酿酒间、洗衣房。都是空的,屋内又黑又凉。他又呼叫起来,这回有点哑,嗓子都喊破了。他靠在厨房墙上,朝着一个什么果壳就是一脚,那东西咕噜咕噜滚到院子那头。怎么就他一个人,他完全搞不懂。应该有人在呀。这儿总是有人的。现在都去哪儿了?怎么办?怎么都出去了?怎么母亲和祖母也不在,照往常应该正拉开灶门在火上炒菜呢。他站在院子里,四下张望,看看通向过道的门,又看看去酿酒间的门,去他自己住房的门。应该去哪里?叫谁帮忙?人呢?
每个生命都有其核心、中心,或聚焦点,万端由此发出,又复归于此。此时此刻属于那个不在场的母亲:男孩,空荡荡的房子,还有寂静无人的院子,没人应答的呼唤声。他站在这里,站在房子的后边,呼叫着他的亲人——那些人曾给他喂饭,把他抱在襁褓里,摇他入睡,手把手教他学步,教他用勺子,喝汤时为他吹凉,过马路时牵着他的手,告诉他别去惹睡着的狗,喝水前把杯子涮干净,还告诫他远离深水。
这一刻将成为这位母亲生命的核心,终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