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郭宝昌执导的《大宅门》,是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
编者按:
10月11日,传奇导演郭宝昌在北京离世,享年83岁。
2001年4月,郭宝昌执导的《大宅门》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首播。此后几度重播,是无数观众心中的国剧经典。
郭宝昌以自己26年宅门生涯写就的《大宅门》,沧桑过同仁堂的荣辱兴衰,剧中90%的情节均有据可查,然而作品同他本人一样命运多舛,四写四毁,却依然在风雨飘摇中顽强生长,直至成为传世之作。
郭宝昌在艺术领域是公认的“有豪气、有面子”,第五代导演集体称他“宝爷”,被他提携的后辈中就有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的名字。在广西电影制片厂任职时,郭宝昌扶植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推出《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作品,奠定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基础。张艺谋曾说:“没有郭宝昌,就没有中国第五代导演”。
我们特转载李陀为长篇小说《大宅门》所作序言(节选),以表怀念。

郭宝昌导演
悲剧小说的诞生(节选)
——长篇小说《大宅门》序言
□李 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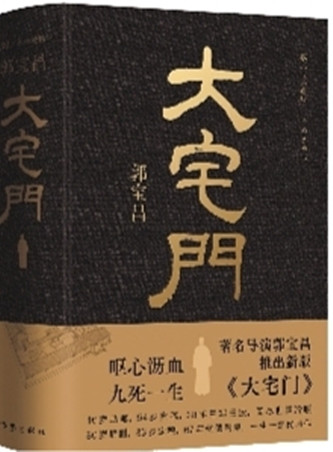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先后推出的两版《大宅门》(上图:2001年3月出版,下图:2023年10月出版)
1 我一直在等待一本小说,里面的人物一个个向我走来,我不但能听得见他们的哭笑和叫喊,看得见他们眼神里的烦恼和得意,而且个个愿意和我诉说自己内心的幽思,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美好的还是黑暗的,就像他们是我一墙之隔的邻居,狎昵的密友,甚至似乎是我熟悉的家人——这些人于是不再是小说的“文学人物”,而是我生活圈子里的“真人”。
现在它来了,郭宝昌的长篇小说《大宅门》。
2 先说它的人物。
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有一个很不平常的特点:其中每一个人物都是悲剧人物。在作家用文字织就的画廊——一个最典型、最有老北京特色的老宅子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上上下下,一百三四十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悲剧色彩浓烈的悲剧形象。不必说白景琦、二奶奶白文氏、杨九红这些主要人物,即使是其中的几个小丑式的喜剧人物,其灵魂里难以平息的乖戾和贪婪,一生中屡败屡斗的恶行,也无不带有悲剧因素。一百多个悲剧形象,使得小说从整体上有一种强烈的、只有舞台演出才能有的戏剧感,悲剧要素弥漫和渗透在作品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里。可以说,小说和戏剧这两种不同的写作,竟然奇迹一样在《大宅门》中共存,作品由此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悲剧品格和美学特征。
3 ……
琢磨郭宝昌的写作,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的成长历史中有一些其他作家所没有的特点,一是他对传统戏剧尤其是京剧艺术的热爱和熟悉,再就是他对视觉形式特别是电影艺术的热爱和熟悉。说“熟悉和热爱”,其实不很准确,因为他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两种艺术门类里的大行家,而且在这两个领域中都做过非常先锋的实验,一个是用京剧大师程砚秋的同名剧作做题材,另起炉灶拍摄的戏曲电影《春闺梦》,另一个是京剧版的《大宅门》。两部作品一个是电影,一个是京剧,一个是影像的想象空间,一个是戏剧表演的舞台空间,但它们的制作都充满了极具先锋特色的实验性,这在《春闺梦》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里要提醒一下,这部电影的创作时间是2004年,这时上世纪80年代曾经火光冲天的“先锋热”,早已灰飞烟灭。因此,郭宝昌不仅是京剧和电影这两种艺术的行家,还是个勇敢的实验家,当他拿起笔写小说的时候,它们不可能不对作家产生深刻的影响。
4 结果就是小说中出现了另一个路数的写作。
当我写下这个断语的时候,是有些犹豫的。另一个路数,那是什么路数?它真够得上是“另一路”?作为一个以小说批评为职业的人,我明白做这种论断是冒险的。但我愿意冒这个险,试一试。
……
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汉语解放了中国人的小说写作。文字语言对现实世界物质性的表现,一下子获得了无比丰富的可能性,准确一点说,就是新白话小说获得了一种新的语言肌理,使得文字能够以足够的质感来具体形容、描摹人和物,让现实世界在语言世界中获得可以“触摸”的物质性。小说叙述由此获得了旧小说、章回小说所不具有的新的统一性,一种建立在新的语言肌理上的统一性。怎么讲故事?怎么刻画人物?怎么结构一个长篇的叙述?作家对现实的认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一切都显示了现代汉语由此成为新文学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且让文学整体跨入了一个新时代。
但这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如新小说的写作,不知不觉就与章回体的旧小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传统章回体小说,毫无例外都是以人物塑造为最高的美学追求,而其刻画人物的基本手段——对话,也是小说得以结构组织起来的中枢和关键。新白话小说中极为重要的语言肌理的质感,对传统小说的写作而言,就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如《红楼梦》第49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里,雪的描写可以说至关重要,可是曹雪芹怎么写的?是说宝玉出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拂鼻。回头一看,恰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读这段雪景,读者会感受到十足的诗意,但它明显缺少对一场大雪有质感的细致描绘,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本来是绝对必需的。可是这种匮乏,对人物刻画和叙事可有半点损伤吗?丝毫没有。不仅是《红楼梦》,传统章回小说都是如此。这就提出了一个对当代写作而言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还可不可以像曹雪芹那样写小说?换句话说,在现代汉语的语言环境里,作家还能不能继承并发展传统古典小说那样的写作?
现在回到郭宝昌的写作上来。读者是不是觉得,他的写作和我们古典小说,有很明显的继承关系?是不是觉得,这个长篇在结构上、叙事上、人物刻画的手法上,和传统的章回小说有种种暗合之处?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当然不是。
只要换一种眼光看这部长篇,很容易能看出,《大宅门》中叙事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对话。是小说中连绵不断的独立和半独立的对话,形成了人物外在行为和内心活动的动力,使得人物个个都“活”了起来。不过,设想一下,如果今天对一位作家建议,完全用对话——也就是基本不依赖白话文提供的几乎是无限多的语言方便——来写一个长篇小说,会如何?我想他或她一定很为难,同时立刻会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有必要吗?现在,郭宝昌的《大宅门》摆在了这里,它是一个很结实的证明:在今天,作家激活中国古典小说以对话来主导叙事的写作传统,原来是完全可能的。
5 一部作品,作家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具有悲剧色彩,特别是其人生最后都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悲凉结局,使得整部作品都笼罩在一种悲剧气氛之中,这在现代小说里固然不多见,可还是有。但像《大宅门》一样,几十万字的作品,一百几十个人物,不但每个人物都是悲剧人物,而且从白颖园、白景琦、二奶奶、杨九红这些主要人物到白玉婷、武贝勒、王喜光、槐花,以及詹王府里的上上下下等次要人物和小人物,个个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大大小小的悲剧冲突之中,这就罕见了。从结构角度来看,《大宅门》其实是由大小几十个悲剧建构起来的,只不过这些悲剧被组织得井然有序:有重要线索,有次要线索,有时两条主要线索并行发展,有时几条线索多头并进。其中有的人世界很大,大到联系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有不少人的世界很小很小,小得那么可怜,可同样走向毁灭。回顾长篇小说史,这样的小说形态实在不多见。
《大宅门》的悲剧形态,不仅来自其主题和内容,而且还来自形式。《大宅门》是多重大小悲剧的集合,但它的叙述仍然是严格的小说叙述,这还要从小说对话这个关节说起。设想一下,如果郭宝昌在小说中,不是如传统的章回小说那样,给予对话一个主导叙事的绝对位置,让对话上升为结构小说的主要机制和框架,借以生成事件和行动,他能够在《大宅门》里装置、组织如此复杂的戏剧冲突吗?此外,让对话和小说叙事的关系产生这样重大的改变,我认为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充分重视白话文运动为现代汉语提供的口语属性这一异常宝贵的财富,并且以这种口语属性作媒介,对对话的美学功能做一番必要的改造。《大宅门》正是做了这个改造。郭宝昌的写作,一方面,让人物对话不但与现代人日常的生活用语密切融合,而且与故事里的日常生活密切融合,另一方面,还最大限度地让对话向戏剧形式靠拢,让每一个对话单元都具有类似舞台戏剧对话那样的精练和密度。不能只把它看作是某种叙述形式上的新尝试、新探索,而是要把它上升到理论层面,看作是当代写作对现代汉语环境下的小说叙事实行的一次改造,一次看来是“倒退”式的改造。不过,这里说“倒退”,不仅是因为它唤醒了人们对章回小说的记忆,还因为在现代小说史的视野里,如此处理对话和叙事关系的写作少而又少;顺便也是强调,需要“倒退”的时候,作家要有勇气倒退。
6 关于《大宅门》的写作,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由于郭宝昌熟悉影视和戏剧的创作,在这两个领域都有丰富的实践,因此,他的文学想象也具有跨界的特征。读他的小说,与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有很大差别:小说的很多章节都类似一场一场的“戏”,其中不少章节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我们愿意,把它们略加改动,就能成为舞台话剧某一幕中的一场完整的戏;或者独立小说中的某一条冲突线索,改写为一个完整的舞台剧。《大宅门》的叙述结构和对话的这种紧密关系,让我们可以猜想,作家在拿起笔写作的时候,他的激情和构思,一定都是跟着“话”走的,不过这些“话”,不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现当代小说里各种各样的“话”,例如细致的环境描写、心理活动的暴露和侦问、叙述人的议论和忍不住的抒情,以及多角度的叙述、间接引语的各种运用,等等,而是连绵不断的对话,以及由对话带动的事件和行动,只不过它们是同时具有现实生活日常性和舞台戏剧性双重品格的对话。对于许多作家来说,以这种有“双重品格”的对话来贯穿和控制小说叙事,是有很大难度的,但郭宝昌由于在跨界上有特殊优势,如此跟着“话”走,反而造就了一种尽可能消除或抑制欧化倾向的、向着章回体回归的写作路数。此外还要说明,这种叙事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依赖的媒介虽然是文字,却有很强的视觉性,使读者在阅读中可以“看见”。我甚至好奇,如果让郭宝昌回顾并且分析自己的创作过程,在他心里涌现的,到底是文字还是影像?他是不是能说得清?
7 《大宅门》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悲剧形态。
过去我们在严格意义上讲悲剧,大多数都是说戏剧,不过20世纪之后情形有变化,批评家开始讨论小说中的悲剧写作,认为悲剧不一定是戏剧形式所专有的美学属性。以这样眼光看《大宅门》,这部小说正是一部悲剧小说。小说中的悲剧人物,以及他们命运中的福祸凶吉,都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的指向,那就是他们和以白家大院为代表的旧时代/旧中国必然死亡的历史命运有着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时代的衰亡不是小说中故事的背景,也不是故事里经受各种各样精神折磨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大宅门故事的悲剧性,在于其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这个时代趋向死亡的细节,就像一棵正在枯死的老树,无论其中的人上人,还是人下人,无论是树干还是细枝,整体都在死亡。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大宅门》的写作是一种带有古典品质的悲剧小说的写作。不过这里有一些问题需要展开:悲剧小说是一种新出现的写作吗?西人对悲剧和悲剧性的概念有过不同定义和解释,或与古希腊英雄的命运乖蹇相关,以英雄悲剧激发怜悯和恐惧的情感,净化人的心灵,或从人本主义出发,强调个人价值和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不管怎样分歧,这些解释基本都以接受或者衔接古典戏剧美学理论作为基础,然后反过来对相关概念进行某种突破。无论如何,假如悲剧小说是个新东西,且由于小说和戏剧分属不同的媒介,那么我们在美学上或写作实践上,是不是需要重新辨别它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另起炉灶,对悲剧小说的悲剧性概念进行重新阐述?《大宅门》中的人物虽然都是普通人,既不负有改造时代的大使命,也不为琢磨人生价值的哲学意义而苦恼万分,可如前所述,他们每个人的悲剧命运,不仅是旧时代死亡的一部分,同时还是自我毁灭的动力。如此,这是什么悲剧?不是值得好好想一想吗?
8 讨论《大宅门》的悲剧形态,可以从很多方面入手。
这个长篇小说的“原型”,是北京乐家老药铺。它不仅是一个“药铺”,而且是一个有着数百年沉浮历史的大家族。郭宝昌依照自己的构思对这素材做了裁量,把推动悲剧发展的主要因果线索,集中于家族内部伦理关系的恩恩怨怨,以及其中人物的命运沉浮上。在旧中国瓦解的大历史中,家庭秩序的瓦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也往往是斗争最激烈的领域。在现代文学史里,书写这种瓦解是一个老主题,自晚清特别是五四以来形成了很大潮流,是五四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时期以后,这类写作虽然相对数量不多,其中有些作品却表现了某种乡愁式的怀旧情结,甚至于一些以乡土农村为题材的作品,其主题恰恰是对以旧道德伦理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怀念和招魂。
郭宝昌的小说,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写作。
白家大家庭里的一百几十口人,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家外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高贵人还是卑贱人,都卷入了一场持续不断、激烈冷酷的事关捍卫家族伦理秩序的冲突之中,而且个个身不由己,都在这冲突中争当卫道者。这是一场混战,但其复杂的背后却有情理可寻。以二奶奶白文氏和七爷白景琦来说,他们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坏人”,可也绝不是“好人”,郭宝昌成功描绘了两个性格十分复杂的文学形象。古往今来,以大时代变迁中社会道德思想和伦理制度变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少,尤其是五四时期和上世纪30年代的作家,创作了很多印证这种时代大变迁的文学形象,郭宝昌所创造的这两个人物,无论其形象所承载的历史内涵,还是艺术刻画上的复杂丰富,都是对这一传统的承接和发展。
《大宅门》的另一个不能忽略的成就,是对以杨九红为代表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一部小说里有这么多的女性形象,而且在作家笔下色调斑斓的画廊里,几乎每个人都善良、率直、聪慧,这不能不让读者联想到《红楼梦》大观园中的女性,这在当代文学写作里是不多见的。杨九红、白佳莉、白玉婷、黄春、香伶、香秀、槐花,每个人都是不屈于命运的叛逆者,可她们各自选择的反抗方式,每种都带有心理畸形,带着不理智的怨愤,从一开始就注定最后一定会失败。但正是她们的失败,凸显了大宅门这个封建堡垒中性别压迫的深刻,说明如果没有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在父权统治的性别压迫和性别政治所织就的天罗地网里,女性无论怎样进行抗争和反抗,都难以求得尊严。
9 最后,我还想就《大宅门》的语言再说几句。
写老北京,一个很大的困难是怎么处理小说的语言。“北京话”是一种非常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它长时期和国家的“官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中国作家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人认为北京作家比较占便宜,比较容易解决小说写作中的种种困难,其实不然。一个作家如果在语言上足够敏感,有特别的音乐的耳朵,想让自己的写作别求新声,他马上就会发现,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今天的汉语书面语,早已改造而且还在继续改造我们的小说语言,当代文学的书写系统已经建起一道严实的石墙,不太容许掺入方言这种杂质。郭宝昌当然也遇到了这困难,何况他讲的基本是“老北京”的故事,老北京的“北京话”和今天的“北京话”,又很不相同——可偏偏就有人愿意用自己的头去撞这道石墙,而且居然撞开了。《大宅门》里充满了“北京话”,或者“北京味儿”的“话”,它是那么从容自然,就像弥漫在空气里的一种草木的香气,你并不会特别注意,可呼吸在其中,给你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这不容易啊,作家是怎么做到的?那还是请读者去读小说吧。前几年,上海作家金宇澄出版了长篇小说《繁花》,其语言也是非常有创造性地、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一点磕碰痕迹地融入了上海方言元素。读者不妨把这两部小说都看看,其生活,其人物,其语言,正好一北一南,且其情趣大异。
10 一个作家,花一辈子的时间就写了一部小说,这是对文学什么样的忠诚?想到这些,我其实有更多话可以说,可还是暂且打住。
(序言原发于《文艺报》2023年10月9日第5版,转载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