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焦祖尧生命的最后岁月
原标题:生命的最后岁月——忆焦祖尧老师
“何枝可依”
人生总有遗憾,而最痛的遗憾,是晚年特别是最后岁月,不能在安居的家中度过,依然在漂泊途中。曹操在《短歌行》中“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诗句,所以能成为千古名句,就是因它拨动了人们的“思乡”“乡愁”之情。著名作家焦祖尧老师,从2007年到2023年,16年间奔波在北京、太原、常州之间,肩负着他难以卸下的文学使命,寻找着一种安定、理想的生存环境,耗尽了他全部的生命之火。
焦老师是2004年从山西省作协主席的位子上退休的,那年他68岁。早在2001年,省作协分配最后一栋新建的住宅楼,焦老师分到了东单元的三层一号,我分到了三层二号。他是大套,我是小套。我们从上下级关系,成为邻居关系。有了精心装修的新房子、新书斋,有了退休后的大把时间,但焦老师却难得坐下来读书、写作。他回故乡常州在多所大学搞讲座,他到广东东莞采访撰写报告文学《云帆高挂》,还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时他的身体已不如从前,糖尿病、神经衰弱等已逐渐严重。

焦祖尧先生
2007年,焦老师定居香港的大女儿,因工作关系迁移北京,买了房子,动员父亲母亲和两个妹妹,前往居住、“团聚”。古稀之年的焦老师,本可以北京为家,安享天伦,但他心系山西、想着文学,常常来往于北京和太原之间,更多的时间住在太原的新居中。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表现平朔露天煤矿历史与现实的《侏罗纪揭秘》上卷,还创作了描写北魏时期杰出的改革家冯太后的电影剧本《梦回云岗》。两部作品都是大主题、大题材。写作之余,他也会抽时间到忻州、大同走一走,待几天,见见文学作者,谈谈文学创作。也会在下午、晚上,到作协院里的活动室打打麻将,“麻友”都是单位退休的干部、工人;焦老师年龄大,又是老领导,跟大家“混”在一起,如同朋友弟兄。在腾腾的烟雾中,混杂着他的笑声、粗口。
焦老师在山西生活了大半辈子,已然“且认他乡是故乡”,很难离开山西了。在北京暂住可以,长居则不行。记得有一年,他和夫人孔维心还有两个女儿回到太原,通过家政公司前后雇了两次保姆,时间不长都辞掉了。焦老师夫妇并非挑剔之人,特别是焦老师对普通民众有一颗天然的同情之心。但他家人口多、活儿多,而来自农村的保姆不熟悉城市人的生活习惯,焦老师又因糖尿病在饮食上须格外注意。这就自然会发生主雇之间的不适应甚至小矛盾。焦老师曾说:“能雇到合适的保姆,我就不离开太原,太原是我的家。”
但是,焦老师的愿望落空了,不得不另谋他途。他的大女儿看着父亲渐渐老去,身体每况愈下,决心把父亲送回南方常州的养老院去养老。2015年,经过一番考察、试住,最后选定常州市金东方颐养园。焦老师的故乡是常州武进县西歧村,离颐养园距离很近,且还有一些亲戚、熟人。回到熟悉的南方、亲切的故乡,焦老师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这是一个集住、食、行、医、玩为一体的现代化养老中心,就像一个小城市。常州市文联、作协、报社的领导、作者慕名而来,不断跟焦老师访谈、请教。焦老师在颐养园举办了隆重的捐赠作家文集的活动。还回母校淹城初中同文学爱好者座谈交流。《常州日报》多次报道了他的文学活动,譬如记者沈成嵩在一篇题为《焦祖尧的乡愁》中写道:“在塞北工作了60多年的焦祖尧,带着妻儿回到了大运河畔,江南水乡。在风光明媚,莺飞草长的金东方花园落户。他到山西一甲子,但乡音未改,说一口地道的武进乡音。”

2016年在金东方颐养中心捐赠文集
2015年到2019年的四五年间,每到夏天焦老师就会回到太原,他说:“南方的夏天就像蒸笼一样,让人出不上气来。还是太原的夏天好。”有时是他一人回来,有时老孔大姐同行,有时老孔的大哥也来。焦老师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又患了帕金森病,双手震颤,拿笔写字、按动键盘,都很困难,甚至拿不稳筷子。他感叹地说:“没有准备好就老了。”但他依然自己做饭,每天清晨出外散步。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
在住养老院那几年,焦老师还发表了多篇文章,有《奥斯维辛的警钟长鸣》《说自己的话》 《我的国文老师何祖述》 《头发》 等。《山西文学》2020年第10期发表的 《故乡·母亲(外一篇)》是他的封笔之作,他深情地回忆了母亲的一生,刻画了一位善良、坚毅、具有拳拳爱心的母亲形象。他似乎听到了母亲的呼唤:“家来吧,小佬!家来吧,小佬!你离开家的晨光太长了!”我惊讶地发现,八十多岁的焦老师,笔下依然洋溢着细腻、抒情、丰盈的青春气息。
2020年初,新冠疫情开始在全国肆虐。焦老师困在封控严密的常州养老院,他每次打电话总是说:“我还是想回太原,有什么办法可以回去呢……”他身在故乡,却心向山西,熬着看不见头的岁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
师生之交
我与焦老师相处30余年,始终是一种工作关系、师生关系;直到他退休之后,才似乎增加了一种朋友成分。在人生道路上,他于我有知遇之恩。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真正的文学时代。为了从事文学写作,我竟心血来潮从山西大学中文系调回了忻州地区文联。但很快发现,在一个地区对我的研究与写作局限太多,于是想着调到省作家协会。1988年《山西文学》主编冯池老师去忻州参加文学创作会,见到我表达了想调我到编辑部的想法。这时,焦祖尧老师给我所在的《五台山》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对刊物中小说、评论等作品的印象与好评,特别提到我的一篇评论,表示了赞赏。主编杨茂林老师把信件转给我,嘱我给焦老师致信,看是否可把信发在刊物上?于是我给焦老师修书一封,同时谈了想调到省作协的想法。时年七月,收到焦老师的回信,他说:“借调事《山西文学》说过,此事可行,上会研究即定。勿念。”又过数日,收焦老师信说:“你的借调党组会已研究,可即来。”那时,我在省里的文学会议上见过焦老师,但并未说过话、有过交往,他对我的事如此上心,让我感动。当时作协调人,先要“借调”一段,待时机成熟即可办理正式调动手续。于是这年炎热的八月,我到了《山西文学》编辑部,做小说编辑。事后,我请朋友、同事毕星星,领我去住在水西关文联宿舍的焦老师家拜访,竟是两手空空去的。焦老师很真诚地向我们讲述了山西文学当下的形势,希望我们做好编辑工作。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对文学事业的热忱,对年轻编辑的关爱。调回省作协之后,我和焦老师的接触多了起来,有时他会叫我到他办公室,谈谈对当前山西文学的分析、评判;有时会送我他刚出版的小说集,让我提点意见。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信任,总是努力地、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感受、看法,也为他的小说写过几篇短文。1988年冬,山西省作家协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焦老师当选主席又被任命为党组书记。
1992年冬天,省作协党组对《山西文学》编辑部的人事作了调整,成立过渡性的编务组,由我担任组长,祝大同、张小苏担任副组长。我对这一决定感受到不小的压力,去找焦老师,他说:“有党组和我支持你们,一定要干好。”我知道这是党组和焦老师,推动山西文学发展规划中的一部分,没有再说什么。从1992年冬到1999年底,我先组长后主编,主持《山西文学》工作六七年,刊物在继承过去优秀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又积极取法现代主义思想与方法,推进乡村小说的现代转型;努力加强对山西第四代青年作家的扶持,不间断地推出他们的作品合辑、专辑;当时是印刷业变革的时期,刊物率先实现了从铅字排印到激光照排的转变。同时,我和编辑同仁们,接受党组安排的任务,在编辑书刊、办读书会、改稿班中,都尽了自己的责任和努力。焦老师很少表扬人,也不多批评人,但我看得出他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对我是信任的。他很关注我的写作,看了我的评论说:“文学评论还是要写得感性一点,干巴巴的谁看呢?”他鼓励我写点散文,我的散文集《蓝色的音乐》出版时,他欣然写了序言,说:书中“折射出他浓厚的文人心态,洋溢出一种‘淡泊、宁静’的书卷气”。
我常常觉得,我与焦老师有诸多不同。他是典型的南方人,我是地道的北方人。他敏感、好动、好跑,是一个十分感性的人。我迟钝、好静、喜坐,是一个格外理性的人。他喜欢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我则倾向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在人际交往上,我比较淡泊、超脱,追求的是君子之交。跟焦老师相处多年,我竟从未请他吃过一次饭,倒是有朋友请他,他会顺便把我喊上。但他为什么关注和信任我呢?我不大明白。
焦老师退休之后,我们成为邻居。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的交往增加了许多。在他最后的十多年中,他常常一个人回来独居家里,我不时过去看看他,招呼一下。他一个人做饭,我们如果吃粗粮如莜面、豆面之类,春莲就送过去一碗,他还碗时就会带一些食物。如果叫他过来一起吃,他会说:“这手连筷子也拿不住了,不去了。”如果有亲戚、朋友送了鱼虾之类,春莲会做但不想做,我们就送给焦老师,他会做好送过一大半来,他是做鱼的高手。他对我们不喜欢吃海鲜一直很纳闷。2007年开始,他把家门、地下室钥匙交给我,托我为他看家。诸如拿报纸信件、交纳电费水费等,我就一并办一下。还有给花浇水,焦老师喜欢养花特别是君子兰,阳台上除了一两株仙人球、发财树,有六七株君子兰,总是养得很茂盛,但他一走花就让我浇得垂头耷脑。2021年底,焦老师的花大都干枯了,只剩下一株君子兰活着。我给焦老师打电话,他说:“枯就枯了吧,这疫情闹得人活得也艰难,你把那株好的端到你家吧。”现在,焦老师那株君子兰,还在我家的阳台上,虽然老了但叶子依然油绿、坚挺。

在农村地头采访农民
散漫聊天
焦老师入住常州养老院,夏天回太原过“暑假”,要住近两个月时间。他不再有精力、兴致往下面跑,也不怎么在院子里跟“麻友”们打麻将了。他就在家里看看书报、上上电脑,或写点文章。常常是下午三四点钟之后,他敲开我家的门,坐在沙发上聊一会儿;我也会敲开他家的门,坐在沙发上聊一阵。真是一种自由的、散漫的聊天。没有主题、没有限制,随聊随止。但仔细想来,还是有重点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当下全国文学以至山西文学的现状、发展,是我们常常说到的话题。焦老师经历了当代文学60余年的曲折历史,逐渐形成了他稳固的文学思想与观念。譬如他认为文学要坚持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条道路应该是开放的、现代的,充分汲纳现代派的表现思想与写法的。在创作上要把塑造人物当作文学的重要使命,努力刻画出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独特形象,特别要重视对人物心理和精神世界的发掘。他在创作实践上这样要求自己,也期望当下文学能在这些方面有重要开拓。但是,新世纪之后的中国文学,逐渐脱离了既往的轨道,呈现出一种新的、陌生的面貌与态势。这是让焦老师感到困惑和不满足的。而我认为,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已经越来越滑向了社会的边缘地带,正处在转型与变革之中,文学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与路径。文学要实现彻底的变革与转型,道路还很漫长。至于山西文学,经历了“山药蛋派”和“晋军崛起”两次高潮,现在也处于探索、低潮时期,要走向新的高潮,任重而道远。两个人谈着谈着,一个人会突然笑道:“我们都是过时的人了,还在杞人忧天呐?外面凉快了,出去散步……”
谈论更多的是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即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当年焦老师着重关注、扶持的那一代人。山西文学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前代与后代作家携手同心、薪火相传。焦老师像“山药蛋派”作家扶持他们那一代作家一样,在第四代作家身上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与辛劳。他注重他们在思想理论和文学原理上的学习与提高,亲自安排、组织了多届青年作家读书班。他像编辑一样给青年作家看稿子,有些文学青年直接把稿子寄给他,他读后把有基础的稿子推荐给《山西文学》或《黄河》编辑,每年要读数百万字的原稿。他邀请《当代》《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芙蓉》等全国名刊的主编、编辑来太原,召开组稿、改稿会,成熟的稿子在刊物上以“山西青年作家专辑”的形式推出,提升了这些作家的文学境界,扩大了他们的影响,使山西文学后继有人,形成了当时所谓“四世同堂”的文学局面。他还想方设法帮助解决这些青年作家创作和生活上的具体困难,如请创作假、评专业职称、调动工作等等。他和许多作家成为“忘年交” “好朋友”。这些都是我经见过的。在散漫的聊天中,焦老师常常会谈到他们,如彭图、谭文峰、房光、张行健、常捍江、宋剑洋、许建斌等等,谈到他们的人生、创作、故事、现状。这时焦老师的脸上就会露出开心、欣慰的笑容。
自然也会说到院子里的历史变化、人际关系、矛盾纠葛等,有时焦老师就会表现出一种委屈、困惑、不平的神情。这时我会息事宁人地劝他:“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又给他分析说:“八九十年代这院子里强者如林,强者有能力有才华,聚在一起难免文人相轻、磕磕碰碰,但也会创造文学的辉煌呀!大家都觉得脸上有光,可以称山西是‘文学大省’,别人也高看一等。如果都是些平庸世俗之辈,或许没有什么矛盾、意见,但哪里会有文学的崛起和发展呢?”焦老师就会点点头说:“那倒也是。”他有时很固执,有时又很单纯、随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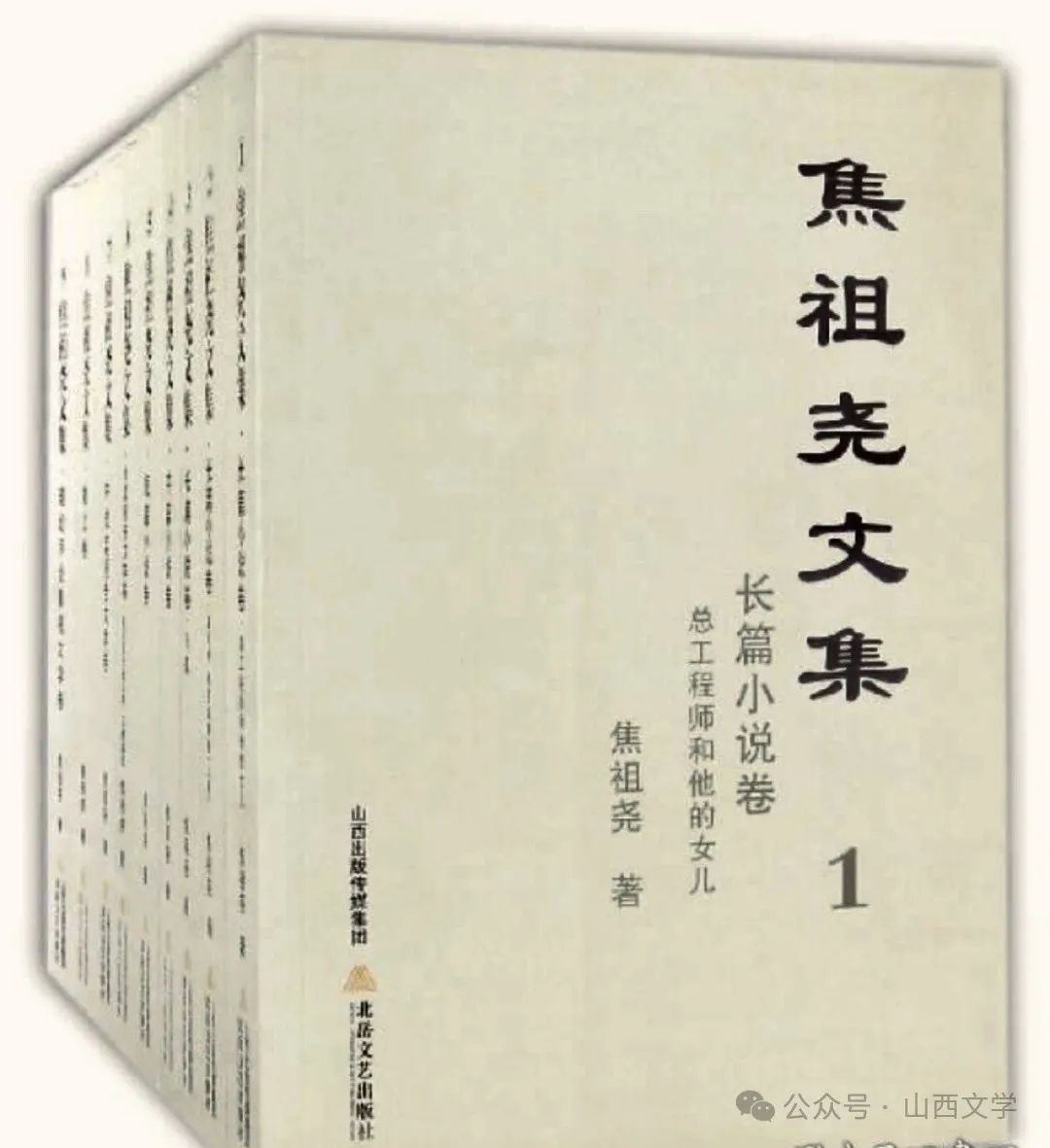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9卷本《焦祖尧文集》
寂寞而逝
2019年夏天,焦老师又像往年一样,回到了太原。他显得更瘦削了,帕金森病使他走路也有点摇晃,他配了一根拐杖,但没几天就不用了。但他还是自己做饭,早上出去散步。有时到我家里聊会儿天。他说中国现代文学馆要收藏他的著作和重要藏书。他待在闷热的家里整理了好几天,最后叫快递公司托运走了。
焦老师跟我聊天,絮絮叨叨说他的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出版一套两本《焦祖尧中短篇小说精选》。我说:“你的《焦祖尧文集》九卷本中不是有二卷就是中短篇小说吗?”他说:“我喜欢中短篇小说文体,自觉有多篇还是不错的,但放在文集中就被掩盖了,没人关注了。”焦老师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长中短篇小说皆擅。《中华文学通史》中有他的专章,称:“他是我国当代仅见的执着地在煤矿开拓艺术天地的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跋涉者》《飞狐》在文坛和读者中颇有影响。但他还有一批中短篇小说,如短篇《时间》《晨雾》《复苏》《归来》,如中篇《病房》《故垒西边》《魔棒》《归去》等,均为优秀之作,却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与评论。
焦老师的第二个愿望是回到太原。在金东方颐养园,吃饭、看病都很方便,但焦老师和老孔大姐始终没下定居的决心。焦老师则一直幻想着自己的身体好起来,一家人重回太原。但没有想到,这同样成为一个幻梦。2019年8月底那天,焦老师又要回常州了,退休的贾志民和他爱人张改香,开着自家的车来送焦老师到高铁站,我和春莲在楼下送行,焦老师坐在车内,笑眯眯地摆着手说:“明年再见!你们保重!”
焦老师“文集”后记中最后一句话是:“遗憾的事还很多,人生是充满遗憾的。”

1990年在河曲黄河边
新冠疫情就像是给中国、给世界按下了暂停键。从2020年1月到2022年冬天持续了三年之久。焦老师自然不能再回太原,我和他保持着电话、微信联系。焦老师一定在严格封控的养老院寂寞难耐,因此时不时给我打一个电话,说说他的身体,问问太原的疫情,表达着他想回一趟太原的愿望。有时也发微信,问询一下。但渐渐地,他的手颤抖得连手机也拿不稳了,只听得听筒里唰唰的声音,嗓音也变得喑哑、含糊。2021年底,我给老孔大姐发微信问候,她回复说:“老焦近况还可以,我只觉得他焦虑、固执、忘性大。他每天在心理活动室做康复训练,自诉病好多了,但我不大相信。帕金森是治不好的病,顺其自然吧……”
又过一年,到2022年冬天,疫情还未结束,已有松动。院里的朋友、同事秦溱对我说:“焦老师病情不好,咱们去常州看看吧。我已给老干处打了电话,让他们派一个年轻人陪咱们一下。”我有点犹豫。单位领导不放心,没有同意。
2023年春节前一天,焦老师从养老院护理室回到家中,算是一年的团圆。我打过去电话提前拜年、问候,焦老师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疫情总算过去了,我的身体不知能不能好起来?不知能不能回去?代我问春莲好……”我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想在太原度过,太原一定还有他未了的事情。我的心情沉重起来。
3月21日上午9点,老孔大姐突然打来电话,告我焦老师早上八点去世了,走得很平静。让我告知单位领导。我的脑子里只听得“轰”的一声。我立即打电话告知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罗向东,还有老干处负责人。作协领导随即碰头商定,委托我写一个追悼词,委派罗向东、潘培江、贾志民、张改香四人,下午乘飞机前往常州。23日在武进区殡仪馆举行了最简单的悼念、告别仪式。养老院为照顾老人们的情绪,不许办丧事方面的活动。吊唁室摆放了一圈花圈,罗向东致罢悼词,一二十个人默默地向焦老师告了别。罗向东在给我的微信中感慨说:“感觉有点凄凉。焦主席很想回山西,可是再也不能了。月余前焦主席在家摔了一跤,估计是这一跤使他过早离去了……”
他的家还在那儿空着,我不时进去看一眼,数年前的情景清晰如昨。看到写字台上搁一摞音乐CD,封面上大都是英文。我知道他喜欢西方古典音乐,这些大概是他早年出国访问陆续买到的,他曾经有过一台日本建伍落地音响,那是用他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全部稿费购置的。我把焦老师的音乐CD放进我的音响,听到了较熟悉的贝多芬、莫扎特、德彪西、巴赫等的乐曲;还有一些陌生的如格里格、亨德尔、亚当、马斯卡尼、拉威尔等的曲子。我发现这些西方古典音乐大家,在他们的乐曲中都流淌着一种沉郁、抒情、激越情调,我感觉自己似乎走进了焦老师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