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用“理解”证明了独立批评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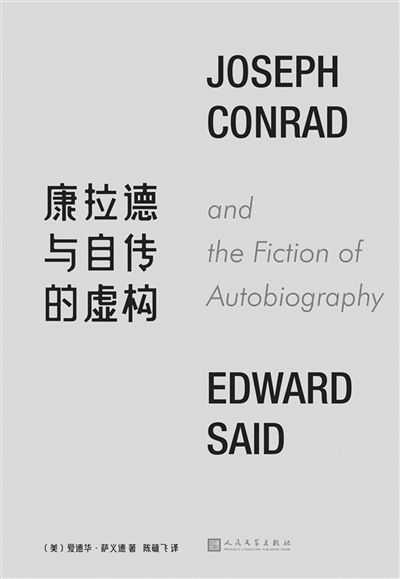
“再现”康拉德:一次现象学探索
《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脱胎于萨义德在哈佛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如他所言,这是“一次对康拉德的意识的现象学探索”。
萨义德创造了一套探索康拉德作品主题的动态批评方法。这套方法基于对语言之有效性的关注:如果康拉德通过信件传达他和自我的矛盾关系,那么这种通过语言“再现”的关系会影响同样依赖语言的文学创作。甚至可以说,康拉德的书信包含着一种能够阐释其小说错综复杂主题的潜在机制。大胆假设之后便是小心求证,萨义德详尽地考察了康拉德书信中的自传性书写如何与其短篇小说互动。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康拉德对生活的描述等同于其小说的叙事,而是在仔细审视书信和小说互文关系的过程中,发掘康拉德精神生活的困境如何在其创作中被遮蔽或凸显。
作家在作品中存活的时间远超于他们的肉身,而批评家的工作则会不断赓续作家的文本生命。那些作者的未竟之言,若未能经由本人倾吐,则可能被最勇敢的批评家从文本中掘出。萨义德将康拉德的文学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1896年至1913年,他努力塑造的“作家”身份得到了认可;1914年至1918年,战争让作家的内心世界经历了严酷的考验;1918年至1924年,欧洲旧秩序“死得其所”,而作为“幸存者”的康拉德也进入了短暂的和平阶段。
萨义德在“意义”与“生活”的对立冲突中动态图解了康拉德的精神世界,同时又在社会历史和个人生命史的坐标系里重新定位了康拉德。他将康拉德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关系概括为康拉德在写作中的真实声音和作品的叙述声音的对抗,而介于这两重声音之间的书信就可能隐藏着解码康拉德小说主题的关键。
《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奠定了萨义德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在为康拉德绘制精神肖像的过程中,萨义德思想谱系中的诸多关键概念也从中浮现。
萨义德的“开端”:他为何而写作?
萨义德认为,康拉德在书信中倾向于以悲伤和愧疚的态度回顾往事,他必须通过写作发现痛苦的真正根源,同时向世界解释自己。或许恰是他这种不断为自己寻找“起点”的冲动启发了萨义德关于“开端”的研究。
萨义德的《开端:意图与方法》向20世纪早期一众苦吟苦活的经典作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语言的再现能力必然受限,写作又不过是一种将现实转化为文本的偶然行为,那么这些作家究竟因何开始写作,又为何只能靠写作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感?
在萨义德看来,康拉德的小说就是作家不断有意识地形塑自身品格的写照,不能像父亲那样能够投身于现成的波兰民族革命,而是必须凭自己创造出一项事业,以自我发明的角色代替“残缺不全的民族身份遗产”——后者让康拉德感受到的巨大屈辱,让他一再将生活阐释为“一场乞求解脱的噩梦”。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进一步指出,康拉德的写作提出了以反本质和非强制的方式“再现”世界的可能性——而这正是萨义德的思想底色。康拉德对语言再现能力的质疑,及其将写作视为纯粹意志行为的观点,又成了萨义德最为知名的著作《东方学》的引子。可以说,萨义德每一次重返康拉德的精神世界,都是一次对自己“开端”的再确认。
康拉德对人性、现实和知识的认知让他在创作中饱受绝望之苦,而萨义德则始终怀揣拯救的决心营构不乏希望的批评工程,“相信并想象另一种可能性”于他而言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献身于具体事业的劳作——体现在积极投身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深度参与关键问题的公共讨论,哪怕代价是忍受无尽的毁谤和死亡威胁。正是不懈地为弱者执言的实践诠释了他的思考。因此,写作——作为一种忠于内心但逆势而为的行动,充分展现了萨义德在“格格不入”的精神流亡中锻造自身批评意识的过程。
不为认同的“理解”:“绝不把团结置于批评之上”
事实上,萨义德对康拉德的“理解”并不依赖“认同”,尽管二人在经历上有很多相通之处:两人的故土都经受过殖民;离开家乡后,都用并非母语的语言写作。
在萨义德看来,没有哪个作家能比康拉德更了解流亡生活的极度复杂。但同时,他也无法原谅康拉德对欧洲殖民神话的维护和对殖民地所持潜在的悲观态度。这也是萨义德之“理解”的可贵之处——他总是被那些与他观点相左的作者吸引,而其批评的力量恰恰从歧义的张力中涌现。在萨义德生前最后一次正式采访中,他说道:“康拉德和我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对他而言,在政治上没有真正的其他可能性。我不同意这一点:总有别的可能。”在康拉德那里,一切政治都会沦为无休止的腐败,而萨义德则始终坚信更好的替代方案的存在——坚持拯救不可拯救之物的勇毅,以及在无望的世界里保持希望的倔强,也是令萨义德成为一名真正思想家的关键品格。
康拉德曾在信中将存在本身比作“针织机”,认为这台冷漠的机器操纵着时间、空间和个体的命运——虽然写作可以模仿“针织机”的运行,作者也似乎掌握着故事中人物的生杀大权,但他们终究无法摆脱“针织机”的魔掌。易言之,康拉德的生活便是其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例证,写作未必足以缓解他的存在主义焦虑,但注定是对自我无赦的酷刑。“如此长久地、狂热地忠实于他对人类极度悲观的态度必然是艰难痛苦的”。但即使写作注定受限于语言巨大的偶然性,萨义德也并未轻视康拉德用于自我剖析的这套叙事。无论多么精致复杂的理论体系,都不能压抑个体的真实生活,尤其是那些承受着殖民化的惨痛后果的个人生活。
自康拉德之后,作家们都开始借文本进行自我表达。而在萨义德之后,则少有公共知识分子能像他一样将自己的智识工作和公共生活彻底地融为一体,让追求社会公义、对权力说真话的热情驱动自身的工作及生活。
萨义德总是会一次次重返康拉德,从《开端》到《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用最朴素也最真诚的“理解”证明了批评独立于文学创作的价值。文学批评就此跃入道德和生命写作的全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