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启蒙之变奏:《中学生》史论(1930—1953)
《中学生》,1930年由开明书店创办后,出版社将其运营至1953年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止。作为民国时期维系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学生杂志,从蔡元培到匡互生,从鲁迅到陶希圣,从茅盾到周而复,从冯友兰到胡绳,各方人士都曾在该刊著文立说,它是后五四时期不同青年启蒙话语竞逐的顶级平台。基于学界对此刊物的研究缺少统摄性视野,本文通过概括关捩文章要点,归纳核心栏目特色,追踪杂志宗旨演变,描绘数十年间杂志与青年读者群体互动的变嬗脉络,搭建宏观框架,以推动《中学生》研究的深化。

《中学生》代表作者:蔡元培、匡互生、鲁迅、陶希圣、茅盾、周而复、冯友兰、胡绳
一
自1900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少年中国说》滥觞,经陈独秀1915年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正式宣扬,复由1916年李大钊《青春》一文的再次鼓荡,“青年”演变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元命题。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青年书刊不仅是关乎“启蒙”的利器,更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据统计,1925年全国仅有各类中等学校1142所,学生185981人,到1929年已有学校2111所,学生341022人,1930年更激增至学校2992所,学生514609人,读者数量之庞大可见一斑。[1]概而言之,青年文化的生产——消费——再生产是精英领袖、商业出版社、知识青年三方均角逐争夺的核心场域。在此背景下,开明书店决议发行一份面向中等教育程度读者的杂志。
1929年11月20日,《申报》报道了出版社拟推新杂志的举动:“开明书店向以出版中学生用书闻名于读书界,所出各书,如《开明英文读本》、《开明算学教本》及《活页本文选》等,颇为各中学校所欢迎采用。近闻该店又将于明年一月起,出版一种月刊杂志,名曰《中学生》,专供中学生阅读。创刊号已在印刷中,可于年内提前出版。其中执笔者,有陶希圣、舒新城、叶圣陶、郑振铎、丰子恺、徐调孚、夏丏尊、李宗武、刘薰宇诸氏,而编纂者则为章锡琛、夏丏尊、顾均正、丰子恺四人云。”[2]
1930年1月1日,《中学生》正式发行创刊号。夏丏尊所执笔的《发刊辞》全文如下:
中等教育为高等教育的预备,同时又为初等教育的延长,本身原已够复杂了。自学制改革以后,中学含义更广,于是遂愈增加复杂性。
合数十万年龄悬殊趋向各异的男女青年于含混的“中学生”一名词之下,而除学校本身以外,未闻有人从旁关心于其近况与前途,一任其彷徨于纷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这不可谓非国内的一件怪事和憾事了。
我们是有感于此而奋起的。愿借本志对全国数十万的中学生诸君,有所贡献。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
啼声新试,头角何如?今当诞生之辰,敢望大家乐于养护,给以祝福![3]
1931年叶圣陶入职开明书店,从第12期起杂志署名编辑“夏丏尊、叶圣陶、章锡琛、顾均正”,到了1936年第61期起署名“社长 夏丏尊 编辑:叶圣陶 金仲华 徐调孚 贾祖璋”,此情况一直持续到1937年第76期为止。夏丏尊与叶圣陶两位作为刊物的灵魂人物,主导了此阶段《中学生》的风格。
夏丏尊提出“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的定位。叶圣陶如是谈到“编辑《中学生》……共通的观点用夏丏尊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受教材’不等于‘受教育’”。[4]夏丏尊的《受教育与受教材》发表在杂志第4期。基于在浙江一师、春晖中学、立达学园等的丰富任教经历,他断言“中等学校教育的课程,只是一种施行教育的材料,从诸君方面说,是借了这些材料去收得发展身心能力的。诸君在中学校里,目的应是受教育,不应是受教材”,他更看重的青年能力的培养,教育的形式问题反而是第二位的。[5]对应于《中学生》杂志,他们寄望青年读者在阅读《中学生》后,能“经过一番消化作用,生出新的血肉来”。在编读之间的关系上,夏叶二人观念平等,他们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曾经当过老师或是现任老师,就承认自居于老师的地位也不要紧”,但这不是“教训态度”的老师,是“辅导态度”的老师,因此“我们时常把读者诸君称为青年朋友,这个‘朋友’不是一种浮泛的称谓,却表示我们真心诚意的把诸君认作朋友。”概而言之,1930—1937年的《中学生》,是以综合性杂志面貌,亦师亦友的态度,对青年读者进行全方位的启蒙。
此时期的《中学生》,每年10期,7、8两月停刊(1930年停7、12月,1932年停3、8月),一直持续到1937年6月杂志出至第76期。杂志栏目颇多,其中的“特辑”堪称代表。“特辑”是针对特定议题,由知名人士约稿或普通读者征文构成的栏目,基本每年两辑,自1932年起固定在每年1月的新年特大号和6月的暑期特大号,部分特辑名甚至会特别标注在杂志封面以作卖点。特辑文章少则数篇,多则可占据杂志一半版面。徐调孚自诩“本志时设特辑,汇集同类性质的文字在一起,为极有意义之举”[6],可见《中学生》编辑对此栏目极为自傲。
“特辑”作为不同代际精英知识分子与青年学子交流与碰撞的媒介,是时代精神症候的风向标,此阶段杂志特辑如下:

上表有如下要点:首先,议题广泛,包罗万象,涵盖了时势、就业、升学、战争、文艺、科学等等,体现了《中学生》的“杂志”定位。其次,文艺类话题占据相对多数,表明作为一种职业可能的“文学”对青年的吸引力之强,而杂志亦切实履行了培养与提携之责。再次,征文从文化精英逐步向青年学子倾斜,后来甚至出现了数期全由青年来稿组成的特辑,年轻人的活跃参与,佐证了杂志在青年界的影响力。
《中学生》发行适逢其时,目标准确,加之编作者的名人效应,杂志深受认可,创刊号初版两万册在二十天内销售一空,迅即再版[7],至年底已有一万定户,打破了民国杂志销行记录[8],1934年创刊五周年时,印行更超过五万份[9]。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令嘉奖“内容丰富,且适合中学生程度”,将其选入中学生阅读参考图书目录[10]。市场和官方的双重肯定确认了《中学生》在青年刊物的龙头地位。
二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悍然炮击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守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突袭上海闸北中国守军,淞沪会战爆发,不久开明书店梧州路总厂遭遇炮火焚毁,出版社资产损失百分之八十以上,包括正在排印的第77期《中学生》在内的一切出版物被迫中断。[11]虽然遭遇困境,开明书店仍希望快速恢复《中学生》。据王伯祥日记,“(1937年10月8日——引者注)下午仲华来,雪村与谈《中学生》复刊事。大氐约其计画进行并担任拉稿等工作。”“(1937年10月21日——引者注)午后仲华来,商《中学生》复刊计画。”[12]不过因叶圣陶、傅彬然、宋云彬、金仲华等先后离开上海,缺乏人手,杂志只能停刊。
内迁诸人谋职之路恰如叶圣陶的戏言“西行乃交了教书运”[13]:叶氏先后执教重庆巴蜀中学、国立中央戏剧学校、北碚复旦大学,最后落脚乐山武汉大学;丰子恺、傅彬然、贾祖璋等则均曾在广西桂林师范学校任教。因缘际会他们与年轻人有了更为直接地接触,战时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圣陶在给上海友人的信中感叹:“现在希望到底在青年。这回小墨回来,有许多同学来看他,弟与他们谈话,觉识力充富,饶有干才,大致均不错。此非学校教育之成绩,乃时代锻炼之功也。”[14]傅彬然持同样观点:“与两百个青年相处了一个多月,使我知道青年没有不纯洁的,真诚的。工农青年尤其真率可爱,他们只一心想立刻去和隔江的敌人拼命。……青年,即使年龄稍大,即使已经沾染着旧社会的不良习气,只要领导得当,在集体当中,是很容易把他锻炼成为一个勇敢前进的新青年的。”[15]
然而,战时就任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告全国学生书》中表态:“教育之任务,为在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视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即国家衰亡之危机。”[16]在此思想的主导下,内迁各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未因抗战的爆发而有任何实质的应对转变。叶圣陶就对武汉大学提倡学生安心读书,不问世事的做法深表疑问:
校中风习素称良好,主者以安心读书为标榜,今来嘉之学生均曾署决不游心外鹜之志愿书。以故入其校门,空气恬静,如不知神州有惊天动地之血战也者。如此教育,于现状究否适应,亦疑问也。[17]
1939年初,在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等的私人资助下,马一浮在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这对《中学生》诸位编辑更是一大直接刺激[18]。因友人介绍,叶圣陶与马一浮时相过从,对其倡导儒学,培养通儒的构想有所了解。在他与上海诸友的书信中对此多有讨论,大家齐表质疑:
调孚兄以为此举系开倒车,弟均同感。丏翁言其六艺之教为礼、乐、射、御、书、数,而其所教非此六艺也,盖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最难通者,谓此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艺,如文学、艺术统摄于诗、乐,自然科学统摄于易,法制、政治统摄于礼。其实此亦自大之病,仍是一切东西皆备于我,我皆早已有之之观念。试问一切学艺被六艺统摄了,于进德修业,利用厚生又何裨益,恐马先生亦无以对也。[19]
有感于各式青年教育脱节于时代,开明人再生复刊《中学生》念头。年轻人对《中学生》的称誉更是复刊的一大动力。叶圣陶明告上海:“(武汉大学学生——引者按)其中阅《中学生》杂志者不少,均于此志之注重语文研究特感兴味,且谓获益颇多,闻暂时未能续刊,皆致惋惜。”[20]他力主如若复刊应选址内地:“《中学生》复刊,自是佳事。但在上海出版,为店之安全计,下笔不免多所顾忌,于是即不配内地人胃口。岂唯内地人,恐怕也不配上海租界中青年之胃口……而且,上海出版了,寄递迟缓,使内地人三月中看一月出的杂志,亦殊不妥。”[21]
1939年春,云集桂林的开明人正式将复刊《中学生》一事付诸实施。据宋云彬日记:
(1939年3月11日)晚八时,鲁彦、锡光偕同章雪山来,谈甚快。雪山主张恢复开明之《中学生》,余表示赞成,但无适当编辑人。
(3月13日)又致彬然函,告以《中学生》复刊事。
(3月28日)子恺、彬然先后自两江来。开明《中学生》决复刊,请彬然任编辑。
(3月31日)锡光或可任《中学生》编辑事,明日当与雪山切实一商。[22]
一直力促此事的丰子恺颇为动情:
(3月27日)下午电两江傅彬然,请其明晨来桂林,共商《中学生》复刊事。盖此次若不复兴,后恐不再有机会,直须到太平后复刊。昔曾子居师宾之位,尚有人讥其寇至先去,寇退则返。况《中学生》一册杂志,岂可于患难中逃之杳杳,而乱平后再来做生意哉?
(3月28日)晚章雪山兄宴客于美丽川菜馆。彬然被推戴为《中学生》主编。列圣陶为社长,联棠为发行人。吾亦列名为编辑委员。固辞不得。一年半以来,青年学生以此相询者甚多,吾每答以“不久终当复刊”,故今日竭力玉成之,使吾对询者可以践言耳。[23]
王鲁彦、宋云彬、胡愈之、唐锡光、张梓生、傅彬然、贾祖璋、丰子恺等八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其中唐锡光负责杂志具体事务。远在乐山的叶圣陶欣然领命社长一职,他对《中学生》复刊应持的立场提出了明确要求:
彬然信中言将恢复《中学生》,彼与祖璋主之,而令弟居社长名义。弟答谓他人或有未便,弟居其名自无弗可。今后我们要说真有所见的话,不效一般人搬弄几个名词术语,一切都是从嘴唇边滚下来的。又,我们要特别提倡个人之志概与节操,天下事未可料,今日之读者或者命里注定要当“遗民”,须有志概与节操,将来乃有生望。此二意皆有感而发,言之有深痛,兄当解之。[24]
1939年5月5日,《中学生战时半月刊》正式推出,《复刊献辞》对战时青年提出期望:
在复刊之始,我们愿意和中学生诸君共相勗勉的——
第一是努力追求文化和智慧。用文化和智慧的光辉,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
第二是民族利益超过一切,牺牲一切个人的利益,时刻准备为救国救民而奋斗。
第三是学习、工作、生活打成一片。生活是为工作,为工作而学习,而且从工作中学习。
最后,请大家谨记,领袖的训示:
“我们要集中国民的精神,就必使全国国民对自身都确立共同的道德,对于国家民族坚定共同的信仰,而每一份子能够根据这个共同的道德观念,共同的建国信仰而努力,而奋斗,而牺牲。这个共同的道德是什么?就是舍小我为大我。我们的共同信念是什么?就是三民主义,根据这个信仰去实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政治的最高理想——大同世界。”——录自蒋议长致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开会词[25]
为了配合抗战,杂志增设“讲坛”“半月时事分析”“时事特写”“战时社会及自然常识”等栏目,宣传普及各种知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杂志编辑意识到在战争作为常态的前提下,不能忽视青年读者的日常教育,“自从恢复月刊以后,随着篇幅的增加,叙述关于各项基本学习的文章渐有增加,直接谈到抗战的文章似乎比较地减少了。”编辑解释这样做的原因“优秀青年的培养实非现时所流行的短期训练之类的办法所能济事,也必须经过一个较为长期的锻炼才能够成功。怎样使青年身体、品性和知能各方面的基础坚实起来,这是一个很迫切而实际的问题,这问题最近一年来,本志同人,常常在注意着,今后的本志,还是想就这方面来多用一点力量。”[26]可以说,1939—1945年的《中学生》,“救亡”与“启蒙”的并重是杂志的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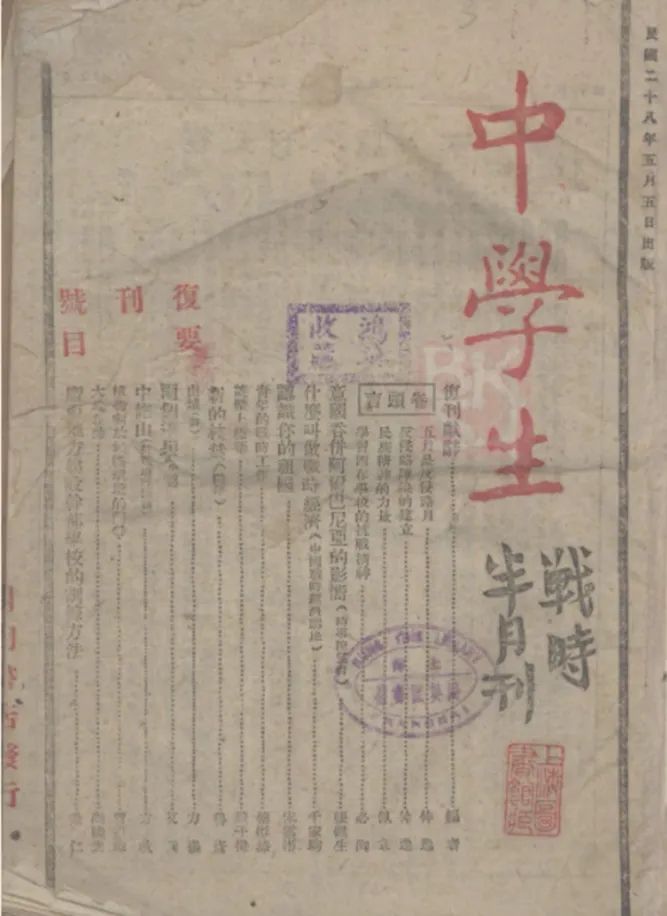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复刊号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受制于战事环境限制,杂志的发行与出版事宜不断更迭。1941年10月第49期起,杂志重启《中学生》刊名,恢复为月刊,年出12期。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7月,开明书店被迫迁离桂林,杂志自77期起改在重庆出版。虽然困难重重,但杂志复刊号发行六千份,此后印数不断增加,到了1941年,已有一万九千份的发行量,[27]可证其在青年群中号召力依旧不减。
抗战初兴,开明人与彼时的中国人一样,同仇敌忾,并将民族复兴的希望系于内迁的国民政府,复刊辞申言“不光是抗战必胜,而且我们坚信建国必成”,更以蒋介石国民参政会发言作结。抗战中后期,面对国民政府的吏治腐败、军事无能、舆论控制,杂志编辑纷纷走上十字街头,《中学生》的政治性随之增强。1945年1月,杂志新年号发表卷头言文章《今年是民主胜利年》,宣告“只有民主才能获致胜利,获致胜利必须以民主来做前提。没有民主,胜利是永远无法争取到手的”,并呼吁“努力民主运动是当前每一个中国青年应尽的迫切任务”[28]。8月,傅彬然代表《中学生》与重庆16家杂志代表共同起草了联合声明,宣布自9月1日起杂志不再送检,拉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
1946年《中学生》回沪出版(自1月起战前和战时所出期数合并计算),杂志更积极地融入到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之中,重庆“较场口血案”发生后,杂志社刊发《我们的态度》,向全社会宣告“本社同人不敢妄自菲薄,愿意参加全国青年的队伍,为争取国家的和平民主与人民的自由而共同努力”[29]。同时,编辑群体还加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胡绳对此有回忆:“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恩来同志安排上海的工作,他要我把出版界和杂志分成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三类。……《中学生》和开明书店属于第三线,应该尽可能存在下去。总理这个安排,我和叶圣老谈过,请圣老尽力维持开明书店,维持《中学生》。”[30]“第三线”杂志成为此际《中学生》的形象表述。
与1937—1949年的历史互为表里,《中学生》“特辑”如下:

虽然囿于外部环境,此十年“特辑”的刊出不稳定,但依旧有着明显的时代印痕。抗战时期,栏目密切联系战争征文。1945年以后,对中外名人的悼念议题频出,编辑显然是以此为突破口开展饱含政治意涵的讨论。上海解放前后,杂志则率先推出“迎接新时代”特辑。
1949年初,叶圣陶离沪北上,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张明养接任主编。[31]上海解放后的8月,第214期《中学生》的“编辑室”宣告“本刊从十月号起,将有重大的变革”,[32]预示杂志即将步入新的阶段。
三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行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之时,以叶圣陶、傅彬然、宋云彬为代表的大批出版文化人受邀齐聚北平参与建国大业。在他们到达后,中共文化界的领导人考虑到南方尚未解放,希望他们出面创办一种类似《中学生》的杂志,结合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开展青年教育。
据叶圣陶所记:“(1949年4月11日)昨日与柳湜、胡绳、彬然谈办一种类似《中学生》之杂志,以应目前青年界之需。此事他们三位甚感兴趣,而芷芬亦然,以为可由开明出资。此在开明,一方面可登载广告,一方面亦尽服务社会之义。谈及主编之人选,共谓各人有事,兼顾必致两失,须有较闲之人专主之。因思及超构,今晨与超构谈起,承渠应允。今时人事变动至多,不能作长久之计,但请渠暂主二三个月,亦是佳事。出版之期定于五月四日。今年为‘五四’三十周年,又当华北解放之际,自不宜放过此大有意义之日子。然为时已催,写作编排,均须用突击方式出之,乃可有济。论余之体力与精神,实不堪任,然大家有兴,亦唯有努力促其成耳。”[33]
宋云彬对此的记录可做补充:“(1949年4月13日)前数日,柳湜、胡绳怂恿余等编一青年杂志,经连日商谈,已得结果,决由开明书店印行,并组一编委会,请赵超构负总责。今晚由开明书店出面邀请,在□□饭庄宴饮,到袁翰青等约二十人。席间经商定,定名为《进步青年》,由叶圣陶、傅彬然、胡愈之、金仲华、袁翰青、周建人、孙起孟、赵超构、茅盾及余共十人,组编委会,五月四日出创刊号。”[34]

《进步青年》创刊号
1949年5月4日,《进步青年》在北平正式发刊,发刊辞摘要如下:
在“五四”三十周年纪念的日子,在解放了才不过三个月的北平,我们创刊这个杂志——《进步青年》。我们非常之兴奋,愿意尽我们的力量把它办好,对于青年们有一点儿切实的帮助。
我们一班朋友对于教育都有些儿兴趣,有些儿信念。我们以为教育为政治服务是必然的,世间决没有跟政治不相干的教育,教育独立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想头。教育有糟糕的,有进步的,正同政治一样。……所以,政治跟教育并家,一切政治化为最广意义的教育,那成功是无限伟大的。目前咱们已经看见了成功的实迹,将来的成功还要尽量扩大。
教育的方式不只是一个。一个方式是分成施教的跟受教的两边儿,施教的拿出来,受教的收进去。另外一个方式是不分施教的跟受教的,大家打成一伙儿,共同商量,共同学习,共同实践,共同检讨,结果是彼此互相教育……我们办这个杂志,愿意采取后一个方式。……
以上说的是我们的理解跟态度。以下说一点关于创刊的日子“五四”的话。
“五四”运动是我国现代史上青年运动开始的标帜。……
若问谁是这一道主流中的主力,那必得推中国共产党。……“五四”当时所号召的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跟努力,经广大人民的拥护跟奋斗,才彻底化为有血有肉的现实;这样说法是最为确切公平的。……进步,不断地进步,咱们应该以此自勉,也以此自傲。我们愿意把“进步”这个词儿标在杂志的名儿里头,作为跟青年挽着胳膊,齐步迈进,争取不断的进步的要约跟凭证。[35]
发刊辞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全新的政治认同与自我定位:首先,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有了根本转变。叶圣陶在编辑《中学生》时曾坚持“教育与政治固然无法绝缘,可是两者的着重点究竟不同。”[36]但在《进步青年》中,明确提出“我们以为教育为政治服务是必然的,世间决没有跟政治不相干的教育,教育独立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想头”。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论述为编辑们所信服,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得到清晰表述。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主流中的主力”,“这样说法是最为确切最为公平的。”最后,编辑不再遵从由晚清开启,新文化运动强化的根植于进化论时间观的“新”“旧”二元划分,转为认同基于革命视野的“进步/落后”意义体系,并否定了主持《中学生》时的启蒙精英意识及导师心态,转而提出需要“跟青年挽着胳膊,齐步迈进,争取不断进步”。与之相应,《进步青年》自然不再以学习与文艺为主,而是着重于推动青年政治教育与思想改造。必须提及的是,叶圣陶撰写的发刊辞初稿完成后,经胡绳仔细审阅并“指出一重要之不周密处”[37],可见新政权方面代表对刊物态度极为审慎。
叶圣陶对刊物前景非常乐观,“《进步青年》已印成,大家观玩,甚觉有味。多打纸型一副,将托便带至南京,俟上海解放,即在上海重版,想可风行一时。”[38]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出版社酝酿大动作,9月第215期《中学生》卷头言《〈进步青年〉与〈中学生〉合并》赫然醒目:
合并之后的杂志用什么名称呢?我们决定用《进步青年》。在《进步青年》创刊号的发刊词里,我们说过这样的意思:我国近三十年的进步那么快,目前已经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进步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我们愿意青年们与时代呼吸相通,争取进步,所以取《进步青年》作杂志的名称。现在仍然用这个名称,意思也照样。[39]
出版社经营《中学生》多年,如今毫无留恋地舍弃,选择《进步青年》作新刊名,说明了开明人思变之心的坚决。对杂志的变化,年轻一代非常认可,读者卢弓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和期待:“我想这一改变绝不是随随便便,而是有其巨大意义的。这里面表示了一个跃进,一个变革。在《进步青年》的新名称下,《中学生》一定会把立场站得更坚定,与现实结合得更紧密,把马列主义的精神贯彻到杂志的每一页里去,指导青年的思想改造和学习改造。”[40]
从《中学生》到《进步青年》的更名反映在编辑方针“综合各方面意见,《进步青年》的读者对象应为高中学生,大学生和各界青年中想求进步的广大青年群;因而也就决定了我们的编辑方针应为帮助这广大青年群加强学习,认识时代,争取进步。”[41]整体而言,易名后的杂志青睐老解放区作家及年轻一代就思想政治问题的来稿;同时,配合“一边倒”的政策,俄语学习与苏联介绍成为常设栏目;而因“新解放区作家鉴于自身思想上的缺点,不敢轻易写作”,[42]以“特辑”为代表的老栏目无形中止。开明书店对《进步青年》寄予厚望,在编定出版计划中表示自1950年起要将每期7万字的刊物扩充至11万字,争取三年内出版三十六期四百万字。[43]
此时青年团中央的《中国青年》尚未实现从战争动员向思想指导的转换,《进步青年》在过渡期适时扮演了全国青年引导刊物的角色。[44]据读者来信,“(解放后)各地的青年普遍地掀起了学习的热潮,政治学习的空气尤其浓厚,参考书在每个同学的手中传阅着,新的书刊更是充塞在每个角落里,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进步青年》”,甚至读者还呼吁“希望每一个《进步青年》的读者,都能自己检讨一下:自己是否对《进步青年》负责?”[45]上级领导部门对杂志同样高度认可,特别提到“由《中学生》改名的《进步青年》比较充实一点,为一般进步的青年学生所喜爱。”[46]从销量上亦可佐证,《中国青年》在上海销量仅有2000份,《进步青年》的发行量高达1万份,叶圣陶“风行一时”的预测得到了应验。[47]
1950年2月,开明书店申请公私合营,4月出版总署批复同意开展“公私合作”,并指示出版社北迁。开明书店到达北京后,与团中央直属的青年出版社有了接触,两社决定开展分工,其中就涉及到开明书店《进步青年》与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的分工。经协商,大学生读者及政治内容由《中国青年》负责,《进步青年》剥离相关栏目,改为高中程度读者服务,内容集中于课程学习。[48]出版社展望以后的《进步青年》:
《进步青年》从一九五一年起将以配合中学课程辅助中学青年文化学习为中心任务。环绕这个任务,刊载的内容将有相当大的变动。它将以更朴实的姿态与读者相见,可能不如以前活泼生动,但主观上希望能对中学同学有一些更大的帮助。
一九五一年起,《进步青年》将分为下面各栏:卷头语,文化学习资料,青年修养,问题解答,青年文艺,青年生活,时事特写,时事述评,俄文之页。各栏之中,文化学习资料占最大比重,它将包括语文、史地、数、理、化、生物、艺术和体育。[49]
在发行一年之后,出版社又将《进步青年》与旗下以儿童为对象的《开明少年》合并,并恢复使用《中学生》的名称,并再次下调服务对象为帮助初中学生进行文化学习,由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联合组织委员会编辑。[50]据叶至善回忆,改版后的杂志深受欢迎,印行10万册,大大超过1930年代的记录。[51]1953年4月15日,开明书店被青年出版社吸纳组建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书店与《中学生》之间的关系划上休止符,杂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接手,1956年6月再交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负责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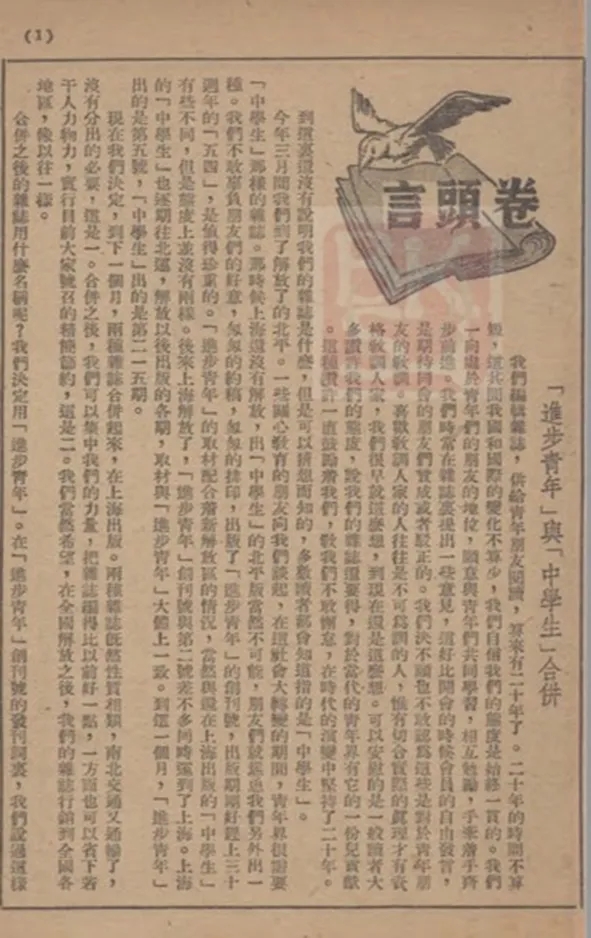
《进步青年》与《中学生》合并
结语
开明书店《中学生》,维系时间长达23年,历经1930—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创刊发展期,1939—1949年战争主基调的复刊期,1949—1953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合刊期,以夏丏尊、叶圣陶、张明养等为代表的编辑,敏锐感知时代脉动,杂志主旨经历了从新文学到抗战建国、再到民主运动,直至阶级话语的递变,因能共情于不同时段年轻学子的“常”与“变”,杂志深获认可。同时,正如读者的回忆“那个时候,不但我们正是中学生,而且我们由《中学生》杂志的介绍,而认识,而团聚”[52],杂志更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参与到后五四时期青年群体的历史化进程之中。但,1949年后,青年读者的迅速成长与出版物的政治属性决定了《中学生》的畅销只能是昨日黄花,急变的内外环境决定了杂志的未来。
一方面,“《中学生》渐渐使我感到不够劲儿了”“《中学生》慢慢地不能满足她的读者了”[53]的批评,说明编辑旧有知识结构已经不能再满足阅读趣味激变后的年轻读者需求,杂志已然落后于时代。另一方面,出版物的政治面相业成为新政权的核心考量,恰如1951年胡乔木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中所提“出版物是思想方面的东西,虽也是商品,但是是政治的商品,党对这方面应当负最大的责任”[54],加之社会主义新人培养与新型国家建构的高度融合,更决定引领青年思想的使命必须由党的刊物承担,才能形成正确导向,民营性质的杂志自然无法再继续维系原有角色。最终,《中学生》从对象到内容降级,褪去“杂志”色彩,转型为纯学辅刊物,离开青年思想前台,而《中国青年》顺利接棒,承担起指导青年的使命,杂志扬弃“进步青年”,代之以“社会主义新人”的全新命题,成为了当代中国青年思想的风向标。
注释:
[1]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428页。
[2]《开明书店创刊〈中学生〉杂志》,《申报》,1929年11月20日。
[3] 《发刊辞》,《中学生》第1期,1930年1月1日。
[4] 叶圣陶:《我们的宗旨与态度》,《中学生》,1948年6月1日第200期。
[5] 夏丏尊:《受教育与受教材》,《中学生》,1930年4月1日第4期。
[6] 徐调孚:《〈中学生〉点滴》,《中学生》,1946年1月第171期。
[7] 《开明书店〈中学生〉创刊号再版出书》,《申报》,1930年1月25日。
[8] 《一万份销路》,《读书月刊》,1930年12月1日第1卷第2期。
[9] 《〈中学生〉杂志社启事》,《申报》,1934年2月27日。
[10] 《教部嘉奖〈中学生〉杂志》,《申报》,1934年2月21日。
[11] 《开明书店报告》,1950年11月,第2页。
[12] 王伯祥:《王伯祥日记》(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310页,第2317页。
[13]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14]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4卷),第156页。
[15] 傅彬然:《智识份子要检讨自己》,《国民公论(汉口)》,1939年7月16日第2卷第2期。
[16] 陈立夫:《告全国学生书》,《党国先进抗战言论集》,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年,第56页。
[17]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4卷),第176页。
[18] 参见龚晓:《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始末》,《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9]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4卷),第203页。
[20]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4卷),第188页。
[21]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4卷),第163页。
[22] 宋云彬:《宋云彬日记》(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6—31页。
[23]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7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19—120页。
[24]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4卷),第198页。
[25]《复刊献辞》,《中学生战时半月刊》,1939年5月5日复刊号。
[26] 《本志复刊四周年》,《中学生》,1943年6月第64期。
[27] 傅彬然:《从复刊到复员》,《中学生》,1948年6月1 日第200期。
[28] 《今年是民主胜利年》,《中学生》,1945年1月1日第83期。
[29] 《中学生》杂志社:《我们的态度》,上海杂志联谊会:《为陪都血案争取人权联合增刊》,1946年3月15日。
[30] 胡绳:《我和〈中学生〉》,《读书》1985年第11期。
[31] 张明养:《我和〈中学生〉》,《〈中学生〉杂志六十年》,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29—30页。
[32] 《编辑室》,《中学生》1949年第214期。
[33] 叶圣陶1949年4月11日未刊日记。本文所征引未刊日记由卓玥女士提供,特致谢意。
[34] 宋云彬:《宋云彬日记》(上),第163页。
[35] 《发刊辞》,北平:《进步青年》1949年第1期。
[36] 本志同人:《谈谈本志的旨趣》,《中学生》第190期,1947年8月1日。
[37] 叶圣陶1949年4月15日未刊日记。
[38] 叶圣陶1949年5月3日未刊日记。
[39]《〈进步青年〉与〈中学生〉合并》,《中学生》1949年第215期。
[40] 卢弓:《从〈中学生〉到〈进步青年》,《进步青年》1949年第218期。
[41] 《编辑室》,《进步青年》1949年第216期。
[42] 《开明书店报告》,第16页。
[43] 《开明书店一九五〇——五二年编辑出版计划》,上海档案馆藏,B1—1—1887。
[44] 参见拙文《建国初青年教育的呈现与展开:围绕〈进步青年〉的讨论》,《澳门理工学报》2024年第1期。
[45] 王振华:《清算我的阅读态度》,《进步青年》1950年第225期。
[46] 《解放以后的上海杂志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第41页。
[47] 《解放以后的上海杂志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第51页。
[48] 顾均正:《生产部报告》,《开明通讯》1950年第5期。
[49] 胡叔循:《一九五一年的〈进步青年〉》,《开明通讯》1950年第 5期。
[50] 《文化简讯》,《人民日报》1952年3月3日。
[51] 叶至善:《我编〈中学生〉的那些年》,《〈中学生〉杂志六十年》,第23页。
[52] 子冈:《怀念振黄》,《中学生》第84期,1945年2月。
[53] 卢弓:《从〈中学生〉到〈进步青年〉》,《进步青年》1949年第218期。
[54] 胡乔木:《改进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年),第258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