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显与隐——以巴金《旅途随笔》的文本变迁为例
巴金的思想是丰富多彩的,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恐怖主义、爱国主义等均有体现。但并不是每种思想都凸显于巴金人生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自有其思想主脉。作品是作家思想的载体,巴金不同时期的作品留下了巴金思想的印痕。学术界在论及巴金的思想时,主要以其小说为论述的对象。事实上,作为非虚构的散文,由于“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1],自然也是窥探巴金思想的重要载体。加之巴金不同时期又不断修改旧作,故其散文文本的变迁也是巴金不同时期思想显与隐的直接体现。《旅途随笔》是巴金早期创作的代表性散文作品集。自30年代初至90年初,巴金对《旅途随笔》不断修改达8次之多,产生了近十种版本。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巴金经历了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随着大时代的更迭以及共和国不同时期,巴金的思想也有剧烈的变化,巴金在反复修改旧作时也就留下其思想变迁的烙印。拙文试图以《旅途随笔》为例,在梳理不同时期的文本变迁中一窥巴金从30年代至90年代初思想主脉的显与隐。
一、初刊到初版再到开明本:无政府主义作为思想主脉
1933年5月到7月间,巴金从上海出发游历了福建、香港、广东等地。在旅行之余,他把沿途的见闻和感想写成了一系列散文,相继在《文学》、《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1934年初,生活书店决定编选“创作文库”丛书,巴金被邀成为该丛书的作者之一。借此机会,他就把1933年南方之旅途中所写的系列散文以“旅途随笔”[2]为名纳入,并为该书写了《序》,初版《旅途随笔》于1934年8月出版。初版本原计划是28篇,但《捐税的故事》、《海珠桥》、《薛觉先》和《鬼棚尾》四篇“被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老爷用朱笔勾去,仅在目次中保留了篇名”[3],故初版本只收录24篇。1934年10月,《旅途随笔》再版时,巴金把刚发表的《一个车夫》增收入《旅途随笔》,书末又增加了一篇《再版题记》,再版本收录25篇。1939年,巴金把《旅途随笔》交开明书店重版。利用这次重版之机,巴金对文字上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在篇目上补上了《海珠桥》、《薛觉先》和《鬼棚尾》三篇,但又删掉了《亚丽安娜·渥柏尔格》一篇,共27篇。他还为此写了一篇《重排题记》。

1934版《旅途随笔》·巴金著 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旅途随笔》中的作品大多写作于巴金的旅途之中,从每篇文末的写作时间地点以及发表时间可知,巴金事前并没有结集的计划,大多是边写边刊,写作和发表都比较随意。利用纳入“创作文库”之机,巴金对收入的篇目做了第一次修改,笔者依据初刊本和初版本对校,粗略统计共修改156处[4]。以生活初版本为基础,开明本《旅途随笔》共修改了317处(包括《序》的改动)。这两个版本的修改,初步实现了作品艺术的完善,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删改和调换部分词句和语序,使表达更加准确规范。这一情况的修改最多,初版本约有96处,开明本约有274处。初版本的修改如在《亚丽安娜·渥柏尔格》中,“描写的的情景”改为“描写的那情景”,对手民之误进行了更正,“刚不过二十岁”改为“刚过二十岁”是为了表达的规范; 开明本的修改如把初版本中描述一个朋友“这朋友是很可爱的,他平日被我们称为粗暴的人”改为“这朋友平日被我们称为粗暴的人”,因为“可爱”和“粗暴”在表意上有明显的矛盾;等等。二是关于思想感情方面的改动,这类改动较少,初版本约有11处,开明本约有3处。初版本的修改如《海上》一篇,巴金把初刊本开头的五个段落整个删去了,这五个段落详细地描写了巴金在上海 “一·二八事变”期间经历的种种,包含了作者压抑沉闷情绪的释放。三是增加调整一些词句,对文本做出补充,使表达更加明确。这类修改初版本约有28处,开明本约有33处。如《赌》的修改:
赌博并不是人的根性,但是在我们的这种混乱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发横财却成了一般人的渴望,以极少的代价得最大的报酬,而且有的人,他们一生就只有极少的代价。(初版本)
赌博并不是人的根性,但是在我们的这种混乱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发横财却成了一般人的渴望,以极少的代价得最大的报酬,而且有的人,他们一生就只有极少的代价。但他们却不能没有获取最大报酬的妄想。所以打花会,买彩票的大半是贫苦的人。这些“生意”能够顺利发展,这是无足怪的。从前有人把State Lottery翻译作“国赌”,我觉得十分恰当。(开明本)
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大段的评论,更鲜明地表达了巴金对于赌博的批判态度。四是对文章的准确性和客观性进行确证,初版本约有21处,开明本约有7处。初版本的修改包括对人称的修正如“朋友B”改为“朋友N”;对作品中字母符号的解释如“NM”改为“马哈诺”,“L.F”改为“发布里”; 开明本的修改如在《西班牙的梦》中把“巴斯罗纳”改为“巴塞罗那”,是对翻译标准的调整;在《朋友》中将“日军”改为隐晦的“X军”,显示了作者不得不考虑时局的无奈;等等。
除了对文本内容的修改外,不同版本篇目上的变化值得探讨。由于当局的图书审查制度,从初刊本到初版本(再版)原拟的四篇未能收入。《捐税的故事》讽刺了当局的捐税制度;《海珠桥》对当时的广东省省长胡汉民有不敬之词;《薛觉先》讽刺了当局的文化政策并宣扬民众教育和启蒙,有煽动民意的嫌疑;《鬼棚尾》讽刺了当局“靠着女人的皮肉吃饭”还要“摆起庄严的面孔”的一帮老爷。这四篇文章表达了巴金对当局的不满,自然会被图书审查的“老爷”勾去,初版本目录上尽管列出了这四篇的题名,但注明“缺”。显然,巴金此举不但可引导读者“按题索骥”,更是向当局的一种示威。1934年10月,巴金在《旅途随笔》的再版中增录了《一个车夫》,文中那个倔强、坚定不惧任何权威的少年车夫正是在生活洪流中得到了锻造,巴金以之作为此书的结尾,其暗示意义颇为明显。七·七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联手抗日。国民党执政当局忙于正面抗战,无暇兼顾文化上的审查,出版的管制曾一度放宽。开明本《旅途随笔》借此补上了初版时被当局删掉的《海珠桥》、《薛觉先》和《鬼棚尾》三篇,《捐税的故事》“因为原稿已失,而且这篇短文也应该重写了”[5],故未能补入。同时又因《亚丽安娜·渥柏尔格》已收入《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所以不再收入,这样开明本《旅途随笔》一共收27篇。

年轻的巴金
早在20年代初,巴金就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并不断联合同道,从事社会活动,渴望通过革命行动改变眼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梦想着消灭人类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建立一个万人安乐和幸福的社会。1927年,国民党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并且在随后逐步巩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镇压后迅速瓦解。巴金才将这种剩余的政治热情与无可奈何的失望情绪倾吐在创作中,用他的文学活动来宣泄已经死亡的政治激情。正如有论者所说:“安那其是巴金人生道路的起点,是连接他与世界之关系的重要纽带,是他观察社会、考量历史、自我认识和评价的重要尺度”,[6]1933年这次南方之旅,也可以看作是巴金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表达理想和信仰,审视友情、城市、民众等主题的精神漫游。在《旅途随笔》从初刊到初版以及开明版的版本变迁中,涉及与无政府主义相关人物的文字不断增加。如《机械的诗》的修改:
克鲁泡特金的一生就证明出来他的确是一个懂得诗的人。(初刊本)
克鲁泡特金的一生就证明出来他的确是一个懂得诗的人。所以左拉说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是“一首真正的诗”。(初版本)
增加了左拉对克鲁泡特金的评价,加强了巴金对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的推崇力度。又如《南国的梦》的修改:
他们和匡互生一样,都是献身于一个教育理想的人。(初刊本)
他们和最近在上海逝世的匡互生(对于这我所敬爱的人的死,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表明我的悲痛。他的最后是很可怕的。他在医生的绝望的宣告下面,躺在医院里等死,竟然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许多人的眼泪都不能够挽救他。)一样,都是献身于一个教育理想的人。(初版本)
对在初刊本中仅仅出现一个名字的“匡互生”增加了大段注释,表达出巴金对友人逝去的怀念之情。匡互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驱者,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无政府主义者。巴金最初是在友人的交谈中认识匡互生的,他对匡先生的教育思想方法很欣赏,并且也很敬佩对方的道德人品和教学主张,“把他当作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 [7]
《旅途随笔》记录了巴金敏感的心灵的反应,他是“怀着歌德式的悲哀而旅行的,于是所遇见的都引起他忧郁的回忆,宗教式的忏悔”。[8]他不断诉说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在对城市、乡村和教育的书写中展示了无政府主义者早期的实践活动;在对友情的书写中进行了无政府主义者对个体和集体关系的自我省察与思索;在对底层民众的书写中既表达了同情,也表达了对民众力量的信心等等。总之,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旅途随笔》诸篇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但不可否认,巴金又是深受法国的伏尔泰、卢梭、俄国的拉吉舍夫等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影响,他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旧文化,对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倒行逆施给予严厉的批判。《旅途随笔》在三十年代诸版本中,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紧密融合在一起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初版时被当局删掉的《海珠桥》、《薛觉先》和《鬼棚尾》、《捐税的故事》四篇就是向反动当局及旧制度、旧文化的批判与反抗。笔者看来,尽管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三十年代《旅途随笔》诸版本中都有体现,但无政府主义无疑是此时期巴金的思想主脉。
二、平明本到新文艺本再到文集本:逐渐强化的革命民主主义
建国后第一版《旅途随笔》于1953年6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篇目上较开明本少了《西班牙的梦》和《薛觉先》2篇,删掉了《重排题记》,增加了《前记》。在文字上,巴金对收入的篇目均有修改。1955年11月,平明出版社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中合并于新文艺出版社,《旅途随笔》又获得了重版的机会,借此机会,巴金对《旅途随笔》再次做了一些修改。正文前有《前记》和《序》,篇目上较平明本,又删掉了《南国的梦》。正文共收录了24篇。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巴金文集》,这是第一套系统地展现巴金“三十年文学工作的一点成绩”[9]的丛书。利用这次出文集的机会,巴金于1957 年到 1961年间对选入文集的作品做了最为集中和最大规模的一次作品修改。《旅途随笔》收入《巴金文集》第10卷,于1961年10月出版。如果说平明本、新文艺本的修改更多是作家主动修改的结果,而文集本的修改则增加了外界的压力,外力之一是1958年写的《法斯特悲剧》招致的批判让巴金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另一外力则主要指1958年至1959年间巴金遭到一场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拔白旗”运动,而这场一年多的运动中,“对巴金作品的批判集中在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立场、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人类爱、对工人阶级的歪曲、未指明革命道路等方面”[10]。文集本《旅途随笔》收录24篇,主要以新文艺本为参考版本,对收入的每篇作品又进行了一次修改。

1958年《巴金文集》,该卷收录《海行杂记》《从南京回上海》《旅途随笔》《旅途通讯》《旅途杂记》《短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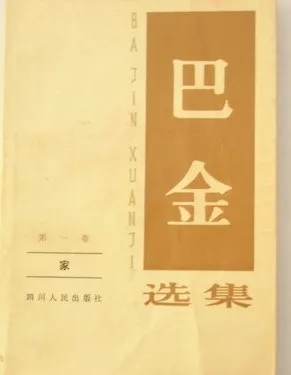
1982年版《巴金选集》巴金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版《巴金全集》巴金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旅途随笔》从开明本到平明本的改动比较少,共有约40处。新文艺本《旅途随笔》又在平明本基础上修改1000余处,对《前记》和《序》都做了很大改动,是版本变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文集本《旅途随笔》以新文艺本为底本,又改动了462处。这三次修改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字词和语句进行调整,使表达更加书面化、准确和简洁。这类修改平明本约有24处,新文艺本约有911处,文集本约有394处。平明本的修改如“入了”改为“落到”,“从前”改为“以前”,“洒布”改为“散布”等,将方言口语改为书面语,是巴金响应新时期文字规范化的一种表现。新文艺本的修改如“清朗的早晨”改为“晴朗的早晨”,“两点钟”改为“两个小时”,“我所过的生活”改为“我的生活”,“我的沉闷的光阴”改为“光阴”。文集本的修改如“星子”改为“星星”,属于用词规范的修改;“他那个地方是我常去的”改为“我从前常去他那个地方”,属于语序的修改;“回到故乡去了”改为“后来就回到故乡去了”,增加了连接词,使上下文衔接更顺畅;“笔墨和纸”改为“纸笔”,将同类描写合在一起,使行文更简洁等。
二是增加一些内容,对细节做出补充。这类修改平明本约有8处,新文艺本约有143处,文集本约有7处。平明本的改动如把“机械是完全的,有力的”改为“机械是创造的,生产的,完美的,有力的”,明确表明了巴金对于机械文明推崇赞扬的态度。再如把“布南德斯”改为“文学批评家布南德斯”,是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新文艺本的改动如“校前”改为“学校门前”,增加了方位细节的表述;“带笑问我”改为“她带笑问我”,表明了说话人的身份;“Delage”改为“德拉日(Delage)”,对读者可能不清楚的名词做了补充。文集本的修改如《一个回忆》里对“消磨时间的工作”加了“我拿起了我的笔”的补充说明;《香港》里对英文Peak Hotel做了“旅馆”的注解;《鬼棚尾》里“南京XX部”改为“南京铁道部”,对朋友郑工作过的单位恢复具体所指。
三是对用词错误以及客观内容表述方面的修改。这类修改平明本约有4处,新文艺本约有28处,文集本约有6处。平明本的修改如《游了佛国》将“大竹敲杠”改为“大敲竹杠”,《农民的集会》中“知土豪劣绅斗争”改为“跟土豪劣绅斗争”,都是对笔误的修正;《朋友》中将“X军”改为“日本兵”,是由于时代背景变化做出的调整。新文艺本的修改如将朋友的病情“染着不治之疾”改为“害肺病”;再如将“A”改为“洪”,“朋友Y”改为“朋友梁”,“X”改为“叶”,“N”改为“陈”,对于之前以字母形式出现的人物改成文字,便于对人物的真实身份进行查证。文集本的修改如《一千三百圆》中“这些女人都是大家庭里的姨太太”改为“据说这些女人都是大家庭里的姨太太”,加了“据说”二字,使描述更为合理。《鬼棚尾》中“十多个字”改成“十个字”,属于对准确性的修改;《赌》中“我就从不会做这样的梦”改为“我就从不敢做这样的梦”,由“从不会”到“从不敢”表述更加真实,属于对错误的更正等。
随着抗战以及四十年代的到来,残酷的社会现实让巴金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有了反思,他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不要国家,反对一切战争的观点。他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现实斗争的冲击下,巴金思想中的诸种因素,必然有一番消长得过程,会促使巴金的思想,发生相应的变化。”[11] “在现实社会的矫正下,他更加靠拢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力量。到了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种发展倾向更为明显。”[12]解放初的巴金一直颇受文艺界高层重视,他积极向新生政权靠拢,以真诚热烈的态度歌颂新中国。巴金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13]新政权的成立促使巴金思想上发生了改变,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就是利用作品重版(再版)之机不断修改作品的内容。为了适应新的时代的语境,“改”更多意义上代表着一种态度和立场。除了对字词句斟酌外,巴金在五十年代对《旅途随笔》的三次修改也留下了特殊时代的烙印,反映出巴金的思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对工人、农民叙述的修改。如《省港小火轮》开明本到平明社本(新文艺本、文集本同)中一段对工人的叙述的大幅度修改,增加了许多细节的描述。由“工人”到“工友”这一称呼的变化以及增加的“工友”和“我”相互“笑了笑”的互动,反映了工农兵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带来的时代语境的改变。其他如文集本的修改如《农民的集会》里把“简单的农民”改为“单纯的农民”,由“简单”到“单纯”的修改,应是出于担心会丑化农民形象的考虑;《谈心会》里“热烈的爱人”改为“热烈地爱人民”,从“人”到“人民”体现了和时代主旋律的一致性。新文艺本《省港小火轮》中删掉“中国人嗑瓜子的习惯简直无法改掉。”和《扶梯边的戏剧》中删掉“在中国大概没有人会把时间看得很贵重的。” 在文集中,对于一些感性用词巴金也进行了改动,如“憎恨”改成“厌恶”,“我感动地说”删改成“我说”等等。显然,这些旧时代的语句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中不合时宜,必须删掉。
第二、对薛觉先、梅兰芳等旧戏剧人物叙述的修改。在开明本中有《薛觉先》一文,巴金在文中显然对薛觉先这样的旧戏剧人物给以批判。解放后,薛觉先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先后当选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员,全国政协委员。显然,《薛觉先》这样的文章在新的时代里不利于文艺界的团结,故《旅途随笔》平明本、新文艺本和选集本均未收入。此外,《平津道上》曾涉及到梅兰芳的叙述,巴金把“梅兰芳”替换成“青衣们”,显然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第三,清除无政府主义的痕迹,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相关的叙述逐步被删削或遮蔽。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无政府主义则被视为反动思想,必须进行批判与清算。从50年代中期始, 就陆续有文章揭露和声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毫无疑问,五十年代初的政治语境给了巴金以压力,借编选自己的作品之机,巴金对《旅途随笔》中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人物、语句、篇目都被一一删去。《旅途随笔》平明社本、新文艺本以及选集本自然也是如此。平明本的修改如《机械的诗》中删去了对克鲁泡特金“一生就证明出来他的确是一个懂得诗的人”的一段评价。在新文艺本《谈心会》里,巴金对第二部分妃格念尔的故事和苏菲·波停娜的故事做了大段删改。这两个俄国的女革命家曾经对巴金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思想产生过很大影响,此处的删改表明了时代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对于他个人思想上的影响。《西班牙的梦》中有关于早期无政府主义暴力革命理念的书写,已经不符合时代语境,在平明本时删去;《南国的梦》赞扬了一位平民教育家的感人事迹,但文中涉及到赫尔岑、匡互生等无政府主义人物,故在新文艺本时又删掉此篇。
平明本《旅途随笔》删去了开明本的《重排题记》,增加了一篇《前记》(新文艺本正文前也收录了这篇《前记》),则是为了表明态度和立场。巴金在这里检讨了自己作品的不足:“我的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薄弱,所以我的作品中含有忧郁性,所以我的作品中缺少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构思。我的作品的缺点是很多的,很早我就说我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作品。”[14]巴金所说的思想性不够更多的是指作品中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现得少。在文集的《前记》中,巴金又再次检讨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种种的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生活,全作品。”但他再次重申:“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从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15] 巴金以此表明自己是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强权,反对压迫,突显自己思想进步的一面。
此外,巴金对作品中革命民主义思想的强化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色彩的削弱可能还与五十年代末的一场论争相关。扬风在《巴金论》和《巴金的民主主义思想》中认为巴金是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杰出的现实主义者。[16]他的这一结论遭致刘正强的反驳,他在《巴金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中则认为巴金世界观中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超阶级的人性论,让巴金只能停留在一般的民主主义阶段。其作品缺乏一种概括现实的逻辑力量,背离艺术的真实,对现实生活做歪曲的描写,具有反现实主义倾向。[17]李希凡也在《关于巴金作品的评价问题——评扬风的<巴金论>》中不认同扬风的结论,他认为巴金的作品中,“民主主义思想当然占有着显要的地位,但是,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在他的前期作品里,也占据着一个不可抹杀的地位。”[18]
总之,五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以及遭受到的批判被迫让巴金多次对《旅途随笔》做了与时俱进的修改。由于对涉无政府主义的人物、语句、篇目都被一一删去,而体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相关的篇目不但得到保留,而且在文本修改中又不断强化。正如新文艺本版权页上的《内容提要》中指出作者“写出他在中国南方和北方的见闻,也写出他的爱与憎”。[19]故《旅途随笔》在五十年代的文本变迁中,除语言表达上日趋完善外,但更重要的是,修改使《旅途随笔》的思想主脉从无政府主义置换为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巴金被极力隐去,革命民主主义的巴金却得到凸显甚至强化。
三、文集本到选集本再到全集本:革命民主主义为主无政府主义为辅
对于六七十年代遭受各种屈辱摧残的巴金来说,他经历了从盲目跟从到逐渐醒悟。在他重获写作的自由之后,他通过翻译《往事与随想》、撰写《随想录》来反思历史、解剖自己,重新找回追求理想与真理的勇气。当四川人民出版社提议为他编一套《巴金选集》时,鉴于他编的《巴金文集》被认为是“十四卷邪书”受到严厉批判,丧失了再版的机会,他决定编一套按照自己意思,保留自己真面目的选集:“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20]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十卷本的《巴金选集》[21]。由于是选集,《旅途随笔》一书只选了12篇。编入第八卷第一辑。据对校发现,所选篇目根据文集本排印,编选过程中巴金仅对一些字词做了少许改动。在《巴金选集》第七卷(短篇小说选)中收入了《亚丽安娜·渥柏尔格》。
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计划编印《巴金全集》,主要由该社编辑、巴金的老朋友王仰晨(字树基)负责。1985年11月14日,巴金在致树基的信中说:“《巴金全集》的事我看只有你一人关心,你在抓,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这究竟是我的事。那么明年我也来搞搞,不管大小,总得出点力。”[22]在巴金和王仰晨两人的努力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6-1994年间出版了《巴金全集》(26卷),收录了巴金除译文以外的绝大部分作品。《旅途随笔》收入第12卷。在篇目上,相比文集本多了《南国的梦》,《西班牙的梦》,《捐税的故事》,《薛觉先》和《亚丽安娜·渥柏尔格》5篇。正文前有《序》、《再版题记》和《重排题记》。全集本《旅途随笔》共29篇。至此,《旅途随笔》终成全本。
从《巴金选集》到《巴金全集》,时间从七十年代末到了九十年代初,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此也可一窥巴金思想的细微变化。新时期初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仍然是颇为敏感的话题。巴金在1978年写的《〈巴金选集〉后记》中对自己早年接触各种思想有如此描述:“后来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刘师复、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来的,再加上托尔斯泰的象《一粒麦子有鸡蛋那样大》、《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一类的短篇小说。我还读过一些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记。我也喜欢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是我多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就渐渐地丢开了它。我当时思想的浅薄与混乱不问可知。”对于无政府主义带给自己的影响,巴金也有自我批评:“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无政府主义找寻一条道路,我读过好些外国书报,也译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尔这类人的回忆录,可是结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虚。”[23]所以,选集本所选《旅途随笔》中篇目几乎没有明显无政府主义的烙印。加之选入的12篇又依据文集本编入,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语句也全部清除掉了。以短篇小说入选巴金选集的《亚丽安娜·渥柏尔格》一篇中对涉及亚丽安娜的叙述,巴金也删掉了“后来就做了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一句。可见,巴金在70年代末仍对自己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有所顾忌。
随着思想逐步解放,中国史学界在质疑和减弱加诸在无政府主义的政治预设的基础上,对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渐趋平和,充分肯定了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作用,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进行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24]与此同时,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系也重新得到了深入的探讨。1980年,陈思和、李辉在《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一文中论证了巴金早期的主导思想是无政府主义,但他们并未像五十年代的论者那样,把巴金推向反革命的深渊,而是适度地肯定了无政府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进步意义:“无政府主义的‘反强权’思想在当时起到了反对封建军阀专制, 反对封建文化道德的战斗作用。”“正因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特定条件下产生了反封建反专制作用, 它才跟巴金反封建的斗争合了拍, 成为巴金的战斗武器。”[25]此后,牟书芳、李存光、花建等人也对巴金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以及对学术界对无政府主义的客观评价影响了巴金,他开始直面自己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如在1982年编辑《怀念集》时,收录了回忆无政府主义者的两篇旧文:《悼范兄》和《忆施居甫》;1983年,他写了《怀念一位教育家》;1986年,他又写了《怀念非英兄》,这些文章系统地表达了巴金对无政府运动及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借编选全集之机,巴金又把早年他在上海、法国等地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一些文章收入,希望给人们提供全面了解自己精神追求和思想实质的原始资料。同时,晚年的巴金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了深入的反思。正如他在《巴金全集》第6卷代跋中,用理想主义的称谓代替了对《爱情三部曲》中无政府青年“革命者”的称谓,“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他们并不空谈理想,不用理想打扮自己,也不把理想强加给别人。他们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最后,他解释了他一再重申的“我有信仰”的所指:“一直到最后我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仰,对人民的信仰”[26]。可见,巴金站在人民的立场否定了无政府主义革命实践的一面,而对其社会实践(如教育活动)以及精神实践的方面则给以肯定。[27]
巴金对编印全集十分慎重,把它视之为自己对人民最后的交待。“以年届八九十的高龄,坚持扶病校阅了这套全集的全文,并对26卷中的15卷写了《致树基(王仰晨)》(《代跋》)共16篇,表达了他此时此地的心境,也谈了许多他对具体作品的编辑意见,和某些写作背景。”[28]在收入《旅途随笔》时,巴金又做了一些修改。全集本《旅途随笔》收录29篇[29],每篇前注明初刊的时间和刊物,文末又标注出写作的时间。正文前有《序》、《再版题记》和《重排题记》[30]。显然,巴金试图恢复到三十年代的《旅途随笔》。但据对校发现,全集本原则上根据选集本排印,选集未收录的参照最后一次印刷的版本(即文集本),因此全集本主要是综合了文集本和选集本的一个版本。字体全部采用了简体字,仅有6处[31]关于字词的修改,如“湿”改为“湿润”,“撒在”改为“洒在”,“受”改为“接受”,“震得快聋了”改为“快震聋了”。从文集本到全集本,《旅途随笔》值得注意之处在于收录了自初刊本以来的全部篇章,包括了以前被反复删减的敏感篇目如《薛觉先》、五十年代被删去的《南国的梦》《西班牙的梦》,《捐税的故事》得以首次收录,《亚丽安娜·渥柏尔格》从巴金选集的短篇小说卷中重新收入。全集本《旅途随笔》终得首次以完整面目示人。

全集本《旅途随笔》(2017年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尽管全集本在篇目上恢复到了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梦》、《南国的梦》《亚丽安娜·渥柏尔格》等原无政府主义色彩较浓的篇目也得以再次收入,但由于其余诸篇仍以文集本收入,原文集本所收篇目中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叙述又被大量删除。全集本篇目上尽管恢复了历史的全貌,由于文本中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相关的人物、叙述已消除殆尽,故全集本中无政府主义烙印远没有生活书店本、开明本明显。而全集本在体现革命民主主义方面,除了继续采用文集本、选集本的修改和篇目之外,还增加了批评三十年代各地各种苛捐杂税的《捐税的故事》一篇,该文文末结尾如此:
这情形是不能够长久继续下去。将来不是那一群贫民被压成肉饼,就是他们站起来,抛开桌面,去干他们自己的事情。然而无论如何,那时候是在没有人去给那些怪物抬圆桌面了。
显然,作者在这里暗示被苛捐杂税奴役的民众终有一天会揭竿而起,推翻压在他们身上的统治阶级。总之,全集本《旅途随笔》未能完全恢复到三十年代的原貌,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为主,无政府主义为辅的思想底色。
结 语
时代的更迭,政治风向的改变,以及巴金个人思想的变化,都在《旅途随笔》的文本变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旅途随笔》经历数次版本变迁,巴金对文本进行了多次修改,使得作品在文本艺术上不断得到完善,体现了他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但原作为作品思想主脉的无政府主义却在巴金的持续修改中被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所代替,至全集本时仍然未能恢复历史的原貌。在笔者看来,在众多版本中,开明修订本虽然在语言规范方面和今天的标准仍存在少许差别,但收录篇目比较完整,尤其是一些反映巴金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篇目都收录其中,内容上也没有经过建国后的大幅删减,这是最能体现巴金早期的思想和写作风格的“善本”。
《巴金全集》主要由巴金以及编辑王仰晨合力编选而成,对于全集篇目的选定以及删改主要由巴金亲自操刀。对于他早期有关无政府主义的相关著述,最后也只是选择性地收入了一部分,这体现作家和出版社对文本的控制。[32]显然,《旅途随笔》也并没有全面恢复历史的原貌。巴金曾说:“几十年来我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的思想不断地在变化,有时变化小,有时变化大。”[33]在他看来,时代在变,作家思想在变,而文本自然也需要变,而最近的文本才是他心目中的定本。“不论作为作者,或者作为读者,我还是要说,我喜欢修改本,它才是我自己的作品。”[34]巴金不辞辛劳对所选全集的作品逐一过目或删改,显然是以收入全集的文本作为定本。作为文学研究者而言,作家全集更应该注重作品原貌的呈现,面对巴金的《家》、《旅途随笔》等这样不停修改的文本,我们是尊重作品的原貌还是作者最后的定本?是尊重历史还是为尊者讳?2009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启动了新版《巴金全集》的修订工作(据悉,这项工作至今仍未完成),将增补巴金在全集出版以后陆续写下的文字、全集出版时遗漏未收的文字和20多年间新发现的佚文佚信。此外,还将陆续整理出巴金在“文革”期间被迫写下的部分检讨与交代,编选进新版全集。[35]窃以为,作家全集自然应最大努力实现全,增补是必要的,但重新考量已出版的《巴金全集》各卷文本的底本选择,并对其修订加以汇校也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ZDA279)]
参考文献:
[1]巴金:《谈我的“散文”》,《萌芽》第9期,1958年5月。
[2] 其中《平津道上》《一个车夫》写于北平,《三等车中》写于天津,这几篇记录了巴金北上的见闻。
[3]巴金:《重排题记》,《旅途随笔》,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4月版。
[4]修改标准:标点符号变化未统计;字、词的更换或删减为一处;字、词的增加为一处;字、词在一句中的顺序发生变化为一处;一篇中的同类同字修改算一处;一句中多次修改视为一处;增加一句话或一段话为一处;删掉一句话或一段话为一处;有连续的段落增删亦算作一处(一句以逗号分隔的字段为标准;段落修改以篇幅较大的改动为标准,其外分布零散的改动仍分别计数)。具体统计中修改次数会有出入,难以做到绝对准确,仅供读者参考。
[5]巴金:《重排题记》,《旅途随笔》,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4月版。
[6]张全之:《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194页。
[7]巴金:《怀念一位教育家》,巴金《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9月版,第584页。
[8]大灾:《〈屐痕处处〉〈欧游杂记〉〈旅途随笔〉〈欧行日记〉》,《华北日报》1935年11月5日。
[9]巴金:《<巴金文集>前记》,《巴金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版。
[10]张永新:《“拔白旗”运动中的巴金作品“讨论”》,《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1期。
[11]吴定宇《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
[12]陈思和 李辉:《巴金研究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94页。
[13]巴金:《巴金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页。
[14]巴金:《前记》《旅途随笔》,平明出版社1953年6月版。
[15]巴金:《〈巴金文集〉前记》《巴金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3月版。
[16]《巴金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巴金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发表在《读书》第19期(1958年10月)。
[17]刘正强:《巴金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读书》1959年第2期。
[18]李希凡:《关于巴金作品的评价问题——评扬风的<巴金论>》,《管见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9月版,第195-196页。
[19]《内容提要》,《旅途随笔》,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
[20]巴金:《〈十卷本巴金选集〉后记》,《读书》1982年第3期。
[21]以《巴金选集》为名的书有不少,如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4月版,开明书店1951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等。此处选用巴金认可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2]巴金:《致树基》(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巴金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23]巴金:《〈巴金选集〉后记》,《读书》1979年第2期。
[24]李华兴:《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复合体——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
[25]陈思和、李辉:《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
[26]巴金:《〈巴金全集〉第6卷代跋》,《巴金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0页。
[27]胡景敏:《巴金: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
[28]丹晨:《读〈巴金全集〉》,《书城》1995年第5期。
[29]这29篇,除了根据选集本和文集本的收入24篇外,其余5篇依据的版本情况如下:《南国的梦》、《西班牙的梦》依据初版收入;《捐税的故事》和《薛觉先》依据初刊收入;《亚丽安娜·渥柏而格》依据《巴金选集》第7卷编入。
[30]有意思的是,巴金五十年代为《旅途随笔》所写的《前记》则未收录,这表明全集本《旅途随笔》试图向三十年代的《旅途随笔》回归。
[31]《一个回忆》1处,《农民的集会》1处,《鬼棚尾》2处,《三等车中》2处。
[32]陈思和:《我心中的巴金先生》,《巴金晚年思想研究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330-331页。
[33]巴金:《关于〈火〉》,《文汇报》(香港),1980年2月24日。
[34]巴金:《关于〈海的梦〉》,《文汇报》(香港),1979年7月15日。
[35]《新版〈巴金全集〉修订工作启动》,《人民日报》2009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