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故事之后 ——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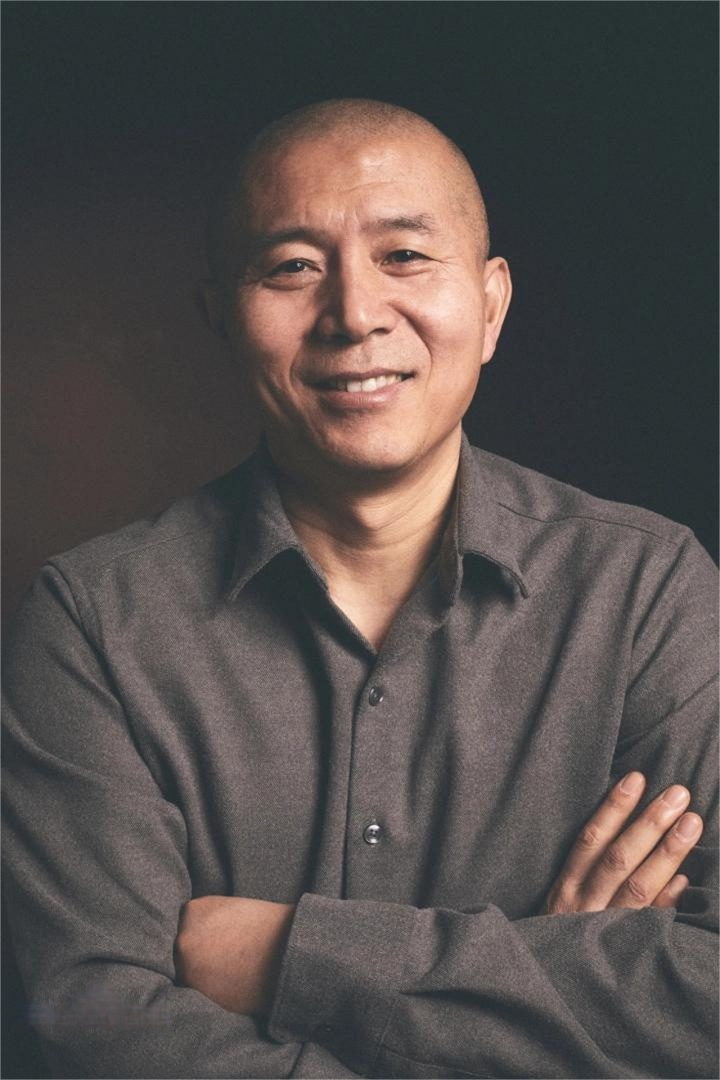
毕飞宇

霍安琪
我看到了时间
霍安琪:毕老师您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在“云上”与您进行这次对谈。我很喜欢您的新作《欢迎来到人间》,但是我最开始对它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您在采访中说这本书成了您的一个“噩梦”。我很好奇,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您这样一位成熟作家的“噩梦”?
毕飞宇:我三十五岁那一年,依仗《京剧知识一百问》,写了《青衣》。《青衣》的成功给了我不算健康的启示:虚构无所不能。后来的《推拿》进一步激发了我,你看,那样的世界我也可以自由地出入。决定写《欢迎来到人间》之后,我在医院里学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隔行如隔山”的“山”有多高。我得承认,那个时候我很盲目,我在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刻开始写作了,很快我就遇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不能出错。写京戏,《青衣》有容错率,写推拿,《推拿》也有容错率。但是,写外科手术,如果出错,就成了草菅人命。这是一个很致命的感受。先不说别的,关于知识,《欢迎来到人间》就可以要我的命。写到一半,我全部推翻了——这个故事现在广为人知,你看看,这个作家多好,对自己的要求多高,写了一半的作品他都可以推翻。我还是说实话吧,我实在继续不下去了,我完全没有能力去完成医院内部的一部小说,我能做的,只能是把小说拉到医院的外部来。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但是,这个“之一”就可以构成一个作家的噩梦。
霍安琪:很有意思,我以为您写《青衣》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资深的梨园爱好者,没想到依仗的竟然是《京剧知识一百问》。医学确实艰深复杂。医学博士比文学博士或者戏曲博士难读多了,也就没有《外科手术一百问》这种书可以帮您了。虽然没能在知识或者技术上理解外科手术,但您为了准备这部小说,也在医院里观察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在您的新书发布会上,戴锦华老师说她在您的这部小说中,特别是在医生、护士、病人这三者的关系中感受到了一种寓言性。您对医生、护士、病人三者的关系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吗?
毕飞宇:戴老师的话犹在耳边,我很感谢她这么说,这是一个批评家的宽度。我们必须承认,作品的寓言性有时候就是作品的生命。不过,在这里我要做一个反向的强调,我是写作者,写作者过分在意寓言性,大部分时候会很危险,弄不好就会丧失你的诚实,还有可能把你带进象征主义的泥沼。我的极端看法是,写作者不应该纠结于作品的寓言性。相对于抵达了某种程度的作品来说,寓言性是天然的,寓言性是好作品投在大地上的影子,苍天在上,你怎么能拒绝阴影呢?准确性到了,寓言性必然就如影随形。某种程度上说,寓言性是作者与读者彼此相爱的结果,它是彼此生命力的富余。我认为,作者不应该刻意提供寓言性,这个念头他不该有,他能够提供的仅仅是寓言的可能。作者如果把寓言性放在首位,什么都得不到。关于寓言性,我想这样做一个总结,寓言性是非自觉的,是非自觉导致了它的必然。
霍安琪:的确,批评家和作家有着不同立场。当作家忠实地面向现实本身、对象本身,寓言性就会自然地生成,而批评家也就有了可以开掘的富矿。您曾说过这本书最初来自于一个 17 年前的新闻。我很好奇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闻?
毕飞宇:它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许多作品都存在一个第一动因的问题,对《欢迎来到人间》来说,那个新闻就是我的第一动因,它为我提供了一个人的命运。我的工作是,展现另一个人的另一种命运。
霍安琪:有意思的是,小说写的是“非典”时期的故事,而小说的出版也正好赶上了后新冠时期,无意中构成了历史的前后呼应。您能否谈谈您对“非典”的记忆?这段经验对您创作《欢迎来到人间》意味着什么?
毕飞宇:我生活在江苏,对“非典”几乎没有记忆,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概念,或者说,时间的刻度。《欢迎来到人间》有相当一部分是疫情期间写的,它和“非典”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一部小说来说,即使是概念和时间的刻度,它们都有意义。
霍安琪:您说《欢迎来到人间》有相当一部分是疫情期间写的,是因为疫情的封控给了您大段的写作时间?还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生活经验让您对这个发生在医院里的、有关生死的故事有了很多新的灵感?
毕飞宇:我不缺时间,时间对我来说从来都很宽裕,我感觉不到时间。我在疫情期间重新捡起这部作品,恰恰是因为我看到了时间,时间本身。老实说,时间是不该被看到的,当一个人看到了不该看见的东西,他会惊悚。我坚信,惊悚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在惊悚的时候嘴巴一定会张开,或表达,或胡言乱语。事实上,在疫情来临的时候,这部小说我已经写好了,但是,从天而降的时间让我改变了主意,我把小说的后半部分删去了,我觉得它配不上我的经历。我哪里能想到我在此生会遇上这样的场景呢?我不想浪费它。当然,我并没有直接去表现那样的场景,我想表达的,是场景与傅睿之间的内在关系。
霍安琪:从“感觉不到时间”到“看到了时间”,听起来是一个不太令人愉快的变化。因为当时间被人感觉到的时候,通常伴随着焦虑。
毕飞宇:不太令人愉快?我很羡慕你这个说法,你真年轻。
霍安琪:可能我还“不知晦朔”吧!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您说在这本书中,您想让中国的当代以现代汉语的形式从您的身体里捋一遍。这里的“当代”应该不只是一个历史的时间概念?能否说说您对“中国的当代”的理解?
毕飞宇:这当然是我对自己的期许。对一个靠虚构为生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当代”更召唤虚构的呢?生活在延续,那些时时刻刻都伴随着你的内容,具体的或者抽象的,它们构成了当代。参与当代是每个人的必然,然而,表达当代不是人人都有机会的,这是极大的幸运。
霍安琪:《欢迎来到人间》达成了这种期许吗?
毕飞宇:那当然,作品从我手上出去的,达到我的愿望我才可能放行。但是我也知道一个常识,作家的自我判断通常一分钱都不值,能够做出判断的只能是未来。
霍安琪:我也很好奇未来会如何判断。至少现在,我是同意您的判断的。那么,我们来谈谈城市。您是从城市的空间开始写起的,这在当代小说中倒也不少见。在南京生活过的读者会意识到您写的这个千里马广场特别像新世纪初南京的新街口。但是,我注意到您没有给这个城市命名,真实的地名和虚构的地名都没有。
毕飞宇:我完全没必要去命名。除了乡村题材的“王家庄”,我的许多小说都没有地名,《青衣》没有,《推拿》也没有。我不写区域小说,我对区域文化也没兴趣,城市有没有名字要什么紧呢。小说就这样,即使我用了“南京”或者“武汉”,它依然是虚构的,谁也不会把它看作“南京故事”或者“武汉故事”。有时候,用了具体的地名,反而会影响作品的涵盖面。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做过极好的示范,如果阿 Q 叫赵国富,我们会得到了一个赵国富,如果他是阿 Q,读者的所得就多的多。
霍安琪:不好意思,但我得较个真,追问一下。为什么在乡村题材里,您要构建一个具体的“王家庄”,在城市题材里却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呢?
毕飞宇:王家庄嘛,对吧,那就该是“王家庄”。《欢迎来到人间》重点是当代性,我觉得,哪个城市的当代性都一样。如果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到了上海或者广州就不成立,我觉得,《欢迎来到人间》就要倒在起跑线上。
霍安琪:我很赞同您这个观点。我觉得,现在的城市,如果说还有什么个性化的特质,那这个特质很可能是前现代时期就有的,遗存下来了而已。而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以后,城市就千篇一律了。《欢迎来到人间》中傅睿所在的这个城市,它既可以是现代以来诞生的大都市中的任意一个,也可以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现代化的总和。
毕飞宇:是的。
霍安琪:我感觉《欢迎来到人间》对城市化与现代性是有批判的。这种批判跟您这些年的城市生活经验有关吗?
毕飞宇:你这么一说似乎提醒我了,有那么一点的。但是,这部小说的重点不在这里,再怎么说,这部作品的主旋律不是这个。我在年轻的时候受到一些西方观念的影响,对现代性很怀疑,这个在我的小说里也有体现,《哺乳期的女人》里多多少少就有这个意思。后来我明白了,西方人批判现代性有他们的依据,他们进入现代性的时间是如此漫长,他们当然要反思。讨论现代性怎么能绕得开探讨理性呢?从启蒙的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理性是如何发展成为工具理性的?这自然要反思。但问题是,我们当初所接受的观念、理论和我们的历史现实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呢?我的看法是,批判现代性也许是必须的,但是,迎接现代性更重要,首当其冲则是建设理性。
霍安琪:在我的印象里,小说里唯一一个确切的地点好像是旧金山。
毕飞宇:对。唯一的地点是旧金山,在那里可以回望,老赵可以眺望他的家。
霍安琪:小说的题目叫《欢迎来到人间》,一个很温暖的名字,却不是一个那么温暖的故事。您是怎么理解“人间”的?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这个名字?
毕飞宇:我原先的小说名叫《琥珀》,直到把小说给了《收获》后,我都不满意。后来我就对程永新耍了个赖,我说我再也不想面对这个小说了,你给起个名字吧。我耍赖是有原因的,我再也不想看那个该死的文档了,都想吐。程永新最终从小说里选了六个字,欢迎来到人间。我很喜欢这个书名。
霍安琪:其实《琥珀》也很好,但如果叫《琥珀》,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毕飞宇:我放弃它是因为它太象征了。如果是 20 年前,我会果断地使用《琥珀》。但是,你知道,人都会变,我现在就很不喜欢那些东西。这个书名也充分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是一个作家,写完了,我已经是另一个作家了。我也欢迎这个结果。
普通人傅睿
霍安琪:接下来聊聊亲子关系吧。这些年“原生家庭”是很火的一个话题。小说中也用了很多笔墨去书写傅睿的父母以及他们和傅睿的相处方式。
毕飞宇:在我描写过的所有家庭里,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着力点,权力大于亲情。我喜欢考察这个,它也成了我挥之不去的写作惯性。这个问题我是当作母题来面对的。在不同的作品中,这个问题时隐时现。我不能说《欢迎来到人间》是一部关于家庭权力的书,但是,因为家庭的比重比较大,权力关系的书写就变得不可避免。一般来说,我不会避开权力这个话题,对我来说,这是一生的问题。
霍安琪:为什么会有这种习惯?是源于经验,还是源于观念呢?
毕飞宇:都有。
霍安琪:您在《小说生活》里好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说您是一个不抗拒“观念先行”的作家。这挺酷的。大部分作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特别是青年作家。
毕飞宇: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作家都有他顽固的价值观。价值观当然是观念,价值观是不是“先行”,我们另说,一个没有相对稳定价值观的作家通常都很可疑,那是一定走不远的,我从不回避这一点。作品好不好,取决于作家的能力,永远也不存在没有观念而可以把作品写好的事。
霍安琪:像傅睿家这样的城市里的核心家庭与王家庄里的乡土宗族相比,其权力关系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毕飞宇:我觉得所有的区别都只发生在作家这里,如果你要表达它们,你的叙述方式确实不一样。但是,跳过作家的叙述,就本质而言,它们毫无区别,我没有看到它的文化背景和心理机制有什么差异。换句话说,关于权力,我们的差别仅仅是修辞,语法则一模一样。再换句话说,在权力的结构上,没有什么不同。
霍安琪:傅睿是一个很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是一个天才,一个精英。但其实,现代作家们通常更钟情于书写社会的平凡者甚至是边缘人。您为什么会想写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的故事?
毕飞宇:不,傅睿是一个普通人。
霍安琪:也就是说,他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看来,您并非以外在的功利的标准看待所谓的“普通”和“不普通”,而是以内在的标准。
毕飞宇:傅睿一定不是遗世独立的,不是个别的,虽然很难说他有多大的普遍性。这个“拯救者”我并不陌生,尤其在过去的这几年。有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医生;有时候,他可能是一个教师;某些时候,他也可能是套着红色袖箍的保安。他自我感动,满怀着弥赛亚的冲动。他怀揣着遥远的爱,他爱远方,但他不爱自己,不爱自己的亲人和身边所有的人。他的拯救永远伴随着灾难。关于傅睿,我们还是不要先入为主了吧,不能因为他是医二代,高学历,他就不再“普通”,他哪里不“普通”了呢?
霍安琪:确实,“普通”和“不普通”不能靠这些判断。但这样一种分类的方式却是当下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人们靠外在的标准给人归类,把那些高学历、高收入、高名誉的群体驱逐出了普通人的行列,使他们神化。然而从人性内部看,这种分类并不合理。您对“拯救者”形象普遍性的表述对我很有启发。他们爱抽象的人,而非具体的人。而爱具体的人往往比爱抽象的人难得多。不过在我看来,傅睿“拯救”小蔡的行为除了出自“遥远的爱”,好像还伴随着一种更隐秘的私心。我的意思是出于嫉妒和占有欲。
毕飞宇:傅睿拯救小蔡不是我设计出来的,从他为田菲修肾的那一刻起,他就在单行线上。我能做的就是盯着他,等着“那一刻”的到来,我知道,那一刻会来的,伴随着那辆黑色的帕萨特。
霍安琪:在傅睿的家庭中还有一个人物,她在小说中很不起眼,着墨不多,但是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个人就是傅睿的妹妹傅智。小说里着重写了她跟母亲闻兰的关系并不好,但是从敏鹿的视角来看依稀能感觉到傅智比傅睿要活得更自洽、洒脱。
毕飞宇:在我最初的稿子里,这个人物是一个轴,许多关系都集中在她这里。但是,第一稿被我推翻了,她的作用就下降了。实际上,第二稿的后半部分也被我推翻了,她的作用只能进一步下降。老实说,她和敏鹿的关系我写得相当好,可是再好也没用,在最终的定稿里,她和敏鹿的关系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属于可有可无,那我就果断地把这个部分删了。你很敏感,虽然她的篇幅已经很少了,你还是注意到了她,这让我这个作者很愉快。最起码,她还是一个小说人物,不是符号。我的第一稿其实是有故事的,有讲故事的愿望,但是,写到后来,我觉得这个作品去讲故事毫无意义,我就放弃了故事。故事性下降了,小说没那么“好看”了,可它的体积和密度都上去了,它成了一部质量更好的小说。
霍安琪:原来如此。我的直觉告诉我,傅智这个人物可能通向另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可能并非小说试图抵达的,所以留给读者的只是惊鸿一瞥。您删掉了关于她的故事线,却没有直接删掉这个人物,说明她确实凝结了您的心血。虽然很好奇傅智的故事,觉得她这个人物身上还蕴含着巨大的叙事能量,但不得不说,她的退场也是值得的。
毕飞宇:在原先的小说里,老傅,也就是傅睿的父亲,他出轨了。傅智,作为傅睿的妹妹,意外地知道了一切,却什么都没说。敏鹿也出轨,傅智同样知道这一切,依然什么都不说。她不说是因为她在内心把自己从这个家排除出去了。所有的欲望汇聚在她这里,她却心如止水。当然,她什么都不说也有这样的意思,傅睿最终失去了一切,包括他这个妹妹。我想强调一下,傅睿是一个弱者,从头到尾都是。我现在最为满意的是,我最终的定稿里体现了弱者的虚妄和疯狂。
霍安琪:说到傅睿的虚妄和疯狂,似乎正契合了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症候。网络上许多人戏言,“人哪有不发疯的?”好像发疯的才是正常人,不发疯的才不正常。您觉得傅睿的疯狂更多是指向当下的时代还是更多代表了一种永恒的人本困境?
毕飞宇:这我不知道。我所关注的是乌托邦,还有乌托邦下面的工具理性。当乌托邦与工具理性见面的时候,剩下来的人都是小蔡。
霍安琪:也就是说,小蔡在乌托邦和工具理性之外。那傅睿呢?
毕飞宇:你觉得呢?工具理性不是理性,是癫狂。
霍安琪:我觉得傅睿最开始是工具理性的受害者,后来他却成了工具理性的仆人。
毕飞宇:我同意你的这个说法。
可供写作的生活不会停止
霍安琪:这些年您也在大学里给同学们上课。从事文学教育的这个过程,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毕飞宇:没有,或者说,即使有,我也没有意识到。
霍安琪:那么,与青年人的相处呢?在您的讲堂中,听众大多也是青年学子。您有没有从他们身上获得新鲜的感受或者认知?
毕飞宇:实际上,在日常的生活里,我并不存在一个“与年轻人相处”这个理念,在我眼里,人与人的不同可比人与人的代际差别大多了。就说与年轻人相处吧,我的确能感受到年轻人的锐气。可是,你也得承认,有些年轻人比我还要老旧。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改革开放狂飙突进的时刻成长起来的,自我革新的愿望极其强烈。我不能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自我革新的愿望,有,但是,它没那么普遍,势能也没那么巨大,他们总体要安静得多,有一个词是怎么说的?佛系。实际上,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会避免从代际或者类别上去认知一个人,我更习惯从个体去感知。对我来说,类的感知或者说代际感知往往是靠不住的,我更认可个体,也更认可个体给我带来的共振。
霍安琪:比之群体,更愿意体认个体,这是一位写作者的敏感性。但代际特征的差异肯定也是存在的。我认可您对您这一代人精神气质的整体判断。您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曾经阅读大量八十年代初的文学作品、报纸、杂志。阅读的时候,我常常感叹,八十年代真是黄金年代,要是我能回到那个时代上大学就好了。那个时代人人都有理想,处处充满了希望。那是秩序新建的历史时刻,你们认识到你们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走向一个新的纪元。但现在不是了。当下年轻人之所以缺乏自我革新的愿望,是由于革新的意义感减弱了。一切都被规定好了,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秩序,秩序之外的人似乎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所有人都挤在同一条道路上拼命竞争,意图杀出重围。考大学、考研、考公……但考上以后又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变得虚无,所以年轻人没有精力去自我革新了。被动地参与社会内卷,连自我都丧失了,何谈革新呢?于是这一代人变得倦怠了,也就变得安静了。我之所以和您探讨这个问题,是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里的傅睿或许比上一代要更多了。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不会诞生像傅睿这样的文学形象的。
毕飞宇:我觉得我面对不了你的问题。在所谓的知天命之后,我自信过几天,我觉得我可以面对这个世界了,我甚至可以说点什么。后来的生活给了我脆亮的耳光,生活证明,我不是离生活越来越近了,相反,是越来越远,我当然沮丧。我觉得你有一个假设,面对现实,我们这一代比你们有办法,不是这样的。我必须承认,有一度,我老气横秋了,对年轻人产生了失望,好在我很快就明白过来了,我们并没有比年轻人做得更好。但有一点我也不想回避,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之间彼此都对对方失去了信心,这是一个诡异的场景。
霍安琪:您刚刚说生活离您越来越远了。这是您选择改变自己的写作方法,不再在这部小说中“讲故事”的原因吗?
毕飞宇:不是,生活永远不会停歇,可供写作的生活更不会停止。是我自作聪明的、一厢情愿的生活离我远去了。
霍安琪:可供写作的生活不会停止,这我很认同。不过,我最近也听到不止一位作家或者学者认为现实生活已经基本被穷尽了。人生活在一个碎片化、原子化的时代,个人经验贬值了,所以写个人经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您怎么看?
毕飞宇: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小说的现场吧,有一句话我们是很难说出口的,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这么多的小说?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这么多的作家?我们每年都会看到大量的新小说诞生,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复的经验,可是,这不等于说我们的经验穷尽了。这不是同一个问题。现实生活怎么可能被穷尽?个人经验怎么可能贬值?如果说,个人经验贬值了,那只能说,个人的整体价值贬值了,这不是文学的问题,更不是小说的问题。小说的价值之一就是提升个人经验的价值,从而提升个人的价值。道理很简单,构成小说的基本元素从来都是个人,我至今没有读过一篇离开了个人的小说,《战争与和平》面对了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庞大的家族,别忘了,这一切都是通过安德烈、娜塔莎他们来体现的。如果我们不能从个人经验那里看到生动性和意义,那只能说,我们麻木了,我们体内的势能处在了不应期。
霍安琪:的确,哪怕是同质的个人经验也有不同的表达效果和处理方式。这才是考验一个小说家的地方。我也认为遭遇危机的不是小说本身,而是小说处理经验的方式遇到了考验。说到经验的问题,《欢迎来到人间》中写老赵在网上发帖,但是无人回应。您说他是“亲手在鬼城建造了一条鬼街”。现在也有许多小说涉及网络经验,但是将网络世界比作一个“鬼城”,还是使我在读到的那一刻冷汗涔涔。这是一个十分有穿透力的比喻,它穿透网络的表象直达了其本质。
毕飞宇:说起“鬼城”的这个部分,它可不是想象,它是个人经验,我也可以说,它是公共经验。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我时常站立在窗前,望着窗外的小区,这是我多么熟悉的小区,然而,它失去了人间的迹象,所有的人的行为停止了,无限的熟悉就这样变成了无限的陌生。很多次,我几乎都要怀疑,这是不是“史前”呢?那是不寒而栗的。我很高兴你留意了这个部分。
作者单位:毕飞宇 南京大学
霍安琪 清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