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雷:寻访京畿现代人文故迹
我今天要讲得题目是“寻访京畿现代人文故迹”,这是一个比较学术化的表述,其实对于我来讲,最开始就是“逛胡同”,在逛的过程当中,慢慢有一些发现和一些想法。比方说我们看这三张图片,这实际上是一个地方,就是陈独秀故居、《新青年》编辑部,左边的这张是一个资料图片,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间的这张是我十年前去看的时候拍的,右边的这张是2021年翻修后的样子。所以我觉得“逛胡同”不光是看个热闹、新鲜,而是在空间和时间当中去寻找、发现一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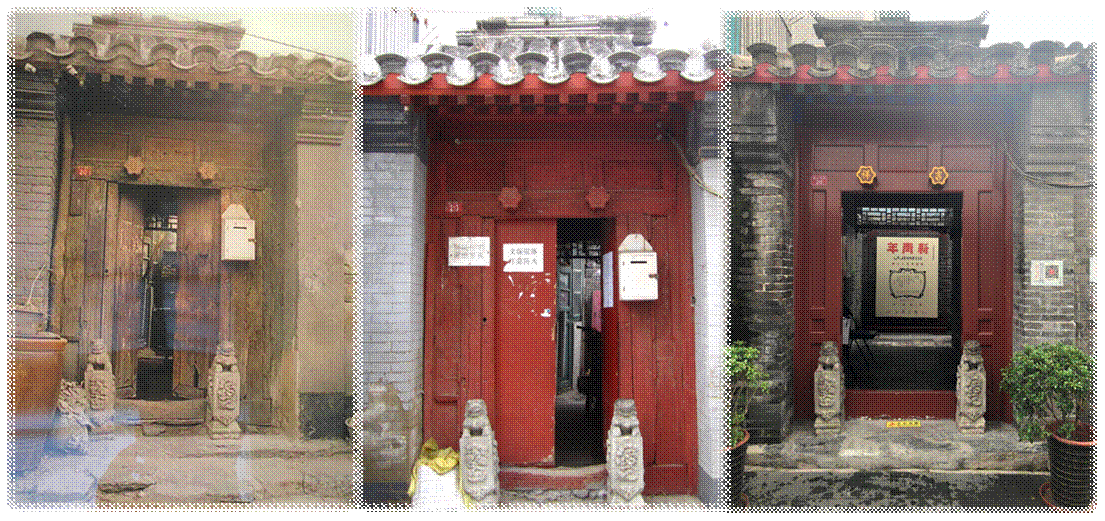
在讲座的开始,先来跟大家互动一下,有没有哪位能够认得出来这是哪里?确实,这里看起来非常普通,前面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张一元茶叶店,后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塔楼。如果大家觉得这样是故弄玄虚的话,那我再提供一些信息,这个位置一边是香厂路,一边是万明路,在香厂路、万明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就是这张照片的位置。有没有谁能够看得出来或者猜得出来这张照片是哪里?这里曾经是“新世界”游乐场,就是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发传单然后被抓走的地方,当年陈独秀是在这个位置、或者说这个时空坐标上被抓走了。后来这座楼因为各种原因被拆掉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只是照片里所呈现的样子。所以我自己有一个说法,我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些“二手的第一现场”。

为什么我会关注到这个话题呢?实际上也跟我自己的教学、研究有关系。我是做文学研究的,尤其侧重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我刚刚从教不久的时候,因为要在《现代文学史》课上讲沈从文,备课时我看了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其中就讲到了上世纪20年代沈从文来北京以后住在酉西会馆的情况。书中写到:“酉西会馆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沈从文便不再作正式升学打算,他只好独自在酉西会馆里,开始来北京后第一阶段的自学。每天早上吃三两个馒头、一点泡咸菜,就出酉西会馆,进宣武门,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直到闭馆时才返回住处。……从酉西会馆向西走15分钟,就到了闻名于世的琉璃厂——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窗口。……向东走20分钟,就是北京著名的繁华闹市之一的前门大街。那里依旧保留着明清两朝的规模……”。琉璃厂和前门大街我都去过,但是却没有注意过在这些地方附近还有一个沈从文故居,于是我决定找一找看。这是我2011年拍到的杨梅竹斜街的照片。2013年左右,政府对这条街实施了腾退改造,现在非常整洁,基本上跟南锣鼓巷很相似,街上有很多咖啡馆之类的。但2011年我去的时候,这里还是一条非常破旧的街道,酉西会馆所在的宅门也并没有被贴上沈从文故居或是旧居的标牌。我跟学生讲,如果真的可以时空穿梭的话,那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杨梅竹斜街里,跟你擦肩而过、穿长衫、说湖南话的,很有可能就是沈从文。这是我的第一次寻访。
后来要讲左翼文学,要讲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我就从我们学校图书馆借了这本书。很巧的是我借的这一版有一个萧军写的“重版前记”,文末注明写作地点是“北京银锭桥西海北楼——‘蜗蜗’居寓所”。银锭桥就是后海那边嘛,我也去过啊,但我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个地方还有一处萧军故居。当时智能手机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我就上网查好地点,手绘了个简单的地图,还专门去找了一些资料,其中包括这幅画,画的就是萧军住的“蜗蜗”居。但到了实地后,找“蜗蜗”居特别费劲。资料显示“蜗蜗”居是在鸦儿胡同,但是我前边绕、后边绕,怎么也没有找到画中的那栋楼,还想是不是已经拆掉了。正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一抬头,发现前面有一个二层小楼,我看到的是楼的背面,而周围都是平房,没有二层的建筑,我就绕到前边,有个大杂院,旁边挨着个公共厕所,我从那个院门进去,往东一拐就看到一栋二层楼,再看它的阳台、看它的窗户,应该都是那种西洋风格的吧,和画里画的一样,可以断定这里就是萧军当年住过的“蜗蜗”居。当时那儿还没有人拦着,是可以进到这个二楼里的,我也特别想进去看一看,但是我实在没敢进去,因为这栋楼已经特别破、特别烂了,东边的墙整面都没有了,感觉随时都有可能倒塌,我就怕楼塔了,把我埋在里面,我喊人都没有人应。所以当时我也很诧异,因为印象里作家故居似乎都是被当作“文物保护单位”的,萧军是一位知名的作家,那为什么萧军的故居破成这样?2023年夏天我又带着学生去,“蜗蜗”居就已经被蓝色彩钢板给挡起来了,已经无法靠近了。这就是我最开始的两次寻访作家故居的经历。

有了这两次经历,我对这个事情产生了兴趣。北京还有很多知名作家,那么他们的故居在哪儿,他们曾经在哪个胡同里生活过,当年那个院子、那个胡同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去找、去看。所以最开始,我也纯粹是因为这种兴趣才去寻访的。2011年以来,一趟一趟地我去看过很多,到现在数下来至少看了有六七十处故居、故迹吧。不过我觉得,与其说我看过了这么六七十处,倒不如反过来说,说北京至少有这么六七十处作家、知识分子的故居等故迹。
这些年来,我也不断地带我的学生去看。这张照片是2011年拍的,当时学生们兵分两路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其中一路由我亲自带队。很多故居、四合院由于沦为大杂院,保护不善、年久失修,木制的宅门大多已经糟烂了,不过这样倒也方便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自由进出。到了艾青故居门口的时候我们有点傻眼了,因为发现人家那个院子装的是个防盗门。其他那些大杂院,你厚着脸皮也就进去了,但防盗门进不去啊。我就派一个学生去敲门,一开门出来一位女士,可能她看我们都是学生,就把我们让进去了,特别幸运的是,我们还见到了艾青的夫人高瑛阿姨,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另外一路同学是去了阜成门附近的鲁迅故居,其中一位今天也在座,是我当年的学生,现在也在政法大学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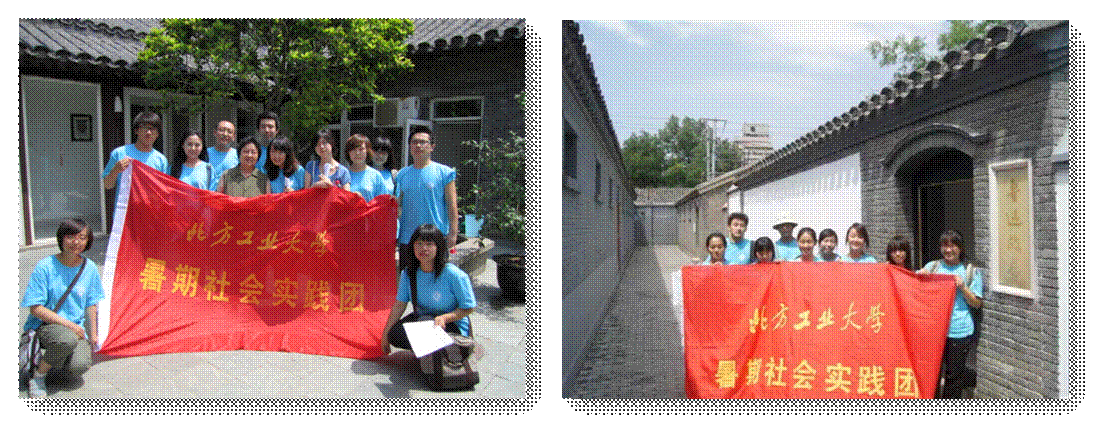
这张照片是在八道湾胡同,我们知道周氏兄弟在八道湾胡同的11号院住过,一直到1923年兄弟失和,自那之后鲁迅搬走了,先是去了砖塔胡同,最后又去阜成门附近的西三条胡同,但是周作人还一直住在那。2011年9月我第一次去八道湾胡同,在前公用胡同和后公用胡同一带反反复复绕了好几遍,怎么也找不着11号院。当时附近正在拆迁,我想可能11号院也已经拆了吧,就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恰好一扭头,看到一个宅门的门框边上有一个灰色的报箱,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了着“八道湾十一号”。之前我找的时候一直盯着门框右上角,就是通常钉门牌号码的位置,这个院子的门牌可能已经丢了,所以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院子。当时周围已经都是一片残垣断壁了,虽然我无法确定这个11号是否就是周氏兄弟住过的老11号,但仍然非常高兴。不久,整个八道湾胡同包括周边全都被拆掉了,现在全都纳入到了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里,校园里修了一个崭新的“周氏兄弟旧居”。2016年夏天,赶上三十五中的校园开放日,我带着当时我班上的学生特意去参观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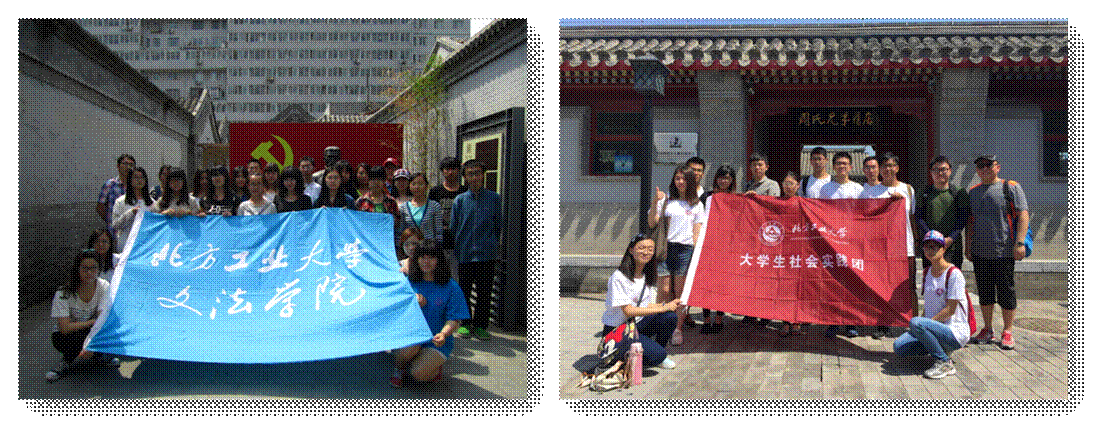
除了带着我的学生去寻访以外,我曾有幸带着北京育才学校的中学生们去参观过北大红楼、梅兰芳故居、赵家楼遗址等。疫情之前我喜欢骑行,我曾带着骑友骑着自行车在胡同里转。骑友们基本都是北京人,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胡同里曾经住过谁,那个胡同里曾经住过谁,他们转起来也很新奇。我和骑友们的这张合影是在史家胡同博物馆拍的,而这里实际上是凌叔华的故居。

2021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时候,我带着我班上的学生又去“逛胡同”,在设计路线时特意经过了几处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故居、遗存。这张合影是在鲁迅中学门口,鲁迅中学的校址当年就是女子师大,就是许广平、刘和珍当初就读的学校。这张照片,是今年我带着学生去寻访,途中经过位于细管胡同的田汉故居,在田汉故居的门口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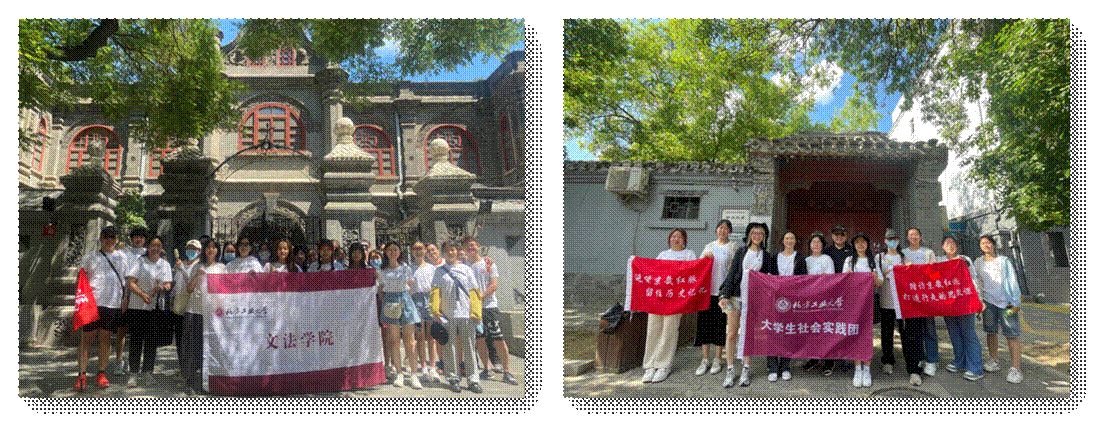
从2011年到现在,除了疫情和我在国外学习期间,其他时间差不多年年都会组织学生去逛胡同,要么就是我亲自带队去,要么就是组织学生自己去,比方说在我的大学语文课堂,我就把这个布置成作业,给学生提供二十来条路线,让他们去选择,要求他们去转一转、拍一拍,回来做个PPT或者Vlog。所以我们这个活动的特色可能就是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并且非常贴合北京。今年上半年北京市规自委有一个征集评比,我以《踏访京畿红迹,打造“行走的思政课”》为题也报了名,最终入选了“‘我们的城市’北京青少年城市规划社会宣传项目共创伙伴”。
正如我前面说的,我逛胡同一开始纯粹是出于兴趣,因为和我教的课相关。后来,因为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看了这么多的故居,慢慢地也在想怎么把这个东西拿来说事,怎么写文章、怎么申项目,我也在不断思考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些故居、胡同对于宣传北京城市文化或者城市形象还蛮有意义的。
比方说我们看这张图片,它所表现的是北京的“天际线”,其中的代表性建筑其实是可以分为两类的,一类就是像天安门、天坛这种象征传统社会皇权的建筑,还有一类就是新建筑,包括国家大剧院、中国尊、新央视大楼、鸟巢等,这些就代表了今天的北京。这些某种程度上彰显的都是首都的特殊属性,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北京突出强调的还是它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北京也是一个文化中心,那么文化中心的这一面如何体现出来呢?在这方面,如果选取故宫、央视、中国尊这些地标建筑可能都不太合适。
北京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曾经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聚集,他们在这里彼此争鸣、彼此砥砺,留下了大量的著述,我觉得这也是北京文脉的延续及其具体化的表现。他们在北京生活、工作、学习,有的甚至最后埋葬在北京,他们留下的那些故居、墓葬等历史遗存似乎也不应该被忽略乃至遗忘。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可以从民间、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讨论北京文化中心的属性特征,而且似乎还有一定的空间和新意。
那些知识分子住过的四合院,有些保留了下来,还有一些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你根本无从确定他到底当年是在哪个院子里,但是至少那个胡同还在、这个街区还在,甚至于即使这个街道不在了,周边还是有一些地名能够帮助我们大致判断曾经的位置。还有大量的会馆,像康梁、鲁迅、沈从文,他们都曾住在家乡在北京的会馆里。住下来之后,他们去公园、书局、酒店、茶肆,去喝茶、去饮酒、去聚会。再比如说楹联、题字,这些都是这些知识分子书斋生活的延伸。最后还有他们的墓葬,有很多人在北京去世,除了八宝山以外,香山、万安公墓以及北京城区里都有他们的墓葬。这个可能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传奇经历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挺想去看看他们的墓葬的,但一直没有找到愿意跟我一块扫墓的人。这些作家的创作中有大量的文学作品是围绕北京的,比如像《四世同堂》啊、《故都的秋》啊、《城南旧事》啊、《我与地坛》啊等等。
咱们先说说故居。在我寻访的过程中,总体上来说,我感觉作家故居的保护情况并不是很好。郭沫若保护得非常好,鲁迅西三条胡同的故居保护得也不错,茅盾的也还行。但比如这一处,这一处是细管胡同里田汉的故居,田汉故居保护得就很一般。田汉故居是有“文物保护单位”标牌的,还有一些没有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像这一处,这是在后海边上,这个小院是解放区诗人田间的故居,据说现在他的后人还在这生活,就没有挂牌。大家看,也许因为田间是位诗人,他们家的门楣上写了这么两个字——诗风。这一处呢,是我今年偶然发现的李叔同的故居,据说是他小时候在这里住过,现在因为有人住,也不对外开放。如果大家平时对这些不大关注的,大概不大容易知道这种没有被纳入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子是什么来历、有什么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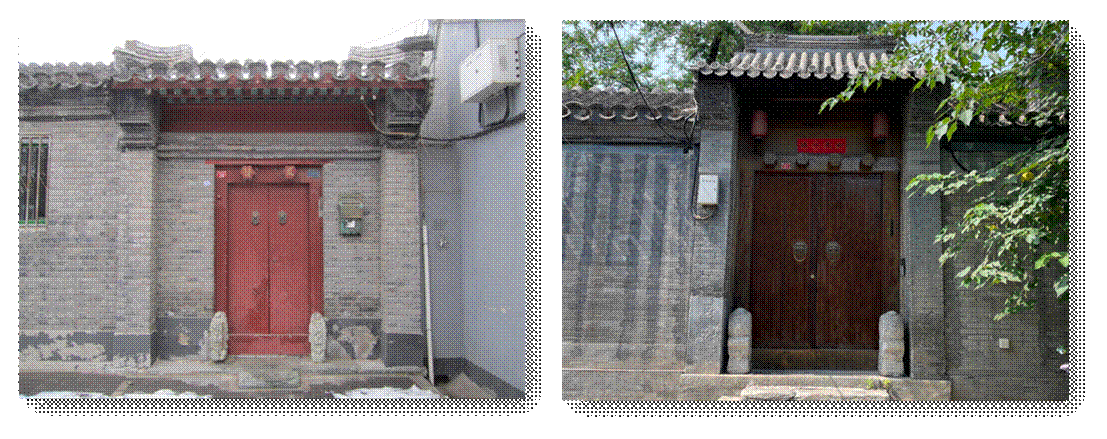
此外,有些院落虽然有明确的标识,但实际上是弄错了。比如说这个缎库胡同,这是官方挂的牌子,上面明确写到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在缎库胡同8号问世,高一涵也曾住在这个胡同。但你去了就会发现这个8号院很小、很不像样的,我总觉得胡适当年不至于租这么小的一个院子,所以这么多年我路过这个地方好多次,一直都有这样的疑问。今年,我看到《中华读书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有人也去找这个地方,他问了住在那里的老人才了解到这个8号其实是民国时期的老8号,而不是我们现在这个8号,老8号那个院子跟有些资料里描述的比较相像,所以现在这个肯定是弄错了。
还有大翔凤胡同,官方介绍里说有著名作家丁玲的故居。这个其实严格来讲也不太对,大翔凤胡同3号院本来是我们山西作家马烽的院子,马烽要回山西想脱手房产,所以他就把这个院子的平价卖给了丁玲,3号院的确是丁玲名下的房产,但是丁玲和她的丈夫陈明一天也没有在这院里住过,因为当时丁玲他们也受到了冲击,他们就是把它当仓库一样堆了一堆东西,紧接着不久,丁玲就到北大荒去了,等到70年代再回来就发现这个院子已经被别人占了。所以这个地方呢,严格来讲它不算丁玲的故居。实际上现在北京城里没有留下丁玲的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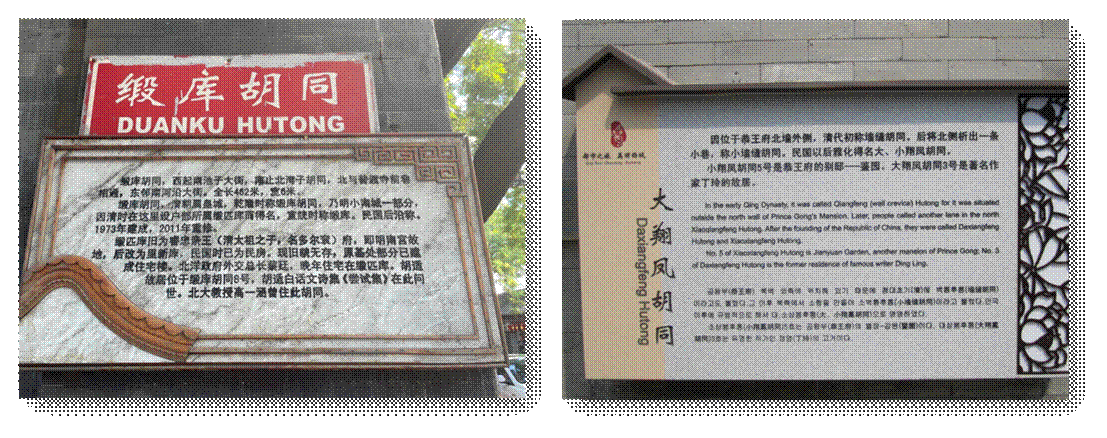
其次,北京有许多明清时期的会馆,比如过去在宣南一带就有很多。这张是位于菜市口附近的康有为故居,也就是南海会馆,当时我就是站在马路上拍的,能够看得出来门口是一个大下坡,院子的宅门是低于马路的路面的,所以我经常想,这个院子如果说赶上了那年的“七二一”大暴雨,那会被淹成什么样。我当初去这里是2012年盛夏,米市胡同那一带都在拆,是我的学生带着我去的。后来再去就发现周围已经盖起来楼了,还有好大一片被蓝色的彩钢板围着,也不知道康有为故居这一处到底还在不在,情况如何,那可是一处地地道道的文物保护单位啊。
这张照片里这一处是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也是一处文物保护单位,鲁迅曾经在这里住过,这个照片是我2012年去寻访时拍的,里面是一个大杂院,当年的什么藤花馆、补树书屋都看不出来了。2021年我带着学生又去打卡这个地方,发现宅门已经被彩钢板封上了,显然里面已经腾退了,到底打算怎么弄、能弄成什么样,这些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也很纳闷或者说很好奇,今天在政法大学也想问问专业的老师,我们在文物保护方面有什么样的立法,或者说有怎样的奖惩措施呢?

这张照片里的是青云阁,它在沈从文住过的杨梅竹斜街,当初是非常有名的商场。右边这张照片里的是松坡书局,在西单汉光百货背后。过去这里是民族大世界,是个小商品商场,就是卖箱包、皮带之类的。今年夏天我刚又专门去看了看,现在这儿被作为蒙藏学校旧址重新对外开放。但这个位置上实际上值得留存的不止蒙藏学校旧址,还有松坡书局,梁启超、徐志摩都和这里有关,所以能给松坡书局留个地方,这个保护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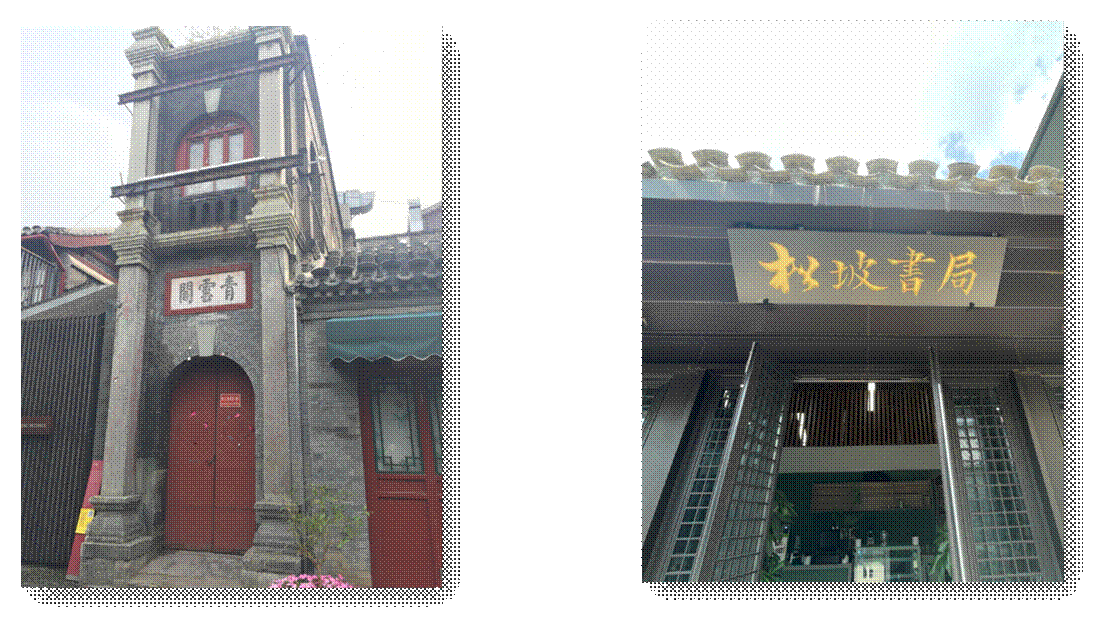
关于楹联、匾额、题字,有时候我会跟外地的朋友、跟学生讲,整个北京就好像艺术走廊一样,在北京你不用专门到什么艺术馆里去看,你就到北京的大街上去转一转、看一看。在北京,我觉得不是人们以名家题字为荣,而应该是书法家以自己的字能挂到北京为荣,因为北京的名家题字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在前门大街和琉璃厂这两个地方,非常集中。这是郭沫若的题字,这是赵朴初的题字,这个“天桥百货商场”也是郭沫若写的,西单的“北京年糕杨”是启功写的,这个“护国寺小吃”是老舍之子舒乙写的,“白塔寺药店”是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写的。有时候我就跟学生开玩笑,我说你去吃护国寺小吃,假如说你吃坏了肚子,你就去白塔寺药店买个药——在老舍儿子题字的地方吃坏了肚子,在老舍夫人题字的药店买点药。
这张照片是我在西山八大处拍的,因为八大处离我们北方工大很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跑那儿去爬爬山。八大处那里有条中华精印谷,我觉得很有人文色彩。在精印谷我发现有一处是林长民写的字,字是竖排从右往左写的,内容是“戊午七月/林长民到/此用王简/棲语刊/石以纪/胜游并/礼释迦”。我们知道,林长民是林徽因的父亲,那就是说林徽因的父亲当年也曾经到我们北方工大附近来爬山游览,那林徽因有没有跟着一起来啊?所以石景山也不是一个文学、文化的不毛之地。

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许多描写北京的作品。我们去了地坛,大家一定会想到史铁生,去陶然亭大概会想到高君宇、石评梅,那去玉渊潭也应该想到汪曾祺。汪曾祺曾经在玉渊潭附近居住,他经常到玉渊潭去,写过很多关于玉渊潭的文章。所以去玉渊潭,除了去看樱花,也应该读一读汪曾祺。我不知道玉渊潭公园的管理层是否了解这一点,我特别想说服他们,让他们在玉渊潭给汪曾祺立个像,突出玉渊潭和汪曾祺的关系,把玉渊潭的这种人文色彩彰显出来。
下面这段文字是选自《四世同堂》,讲的是钱默吟家被日本人迫害,钱太太去世了,作品中有这么一段:“钱家的坟地是在东直门外。杠到了鼓楼,金三爷替钱太太打了主意,请朋友们不必再远送……瑞宣的路,最好是坐电车到太平仓;其次是走烟袋斜街,什刹海,定王府大街,便到了护国寺。可是,他的心仿佛完全忘了选择路线这件事。他低着头,一直往西走,好像要往德胜门去。”老舍作品中的很多地名都是真实的,我根据它的这个路线也走了一趟,发现这个路线的确是可以走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老舍他为什么要安排祁瑞宣走到德胜门去,为什么把终点选在这儿呢?《四世同堂》一开篇就介绍祁家在小羊圈胡同,说它跟北京别的胡同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直的,而是弯弯曲曲,到了中间忽然又宽敞起来,像是这个羊肚一样,围着那么七八家人家,小羊圈胡同的原型就是现实中的小杨家胡同,就在德胜门附近,在平安里那里。小杨家胡同就是老舍的出生地。可见老舍在写《四世同堂》时,在他构想当中,故事的发生地也是在小杨家胡同这一块儿。我带着好几拨学生去过小杨家胡同,胡同很窄,大家看我的这张照片里,我伸开胳膊能够摸到胡同的两壁,那大致就能判断出这个胡同有多宽。
还有一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骆驼祥子》里“西山抓丁”那一段,祥子被抓以后他要跑,但是他要先反应一下“我”是在哪儿,“我”好往哪儿跑。这一段就写到:“最初,他似乎记得兵们是往妙峰山一带退却。……在他的知识里,他晓得京西一带,象八里庄,黄村,北辛安,磨石口,五里屯,三家店,都有养骆驼的。……难道绕来绕去,绕到磨石口来了吗?……磨石口是个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路。……这里是磨石口——老天爷——这必须是磨石口!——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礼王坟,就是八大处;从四平台往东奔杏子口,就到了南辛庄。……从北辛庄,往北,过魏家村;往北,过南河滩;再往北,到红山头,杰王府;静宜园了!”你看老舍这一段描写里头他提到的这么几个地名儿,磨石口、金顶街、八大处、杏子口现在叫杏石口,基本上这条线正好路过我们北方工业大学的后门。所以每次讲到老舍,我都会跟学生强调,我说如果说当年的确有骆驼祥子这个人,发生过这个事儿,那么他逃跑肯定是从我们北方工业大学后门跑的!
再比如郁达夫,1919年他回国考公务员,考文官、考外交官,但是都没有考上,于是郁达夫就写了这么一首诗:“江上芙蓉惨遇霜,有人兰佩祝东皇。狱中钝剑光千丈,垓下雄歌泣数行。燕雀岂知鸿鹄志,凤凰终惜羽毛伤。明朝挂席扶桑去,回首中原事渺茫。”他是写在哪儿呢?他是写在了阜成门附近的一个王府的院墙上。是哪个王府呢?通常人们可能不大计较这一点,但我看了却觉得很有意思。我写过我们北方工大校史,所以我知道我们学校最开始办学是在顺承王府,顺承王府就在阜成门附近。郁达夫当初是住在他哥哥家,他哥哥家在阜成门附近的巡捕厅胡同,所以郁达夫题诗的那个王府应该就是顺承王府,几十年之后这座王府成了我们北方工大的前身——国立北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校址。所以我就说,郁达夫提前几十年在我们学校的院墙上写过诗,算是给我们北方工大“开光”了。
前面讲的这些都是我在北京寻访故居等经历的一些事情。后来我去了日本,当时我去日本也是有目的的,因为我想当时有大量的作家、知识分子曾到日本去留学,那在异国他乡他们有没有留下故居什么的啊?结果刚去了东京大学不久,我在东大的赤门附近漫无目的地转,正巧就看到了一处夏目漱石和鲁迅的故居。夏目漱石半年前搬走,过了半年鲁迅就搬到了这个房子里头来。日本人也挂了个类似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牌,但这个房子现在也没有太多可看的,也不对外开放。在日本我专门去了趟仙台,去仙台就是为了去看那个仙台医专,我发现鲁迅在仙台近乎于一个人文地标,那里有纪念鲁迅的一碑、两像,鲁迅当年上课的教室也保留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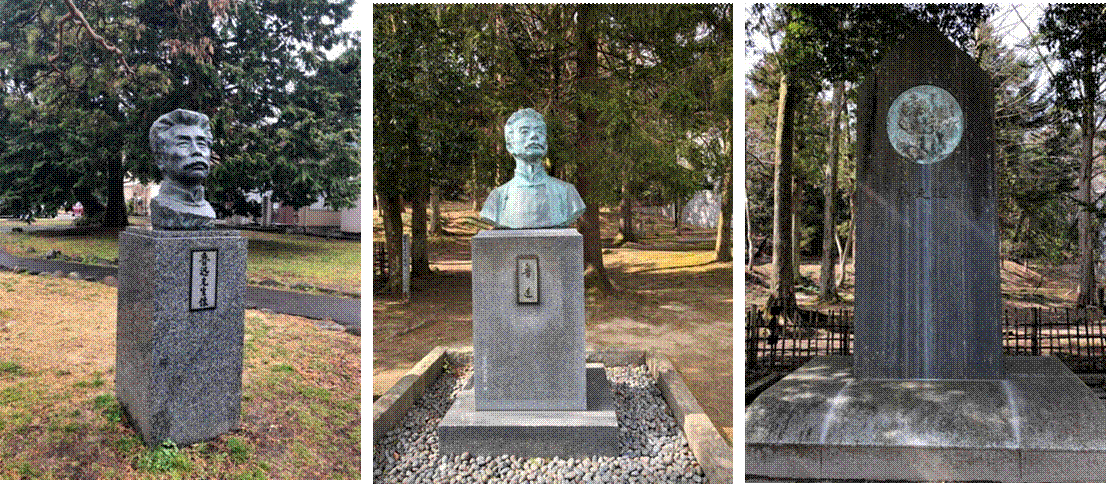
我还曾去过名古屋,发现名古屋大学也为郁达夫立了纪念碑,因为郁达夫曾经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求学。日本的千叶县有郭沫若故居,而且还保护得很好。在东京,李驰老师住的后乐园离水道桥不远,水道桥附近的爱全公园,那里曾经有个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周恩来、聂耳、萧红都在这念过书,但后来因为轰炸,学校炸没了,当地立了这么个石碑,也算是个小小的地标吧。这个是滕泽市设立的聂耳纪念碑。我们今天可能很难想象,每年的7月17日,日本人以及当地的华人会在这里集会纪念聂耳,由藤泽市消防队——清一色的日本人在这里演奏《义勇军进行曲》!我去看过两次,亲眼所见。实际上,还有很多人或长或短地到过日本,比如邓中夏、比如张爱玲,只不过留下来的资料信息太少了,人们对他们在日本的经历所知甚少。那其他城市有没有,其他国家有没有,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有待了解、值得挖掘,对于讲述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显然,日本有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故居、遗迹,在日本期间,围绕鲁迅和聂耳,我也写了两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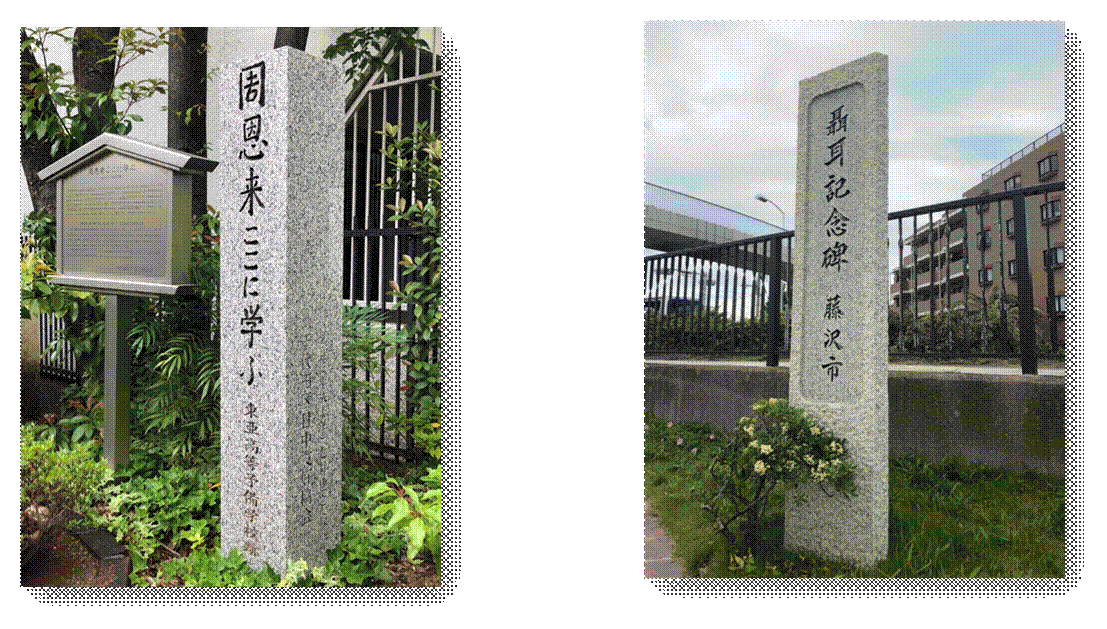
北京有这么多故居,保护得怎么样呢?2012年的时候,媒体上有一个热点新闻,说的是北京的梁林故居被“维修性拆除”。梁思成、林徽因当年为保护北京城做了很多努力,但过了六十年,不但他们的故居被拆了,而且还搞了个“维修性拆除”这么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说法。这个照片里的就是梁林故居。我之所以会去这里,是因为我最初是要去赵家楼,“火烧赵家楼”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那是绕不过去的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现在这里被改成了赵家楼饭店。我总觉得,改成什么也不该改成个饭店,你让我领着学生去那儿搓一顿,这样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看完了赵家楼饭店,我回家上网一搜,才知道梁林故居就在赵家楼饭店的马路对面,于是我就又去了一趟,拍了这个照片。故居周围当时都被彩钢板围着,留了一个出入口,有保安守着。我看了看就要进去,保安拦着不让进。我问保安这儿是什么地方,保安说:“不知道”。我继续问:“这儿是不是梁林故居?”保安说:“是”。
田汉故居,2011年我曾经领着学生进去过,发现里面可谓是杂草丛生啊,这样的文物保护,真是让人难以想象,不知道现在里面是什么样子。
这一处是庄士敦故居,在油漆作胡同。大家看这里的墙上还写着“文物重地,谢绝参观”,要求“来人登记”,但实际上你就算进去了,还有什么可让你参观的呢?里面已经被夷为平地了。这让我想起也是在2012年,济南一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英国领事馆被拆,此前文物保护部门已经明确叫停,但最终还是被拆了,据说拆的时候是先从里面拆,外面看不出来,里头实际上已经掏空了,最后把外墙推倒,就什么也不剩了。

我觉得北京非常难得,不管是放在中国的历史来讲,还是放在世界的历史来讲,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名城。因为整个北京城,在建城之初就作为一个完整的工艺品或者艺术品一样,经过了一番精心的设计规划的。所以北京城的保护,我觉得也不应该只看局部,而应该从宏观着眼。比如银河SOHO大楼,它确实很有创意,施工的工艺我相信也很高、很有挑战性,但是它和整个周围的环境就不那么协调,破坏了景观的整一性,所以当时招致了批评。
这张照片是我自己拍的,前面这个应该是庑殿顶的建筑吧,这是协和医学院,后面的大玻璃外墙的是东方新天地,咱们通常看到的东方新天地都是从长安街上一侧,是它朝南的一面,这是它朝北的一侧。协和医院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但是它的背景却是一个美国式的摩天大楼。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成功的混搭,反而觉得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开发。单独拿出来这个建筑来说,它们都没得说,但是因为它是个房子,它周围是要有邻居的,那和这个邻居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房子就不该在这里,除非把周围的邻居都搬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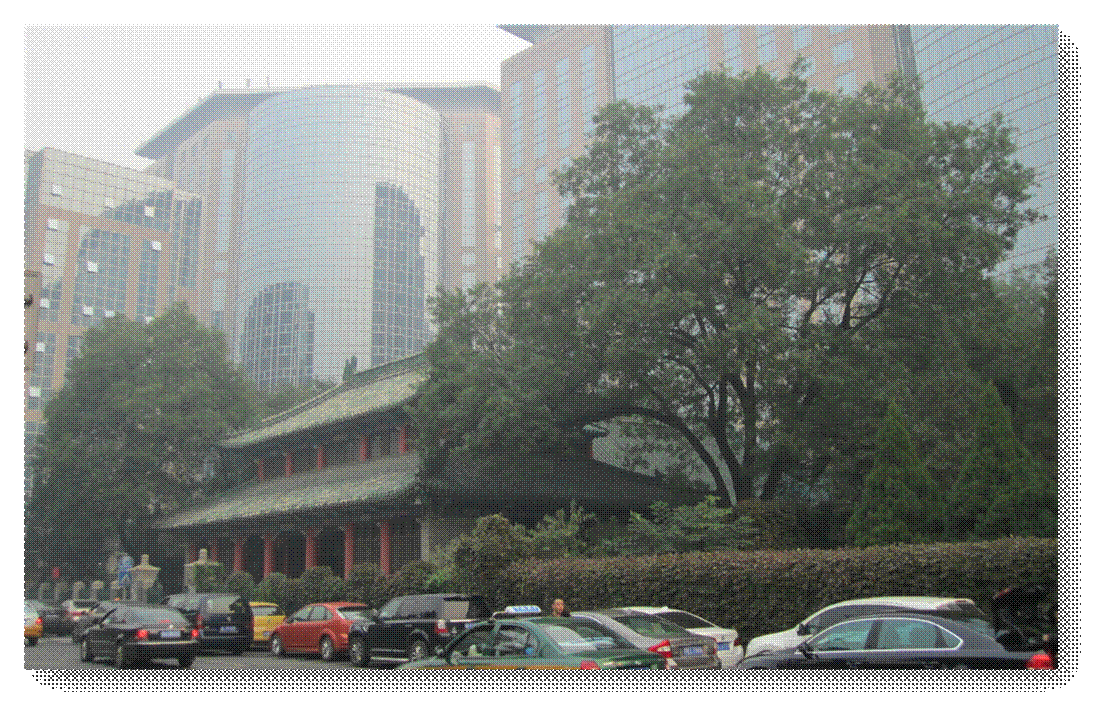
对于北京这些故居的保护工作来说,2021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以建党百年为契机,有31处相关的红色遗迹都得到了很好的修缮和维护,其中就包括李大钊故居、陈独秀故居、京报馆等等。
李大钊故居的这两个照片,一个是我2013年拍的,一个是2021年拍的。这个是陈独秀故居,左边这个是我2012年拍的,当初破破烂烂的,还有人住在里面,我刚进去就被一位老太太给轰出来了。现在也都被修缮一新。
也正是在建党百年的背景之下,2021年《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问我能不能写写李大钊或是陈独秀,让我选一个。我说那我写李大钊吧,因为看过材料,也看过电视剧《觉醒年代》,尤其是去过他在文华胡同的故居。就这样,以李大钊在北京的几处故迹为线索,我写了一篇《寻访李大钊在北京的足迹》。后来,我想既然写了李大钊,那索性就再写篇寻访陈独秀的吧。写完陈独秀,一度想围绕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做点文章,瞿秋白也在北京生活过,那再写写瞿秋白吧。写完瞿秋白,顺着这个思路,早期共产党员我还能写谁?因为我现在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带研究生,既应该也需要往这个方向靠一靠,于是就想着说李大钊、陈独秀都是当时北大的老师们,那当时还有很多学生,于是又开始寻访邓中夏。这样,到目前为止,一共完成了四篇寻访“京畿红迹”的文章,全都发在《光明日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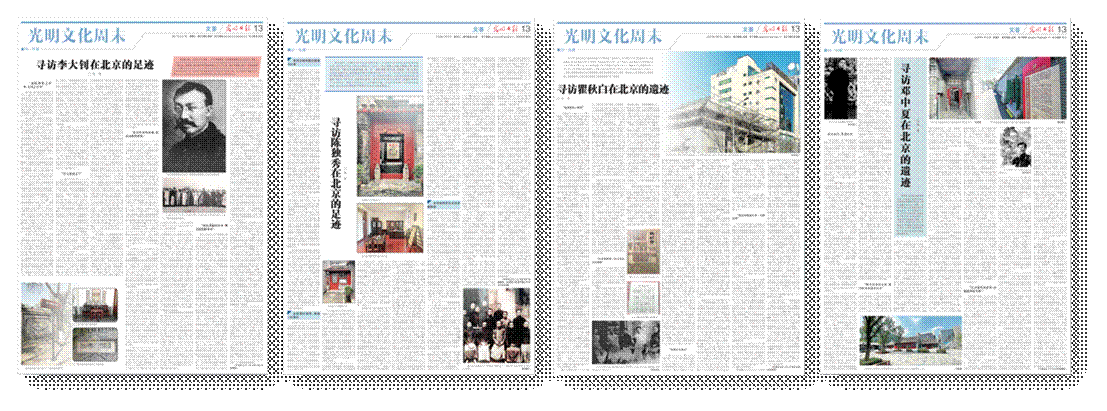
前面我也说了,差不多年年我都会带着学生去逛胡同、看故居,2021年夏天我又带着学生上街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当时正值“党史学习教育”,所以我在题目设计、路线规划上也花了一点心思,算是有意无意地踩到了热点。2021年6月20日,我带着28位学生去寻访,学生通过手机APP做了记录,我们顶着三十六七度的高温,一共走了十一个半钟头,全程31公里。2022年防疫形势特别严峻,所以我们没有寻访。2023年组织了,一共十个人,都是女生,吸取上次的“教训”,我想今年这个行程不要那么“残暴”了,就缩短了一半,实实在在走了差不多16公里,花了七个小时,路线和2021年时完全不一样。虽然当天的天气也很热,路程也很长,但是大家其实对这个活动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后面她们又来找我,问能不能再带着她们去走走以前的路线。2021年正好当时的媒体也需要这方面的一些新闻素材,我2012级的一个学生在《北京日报》工作,她当年也跟着我走过胡同,看到我发了带学生寻访的朋友圈,于是就来采访我,最后在《北京日报》新媒体和《北京晚报》纸媒上都发了新闻报导,说我们这是“别开生面的大学党课”。确实,我们的路线上有不少红色遗迹,差不多每到一处,我作为领队、向导、老师,都会和学生们或多或少地介绍一下,也的确算是实地开展红色宣讲,而且还不那么枯燥,在寻访、行走的过程中,了解北京的红色历史,了解北京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之前我给学生讲胡同、四合院是比较侧重于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的。我经常看到人们给外国留学生讲中国文化,讲中国结、太极拳,我说这些东西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越来越远了,有多少人过年的时候会自己编个中国结挂家里呢?但是建筑常识仍然是鲜活的。像今天农村盖房子、尤其是翻修房子,哪边盖厕所、哪边盖厨房,那不是没有讲究、没有规矩的。北京的四合院也正体现了这些传统的人居文化,这些传统文化依然鲜活地保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2016年的时候,我也曾带着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去逛过胡同,和他们讲四合院、讲中国作家。这几年高校非常强调“课程思政”,所以在讲胡同、四合院的时候,我也添加了一些党史方面的内容。2021年,我们的寻访被北京市教工委评为“北京教育系统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创新案例”,当时报的题目是“踏访京畿红迹,打造专业“行走的思政课”。

这就说到了李驰老师一开始给我的命题作文,让我讲讲“寻访京畿红迹”的经过与感受。“经过”就是像前面讲过的、这十来年这么一次次逛胡同逛出来的。在写文章这个层面,我还是希望能尽量和我的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靠得近一些,尽量有一点学术色彩,而不是搞成那种单纯的游记,所以有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路数和特点吧。一般来说,一个作家或是知识分子的一生都比较漫长,但是因为要结合他在北京的故居、故迹来说事儿,我重点关注的就是他在北京的这一段。比如像陈独秀,我讨论的就是他在北京生活的那三年中,以故居、故迹为重要的切分点,他在哪住过,哪几条胡同和他有关,这段时间他在想什么、做什么,大致就是结合北京的城市地理做这样一种思想脉络的考察吧,其实也很浅薄。
关于“感受”,在我寻访这些历史人物尤其是早期共产党员的过程中,他们的功业确实是让人高山仰止。比如像我刚写完的邓中夏,原来我对邓中夏并不了解,因为我在课上讲现代文学史也讲不到他,但是因为想写他,这次看他的材料就发现这个人确实很能干,建党、建团、建中华全国总工会、北京学联、民权运动、平民宣讲团全部都和他有关系,他当时年纪还不如我现在大,但是他的都是彪炳千秋的事儿,这样的人格力量确实给我们很多感染。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呢,北京许许多多不那么被人们注意的寻常街头,或许都有历史故事可讲。比方说像这张图片,李大钊当年就是从这里——东交民巷被抓走的。大概2021年,这儿立了一块牌子,告知人们前面是李大钊被捕的地方,我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路牌。这个地方过去是苏联大使馆的一个旧兵营,当时李大钊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藏到了这个苏联大使馆里,张作霖的军阀政府找机会冲进大使馆抓走了李大钊。还有最初给大家展示过的香厂路、万明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陈独秀是从这儿被抓走的,这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讲述一个事件,必然得交代清楚时间和地点。只不过关于地点,现在已经找不到当年的痕迹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看过相关的资料,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特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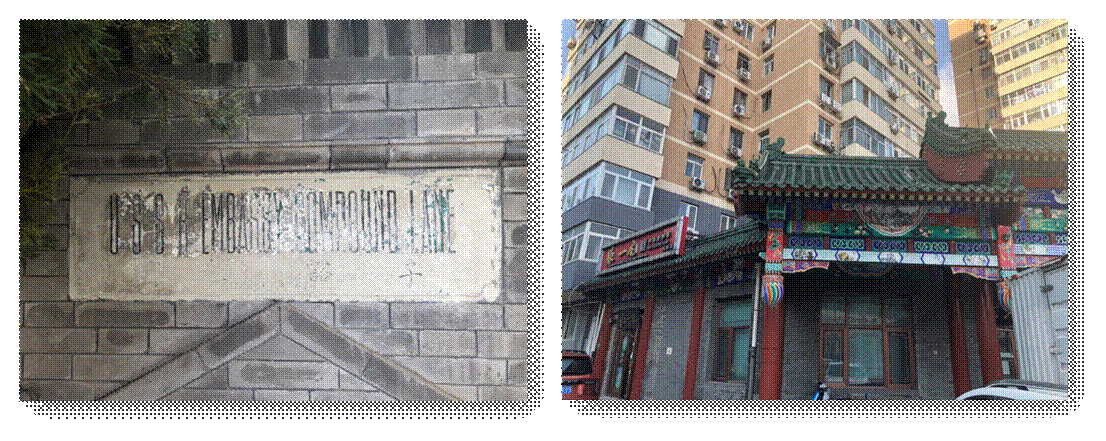
这一处最显眼的大概要数中华圣经会这座楼了,这个地方我去过好几次,丁字路口里面就是蔡元培故居。但是对于中华圣经会北面的那栋楼我一直是熟视无睹,完全没有注意过它的名字。直到后来我写了瞿秋白,我才发现原来瞿秋白当年是在这儿办刊物,他的刊物受到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资助,现在这个楼还保留了“青年会”这三个字,楼底下还有个很小的门脸写着“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我估计没有多少人会把这个“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瞿秋白联系起来。
这一处是小羊宜宾胡同,过去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里,因为沈从文后半生曾经在这儿住过。小样宜宾胡同再往西就是大羊宜宾胡同,后来写瞿秋白的时候,我才发现瞿秋白从苏联回来以后就是住在这里,并且在这里修订他所翻译的《国际歌》。在他之前《国际歌》有几个中译版的,但是基本是跟诗一样,是没法唱的,是瞿秋白第一次根据法文版,让国际歌真正变成了能唱的歌,并且创造性地把“International”翻译成“英特纳雄耐尔”,“英特纳雄耐尔”是八拍,如果直接翻译成“国际”的话那只有两拍,根本没法唱。“国际歌”的旋律第一次在北京响起,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大羊宜宾胡同里。但是过去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大羊宜宾胡同,我路过过好几次,却都没有拍照片,以为那里没有什么历史掌故,所以今天真好给大家拿一张小样宜宾胡同的照片。

正是因为一次一次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北京的大街上不能说随处都是故事,但确实有很多历史故事、红色故事可讲,只是有待挖掘、发现。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是文化中心,这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如何来呈现它的这种品格,我觉得还大有可为。
现在我们上上下下都非常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出身的老师,我总是希望不要把这个东西搞得那么死板、僵硬,我也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点这种有温度、或者说是有品味的思想政治教育。我读张洁《沉重的翅膀》的时候看到了这段话,对我很有启示,这里讲的是一位老革命跟别人讲自己当初是怎么向往革命的,“既不是因为看了《共产党宣言》,也不是因为看了《资本论》,而恰恰是因为看了一本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的《爱的教育》。它使我相信并去追求真、善、美。”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背离“真善美”,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讲“真善美”,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真善美”的东西植入到学生、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那我的“大思政课”至少也不能算是失败的吧。还有一句话也让我印象很深刻,王蒙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说:“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心要单纯”。我觉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也应该是这样——“经验要丰富,但心要单纯”。我们希望把学生塑造成什么样子呢?没有谁希望学生们一个个每天充满仇恨、时刻准备斗争吧?我希望我的学生,至少在我身边的时候,能够追求、向往“真善美”,能够做一个内心比较单纯的人。因此,就像刚才李驰老师讲到的,在我的日常工作上,我也做了一点小小的努力,帮助我现在这个班上的每一位同学都发表文章、作品,有的是小刊物,有的算是大刊物吧,推着每一位同学都去参加学科竞赛,现在我们班上27位同学,每个人都发过文章,每个人都在学科竞赛当中获过奖励,当然有的是国家级的竞赛,有的就是校级的竞赛。实际上还有一个“100%”,就是经过引导、干预,我班上所有的同学都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想一个人如果有追求、如果对自己负责、每天有正事儿可干,那这个人应该不大会走偏吧。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思政教育,或者说一个朝着“真善美”的塑造。
总之就是,在“寻访京畿现代人文故迹”这个话题上,我没有太多太精深的东西,只不过就这些年下了点笨功夫,看了一些故居、遗迹而已这个话题费脑力倒是其次,主要是费鞋底子。今天在政法大学讲这些非常简单的、非常粗浅的东西,真的是造次了。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冯雷,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双聘硕士生导师。本文系作者2023年10月8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讲座实录。刊用时略有改动。原文发表于《赤子》(上旬)2024年第8、第9、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