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生:报告文学是一种有历史使命感的文学 是文学,又是国志,亦是民族史诗的一部分。作为历史,是发人深省的明鉴;作为文学,提供了考证一个时代的蓝本。
来源:中华读书报 | 鲁大智 2017年07月31日07: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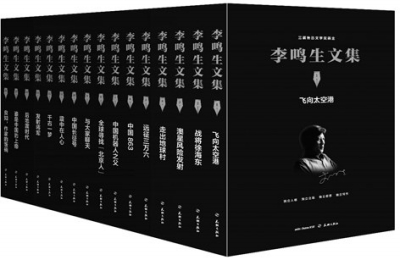
《李鸣生文集》(20卷),李鸣生著,天地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698.00元
报告文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体,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有社会担当、有历史使命感的文学。
李鸣生是当代中国一位重要的作家。不止是因为他的不少作品不仅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囊括了中国所有报告文学大奖,有三部长篇已获得鲁迅文学奖;也不止因为其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都具有较高水准,既有重大的历史文献价值,又有丰富的文学审美价值。
“报告文学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创作,最能体现作家人格与良知、风骨与气质的一种创作,同时也是饱含争议、最具风险的一种创作。在文学这个大家族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种文体能像报告文学这样最公开、最直接、最尖锐地面对社会的挑战、现实的挑战,同时也是面对作家自身的挑战。它挑战的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现实最残酷的伤痕,它挑战的是作家的人格与思想、良知与底线!”李鸣生说。既有知识分子情怀,有史家抱负,又有社会担当,李鸣生被文学界称为“中国航天文学第一人”。
评论家丁晓原认为,建构近三十年中国报告文学史的优秀作家有许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一批穿越上世纪70年代末至新世纪的资深报告文学家,我们称之为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但真正具有文体史意义的,或其创作参与了文体建设的报告文学作家,并不是很多。李鸣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他的写作对报告文学文体具有典型意义。这位写作了《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中国“长征号”》《远征三万六》《千古一梦》《发射将军》“航天七部曲”的作家,以其独特的创作,为我们书写了新中国航天的悲壮历史。
《李鸣生文集》选录了作者在1990~2010年二十年间创作的主要作品,共十六卷约六百万字。每卷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飞向太空港》《战将徐海东》《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远征三万六》《中国863》《中国机器人之父》《全球寻找“北京人”》《与大家聊天》《中国长征号》《震中在人心》《千古一梦》《发射将军》《后地震时代》《谁是中国的上帝》《良知,作家的饭碗》。除两卷为中短篇纪实、小说集和随笔、文论集外,其余十四卷均为非虚构纪实长卷。
《李鸣生文集》是中国首套超大规模的非虚构长篇纪实文集,既有对国家大事的宏阔叙事,又有对个体命运的真实记录;既有对非凡人物的精神观照,又有对底层苍生的悲悯书写;既有对远古文明的探究追寻,又有对现实矛盾的揭示拷问。是文学,又是国志,亦是民族史诗的一部分。作为历史,是发人深省的明鉴;作为文学,提供了考证一个时代的蓝本。
中华读书报:您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谈到过自己与航天题材的缘分。我想知道的是,从您在《科学文艺》发表《用生命编写程序的人》时起,介入航天报告文学,三十多年的写作,如此持续地、长久地在航天领域挖掘一口深井,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鸣生:收获很多,主要有三点。一是获得了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角度。看待人生和世界,除了现实社会的角度,还有自然科学的角度;或者说不能只站在地上仰望,还可置身太空俯视。其好处是,既合人理,又顺天意,让人变得更理性,更清醒,也更坦然。二是科学家们淡泊名利、无畏权势、追求真理、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和特有的人格魅力及精神品格,让我的灵魂和精神得到净化,获得升华。三是我切身感到,作为自然之子的人,在宇宙这位大师面前实在是渺小至极。
中华读书报:写了三十多年报告文学,您的第一部作品都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每一部作品都令人震撼。您在写作中,考虑最多的是什么?写作技巧是否同样纳入考虑范畴?
李鸣生:作家对文本应该有创新精神。我试图希望我的每部作品都有所不同,有所变化。比如,立意上的变化,结构方式的变化、叙事策略的变化、语言风格的变化等。这当然不易。早在80年代初,我就发表了摄影小说《相会在今天》。2009年出版的《震中在人心》,我将其命名为长篇摄影报告文学,这在国内是第一部。这些都是想在形式感上有所探索。至于写作技巧等问题,肯定会考虑的。但我考虑更多的也是最难的,是写作的思维方式和写作理念问题,即面对航天这个全新的题材,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思维去观照、去审视其内容,该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法去挖掘、提炼与众不同的新的主题。
中华读书报:我特别认同您所说的“思想决定作品的高度,决定作品的品质,甚至说思想决定一切。”那么,您又是如何在多年的写作中提升思想性的?
李鸣生:是的,我是很看重作品的思想性的。报告文学是最具思想风骨的文学,或者说是最讲究思想的文学。什么是思想?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作家如果停止了对历史与现实的质疑与发问,便停止了思想,也等于停止了生命。
我曾说过,中国不缺作家,缺的是思想家,像鲁迅那样的思想家。中国只有诞生了大思想家,才可能出现大作家。放眼古今中外,留下来的经典作品,作者无一不是大思想家。因为思想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既可颠倒乾坤,还能穿越时空。所以真正优秀的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应该是个思想家;思想是报告文学能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是当今报告文学的救命稻草。否则在这信息泛滥的时代,报告文学还有何用?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不仅仅因为揭秘性,更在于视野宏阔、人物塑造生动,和国家的历史发展相呼应,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大题材、大视野、大构架、大叙事、大主题、大气场……有评论以一连贯的“大”概括您的作品风格。您认为,这种“大”来自什么?
李鸣生:主要来自两点。一是来自题材本身。比如中国航天,题材重大,题旨宏阔,内容丰富,穿越古今,横跨中外,是一部史诗性的大历史,属于世界性的题材。所以我的“航天七部曲”看似在写航天,其实不限于航天,它所表达的主题和内容有较大的包容性,直接表现或间接折射的是中国的政治、军事、外界、科技、人文等重大矛盾与问题,事关民族乃至人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这就决定了我必须把作品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放在远古、现在、未来的时间轴上,放在天、地、人的空间上来加以构建。唯有“大写”,方能完成。二是来自作者的胸怀。我以为,作品大小,与作家的眼光、胸怀、思想有关。当然我所谓的这种大,不是形式上的大,也不是大而无当的大,更不是假大空的大,而是合情合理的大,有血有肉的大,实实在在的大,与作品长短、字数多少无关。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一系列作品中,《澳星风险发射》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作品中,您将1992年3月22日“澳星”发射失败视作一种客观存在,以一种中性的叙事立场,在中国航天文学中第一次直面失败。这样颠覆常规的写作,在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上也是少数的典型个例。您认为其意义何在?
李鸣生:不客气地说,用一本书来专门写失败问题,在中国我是第一人。其最大的意义,我认为就是突破了写作的禁区——需知这是23年前啊!其实,成功与失败如同硬币的两面,无法分割。事实上中国航天的挫折与失败,自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且一直伴随至今。如诗人惠特曼所言,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写中国航天的失败问题,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
中华读书报:您采访写作的投入、长期关注航天领域的执着都融入了字里行间,阅读您的作品,更能深深地体会到您不止对航天事业和对从事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们有很深的感情,您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充满感情。这是您的报告文学能深入人心的重要一点。但是我想,如此耗尽心血的写作,是否对身体会有很大的损伤?每部作品完成,您是怎样的状态?
李鸣生:完成一部长篇,最短的一年,最长的有20年。譬如《发射将军》,前后拖拖拉拉了20年,《千古一梦》前后经历了9年。而采访对象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采访笔记最少都是几十万字。其实航天不是谁要我写,而是我自己要写,或许这就叫自找苦吃吧。写完航天前四部,腰肌严重劳损,坐一小时就得躺半小时,折磨至今。写完《中国863》,落下颈椎病,苦不堪言,自杀的念头都有。现在,落下严重胃病,还剩半条命。
中华读书报:阅读您的作品,能感觉到您对于当下社会、当下知识分子的忧思和反思。为什么?
李鸣生:报告文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体,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有社会担当、有历史使命感的文学。略萨说过:“文学,首先是对社会的发言。”我个人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挖掘真相更是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