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的批评及其理论意义
来源:文汇报 | 王宁 2018年06月26日0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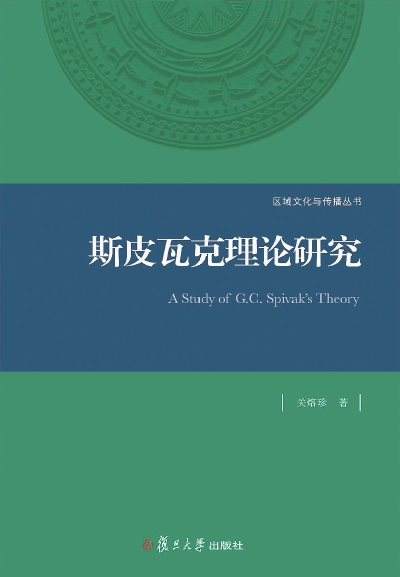
《斯皮瓦克理论研究》关熔珍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当今的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及女权主义运动中,斯皮瓦克的名字一直十分引人瞩目,随着2003年赛义德的去世,斯皮瓦克成了后殖民理论批评当之无愧的最杰出的代表。再加之她本人既是一位多产的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同时也十分关注翻译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性文字和译著,在整个文学理论界、比较文学界和翻译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对她的批评理论进行研究,不仅在英语文学理论界和她的祖国印度的比较文学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且近20年来也开始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1942年2月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进入了康奈尔大学,1962年获得英文硕士学位,后于1967年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导师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德曼,他是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研究权威,解构主义批评在美国的最杰出代表和旗帜性人物。斯皮瓦克也和许多从第三世界来到第一世界留学的莘莘学子一样,获得博士学位后没有回到印度,而选择了在美国发展自己的学术,而且成了少有的成功者之一。她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自1991年以来,一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2008年以来,她又接替赛义德的空缺,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级讲席教授。每每和她谈到这一点,她都感到由衷的自豪:她不仅是整个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女性,而且也是其中的唯一一位亚裔学者。斯皮瓦克著述甚丰,不仅在英语世界影响很大,在中国也一直有着持续的影响。在中文的语境下经常为学界讨论和引证的就有这样几部最有代表性的著译:《在他者的世界:文化政治论集》(1987)、《外在于教学机器之内》(1993)、《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行将消解的当下历史》(1999)、《一门学科的死亡 》(2003)、德 里达 《论文字学》英译等。
在三位最重要的后殖民理论家中(另两位是霍米·巴巴和萨义德),斯皮瓦克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同时也是唯一的专注形而上思考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她就不关心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实践。她对印度“底层研究”小组的介入之深是任何一位印度的后殖民理论家都无法比拟的,因此她并不喜欢人们称她为“后殖民理论家”,而宁愿被称为“底层研究者”,因为她确实也是这三位理论家中最为直接地投身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历史和当下现实研究的一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我早就听到学界有人作过这样的比较,阅读斯皮瓦克的著作,假如不知道她的性别,我们很可能将其混同于一位男性思想家,因为究其思考的形而上特征和理论推演的抽象性,以及风格的雄辩性,她堪与德里达相比美。但德里达本人很少从事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他对文学的阅读和阐释,大都将其作为演绎自己的哲学理论的文本材料,他所处的位置是哲学和文学之间,而且是从哲学走向文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而斯皮瓦克则首先是一个文学研究者,十分关注对文学文本的批评性阅读,而且她的阅读和批评视角也具有鲜明的第三世界特征。可以说,她的学术生涯与德里达的恰好相反,她是从文学走向历史和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在当今的北美乃至整个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界中,斯皮瓦克的批评和学术生涯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同时也自然而然成了来自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批评家们兴趣的中心和争论的话题。这种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正好实现了以斯皮瓦克等人为代表的有着第三世界血统和民族文化身份、同时又有着第一世界的深厚文化修养和良好教育背景的后殖民批评家的这一尝试:从边缘向中心运动,通过对中心的消解而达到消除旧的中心和重建新的中心之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后殖民理论一经被推上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后的学术理论前沿,就立即受到了来自第一世界 (前殖民地宗主国)和第三世界(后殖民地)批评家的激烈批评的原因所在。一些对后殖民理论批评抱有偏见的白人学者甚至断言,所谓后殖民主义不过是几个印度裔学者自己“炒作”出来的,维持不了多久就会自然消退。但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恐怕并不尽然。至少我们读完关熔珍的这本专著后多少会改变这一看法。就目前的研究以及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的现状来看,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研究远未达到深入的地步,而在中文的语境下,对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开始。随着全球化时代以来更多后殖民理论著作中译本以及中国学者的著作的出版,围绕它的争论将结合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实际问题而进一步展开,因而现在就武断地对之进行价值判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关熔珍这部专著的出版不仅对国内的斯皮瓦克及后殖民研究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而且她基于中国学术立场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也可以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和讨论。本书的出版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学者介入到国际性的理论争鸣和讨论中,从而改变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失语”状况的一个契机。
我和斯皮瓦克在相识之前就神交已久,我们于2005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举行的 《新文学史》杂志研讨会上一见如故,并由此成了长期的挚友。当斯皮瓦克得知我下半年要去她曾经作过“底层人能发言吗?”的著名演讲的伊利诺伊大学讲学半年时,立即邀请我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也就是在那次重访哥大期间,我得知斯皮瓦克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坚持学习中文,现在她不仅能够进行简单的口头交流,而且在阅读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2007年,我应邀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从事研究半年,期间斯皮瓦克再度邀请我前往哥大演讲,并邀请了我们共同的朋友戴维·戴姆拉什为我的演讲作介绍。就在那以后,我逐步进入世界文学研究领域。2006年和2015年,我也曾两次邀请斯皮瓦克到北京和广州讲学,她都十分爽快地应允。有鉴于此,我期待着学界对关熔珍这部《斯皮瓦克理论研究》的反应,同时也期待着斯皮瓦克本人对这部中文学界的研究专著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