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文学与禁忌之爱
来源:凤凰网读书 | 马特·格罗斯 2018年10月18日0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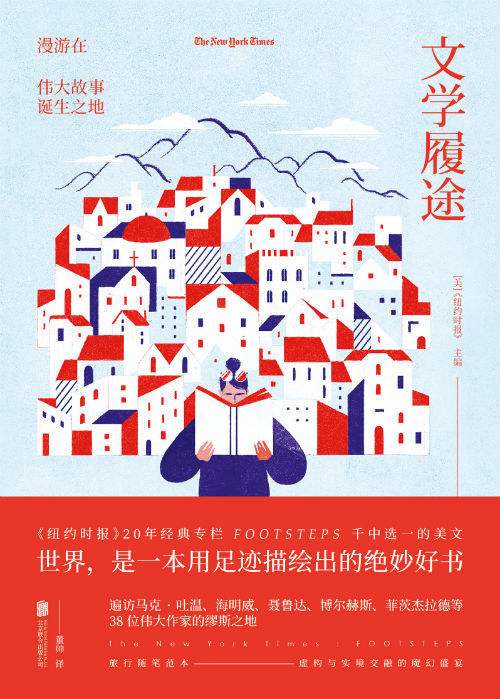
再没有比胡志明市更适合偷情的地方了。这座城市的每个街区几乎都有酒店或小旅馆,在你带着情人办理入住登记的时候,前台接待都不会抬一下眼睛。西贡发生的事,只要不被忘记,就会永远留在西贡。
没人比玛格丽特·杜拉斯更了解这一点。
这位法国作家于1914 年出生在殖民时期的法属印度支那,并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15 岁的杜拉斯和她的母亲与两个兄弟住在湄公河沿岸的小镇沙沥,并在那时与一位 27 岁的中国男子发生了一段关系。那人是一位中国富商的儿子,他们在一艘渡轮上相遇。很快她就开始从寄宿学校逃学,去往这座城市最大的中国城堤岸区(Cholon),到他的“单身公寓”里度过一个又一个热情缱绻的傍晚。
他们的不伦之恋为后来多部作品提供了原始素材,包括出版于 1984 年,杜拉斯最畅销的小说《情人》(TheLover),后来在越南拍摄的同名电影,以及 1992 年她重溯过往写就的自传体电影笔记式小说《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The North China Lover)。
不过,虽然《情人》的诸多版本广受欢迎,杜拉斯的生活轨迹在当今越南却无迹可循。尽管如此,经过几天对她书中细节的寻访,我发现,虽说越南在过去的 75 年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杜拉斯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
我的寻访从东桂街开始,这里是胡志明市第一区的中心地带。东桂街原来叫作卡蒂纳街,曾是西贡首要的购物和娱乐区。现在这里依然人来人往,从圣母大教堂这端到另一端的西贡河,整条街满是精品店和咖啡馆。街的中段有一条两边摆满书架的小巷,便是兰安书店(Lan Anh Bookshop)了。老板是一个 69 岁的西贡人,非常友善,自称为“撒奇先生”,他喜欢收集一切体现“越南狂热”的书籍与物品。
在一番混杂着英语、法语、越南语的笨拙描述后,我终于向他表明了我的意图,撒奇以 20 万越南盾(约合 12 美元)的价格卖给我一份 1953 年出版的《联系国年鉴:柬埔寨,老挝, 越南》(一份带注解的殖民地目录,附有地图、香烟广告以及一本对照旧时法式街道名的小册子),这或许能把杜拉斯提到的地方和西贡如今的地名对应起来。我感觉自己中了头彩。
当东桂街上的摩托车风驰电掣地从我身旁驶过、小贩不停向我兜售昨天的报纸时,我正在翻阅手里这本黄页电话簿风格的册子,突然我留意到一个标题:“电影院”。标题下面便是伊甸电影院,而杜拉斯的母亲曾在那里当过钢琴手。
对杜拉斯来说,伊甸电影院的存在意味着她可以短暂逃离那个悲惨的家庭。当年的电影院,现在已经改名为“东桂迷你录像厅”(Video Mini Dong Khoi),孤零零地躲在一个布满卖越南和欧洲油画复制品商店的回廊后面。原先那宽大的红皮座椅都已经被连根拔起并堆在大厅里,而剧院里面则布满碎石。唯一能让你联想起过去的,是墙上的手绘电影海报,例如《埃及艳后》(Cleopatra),和一些说明此建筑物归伊甸公司所有的标识。
对于这个发现,我既高兴又失望,另外我在任何地图上也找不到杜拉斯曾住过的利奥泰寄宿学校(Lyautey Boarding School),于是我决定追随杜拉斯的脚步,离开西贡。
在西贡人的想象中,堤岸区的面积和电影《唐人街》中的洛杉矶中国区差不多大。它就位于胡志明市的第五区和第六区,却不为外人所知,充满异域气息。尽管这里的街道看起来和西贡一样,并且拥有近百万居民,我的越南朋友一个里面的人都不认识,一条街也不熟。这里与西贡唯一的区别是,路牌上的越南文字下标着汉字,餐厅橱窗里悬挂着烤猪和烤鸭,道路两旁布满了殖民时期带阳台的低矮商铺——在那里,杜拉斯情人的父亲积累起巨额财富。
要寻找一个类似他们的底楼爱巢般的酒店(“看着布置得很草率,配有超现代化的家具”),也似乎不太可能。于是我只好前往第二名的选项:凤凰酒店。酒店的外墙是仿包豪斯风格,有一个楼梯能让人直接绕过前台去到房间,对于偷情者们来说,这是保证隐私的基本特征。(我对此并无兴趣——更何况,我的未婚妻简也肯定不会同意。)
夕阳西下,阮豸街和冯兴街交界处的夜市拉开帷幕。尽管烤鸭看起来十分诱人,但我还是坚持选择了一份杜拉斯式的晚餐。《情人》里著名的晚餐场景发生在昂贵的中国餐厅里——“它们占据了整栋建筑,像百货公司或军营那般大,从阳台和露台上俯瞰整座城市”。在这里,杜拉斯的表哥们因为马爹利和巴黎水而烂醉,忽视并侮辱她的情人,但最终还是由情人买的单。
由于杜拉斯从来不会提到餐厅的名字,我再次翻开了年鉴,上面有一则关于彩虹餐厅的广告,写着“无以匹敌的独特环境”和“香港舞女”。令人惊讶的是,经过了五十多年,艺术装饰风格的彩虹餐厅依然营业,只是没有了舞女的项目。现在这里主要是一家酒店,有三层是餐厅。
屋顶的花园露台正在举办一场婚礼,于是我便和朋友克里斯汀和希塔坐在底楼餐厅,点了一份热扇贝和脆米糕。这里的环境非常优雅,可以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酒店。然后我鼓起勇气,向希塔——这位来自美国罗德岛的已婚女艺术家——提出了一个邀请。你是否愿意,我问道,在沙沥来一场假装的风流韵事?
“当然。”她答道。
第二天,我穿着一套意大利亚麻西装——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接近杜拉斯情人的生丝西服的衣服——从酒店的205房间走出来。外面停着一辆 20 世纪 30 年代产的前轮驱动雪铁龙敞篷车,用来替代小说里情人的那辆黑色莫里斯·莱昂—博来,载希塔和我往返沙沥。司机名叫简先生,体格不错、衣着时髦,他优雅地驾驶着雪铁龙穿过拥挤的街道,前往河对岸希塔的房子。
希塔出现了,就像杜拉斯复活了一般:瘦弱如少女一般的身躯,穿着一条浅色的太阳裙,头发梳成辫子,从她戴的男士软呢帽里垂下来。在她没有假装要做某人的模拟情人时,就已经戴着这顶帽子了。
大概有一刻钟吧,我们沉浸于自己想要表现出来的形象——两个时髦的旅行者在这个国家度周末。然后我们开始出现罪恶感:这也有点太新殖民主义了。与此同时,我们才发现敞篷车里没有空调,也没有什么设备可以阻挡越南高速路上的灰尘。去往湄公河三角洲的路和电影《情人》里拍的不一样,并非是那条两旁种满碧绿稻田的暗红色乡间土路。越南汹涌发展的经济已让这儿呈现出一片城市风光,放眼望去皆是工厂、写字楼和工业园区,一直延伸到几公里以外。
就在我们穿过美顺大桥之前,这样的碍眼景色总算到了头。这座跨度足有 1.6 公里的大桥 2000 年由澳大利亚人建造,横跨在湄公河之上,淘汰掉了当年杜拉斯(当时她还叫玛格丽特·陶纳迪欧)和她的情人初见时所坐的渡轮。从那里开始, 一条颠簸小路带我们驶向沙沥,两侧时不时路过有蜂窝状的砖厂。
拥有 9.6 万人口的沙沥,可以说是一座精致的河畔小镇。它夹在湄公河的两条支流中间,无数溪流和运河从中穿过,水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拱桥。沿着水系,各类商店沿着一条贸易航路将自己的面粉和猪肉运送出去,这条航路已经为全镇人服务了几个世纪。
然而沙沥最著名的居民却没有留下明显的标志。在奉洪酒店,希塔和我住进了不同的房间(说什么风流韵事!),换掉我们的精致行头,等简先生冲洗雪铁龙轿车的空当,我们开始询问当地人:如何才能找到那个富有的中国男子的临河房子?尽管被询问的人并没有谁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但他们都知道我们谈论的是谁:李云泰,那个著名的情人。
即便如此,我们至少还是成功找到了电影中的陶纳迪欧所居住的那栋殖民地别墅(现在是一个教育部门的办公楼),然后我们去了一栋带有中国式屋脊的矮房子。这难道真的是情人住的那栋有着“蓝色栏杆”和“可眺望湄公河的层层阳台”的“大别墅”吗?这房子现在的使用者是戒毒所民警,他们似乎并没有兴趣和我们交谈。
最终,我们乘坐摩托车的士前往统望小学,当地人告诉我们它是由法国人创建的。房屋外观确实带有殖民色彩,而当希塔和我站在安静的院子里,一个穿白色夹克衫和黑色长裤的人从他的办公室门口向我们挥手,并喊道:“你好(Bonjour)!”
这位桑先生是一个害羞而颇具绅士气质的法语教师,六十多岁的他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沙沥。他谨慎地解释说,这个学校很有可能便是杜拉斯母亲曾管理的那个学校,但是没人可以百分百肯定。
“根本没有文件证明,”他说道,“有人说陶纳迪欧女士在此住过,因为隔壁有栋房子是校长住的,用来观察学校。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没有人能找到完全精确的位置。”
我们询问了关于戒毒所的建筑,他确认说这里曾经是情人的别墅。然后他提出可以做我们的向导:“你和你朋友是来我们国家的外国人,所以作为一个越南人,理应带你们四处走走。”我们怎能拒绝?
我们首先来到情人及其中国妻子的墓地,就在我们酒店附近,一个覆满水藻的池塘中央的混凝土小岛上。一个写有中国文字的白色牌楼立在坟墓上方,旁边小岛上还有两处墓地,属于情人的父母,正是他们不让情人与杜拉斯结婚。
桑先生接下来把我们带到了建于 1838 年的香(Huong Pagoda),杜拉斯的情人生前曾在此奉纳无数。进到里面,穿过一个布满乌龟的池塘,我们在一尊装饰华丽的神坛前发现了两张照片。桑先生说,这就是李云泰和他的妻子。
照片上的情人看上去七十来岁,身材清瘦,几近秃顶,但有着曾经吸引杜拉斯的“中国北方人的白皙皮肤”。在他的眼里是否有遗憾?在他们的恋情过去多年后,他打电话给在巴黎的杜拉斯,并告诉她“他在余生将永远不会停止对她的爱”。这或许也是照片上的妻子显得如此不安、不被人所爱着的原因。
塔外开始下起小雨,我们快速冲向我们的车。简先生驾车带我们穿过一条湿漉漉的街道,然后我们请桑先生一起享用了一顿晚餐:炖猪肉和酸鱼南瓜花汤。之后,希塔和我回到酒店各自的房间。我将一张《情人》的盗版 DVD 插入光驱,却不能播放。最后我只好看了部《罪恶都市》,然后独自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