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文书信集》的七封佚信及其他
来源:澎湃新闻 | 雷强 2019年01月25日08:06

《胡适中文书信集》,潘光哲主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胡适纪念馆,2018年10月出版
11月5日,笔者突然收到台北旧香居书店吴先生的留言,告知“中研院”版《胡适中文书信集》和《胡适时论集》即将上架,这着实令人兴奋,尤其是这两种书的定价比联经新版《胡适日记全集》(据吴先生说只是翻印,并未增补)亲民许多。于是,笔者斗胆开口求其代购,承蒙吴先生费心,亲往南港近代史研究所取回厚厚五大本,并以航快寄送北京,19日晚《胡适中文书信集》就出现在笔者的书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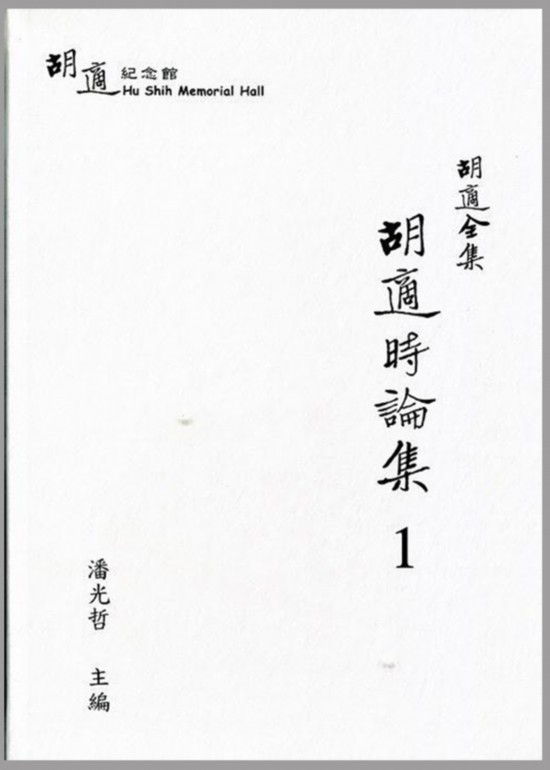
《胡适时论集》,潘光哲主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胡适纪念馆,2018年10月出版
“中研院”版《胡适全集》共分为“文存”“书信集”“时论集”“日记”“诗存”“单行本论著”以及“文章编年”,其中“书信集”和“时论集”最先付梓。相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2013年),《胡适中文书信集》仅收录胡适先生的手札,他人的来函概不入选。此法虽略有遗憾,但编者既然设定了拣选原则,必然有其初衷。即便如此,“较之旧版《胡适全集·书信》字数约为一百一十余万字;新版《胡适中文书信集》多达一百六十余万字,搜罗整理更为完整,从而为了解胡适的思想与人际网络,提供更广泛全面的线索”。胡适纪念馆的介绍绝非虚言,即便不收来函,新版书信集也比《胡适来往书信选》多了近六万字。笔者稍稍翻阅即发现了很多首次公开的书札,譬如1931年4月19日致赵万里函、1958年3月22日致袁同礼函,它们均属胡适档案检索系统中新披露者,从未被学界所知,让笔者为之狂喜。可以预见,《胡适中文书信集》将为广大学人提供更多的珍贵史料,极大地推动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
一、佚信
“中研院”版“书信集”虽然没有冠以“书信全集”之名,但隶属《胡适全集》之下,且“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为目标,期可为学界提供最完整(毫无删易)与最精确(汇总各种版本,进行编校)的胡适著作文本,以便利用”。潘光哲先生在编者序中如此表述,其目标和志向自然是尽其所能求全,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来临之际,假该书为胡适先生作一总结与纪念。
然而就笔者所见所知,尚有胡适先生七封亲笔手札未被编入《胡适中文书信集》,这着实令人遗憾,故撰文希望有所补充。这些佚信的情况各不相同,其中袁同礼先生家人藏有胡适先生书信三封,均写于1919年,笔者获得其特别授权,予以公布;上海市档案馆曾刊布过一封;另有三封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依照其时间顺序,整理如下,原文中的小字改用括弧标注。
(一)
守和先生:来信说清华学生要办一个“白话文学研究会”,我听了非常高兴。那时我若有工夫,一定来加入讨论。定期何时,请早日告我。
弟胡适 敬上。
三月七日
按:此信写于1919年3月7日,清华学校“白话文学研究会”成立于是月初(见《清华周刊》第一百六十一期“校闻”一栏)。此信为笔者所知胡适、袁同礼两位先生交往的最早记录,后者时在清华学校主持图书馆事务,广泛邀请学界人士前往该校演讲。从上款的敬称——“守和先生”亦可推断二人刚刚结识不久,自此友谊日渐深厚,直至1962年初胡适先生去世。
(二)
守和吾兄:那天我从教育部会场回来,翻出我的记事簿,方才知道我曾应许送吾兄一本哲学史,并不是应许孟先生的,是我记错了。所以我把书送上,请你赏收。还有中学白话文学会要我(四月十九日)来演说的事,我一定来。但是如果他们能改在四月廿六日,便更好了。因为二十六日我要来清华做评判员。
适
按:此信应写于1919年3月底4月初。“教育部会场”似指教育部所开“全国教育调查会”,该会自3月27日开幕(见《申报》3月29日第三版“专电”一栏)至4月初结束(见“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教育杂志》第十一卷第五号)。“哲学史”即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年2月初版,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孟先生”待考。4月26日(周六),胡适在清华学校礼堂做“白话文学何以必须研究”的演讲;同日晚八时,清华学校举行国语演说比赛,参赛者罗隆基的发言——“中国留学生”最为引人注目,胡适、金邦正(农业专门学校校长)、赵国材(清华副校长)为裁判员(见《清华周刊》第一百六十八期“校闻”一栏)。
(三)
守和吾兄:前几天在清华,可惜不曾见着你谈谈。现在我因有一事,要想借贵校的留美学生季报(自一九一七年起)一用,准于二十六日带回奉还。不知可以吗?
胡适 敬上。
(四月十五夜)
按:此信应写于1919年4月15日。《留美学生季报》的前身为《留美学生年报》(1911-1914),1914年3月正式改组成为“季报”,其主编多由清华学校(大学)留美学生担任,如陈达、沈鹏飞、罗隆基等人,该刊先由中华书局出版,1917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发行。
(四)
菊生先生:我译的白郎宁的诗,只有二篇曾发表过,今抄出奉上。尚有一篇,系早年用古文译的,一时检不出了。
又闻一多、徐志摩二君有译白郎宁夫人的情诗二篇(见新月第一卷第一号),闻君译了二十一首(见新月第一卷一、二号),徐君作解释,皆甚用功,也送上。
胡适。
十九,七,十三。
按:该信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收录于《上海市档案馆藏近现代名人墨迹》(2014年,435页),陈子善先生对此信有详尽的解读(见2015年11月1日《文汇报·笔会》),笔者不再赘述。
(五)
守和兄:前晚承赏饭,感谢感谢。珍本经籍刊行合股,先缴一股,俟安居后有余力当续缴一二股。另送上拾元零贰角,为购刊之四种书之价,其书已收到了。两项共六十元零贰角,合开支票一帋奉上。
胡适。
十九,十二,十。
按:该信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未曾公布过。1929年11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刊行珍本经籍招股章程》公布,开办费暂定一万元,共分二百股,发起人为学术界、文化界名人,共计三十位,胡适先生与袁同礼先生均在其中(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三卷第五期)。左侧“退十元〇贰角”非袁同礼先生亲笔,可能为具体经办人的备注。
此外,笔者在《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92年,376-378、407页)中亦曾见到胡适的两封书札,分别为1933年5月3日致段锡朋和钱昌明、1935年3月5日致袁同礼,未辑入《胡适中文书信集》。这两封信又经《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2009年,241-242、272页)排印过,笔者就不再重录了。
二、问题
直至今日,笔者尚未翻完五册《胡适中文书信集》,但已发现两个值得商榷的小问题,故提出供学界探讨。一是该书虽然广加引征,利用各种资料,而某些材料的原作者曾修订过旧作,编辑小组的老师们似乎并未就此类文章前后两个版本予以必要的甄别,导致误系;二是胡适先生少部分信札于落款处并未注明日期,编者对此仅做了大致限定,若更加仔细翻阅胡适纪念馆馆藏资源,或有进一步明确撰写时间的可能。
(一)
《胡适中文书信集》第二册中收录了1932年7月9日致江绍原的两封信,其出处为张挺、江小蕙《雪泥复见飞鸿爪——胡适又六封佚信笺注》一文(见《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八期,26-27页)。这两封信又都收录于《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中华书局》,2006年,205-206页),江小蕙女士在手札影印本中将其中第一封信改为1932年6月17日。这一变动似乎并未被书信集编者所注意到,江小蕙女士也并未解释修正日期的缘由,但笔者认为这封信应该写于1934年7月初,另外一封由胡适本人标注“七月九日”的信则,也同为1934年所写。理由有三——
首先是如张挺、江小蕙“雪泥复见飞鸿爪”文中所言,1933年6月1日《新月》在上海发行完第四卷第七期后正式停刊,虽然该刊第三卷第十二期和第四卷第一期(志摩纪念号)间延宕了半年多,但此种停顿并无停刊之虞,而是在收集徐志摩遗作及亲友的纪念文章,如1931年11月26日《申报》登载“徐志摩昨日大殓”,文中明确告知“至徐先生平生创作、将搜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志摩纪念号”(参见本日《申报》第三张第十一版),而“志摩纪念号”的发行时间应为1932年8月;胡适给江绍原信中提到“近日叶公超兄与我们商议把新月月刊在北平复活”,更似指《新月》正式停刊后,考虑到胡适先生1933年6月11日离平、6月18日晚由上海坐船出洋,这意味着此信极有可能是1934年夏所作。
其次,信中提到“小儿子病猩红热,至今已两星期……令姪女调在传染病部”,张挺、江小蕙文中特别注明“令姪女”为“江绍原之兄江亢虎长女江兆艾(名菊)”,事实上江亢虎长女为江兆菊、次女为江兆艾,前者1928年获燕京大学理学士并于1932年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见《私立燕京大学一览》,1931年,323页;《话说老协和》,1987年,479页),后者在1933年秋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话说老协和》,1987年,482页),因协和与燕大有长期合作,培养的医生和护士大都先在燕大读理学科,故1933年燕大发行的《燕京报》中尚有理四江兆艾同学的记录(见《燕京报》1933年5月1日、12日第一版);究竟是谁在照顾“小三”胡思杜,笔者亦不能确定,但更趋向于江兆艾,因为她出身护士专业,具备在病房应对猩红热这类传染病的实操能力,而江兆菊的专长似在妇幼助产方面,且不晚于1934年初即南下到“中央”医院任职(见《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职员录》,1934年1月,25页)。
最后,胡适先生日记中虽无胡思杜患猩红热的明确记述,但1934年8月30日提到“带小三去协和验身体,医生(Dr. Hall)说他可以进学校了,但不宜做猛烈的运动”(见《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2004年,138页)。这位医生的全名是Dr. G. A. M. Hall,与胡适先生亦是旧识(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2004年,630页),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执掌北平结核病防治中心(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 51, p.120),对治疗同为呼吸道传染病的猩红热应有绝对权威,此次就医或许是胡思杜愈后的最终复诊。
(二)
承蒙几位前辈学者照拂,笔者有幸从台湾得到一批有关袁同礼先生的档案资料,其中一通书信为1950年5月20日所作,亦藏于胡适纪念馆。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日前奉到十五日赐书,诸承指示,至为心感。此间所藏英国皇家学会N. C. B.学报适有数期为他人借去,无法检阅。又Zucker及Franke所译之文尚未觅到,俟日后查明再行补入。兹先将近日搜集之论文简目随函奉上,即乞钧阅。至于Hoffman所译之“四十自述”系分期刊载,似未全译,而该期刊亦在第二次大战时停刊,一俟查明其住址,当与之通讯一询也。关于编辑专集事,先生未免谦虚,敝意仍主张印甲乙两集,仍祈考虑。检阅各方志目录,光绪三年鄞县志系最后所编印,以后并无续修之本。普仁斯敦事是一极大荣誉,将来如能打开一条路,亦一大收获,于中美文化促进贡献极大。内人闻尊夫人已抵香港,甚为欣慰,盼不久可以觅到妥便。昨史语所何君(北大毕业)见告,孟麟先生不久可以来美,如能同船来美,实一好伴也。专此,敬颂
著祺
同礼 拜启
五月二十日
《胡适中文书信集》第四册收录了一封标注为1950年5月致袁同礼函(31-33页)。将其与上信对照互见,不难发现其中所谈内容完全匹配,如Hoffmann所译《四十自述》《鄞县志》版本问题、普林(仁)斯顿葛斯德图书馆延揽馆长等事,也无中间再有它信往来的可能,据此断定书信集中胡适先生的信写于5月15日,而仅标为5月的方式就略显不妥了,尤其考虑到胡适纪念馆同时藏有这两份书札。
补语
笔者草就此稿后,突然收到西泠印社陆先生寄赠的2018年秋拍图录,其中“中外名人手迹暨戊戌变法120周年纪念专场”上拍了胡适先生致孙壮(字伯恒)先生五封书札,这着实令人惊叹!孙先生不仅长期执掌商务印书馆北京事务,更是活跃在清末民国学术、文化界,但事迹和学问至今不得彰显,其稿本“商逸日记”除《张元济年谱长编》(2011年)略加引用,一直秘不示人,世间凡有只言片语均可视为稀见史料,何况是胡适先生的书札呢!
回归正题,“全集”古难全,不必过分苛求,倘若学界中人都能为胡适先生的集子尽一份心力,即便先生的墓木已拱,却仍未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