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梁启超全集》:30年编纂之功 90年缘起不灭
来源:北京晚报 | 张玉瑶 2019年02月02日06: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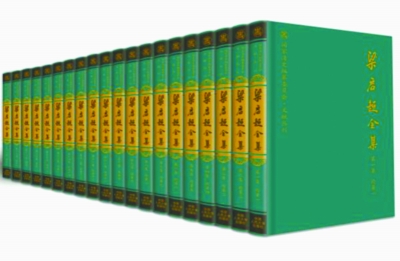

2019年1月19日是梁启超去世90周年纪念日,同在这一天,历时三十多年编纂、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全集》召开出版座谈会,以此纪念怀想梁任公之人格风范。
据介绍,这套全集是迄今梁氏论著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梁启超1889年中举前至1929年去世所见的全部著述,分为论著、演说、诗文、译文、函电五大类共二十集,字数逾1400万字。值得称道的是,它呈现了梁氏著作的原貌,所收资料或录自其手稿,或录自其手订、手校的较早出版品,或录自最早刊载其作品的书籍报刊,特别是收入了近年来在内地和日本、美国、新加坡、港澳台等地陆续发现的梁氏佚文、信件等,如《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等,都是此前梁氏各版文集中从未见过的珍贵史料。
《梁启超全集》的编辑、校勘、出版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花费了两代人的心血。其编纂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后因故中断,一直到1982年,正式由历史学家汤志钧负责,后来其子汤仁泽也加入进来。然而,出版计划数次搁浅,资金一度也十分缺乏,父子二人几乎是孤军奋战,在学界、出版界众人的点滴支持下,穷37年之功,终于编成。汤志钧先生如今已有95岁高龄,汤仁泽也从一个历史系本科生成为花甲老人。座谈会上,上百位老中青几代历史学者闻讯前来,在座尽显华发,谈起编纂往事,无不唏嘘赞叹。
父子两代苦心编全集
梁启超虽然只活了短短57年,却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各类作品。在《梁启超全集》之前,被人引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是900多万字的《饮冰室合集》,这是由林宰平(林志钧,字宰平)受梁启超本人生前之托编成的,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丁文江受梁本人委托,与助手赵丰田编成《梁启超年谱长编》。很长时间以来,这是研究梁启超的两个最重要的资料。
鉴于梁启超在近现代史上的卓著地位,上世纪60年代,吴晗、范文澜、侯外庐等提议编一部梁启超的文集,由中华书局承担这部书的编辑任务,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梁集组”,挂在近代史编辑室。但到70年代初,因书局也卷入到种种运动中去,这项工作不得不中止。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编梁启超集的工作又重新恢复,正式定名《梁启超全集》,由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延请汤志钧先生负责编辑工作,列入了1981年制定的1982—1990古籍整理计划。汤志钧此前出版过《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等,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有专研,巧合的是,和林宰平一样,名字也叫“志钧”。
不料,从1990年开始,中华书局因进行体制改革,向企业过渡,自负盈亏,只好压缩那些“不赚钱”的书,部头大、收益低的《梁启超全集》也在此列,甚至连近代史编辑室都撤销了。2003年,这个项目一度被天津古籍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做了大量筹备工作,还开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但后来还是搁浅了。然而即便如此,汤志钧、汤仁泽父子仍勉力支持,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整理、点校文献资料,多年来不曾间断。
在此期间,《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工作也得到了梁家后人的关注和许多支持。2010年,梁从诫(梁启超长孙、梁思成之子)去世,汤志钧闻讯非常难过,说梁家交代的事情没有完成,一定要加快努力。几年后,梁启超幼子梁思礼也去世了,汤志钧心情更加沉重,说一定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完成。
随着国家对学术经费加大投入,终于在2014年下半年,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支持下,《梁启超全集》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取得成功,这项浩大工程才有了资金支持,时年汤志钧已经90岁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将其列入“文献丛刊”项目,即成为国家清史编纂的组成部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这项工作才终于克服千辛万苦,重新回到了正轨上。汤志钧曾先后于1983年、2011年、2017年为全集写了三个序言,可见其艰难困苦之状。
文献整理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巨细靡遗,可一有纰漏即受人诟病;而在当今学术体系内,短期内又不能计入工作量,看不出成果,不能发刊物,导致能静下心来做这件事的学者越来越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汤仁泽多年“晋升无份”,但他明白,这项工作总要有人不计得失地埋头去做,尤其是父亲汤志钧在编全集时踏破铁鞋、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深深激励了他。梁启超曾外孙、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念群感叹道:“肯干这个事情的人,一定是有自己执着的信念和真实的、一生的兴趣,还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几个要素结合在一起,他才肯干这份工作,而且才能干得出色。”
寻找“世界的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是目前收录最全的梁氏著作集,难得的是,不是以前已有文集的合集,而是一次重新的编纂。汤志钧及汤仁泽从梁启超当时发表文章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知新报》等报纸刊物上一篇篇找到原始文章,参阅异文,进行校订校对,工作量十分巨大。
多年来,汤志钧利用讲学交流的机会,赴台湾、香港、澳门、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检索书藏,搜集散落在海外的梁启超诗词、文稿、信札等。如上世纪八十年代访日期间,在日本搜集到梁启超的一批佚文书信《〈乘桴新获〉中的梁启超佚札辑存》,包括《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致大隈重信书》《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致山本梅崖书》以及《致犬养毅书》中的一部分,是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写的,对“保皇派”的“勤王”活动有参考价值。还有《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包括了梁启超写给家人的一些书信,这些都是此前从未见过、披露过的。值得一提的是,梁任公的书信书法精美,又一向纸墨上乘,收藏价值非常高,故而虽遗散多处,但保存较为良好。
汤志钧先生一直感叹,全集的编成是群策群力之功。曾参与编辑出版工作的人大教授王汝丰谈到一件事: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晓虹曾花费工夫辑过一部《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汤志钧先生看到了想采用,但不认识夏晓虹,最后中间通过几位学者辗转联系上,一开始提这个请求时心里很是顾忌,没想到夏晓虹二话不说,就让全集予以采用。王汝丰直感慨,这种修书风度让人敬佩。
海外学者也非常关注这套全集的编辑工作,日本中国近代史专家狭间直树和岛田虔次曾花费十余年时间将《梁启超年谱长编》翻译成日文并增加了许多珍贵的考证注释,在2003年为《梁启超全集》召开的天津会议上,狭间直树等纷纷自告奋勇,恳切表示日本学界愿协助汤志钧父子出力,后来也帮了不少忙。在全集出版座谈会上,台湾学者黄克武感叹道,梁任公一生足迹广布世界,东亚受其思想影响尤深,从中可见一斑,“梁启超不但是中国的梁启超,也是世界的梁启超”。
当然,搜集只是前期工作。这套《梁启超全集》为人称道之处,除了收录之全,还有点校之精。文献点校是一项非常繁难琐细的工作,单一而枯燥,为了抠一个字眼常常得跑多个图书馆翻阅大量资料,比如晚清名人杨度的字,在上海版《梁启超年谱长编》、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和89版《辞海》里作“晢”,而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99年版《辞海》作“皙”。校阅者参阅了刘晴波的《杨度集》,最后确认为“皙”。但汤仁泽在媒体采访中坦言:“当你把一件工作看作责任或使命,你会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去做,忘了枯燥和孤独。如果全身心投入,会有‘乐在其中’的感觉。在比勘同一篇著述相关版本的差异时,在补苴罅漏、芟其重复、校正舛误时,会感到收获无穷。”
有形建树,无形修为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一般人认识和了解他,始于他的政治活动家和维新思想家身份。梁启超经历和参与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在从事政治活动同时,梁启超在近代学术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于文学、史学、政治、哲学、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宗教学、美学、文字学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留下创造性甚至开山性的理论命题,堪称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难得的是,他能够站在中西文化结合、政治变动与社会文化结合的立场上,反思和推进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不过,对更广大的中国人和中国近代社会来说,梁启超在种种头衔称号之外,影响最广远的当是他“启蒙者”的身份。梁漱溟先生即评说道:“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北大中文系夏晓虹教授亦阐释道:“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不变的追求……谓之‘善变’也罢,‘与时俱进’也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铎《梁任公先生》)。”
在诸种社会身份之外,最令人动容的,还有梁启超关起门来对子女后人的教育。“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皆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幼子梁思礼为火箭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在名门子弟里是绝无仅有的,为人啧啧称颂。其余子女,三子梁思忠投身前线、在淞沪会战中为国捐躯,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和幼女梁思宁都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傅斯年曾评价道:“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
梁启超实行中西文化结合的教育,将九个孩子中的七个送出国外留学,和子女间的通信多达几百封,除了殷殷关怀生活和学业,还注重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操,甚至为子女选择专业也是按照当时中国的实际需求,主张他们广泛学习各种现代科学文化,因而九个孩子涉及领域殊异。纪念梁启超逝世90周年座谈会上,梁思成外孙、梁再冰之子于小东提到,到了梁家第三代也依然如此,有学通信的,有学航天的,有学新闻的,尤以理工科为多,延续着梁启超对子女教育的影响。
清华大学老教授刘桂生回忆了他二十多岁在北大时,当时担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的梁思庄对他帮助很大,让他一个“无名小辈”也感受到梁任公留给家族的无形的文化修为。确如梁启超讲的“缘起不灭”,学问也是带有人格魅力的,于后人,于社会,于中国,泽被至今,仰之弥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