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人的美
来源:光明日报 | 杨早 2019年09月06日07:06
1980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这一年,它的作者汪曾祺刚好60岁。《受戒》的迅速走红,使这位当时让普通读者感到陌生的老作家开始广为人知。在《受戒》中,作者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人的内在性格力量和精神美,在新时期文学中较早地体现出对于人情美、人性美的追求。时至今日,《受戒》依然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中的经典美文,令人百读不厌,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小说对民族美学传统和汉语之美的重视与开掘。这对于当今的文学创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受戒》首发于《北京文学》杂志1980年第10期
这样的小说几十年都没有一篇,谁能相信可以发表?
1980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受戒》,小说作者是汪曾祺,当时,这是一个让读者感到很陌生的名字。而《受戒》也是几十年的新中国文学未曾涉及的题材。
关于《受戒》,汪曾祺本人的回忆是这样的:
读了高中二年级,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我在《受戒》里写了和尚的生活。这篇作品引起注意,不少人问我当过和尚没有。我没有当过和尚。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自。(《自报家门》)
《受戒》所写的荸荠庵是有的,仁山、仁海、仁渡是有的(他们的法名是我给他们另起的)……唯独小和尚明海却没有。大英子、小英子是有的。大英子还在我家带过我的弟弟。没有小和尚,则小英子和明海的恋爱当然是我编出来的。小和尚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是我自己初恋的感情。(《〈菰蒲深处〉自序》)
《受戒》的责任编辑李清泉回忆说,初次知道《受戒》,是听一位京剧团的老杨同志说起的,他那时刚读了一位朋友写的小说,“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
李清泉说的“老杨同志”是杨毓珉,他是汪曾祺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汪曾祺“摘帽”(摘去“右派”帽子)后,能从张家口调回北京,到北京京剧团工作,杨毓珉是主要的推荐者。两人曾通力合作,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沙家浜》。因此,汪曾祺写出《受戒》之后,曾在京剧团给少数人看过初稿。据汪曾祺儿女回忆:
《受戒》写成后,爸爸没有想找地方发表,只是在剧团少数人中传看。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爸爸已经很满足。杨毓珉、梁清濂都看过。梁清濂回忆说,一天爸爸找到她说:“给你看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受戒》。看过之后,她才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很激动。但是看过之后又想,这样的小说能够发表吗?给杨毓珉看,也很激动,觉得写得很美,但也认为没地方发表。这其实不奇怪,这样的作品解放几十年都没有一篇,谁能相信如今可以发表?(《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杨毓珉在代表北京京剧团到文联开会汇报工作时,提到了汪曾祺写《受戒》,引起了《北京文艺》编辑李清泉的兴趣。此时正值《北京文艺》即将改名为《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是改名后的第一期,这期杂志也拟定为“小说专号”。身边出现了这么一篇“味道十分迷人”的小说,李清泉当然不肯放过。
不过,虽然李清泉知道了《受戒》这篇小说,想看到文本,也费了一番工夫。李清泉先向杨毓珉讨要,但杨毓珉等人的说法是“这个东西不能发表,送不出去,不能让它流入社会”,李清泉问“传给我看看行不行”,回答是“不行,这可不行,不往外传”。不发表,只是看看,行不行?答复还是说不行。李清泉没办法,只好直接给汪曾祺写了个条儿,大意是听说你写了什么作品,你给我看看好不好?
汪曾祺当天就请人将稿子送给了李清泉,但附上一纸短简,说:“发表它是要胆量的。”李清泉“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倒过来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看不出政治冒犯”,“我倒觉得《受戒》作者,难以自已的艺术跃动,在是否能获得出生许可毫无把握的情况下,终于写了出来,以及听老杨同志说它味道十分迷人,虽然接着又说它毫无意义,我也仍然挖掘出来,欣喜地予以发表,这事于他于我,更为内在的因素都不过是对于艺术的诚实,表现出一点艺术开拓的勇气,硬要说胆量,那也仅仅是艺术胆量。”

《受戒》最早收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1982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汪曾祺为什么写《受戒》
汪曾祺在《关于〈受戒〉》里回忆,写《受戒》的动因有三点:一是他重写了32年前的旧作《异秉》,感到自己的情感、认知,跟早年比有所变化,沉淀在心中的“旧梦”,似乎可以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二是比较集中、系统地重读了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少女形象,推动着他去写出一个自己的“翠翠”;三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说起来汪曾祺甚至有些激动:“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
汪曾祺强调,写《受戒》是一种“感情需要”:
我写《受戒》的冲动是很偶然的,有天早晨,我忽然想起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段生活。这段生活当然不是我的生活。不少同志问我,你是不是当过和尚?我没有当过和尚。不过我曾在和尚庙里住过半年多。作品中那几个和尚的生活不是我造出来的。作品中姓赵的那一家,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那么一家。这家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的年龄正是作品中小和尚的那个年龄。我感到作品中小英子那个农村女孩子情绪的发育是正常的、健康的,感情没有被扭曲。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样式,在当时是美好的,因此我想把它写出来。想起来了,我就写了。写之前,我跟个别同志谈过,他们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我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叫美学感情的需要吧。创作应该有这种感情需要。(《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
除了回顾旧作与重读沈从文,从1979年到1980年,汪曾祺身历目睹的一些事,也成为他写《受戒》的动因。
“文革”结束之后,汪曾祺有一段时间没有被分配工作,过了一段悠闲日子。1979年,汪曾祺被划“右派”前工作的单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作出了给汪曾祺“平反”的结论,当汪曾祺向经办专案的人员表示感谢时,对方回答:“别说这些了吧!二十年了!”
也是在1979年,《人民文学》编辑王扶经过多方打听,找到汪曾祺住址,登门约稿。汪曾祺十分意外,又感到激动,为《人民文学》创作了小说《骑兵列传》,发表于1979年第11期。这是他“复出”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新观察》也于1980年第2期发表了小说《黄油烙饼》。
1979年,《重放的鲜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选编了1976年之前被宣判为“毒草”的作品20篇。这一年年底,沈从文出现在中国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场。1980年,国内开始重新出版沈从文的文学作品,《边城》《沈从文散文选》《沈从文小说选》《从文自传》相继面世。沈从文、张兆和夫妇亦于该年访美。全国文艺氛围有了明显松动。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1980年的春天,汪曾祺重读沈从文的作品,同时,他迎来了分别数十年的大姐汪巧纹。姐弟俩畅谈高邮往事,引发了汪曾祺的“思乡病”。儿女说,常常见他“发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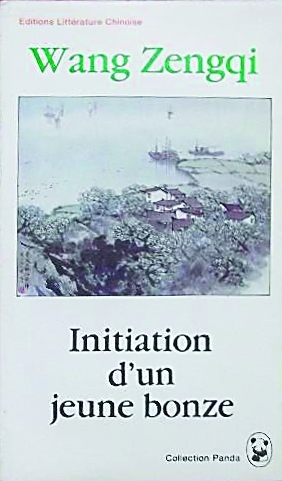
法文版《受戒》
《受戒》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花了两个上午写成的。后来汪曾祺对于写作《受戒》,有一段总括:
我干了十年样板戏,实在干不下去了。不是有了什么觉悟,而是无米之炊,巧妇难为。没有生活,写不出来,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样板戏实在是把中国文学带上了一条绝径。从某一方面说,这也是好事。十年浩劫,使很多人对一系列问题不得不进行比较彻底的反思,包括四十多年来文学的得失。四人帮倒台后,我真是松了一口气。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写作了。我可以不说假话,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几篇东西就是在摆脱长期的捆绑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从这几篇小说里可以感觉出我的鸢飞鱼跃似的快乐。(《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
《受戒》发表这一年,汪曾祺正好60岁。他本人既感慨,又不无自嘲地说,花甲之年“执笔为文,不免有‘晚了’之感”,话虽这么说,终于盼来躬逢盛世的喜悦之情还是显而易见的。

1985年11月作家彭荆风摄于沈从文家中,从左至右:沈从文、汪曾祺、彭荆风的女儿彭鸽子
“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
“欢乐”似乎是汪曾祺赋予《受戒》的“意义”,他说:“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黄子平对此的描述是:“悲愤哀伤惶惑,‘愁云密布’的文学天空中蓦然出现了一抹‘亮色’,却不是主张‘走出伤痕’(其实是‘粉饰伤痕’)的批判家们所希望的那种‘亮色’。”(《汪曾祺的意义》)不能不说,《受戒》不仅是对“文革”文学“政治挂帅”“主题先行”的反叛,同时也构成对同时期方兴未艾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反拨。
汪曾祺强调“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无外乎是希望读者借助小说的精神力量,走出咀嚼苦难与悲情的迷思,平复过于哀伤的人心。汪曾祺曾对《受戒》作自我阐释:“我在动手写《受戒》时,就下决心尽可能把它写得美,写得健康,写得富有诗意!为什么要这样?是有感于当前一些青年人在爱情上的庸俗化、轻率、不忠贞,以及让爱情屈从于金钱的种种不健康思想及表现。若问《受戒》的主题思想,可以借用孔夫子对《诗经》的评价,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在《受戒》以后写的《大淖纪事》,重申了这一主题,这两篇小说,互为姊妹篇。”(陆建华:《魂萦梦绕故乡情——访作家汪曾祺》)
关于《受戒》发表后的影响,责任编辑李清泉的评价是:“《受戒》的出生是炫人眼目的,同行相见是喜形于色的,对于改变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是起积极作用的。”(李清泉:《关于〈受戒〉种种》)这个说法,有不少的评论文章为证,如《北京文学》1980年第12期发表了张同吾的评论《写吧,为了心灵——读短篇小说〈受戒〉》;《北京日报》1980年12月11日发表梁清濂《这样的小说需要吗?——读〈受戒〉有感》;12月12日,《文艺报》刊发唐挚(唐达成)的评论《赞〈受戒〉》,唐达成时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后来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他在文章中盛赞《受戒》,“作者纵横恣肆的笔,剥去了神的冷漠的庄严妙相,还给我们一个人的、温暖的情趣世界”,“这样一篇洋溢着诗情的作品的威力,绝不下于一篇宣扬无神论的檄文。”
《受戒》最终获得了《北京文学》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有人总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出现的一批引人关注的爱情小说,包括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汪曾祺的《受戒》,说《爱情的位置》是“提出爱情的问题”,《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写爱情的现实”,《受戒》则是“写爱情的永恒”,“汪曾祺写欢乐,姜是老的辣”(许谋清:《我感觉到的汪曾祺》)。
对《受戒》的赞誉与肯定,大多数方向与汪曾祺的自我阐述相近,并努力要在其中读出“人民性”“反封建”的意义,诸如“作者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劳动者身上的内在的性格力量和精神美,同时他也对劳动人民在旧社会身受的重重苦难表示深深的同情”(陆建华:《动人的风俗画》);“作者为两个小恋人选择受戒与庙宇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尤其具有诙谐的机智,无疑是对神的嘲弄,对人的自然情感与生活权利的肯定”(季红真:《传统的生活与文化铸造的性格》);“《受戒》中小和尚与村姑的爱情故事,是对禁锢人性的宗教的嘲弄,还是借描写半僧半俗的生活,表示对那种略带原始韵味的人情美的热衷呢?或藉此反衬城市那种物欲横流的丑恶世界?”(周荷初:《汪曾祺小说的美学评析》)
而对《受戒》的批判,则集中于“不真实”“没有教育作用”等评判。如“很难想象,在神权施威的旧中国,一个佛教徒可以无所顾忌,无所羁绊地和一个农村姑娘自由恋爱”,又如“小说冷落了‘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自然就是对人的社会特征、社会意义的冷落,这样的小说,势必要出现我在前面论及过的功能系统的失调,亦即认识作用和教育功能的短缺。”(马风:《从文学社会学角度看汪曾祺小说》)

1991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运河上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汪曾祺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一直想写在这小庵里所见到的生活,一直没有写”,1980年,正好60岁的汪曾祺打算写这么一篇小说时,他心里确实有着反复的犹豫、挣扎与自我辩论。作为一名20世纪40年代就崭露头角的作家,汪曾祺久经风霜,“中国的各种运动,我是全经历过的”,他知道他的写作冲动会触碰哪些禁区,他为自己准备了辩护词:“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他与朋友谈起过小说的大体构思,并进一步为自己辩护: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读者的感受也证明了这一点。据汪曾祺研究会会长陆建华的调查,群众对这篇小说的感受是“文章写得像,也写得美,读了使人欢喜,给人添劲长志”。为什么43年前的民间生活,会给20世纪80年代的一般读者这样的感受?
比如,让很多读者喜欢的“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在《受戒》中共有五处,第一处是两人初见,明海初来乍到,满怀羞涩,小英子却极为主动:“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第二处,小英子向明海打听受戒是怎么回事,结尾是:“我划船送你去。”“好!”第三处,小英子去看望正“散戒”的明海,问他疼不疼,哪时回去,结尾仍是:“我来接你!”“好!”第四处,小英子与明海在路上讨论善因寺的见闻,明海说他有可能被选做沙弥尾。小英子心中有了思量,“划了一气”,于是过渡到了第五段,也是最关键的一段对话: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声说:“要——!”
“快点划!”
人们心照不宣地记诵、默写着这些语句,觉得它们“美”“有劲”。在批评家眼里,这是“风俗画”的展现,是“小说散文化”带来的别致,是“诗意语言”制造的传神意境,是“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的延续。
不过,上述这些,还不能说是《受戒》对读者的全部吸引力所在。小说将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性心理,恰如其分地融化在通篇的诗化语言与风俗画之中。
“我的女儿曾经问我:‘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我说:‘写不出来了。’”
汪曾祺后来有一个颇富趣味的说法:“《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然而,在《受戒》发表的1980年,批评界还没有合适的批评话语来应对这篇如天外飞来的小说。“有什么意义”与“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是横亘在大多数人心头的疑问。《受戒》小说文体的实验与散文化、诗化的叙述后来才渐渐地被评论家和读者认同。
不过,即使是批评汪曾祺“轻浅”“缺乏社会性”的论者,也认同“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十七年’小说最热衷、最强调也最不容动摇的诸如主题的功利性,题材的重大性,人物的典型性,格调的时代性如此这般的创作原则和规范,在《受戒》这里,竟被汪曾祺来了一个彻底的逆反和颠倒”(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一次文学史视角的考察》)。这无异于对新时期小说家进行的一次小说观念的“受戒”,随后兴起的“寻根”浪潮、先锋小说、地域写作,似乎都能从汪曾祺那里寻到源头。
汪曾祺自己,也将《受戒》看作某种时代的产物。他后来说:“我的女儿曾经问我:‘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我说:‘写不出来了。’一个人写出某一篇作品,是外在的、内在的各种原因造成的。”

汪曾祺画作
对汪曾祺的评论“定位”的关键点到1988年才出现。这年9月底,《北京文学》在北京海运仓举办了“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林斤澜、陈世崇、黄子平、陈平原、李庆西、李国涛、李洁非、王干、孟悦、潘凯雄、蒋原伦等,老一辈的吴组缃也到会发言,称得上群贤毕至。在这次会上,李庆西提出的“士大夫气”得到了许多与会者的认同,而地域文化特色则认为相对次要,这意味着汪曾祺超越了“吴文化”或“里下河文化”的局限,被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情趣传人”的位置上。虽然有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这种提法容易忽略汪曾祺的西方文化背景及他对20世纪40年代学院写作的传承,但标签的威力是强大的,汪曾祺在之后的岁月里,被评论界和媒体反复地书写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种定位将汪曾祺与同时代作家有效地区分开来。
(作者:杨早,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