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道明评《拉丁美洲的精神》:理解拉美的文明与民主
来源:澎湃新闻 | 谭道明 2019年11月08日1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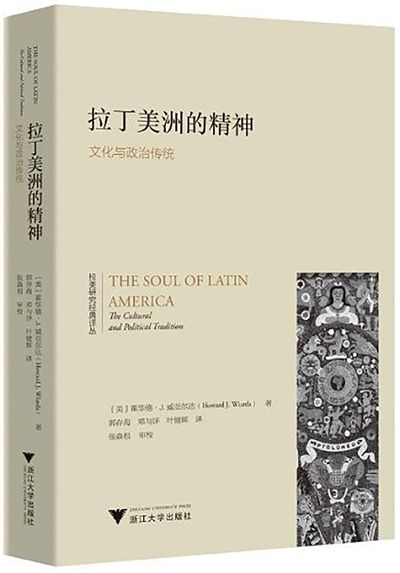
《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美]霍华德J.威亚尔达著,郭存海、邓与评、叶健辉译,张森根审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68页,78.00元
拉丁美洲的灵魂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半个多世纪后,西班牙王室主持了一场著名的神学辩论,辩题是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否有灵魂。道明会的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慷慨陈词,指出美洲的印第安人有自己的灵魂,应当被当作自由人看待,新大陆印第安人的文明完全可以与旧大陆古代人的文明相媲美。拉斯卡萨斯是他那个时代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者。他一生十四次远航于新、旧大陆之间,为捍卫印第安人的权益历难犯险,其作为印第安人保护者的鲜明立场永存于《西印度毁灭述略》等传世名作之中。
近五百年后,有一位来自北美的比较政治学家霍华德·J.威亚尔达教授(Howard J. Wiarda, 1939-2015),积四十多年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拉美地区工作、生活的经验,也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拉美的灵魂:文化与政治传统”(The Soul of Latin America: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中译本题为“拉美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威亚尔达教授似乎有意援引前述拉斯卡萨斯捍卫美洲人灵魂的典故,既有向先贤致敬之意,也许更想告诉自己的美国同胞:拉美的文明不同于北美,它的政治发展道路与北美也截然不同。
长期以来,美国人对拉美的认识是高高在上的,文明优越论的。站在拉美之外,戴着北美偏好的玫瑰色眼镜,导致美国人很难理解拉美。同为一位美国人,威亚尔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力图从拉美内部来理解拉美。用哈贝马斯商谈论的话说,这是一种参与者而非观察者的视角。
在威亚尔达的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几个关键词:文明、民主、理解。概而言之,只有理解了拉美有不同于北美的独特文明,才能更好地懂得拉美的民主将往何处去。它的未来是美式的自由民主,还是拉美人自己的(自由)民主?威亚尔达的答案是后者。他指出政治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并强调这种差异始于殖民之初,他称之为“奠基原则的差异”。
每一本重要的著作都深藏着作者的问题意识,作者试图透过该书与他所在的时代进行对话。如果将这本写于世纪之交的书置于其时代背景下,就会发现威亚尔达与拉斯卡萨斯一样,也参与了当时发生的一些重要辩论,尽管是以较为隐秘的方式。在我看来,威亚尔达通过这本书至少参与了两场大的辩论,其一是围绕大名鼎鼎的“文明冲突论”展开的,其二针对的是普遍流行的“水土不服论”。也许并非巧合的是,这两个辩论的主要对手都是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
塞缪尔·P.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的“冲突”
与文明冲突论有关的辩论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3)一文以及稍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一书引发的。至少在文明冲突论的话语体系内,亨廷顿将拉美文明排除在西方文明之外,认为它构成了一个新的、独立的文明形态,只不过是与“西方有紧密关系”而已。李慎之先生在1997年的一篇著名评论里指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背后隐含着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的理论范式。如果这个判断是准确的,那么,亨廷顿一边将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纳入到西方文明的“大篮子”里,另一边却将同样信仰天主教的拉美文明排斥在外,将拉美与其前宗主国视作两个完全独立的文明体系。且不论其他方面,就这一点而言,他的文明冲突论内部就存在明显的“冲突”。
如何看待亨廷顿理论内在悖论?其实,亨廷顿的文明类型区分并不纯粹是学理上的,而主要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让我们再次引用李慎之先生的上述评论。他在亨廷顿尚未写出《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2004)之前就犀利地指出:“明眼人一望而知,他最深刻、最核心的范式恰恰是他不愿意多谈的种族界限……亨廷顿把对美国前途的忧虑投射到全世界去了。”换言之,国际层面的所谓文明冲突,不过是美国国内种族问题的一个投射,后者才是亨廷顿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框架内,拉美文明只有被定位为一种非西方文明,限制外来移民以保持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在美国的主导性,才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这些移民很大一部分来自墨西哥、古巴和中美洲等天主教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执意要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之墙的特朗普不过是做了亨廷顿保守主义思想的奴隶。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预设了西方文明注定主导世界的文明优越论。一旦预设了这样的立场,美国人是很难理解拉美的。这样的立场也正是威亚尔达通过《拉丁美洲的精神》这本书所要严厉批评的。尽管他与亨廷顿一样,并不严格区分“文明”与“文化”,而是几乎将二者混用。威亚尔达指出,拉丁美洲与它的宗主国西班牙、葡萄牙共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伊比利亚-拉丁美洲文明。这个文明应该被定位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支脉,就像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无论影响有多大,也不过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支脉一样。在我看来,威亚尔达这本书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为拉美文明重新找回自己的根基,同时也为伊比利亚文明找到了更结实的树干。在威亚尔达的笔下,伊比利亚与拉丁美洲原本同气连枝,自成一体。
威亚尔达指出,伊比利亚-拉丁美洲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诸个分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法兰西文明、德意志文明——分享一个共同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希腊、罗马、《圣经》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不同的是,伊比利亚半岛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后,变得比罗马还要罗马化。事实上,拉美地区殖民和独立以来的很多政治制度、文化传统都可以从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中找到根源。当查理五世幸运地得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时,他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统治这个身躯庞大的怪物。我们知道,直到十八世纪末北美独立建国,适用于大国治理的现代联邦制才被创制出来。因此,查理五世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唯一熟悉和了解的就是罗马帝国的那一套自上而下的、“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并且,不仅统治方式借鉴自罗马,封建大地产制度也来自罗马。罗马帝国曾将大量土地分给了取得胜利的军团,这些人之后就住在西班牙。这是伊比利亚半岛封建大地产制度的基础,并在其后的拉美殖民地大行其道。另外,根据威亚尔达的考证,在拉美盛行至今的侍从主义(clientelismo)和庇护主义(patronage),其哲学基础也是来自罗马时期,是从出生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罗马政治思想家塞内加(Seneca,约公元前4年-65年)的“恩惠”(gift)概念中演化而来的。此外,考迪罗(Caudillo)通常被认为是只有拉美这片大地上才会出现的特产,但威亚尔达指出,其实它还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考迪罗主义分别从西哥特人和摩尔人的统治中孕育而来。
如果说,伊比利亚-拉丁美洲文明与西方其他文明的共性来自罗马帝国的遗产,那么,这个文明的独特性就来自它所经历的摩尔人近八百年的统治和几乎同样长时间的再征服运动。被称作天主教双王的伊莎贝拉一世和斐迪南二世将再征服运动的胜利看作是基督徒对穆斯林人圣战的胜利,因而对天主教十分虔诚。当路德在萨克森、亨利八世在伦敦、加尔文在日内瓦发起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运动之时,在伊比利亚半岛,天主教双王和哈布斯堡家族的诸位君主都成了罗马天主教的忠实捍卫者,并以极为严厉的宗教裁判所来捍卫天主教的信仰。
用墨西哥桂冠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的话说:“美国人是宗教改革的子孙,诞生于现代世界;我们墨西哥人是西班牙帝国的后裔,它所捍卫的是反宗教改革——一场反对新现代性却以失败告终的运动。”智利社会学家克劳迪奥·韦利兹(Claudio Véliz,1930-)借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的著名比喻,说西班牙人就像刺猬,沉迷于唯一的一件大事——反宗教改革,而英国人像狐狸,思想开放,善于变通,擅长很多事情。他还不忘增加一句话:“拉美是一头刺猬,却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不顾一切地努力变成一只狐狸。”
由此,当西方其他国家开始进入现代世界、开启“人的国”之时,伊比利亚以及美洲殖民地仍处于“神的国”。正是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拉美大陆与伊比利亚半岛一起被“冻结”在了中世纪。于是,拉美大陆也复制了它的宗主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天主教的、保守的、正统的、新经院神学的、有机主义的、法团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正是在新大陆,行将就木的中世纪封建欧洲被满血复活了,并且生命力强劲,一直活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与亨廷顿等人强调拉丁美洲文明与伊比利亚文明乃至西方文明之间的断裂不同,威亚尔达强调二者之间的连续性。在他看来,1492年不是断裂之年,而是延续之年。这一年是伊比利亚文明与拉丁美洲文明的连接点,一端是再征服的结束,另一端是新大陆的“发现”。这样,横亘在伊比利亚半岛与拉丁美洲历史之间的旧分界线被移除了,二者不可分割、无缝融入在一起。拉美,特别是在其初期,实际上是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延伸。在这本书里,通过梳理伊比利亚和拉美的政治文化发展史并将其与北美进行比较研究,伊比利亚-拉丁美洲文明就在西方文明的内部隐然构成了与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对峙。
“水土不服”的拉美民主?
那么,究竟何为拉美的灵魂或精神?一言以蔽之,伊比利亚-拉丁美洲文明最初并在很长时间内是法团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以圣托马斯-苏亚雷斯等人的思想为圭臬。而美国则自被殖民之日起就奉行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信奉胡克-洛克-麦迪逊等人的思想。独立以后,拉美的政治文化又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美式的自由共和主义、卢梭的民主共和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域外政治思潮都以不同方式影响了拉美的民主政治走向。
在我看来,除了隐秘地参与了文明冲突论的辩论外,威亚尔达还通过《拉丁美洲的精神》这本书参与了另外一场重要辩论。实际上,这场辩论与拉美的关系更加密切。长期以来,流传着一个看法:民主政治在拉美地区水土不服。并且,这种看法在中国至今依然有大批拥趸,但中国人的看法可能主要还是受到了亨廷顿的影响。亨廷顿在他1968年的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解释为什么普力夺社会主导了十九世纪的拉丁美洲时,说道:“独立战争造成了制度上的真空——用莫尔斯的话说,独立战争将国家‘斩首’,当地欧洲人后裔就试图照抄(Copying)美国的和共和制法国的宪法安排来填补这个真空。然而,在一个高度寡头的和封建的社会里,这些宪法无法生根。”在该书同一章的另一处,亨廷顿又重复了这个观点。
与亨廷顿类似的是,威亚尔达并非完全拒斥“水土不服论”。如果通读了《拉丁美洲的精神》就会发现,至少在十九世纪的拉美,“水土不服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如同南橘北枳一样,民主政治植根的土壤也不是无条件的,它有一定程度的“水土”要求。这一点,很多思想家有过很精辟的讨论。比如,休谟在《人性论》中写道“风俗”,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讲到“法的精神”,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提出了“民情”。
正如威亚尔达在本书中所讨论的,拉美地区有很浓厚的精英主义和法团主义的政治传统,这些传统更容易与更晚进入拉美的思潮如卢梭的民主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结合在一起。相反,它更难与基于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洛克式自由主义传统相融合。约翰·基恩用“考迪罗的民主”形容民主在十九世纪的拉美徒有其表。吉列尔莫·奥唐奈说它是委任式的民主,因为有民主而无制衡。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由于国家能力孱弱,拉美地区的民主始终是脆弱的。根据彼得·史密斯的研究,拉美的民主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生根,几经曲折,到二十世纪末才成为地区主要的治理形式。然而,即使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拉美的民主也是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有选举民主而少公民自由。不管在前面加了什么样的形容词,谁都无法否认,拉美的民主与美式的自由民主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但是,与亨廷顿等人不同,威亚尔达并不认为拉美人在独立之初是“照抄照搬”了美国的宪法或法国的《人权宣言》。他没有把拉美的建国精英看成是一群只会照抄照搬别人现成东西的傻瓜。恰恰相反,这些克里奥尔人精英在建章立制之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政治智慧。威亚尔达指出:“拉美的开国元勋们没有幼稚到会实行那些需要美国援助才得以实施的宪法,这既不切实际,也难以实施。相反,撰写新宪法的克里奥尔人都是饱学之士,他们成熟老到的政治经验并不亚于美国的制宪先贤。但是,他们当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美国的情况大相径庭,因而他们只能作出相应的决策。实际上,他们起草的宪法都非常吸引人,有一定的妥协性——并非不切实际——而且非常契合拉美的现实。”
威亚尔达的这个看法并非凭空想象,可以从拉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那里得到印证。玻利瓦尔被誉为“南美的华盛顿”,有丰富的欧美游历经验。在领导独立革命的斗争中,他逐渐认识到应该根据拉美的客观现实来选择本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在《在安格斯图拉国民议会上的演说》(1819)这篇经典文献中,他反对委内瑞拉宪法照搬美国的联邦制:“在我的思想上,绝对没有把美洲英语国家与西班牙语美洲国家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国家的形势和本质混同起来。”他接着说:“永远不要忘记,一个政府的优越性不在于它的理论,不在于它的形式,也不在于它的机构,而在于它适合于所在国家的性质和特点。”
威亚尔达进而指出,在十九世纪初的独立建国时期,拉美国家的宪法就与美国模式有了很大差别。比如,拉美新宪法强调国家统一,将既有的托马斯主义旧思想与卢梭的而非洛克的新思想结合起来。建国之父们担心无政府状态甚于忧虑暴政,在宪法中赋予总统以无上权力——相当于宪政独裁者,立法权和司法权遭到边缘化。他们赋予国家元首紧急状态权,他有权解散国会,关停最高法院,中止基本权利,召集军队,可以通过行政法令统治。这些权力都远非美国历任总统所可企及。还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拉美立宪者赋予军队以维持秩序和安全的特殊使命,军队介入甚至推翻腐败无能的文官政府在很多情况下是依宪干政,并非全无宪法依据。的确,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巴西要到1891年宪法——都采纳了美式共和立宪主义的外观,一方面,诚如威亚尔达所言,他们是为了追随和顺应国际潮流,尽快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也是因为在当时并没有更好的制度安排可供选择,欧洲大陆那时还是南北美洲的建国之父们共同拒斥的君主制的天下。
二十世纪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拉美仍在不停探索自己的民主模式,有过成功,更有失败。就民主性而言,拉美各国的现行宪法比美国宪法要更加民主。罗伯特·达尔早就著书指出:从很多方面来看,美国宪法都是不民主的。特朗普曾将选举人团制度抨击为美国民主的灾难,但正是这个不民主的安排将其送上了总统的宝座。拉美一些国家在军政府时期也搞过间接选举,巴西和阿根廷还实行过选举人团制度,但直选总统始终是整个地区的主流。并且,大多数拉美国家要求当选总统所需普选票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它代表着最低限度的民主合法性,因而通常需要两轮选举才能决出胜负。比如,阿根廷宪法规定,总统当选的法定票数门槛是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或者百分之四十以上但超过第二位者百分之十以上。费尔南德斯正是在首轮选举中获得了百分之四十七的选票,从而无须第二轮就直接当选总统。在选举制度方面,正如达尔所观察到的,拉美地区主要国家拒绝了美式的单一选区代表制,转而采纳欧陆国家的比例代表制。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照搬美国做法?一个重要原因是,单一选区代表制导致赢家通吃,非主流民意无法获得有效代表,而比例代表制可以让尽可能多的政治力量获得代表,显然更加民主。然而,在巴西等国,比例代表制的盛行带来了政党制度的高度碎片化,导致在任总统往往无法得到国会的强力支持。自1985年军政府还政于民以来,巴西已经成功弹劾过两位总统——科洛尔和罗塞夫。反观美国,迄今为止尚未成功弹劾过一位总统,尼克松自请辞职,约翰逊和克林顿逃过此劫。胡安·林茨等政治学家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指出,拉美地区政治危机频发和制度崩溃,与总统制与比例代表制的这种组合不无关系。
国家构建的先天不足
威亚尔达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拉美与北美属于西方文明的两个不同支脉,二者在政治文化上有重要差异,其结果,拉美各国的民主形式不大可能全盘照搬美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美国人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是幸运儿。他们“生而自由”,不论地理还是民情,都远好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拉美大陆。拉美人,还有其他地区的人们,远远没有美国人这样的好运气。如果将北美与拉美之间的差距,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差距,置于不同文明的背景下来考察,就会给予拉美更多的同情理解。就此而言,威亚尔达的《拉丁美洲的精神》与彼得·史密斯的《论拉美的民主》,尽管视角各异,但殊途同归,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拉美的民主不同于美式的民主。由于成书较早,特别是采取文化进路等原因,威亚尔达对拉美民主未来的看法显得更悲观一些。
然而,威亚尔达也不失清醒之处。他既强调文化与政治传统的重要性,又不将其拔高到一种全能的解释地位。一方面,威亚尔达认识到,他的整体性视角只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必然遮蔽了拉美各地区间、各国间潜在的重要差异。过于抽象,必然失真。如果我们将他描述的拉美的“灵魂”生搬硬套到特定一个拉美国家那里,或者由此认为拉美人完全无法接纳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无疑过于胶柱鼓瑟,同样也不能很好地理解现实世界之中活生生的拉美和活生生的拉美人。另一方面,威亚尔达竭力避免自己的分析掉入文化决定论,进而避免得出拉美政治文化传统完全不适合民主政治这样的论断。因为在文化之外,还存在着制度、经济、阶级等重要因素。并且,这些因素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构成一个互动的、联系的整体。
威亚尔达分析视角的开放性也为我们考察拉美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拉美民主政治的艰难曲折,其原因非常复杂。仅就历史遗产而言,除了威亚尔达所谈到的政治文化的伊比利亚传统外,国家构建的先天不足亦值得高度重视。任剑涛曾撰文指出,现代国家建构必须递进式地经历三个关键时刻,才能成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这三个时刻分别是马基雅维利时刻、霍布斯时刻和洛克时刻,对应的是国家必须统一、国家必须强大和国家必须规范这三个不断向上的阶段。西班牙完成再征服运动以后,于欧洲诸国中率先进入了马基雅维利时刻,统一的西班牙开始形成。西班牙著名哲学家奥尔特加就曾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不过是一个意大利人在称赞两个西班牙人。这两个西班牙人,也是马基雅维利眼中“新君主”的样板,一个是与伊莎贝拉一世共治的斐迪南二世,另一个是西班牙裔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切萨雷·博吉亚。
在国家构建方面,如果说英格兰是先发先至,法兰西是先发后至,那么,西班牙则属于先发迟滞。再征服胜利和“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的国家构建就步履蹒跚,踌躇不前了。用佩里·安德森的话说:“主宰这个庞大帝国的却是一个有累卵之危的乌合之邦,只是由于君主的联姻才合并起来。……其内部关系之松散和杂乱,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的确,天主教双王的绝对主义仅止步于卡斯蒂利亚,就连阿拉贡都未能实现有效的中央集权。近年来,加泰罗尼亚人多次闹独立,从西班牙统一伊始的国家构建的松散性之中,可以窥得根源。而导致这种松散性的原因,竟然与新大陆有关。佩里·安德森如是说:“正是新世界重新填满了它的金库,延续了它的四分五裂。……秘鲁的俯首贴耳补偿了阿拉贡的桀骜不驯。”
威亚尔达在本书中强调的是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文化在新大陆的延续性。事实上,西班牙在国家构建上的松散性,不仅在殖民时期,即使在拉美独立后,也几乎原封不动地得到了地区各国的继承。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时,发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治理方式是建立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之上的政府集权,而波旁王朝的法国却是自上而下的、完全不存在地方自治的行政集权。他的这个观察用来说明拉美地区的治理模式也非常恰切。在被殖民的三个世纪里,拉美地区一直实行宗主国自上而下的行政集权,地方自治的实践很早就湮灭不存。独立之初,该地区的社会性质实际上是半封建半专制的,或者说半封建主义半绝对主义的。国家构建被卡在了马基雅维利时刻与霍布斯时刻之间,进退失据,动弹不得。拉美独立后的宪法强调国家统一和行政集权,此后更是大大小小的考迪罗你方唱罢我登场,客观上体现了从马基雅维利时刻过渡到霍布斯时刻的历史要求。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孔德的实证主义在拉美地区盛行。实证主义的口号是“秩序与进步”,强调实证精神,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在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终于将拉美从中世纪推入到了现代国家。约瑟夫·梅尔、阿尔夫雷德·韦瑟黑德等学者将处于两次大战之间的1930年代称作拉美地区的“中世纪的黄昏”,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精神至此终结。然而,拉美地区又碰到了坏运气——再一次。此后历经二战和冷战,在美苏对峙之下,不存在从霍布斯时刻顺利走向洛克时刻的政治空间。自1930年代到1980年代近半个世纪里,军政府与民粹主义政权轮流主导了拉美政坛,旧思潮余威犹在,各色新思潮又快速涌入,使这个地区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活着的博物馆”,一个左右撕裂的“冲突社会”。直到19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它被亨廷顿称作“一个势不可挡的天主教浪潮”,拉美地区才最终走向现代国家构建的洛克时刻。根据彼得·史密斯的分析,到二十世纪末,选举民主在拉美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确立。但是,洛克式的理想,“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在拉美地区还是一项有待完成的谋划。自2014年以来,从巴西的“洗车行动”开始,整个地区掀起了规模和力度完全不亚于中国的反腐败运动,可以看作是国家规范建设——提高国家能力和推进民主法治——的一次重要努力。
缺席的土著主义和民粹主义
总体而言,《拉丁美洲的精神》这本书从整体的视角来理解伊比利亚-拉丁美洲文明,由此考察拉美的民主会走向何处,是颇有说服力的。遗憾的是,威亚尔达在考察拉美的政治文化传统时,竟然遗漏了土著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一头一尾”。威亚尔达对阿兹特克、印加、玛雅等土著文明对今天的拉美民主政治有何影响,几乎未置一词。问题在于,如果不理解由土著文化孕育的“美好生活”的发展理念,就难以理解拉美人近乎偏执地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也难以理解亚马逊雨林发生大火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何以遭遇了几乎来自整个地区的批评。从这个角度看,威亚尔达试图赋予的拉丁美洲的灵魂还是伊比利亚式的,跟新大陆的土著主义关系不大。由此,他在批评北美同胞看待拉美存在美式种族中心主义之时,不免遭遇伊比利亚中心主义或西班牙主义之讥。
此外,他对二十世纪以来影响拉美政治至深且巨的民粹主义,也保持了有意或无意的沉默。从1910年代阿根廷伊里戈延的早期民粹主义,到1940-70年代以庇隆为代表的经典民粹主义,再到1980-90年代的新自由民粹主义,以及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新左翼民粹主义,乃至近年来的博索纳罗的右翼民粹主义,拉美地区的民粹主义浪潮可谓声势浩大,绵延不绝。阿根廷的费尔南德斯已经击败马克里,成功当选阿根廷新总统,庇隆主义在阿根廷卷土重来。作为一本书写拉美政治文化传统的专著,民粹主义居然缺席,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如果他没有去世,并且愿意补写民粹主义这个章节,我能想象得出会有多么精彩!现在,这个工作只能由后辈学人赓续前贤了。
最后,还需指出,尽管威亚尔达的这本书是写给美国人看的,但它对于中国人理解拉美同样大有裨益。长期以来,由于距离遥远、文化异质,中国人对拉美的误读之多,不下于美国人,甚至犹有过之。很多人对拉美只有负面印象,比如强人政治、中等收入陷阱、非法移民、贫民窟、贩毒和革命。他们看不到拉美近年来在民主法治、环境保护、反腐败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更有少数人并不真正尊重拉美的政治发展道路,认为拉美既然学不好美式民主,就应该向它们输出其他模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这些成见和偏见与威亚尔达所要批评的美国人的看法相隔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更应该好好看一看《拉丁美洲的精神》这本书。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