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欧美版中国文学史之比较 ——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
来源:文汇报 | 徐志啸 2019年12月02日08: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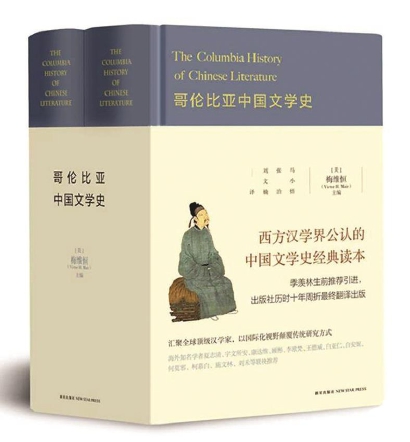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美]梅维恒 主编 马小悟 张治 刘文楠 译
新星出版社 出版
世界范围的汉学研究,三个国家和地区堪称重镇——日本、欧洲、美国。从时间上来说,日本毫无疑问是领先者,欧洲则属于后继者,包括法国、英国、德国等,美国自然崛起得最晚;但从整体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来看,三个重镇在不同历史阶段各具不同特点,可谓各有千秋、难分轩轾。作为汉学研究分支之一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日本早在20世纪初叶即已问世多部相关著作,欧美虽然时间上后于日本,却后来居上,21世纪初的欧美推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超百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这就是《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均以《哥》本《剑》本简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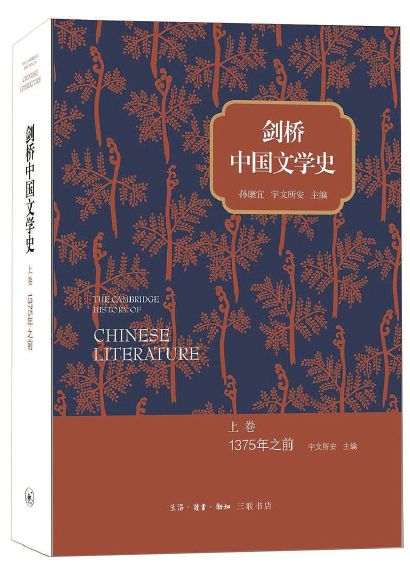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下册)[美]孙康宜 宇文所安 主编 刘倩等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
这两部文学史的英文版和中文版问世时间略有交叉——《哥》本英语版出版于2001年的美国,《剑》本英语版出版于2010年的英国,两者相距近十年;但中文译本《剑》本却比《哥》本早了三年,分别是2013年和2016年。
两部文学史编撰者的主体基本是美国学者:《哥》本主编,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梅维恒,参与编撰者清一色的美国学者;《剑》本,上卷主编: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欧文(宇文所安),下卷主编: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参与编撰者大多是美国学者,有少数英国学者。
整体框架设计有差异:试图超越文体分类,亦或跳脱朝代分期
两部欧美版中国文学史,都系统叙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同中也有异。
首先是整体框架的设计与编排。《剑》本主编在接受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撰任务时,有一个明确的意念,反对将文学史写成以文体分类的史著,而偏偏《哥》本正是一部以文体分类的文学史——整部书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分类。在这一点上,似乎《剑》本就是冲着《哥》本来的。《剑》本主编认为,按文体分类撰写,会割裂各类文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不出作家能从事多种文体创作的综合风格特点。为此,《剑》本主编采取整体性文化溶入文学史的方法,即努力写成文化文学史,不按往常文学史的模式围绕作家个体展开叙述,从而成为一部非同一般文体类的文学史。
其次是令文学史研究者历来头痛的分期问题。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摆脱历史朝代的传统束缚。作为一部文学史著,固然不能脱离历史发展演变的轨迹,但毕竟文学史是围绕文学展开的历史,不是纯历史著作,如果完全围着历史朝代转,没有或看不出文学本身的发展线索,那就谈不上真正的文学史了。为此,两书主编都力图改变完全按历史朝代顺序叙述的方式。但实际做法上,《哥》本兼取年代与主题,不严格按历史朝代为序,也不完全弃朝代于不顾,在全景式的年代框架下,作主题式的探索。而《剑》本则打破传统惯例,努力按文学自身发展的固有线索阐发,于是,先秦与西汉紧连,西汉与东汉分离,西晋与东晋分隔,东晋与南北朝、初唐相连,晚唐与北宋前期挂钩,明代的1375年作为上、下两卷的分隔年等等,打破了传统文学史的历史朝代一统格局。
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有一个很重要而往往被中国学者忽略的问题,即,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对象和所涵盖的实际范围,究竟是哪些地域和人群?也即:今天所谓的“中国”文学史,这个“中国”指的范围是什么?是否包括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是否包括港澳台地区?是否包括海外的华人华侨?以今天流传于市面上的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看,虽然书名皆称为“中国文学史”,实际内涵却并不包含所有的中国人,书中述及的多是汉族人用汉语书写和创作的文学史,很少或几乎不包括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写和创作的其他55个民族的文学,也很少或几乎不涉及港澳台地区文学,更遑论海外华人或华侨的文学创作了(后者主要指现当代文学)。《哥》本和《剑》本两部中国文学史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文学史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应该包含汉族群体和少数民族群体,以及香港、澳门、台湾乃至海外的华人群体,这样做,才符合“中国文学史”的本质定义。
对汉字和汉语根本性质的牢固把握,是准确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学的一道坚实基础,这是两部欧美文学史都十分重视的一环。两书都在全书的开头,开宗明义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比较起来,《哥》本在这方面似乎用力更多,花费的文字也多,阐述的面也广,该书第一编《基础》中,专设了《语言和文字》一章,从多角度予以详尽阐述,内容包括汉字简史、汉字的特性、白话与文言、汉字的审美特征、汉字对文学的意蕴等。作为专述中国文学及其发展史的史著,开篇即对汉语文字的起源、发展、特性,作专门阐述与概括,这样的做法,至少在中国国内的文学史著作中相当罕见,编撰者特别说明并点出了汉字的特点,以及它与西方字母文字的差异,这甚有助于西方读者对东方中国用汉字书写文学的整体认识和切实把握,从而真正体会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异与特质。
力求打通古今,有意识地作中西比较,各有独到创见
两部文学史的立足点和视野确有差异,写法上也不尽一致,但在这些不同中,我们仍可清晰看到它们的异中之同——这同,即两书的编撰者都有自己独到发挥的地方,或谓独创见解,其所论所见不乏精彩之处,这些精彩论断,体现了两书编撰者的潜心研究成果,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参考。
例如,将中国文学发展史历来的划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完全打通,使之融会贯通,汇成一统,浑然一体,这是两部文学史共同的特色,便于对中国文学生生不息、沿袭不断特征的充分展示,也有利于传统与古代文学的互为回应、互相联系、前后对照,俾助于认识古今演变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
《剑》本特别提出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与保存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作品在文坛上的知名度,从而波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受众面和影响力。这当中,早期阶段是后世的评判与价值取向起主要作用,而后期阶段则大多借助于印刷文化的传播手段,这是非常重要的传播工具,在宋元及其后尤显突出,甚至直接决定了作品与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如何看待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动机,《哥》本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文章与官吏的紧密关系可谓贯穿文学史的始终。作家的创作往往都在直接间接地为国家的道德和政治需要服务,真正的所谓“纯文学”或“为文学而文学”观念的形成,大约要在佛教美学来临之际,也即魏晋及其后时期,文学的非实用主义才开始得到系统的欣赏、审视和提倡,文学才真正进入了自觉意识时代。这个看法,应该说比较符合中国的历史和时代的客观现实。
《剑》本有《文化唐朝》一章,不仅别出心裁地将初唐剔出(划归南朝),将中、盛、晚唐合为一体,还将北宋的开朝60年也划进唐朝,这在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史中是不可思议的。对此,编撰者作了如此解释:“北宋文学特有的‘宋代’风格,其形成阶段并没有出现在王朝建立的960年,或是接近于这个时间的任何时段。换言之,北宋,是王朝更迭与文学发展时间上明显不同步的一例,推翻了时代与文学二者在中国文学史上携手并进的这一普遍假设。新王朝的确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但直到1020至1030年代,这一新风格才开始出现,此时距北宋建立几乎已有两代人的时间之久。”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论断,点及了该书主编所主张的意图——文学史应打破历史朝代的传统框架,按文学本身发展的轨迹划分阶段,而北宋正是最有代表性的个案。
两书都可见到有意识作中西文学比较的案例,虽然只点到即止,没作展开性论述,但这做法本身,对于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无疑是非常有启发作用的。如谈到《诗经》“大雅”时,与古希腊荷马史诗作比较;认为明代中叶的文学不比欧洲文艺复兴逊色;将《金瓶梅》手抄本流传与定稿过程和《圣经》及莎士比亚作品的定本类比;将中国古代传统的散文文体风格与古希腊罗马的散文文体风格作对比等等。
瑕不掩瑜,呼吁双向的东西方文化影响
两部欧美版中国文学史虽说在海外汉学领域具有相当影响力,但认真阅读的话,发现遗憾之处也难以避免,这是作为中国读者必须正视的。
《剑》本由于淡化了文类,一些在文学史上出现的特别具有特色的文类,有的便难以觅得其应有的踪影。比如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出现、且在后世仍有相当影响、但历来被文学史界所重视不够的文类——赋,《剑》本对它的描述和评价,出现了前后叙述矛盾、文体特征判断失误的现象。该书第一章在谈到赋时说,汉代盛行的诗歌类型是赋,西汉的赋涵盖了诗歌的所有形式和主题,而第三、第四两章的说法却不一样,认为赋属于散文,或属于特别文体类。很显然,三章的三位编撰者对赋文体的看法和认识判断不一致,导致了同一部文学史中出现对某一特定文类文体特性及其归类的分歧。究实说,赋这个文体,虽然源之于诗,但毕竟与诗和辞有区别。按今天的文体分类标准看,有点类似现代的散文诗。
《哥》本第三、四、五章,分别述及早期中国的哲学与文学、“十三经”、《诗经》和古代中国的说教。这三部分内容,明显有交叉重合处:早期中国的哲学和文学,其实已包含了“十三经”的部分“经”,自然包括了《诗经》;而古代中国的说教,实际与早期中国的哲学与文学,以及“十三经”,都有关系,不能单说《诗经》与古代中国说教有关;而“十三经”中除《诗经》以外的其他不少“经”,其实与古代中国的说教都有关系。这三章内容,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割,无论时间顺序上,还是内容联系方面,现在这样将其分为割裂的三章,逻辑上明显混乱,内容条理划分也不清晰。还有,《哥》本下卷第六编第四十四章,专辟了“经学”一章,其实“经学”并不属于文学的范畴,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或可划归史学,如为了说明中国儒家经典与文学的关系,可将这部分内容与第三、四、五章融合打通,重新组合,分章阐述,统合说明,或许会更好些。
因为是集体的编著,无论《哥》本还是《剑》本,都比较明显地暴露了体例上的不统一和不规范,这无疑给两书各自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带来了遗憾。比如两书的目录部分,各章的标题写法不统一,大多循着历史朝代顺序,有些却标上了世纪,有的还按年代标题。尤为甚者,《剑》本上卷第三章,章标题是“从东晋到初唐”,而章以下的节标题,居然全部是“世纪”,完全不中不西、不伦不类。《剑》本章节标题列出的作家和作品,也多有失误,如曹操、建安七子居然未入章节标题,杜笃和冯衍却入了,而《文心雕龙》《诗品》这样重要的文学理论代表著作,竟然章节的标题中未见,这在中国学者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绝对不可能见到。
话再回到开头部分。实事求是说,海外汉学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学史,确实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与借鉴作用。但这些年来,学界不免有些西化的倾向,过分地渲染西方。笔者赞赏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的态度,她曾说,不能只注意西方理论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新视角,而很少想到中国的文学研究成果也能为西方批评界带来新的展望;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文化常常被忽略为“他者”——这是必须改变的不正常现象。这话说得非常好。我们在阅读和比较《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两书时,也应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