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访谈|意大利翻译家李莎:它又是陌生,又是亲切
来源:中国作家网 | 王杨 2020年03月20日09:09
中国,对我来说,是最难解读的秘密。
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世界”,从金碧辉煌的大都市到便于侠隐的深洞,经过沙漠、圣山、原野、大海。有人怀疑它、有人迷恋它、有人渴望抓住它,可是它神秘地、矛盾地以晃动的身影时有时无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它多么庞大,与我所熟悉的、令我放心的西方世界多么不同。每一处、每一地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且用它的独特性呈现在我眼前。
解读中国是很艰难的任务,因为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中国同时存在,我们必须经过很多深层的理解阶段才能看出哪个是它的真相。同时存在着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中国人眼里的中国、中国想给外界所显示的形象等等。它能同时肯定又否定我脑子里所有的文化定型,在叙事中强力地显现真实的、虚假的传奇使我越来越眼花缭乱,一直到一天我终于觉悟了:停止判断对错,开始观察、细听、触摸、欣赏。
30年前,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毕业的意大利本科生帕特里西亚•里贝拉蒂(Patrizia Liberati)来到中国。如今,她更为人所熟知、也更愿意别人称呼她的名字是李莎。作为翻译了多部中国文学作品的汉学家,在2014年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李莎用开头这段话来回忆和表达自己初到中国的感受。
来中国之前,李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读中文,学习汉字和中国语言文学。大学三年级,她和同学们开始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学者赵毅衡曾给他们授课,推荐了王安忆的“三恋”,李莎读的王安忆第一部作品就是英译本《小城之恋》。
1990年,李莎本科毕业来到中国。之后一年,在欧共体与中国企业家协会合作的MBA项目中担任培训负责人。1991-1992年,李莎任意大利驻华使馆科技参赞私人秘书,同时到使馆文化处帮忙;1995年,她正式进入使馆文化处工作;现任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文学出版项目负责人。除了组织和参与中、意文学交流等使馆日常工作之外,李莎最重要的身份就是译者,翻译推介了莫言、刘震云、贾平凹等中国作家的多部作品,并从2014年开始负责《人民文学》杂志意大利文版《汉字》的选稿和翻译工作。2019年9月,为录制系列短片《文学的力量》,中国作家网记者独家专访了李莎。今年2月,记者就访谈中的部分细节与李莎做了沟通、订正,得知李莎年初时回到罗马照顾生病的母亲,她还对记者表达了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和对中国朋友的关切和祝福。3月7日,李莎按照之前的行程安排回到北京,需在家中隔离到22日。她也期盼意大利能尽快控制住疫情,恢复正常生活。

意大利翻译家李莎接受中国作家网采访
“它又是陌生,又是亲切”
读了王安忆的“三恋”之后,李莎又看了王朔的《动物凶猛》等作品。到中国后,因为参与一个文学项目,李莎采访了王安忆,还写了一篇小论文,同时也认识了王朔。她开始觉得中国文学非常有意思,想多读一些,但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要做翻译。一段时间后,李莎觉得光靠工作没法提高自己,需要回到学校,于是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从1998年到2001年,看剧本、分析剧本,又读了一个硕士学位。毕业后,用李莎自己的话说:“就继续看书,但还是没有想过要翻译书。”
有一次,李莎和意大利翻译家米塔(Maria Rita Masci)一起逛美术馆后街的三联书店,被一本书的封面吸引——莫言的《檀香刑》,米塔买下这本书送给她。李莎说,一般外国学生读中国文学作品,10页或15页之后才能被作品抓住,一是因为语言问题,一是确实很多作品节奏比较慢。“但《檀香刑》我刚看了两页,就觉得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我最后就放不下了,连续看完。”她把阅读感受告诉米塔后,曾经翻译过凌叔华、阿城、残雪、苏童、余华、白先勇、刘索拉、王安忆、刘恒以及韩少功、莫言和徐星等作家作品的米塔鼓励李莎把这本书翻译成意大利语。李莎不敢,米塔就帮她写了一个内容梗概,说服出版社为什么要翻译和出版这部书,最终,意大利第二大出版社艾因奥蒂(Einaudi)同意了这个出版计划。2002年,李莎一边准备迎接双胞胎女儿的出生,一边开始了她的翻译生涯,《檀香刑》成了她翻译的第一部中文作品。
由此,李莎的翻译热情日益高涨。她又陆续翻译了莫言的《生死疲劳》《四十一炮》以及一部自传性质的中篇《变》。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李莎又应出版社的要求翻译了莫言的《蛙》。采访中李莎告诉记者,她和朋友合译了一部莫言的“鬼故事集”,即将出版。
“中国离意大利那么远,又是当时不太了解、比较神秘的国家,文学是非常重要的帮助你沟通的一个方法。”“一个外国作家为什么吸引你基本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他跟你相似,一个是因为他离你远。”李莎认为,莫言对这一点把握得非常准确和成功。“你看他的东西,觉得这个人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人;然后突然他做了一个事儿,我又没想到他怎么能往那个方向走,你的好奇心、注意力都被吸引了”,“因为它又是陌生,又是亲切,最重要就是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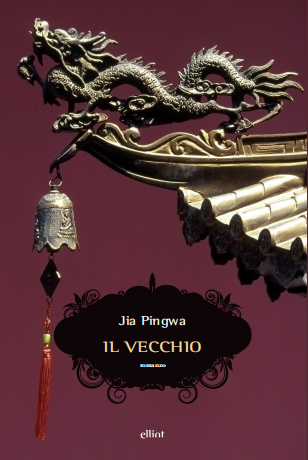
李莎翻译的贾平凹《老生》意文版
除了莫言的作品之外,李莎的译作还包括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贾平凹的《老生》、韩少功《马桥词典》(与米塔合作翻译)以及孟京辉话剧作品《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台词意文版)等。
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李莎也试图找到解读中国当代文学的关键词,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的论文中,她用三个词来形容中国和当代中国文学——痛苦、韧性、重生。从自己的阅读和翻译经验出发,李莎认为,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直至90年代,描写痛苦以疗愈创伤成为了一批中国作家的创作目标。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岁月之后,中国人以独有的韧性对付苦难、找回自己、确定独立的角色。虽然也受到了世界文学潮流的影响,吸收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和表现方式,但中国作家也在寻找自己独特的文学样式和风格。实验、先锋的90年代之后,同时伴随着传统文化的重启,中国当代文学也在世界文坛初步亮相。进入21世纪,网络的普及让更多人获得了想象和沉思的机会,也为人们的表达和交流提供了平台;而中国自身的进步也使得文化事业在提升的同时有了“走出去”的战略要求——在李莎看来,第一个成功的表现就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现在,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还有电影、话剧、音乐、美术……多种艺术形式在世界范围传播,增强着“‘中国故事’在世界千万个叙事中的独立地位”。
“你得看见那个人,看见他怎么做事”
初到中国,李莎常常感到疲惫,到王府井大街采购,往来人流、身体与身体的接触摩擦都挑战着她的神经。她说,在中国的老外有一种说法:谁在中国待一周,能写出一本书;待上一个月,差不多能凑合出一篇文章;时间再长就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时间长了,李莎也患上了“沉默症”。所幸她可以阅读和翻译,在快速变换的环境中,以此慢慢地“重新发现自己”,调试从间离到归属的过程。在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的自述中,李莎说,突然有一天她意识到,“中国是一条巨大的鲸鱼,混杂于上万个黑色头发的人山人海中的我是最安全的、最舒适的、最温暖的”,她开始初步明白“为什么不管是什么外来的文化终于都被中国吸收了、消化了并纳入其中的原因”,她开始学会“不让第一个印象占满我的心里”,学会“观察细节,细听语调”,重新发现了自己在中国的独特性,并获得了一种归属感。
当然,30年的中国生活中,李莎和很多中国作家成了朋友。
在翻译过程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李莎的破解之道是从作家本人身上找答案。她会找作家询问、沟通和对话,得到解释。不用像翻译已经去世的作家那样要靠不同译本之间的比较和理解,“直接找他”是翻译当代文学的优势,在她看来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一来二去,李莎和很多中国作家的交情就不只限于译者和作者。她经常和刘震云一起吃河南菜,一块喝酒。她的女儿和刘震云的女儿也是朋友。刘震云女儿导演电影的时候,也请李莎过去待几天,分享心得。她去过阿来家,见到了阿来的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和他们一起吃饭。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邀请李莎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了颁奖典礼……李莎和作家们的交流就是日常的交流,“就是生活吧,一起分享”,但是“特别有意思”。她在翻译徐皓峰的《师父》时,因为写的是武术,有一天她跟徐皓峰说一块儿吃个饭吧,说一下这个事儿。在饭馆席间,徐皓峰说着说着站起来,开始摆一些武术动作,“整个饭馆都在看,好玩极了”。
这种朋友间的交流对于李莎来说非常重要,不仅仅在于作家回答了翻译中某个具体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多知道他们,你(就)多明白他们写的东西”。李莎一个人做翻译的时候,看到一句话,会想起来那个作家的脸或者他正在写的东西,这可以激发她的想象力。多年来,李莎积累了一套翻译心得,“你得明白他怎么想,才有方法把他的思维变成自己的语言。你得看见那个人,你得看见他怎么做事,你得进入他的脑子,才能翻译(他的)东西。”
“把中国文学介绍到外国,是我们愿意做的”
随着对中国文学的熟悉,李莎的翻译工作开始忙起来,到现在,“几乎没有一分钟闲着的时间了”。忙归忙,李莎觉得很满足,她觉得“中国故事”她只解读了一小角,虽然很难,但越看越有趣,各种各样的工作也会给人成就感,让人变得越来越敏锐。

中意作家同题合作互译作品集意大利文版Gli insaziabili

中意作家同题合作互译作品集中文版《潮166•食色》
近几年,李莎的确是在中国文学的意大利语翻译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3月12日,意大利夜间出版社凭借(《关于爱欲和食物的8篇中国小说和8篇意大利小说》)一书获得了2019年意大利国家奖中的翻译及文化交流奖项。该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夜间出版社共同策划的的意大利文版,2019年由夜间出版社出版发行。李莎是该书的主编之一,从2017年开始,她和另一位主编、意大利汉学家、翻译家傅雪莲一起,负责为这本书寻找意方出版社、中意双方的联络、选取合适的意文和中文小说,并组织和参与该书的宣传活动,她还翻译了作品集中的4个中文小说:文珍《西瓜》、冯唐《麻将》、葛亮《浣熊》、殳俏《双食记》。目前,她正在与人文社讨论其他主题的中意双语互译作品集。
李莎和傅雪莲的相识始于《人民文学》意大利文版《汉字》(Caratteri)的创办。2011年,《人民文学》杂志创立英文版《路灯》(Pathlight)。2012年,李莎应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邱华栋邀请,参加《路灯》的研讨会。看了《路灯》后,她非常喜欢,从长城饭店往杂志社走的路上,李莎和邱华栋说,你们老是英文英文,还有别的外语呢,我们也重要,咱们做一个意大利文版的吧。两年后的2014年,邱华栋给李莎打电话说,可以做意大利文版了。经邱华栋介绍,李莎认识了米兰比克卡大学的傅雪莲,两人开始合作《人民文学》意大利文版《汉字》。
《汉字》第一期于2014年出版,刊发了铁凝、李敬泽、麦家、范小青、李洱、刘慈欣、翟永明、于坚、鲁敏、盛可以、田原、阿乙、路内、笛安、任晓雯等作家的作品,涉及小说、随笔、诗歌等。李莎说,第一期对于作品的选择意在提供对中国文学的全景式扫描,反映当今中国社会人们所关注的不同方面以及对历史的认知和思考,并有科幻等不同形式;在作者的选择上则侧重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和新生代作家。之后,每期《汉字》都有不同的主题和侧重,比如2015年第二期以女性为主题,之后有一期以城市为主题,还要一期以“丝绸之路”为主题,选择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2019年最新的一期则以科幻为主题,选择了刘慈欣、陈楸帆、夏笳等作家的科幻作品。

2014年《人民文学》意大利文版《汉字》
从2016年开始,《汉字》在原有一年一期的基础上,每年增加了一本中意双语版,李莎介绍说,双语版是考虑到能够给意大利的出版社提供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和获得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品。在主题和内容选择上,李莎有自己的观察角度和想法。“我们不是做了科幻吗,那也可以做一个系列,就叫类型文学,按主题选择一些比较经典的作品,比如悬疑。”她也在考虑应该做一期网络文学,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多比较成功的网络作家,“这个事情比较重要”。李莎甚至想,在每一期固定的诗歌板块,也许可以选择一部分rap歌词,把这些rap歌手自己的语言作为诗歌艺术来呈现。“好玩吧?这是中国年轻人喜欢听的也关注的东西。我觉得重要的是新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介绍给意大利的年轻一代,可以把这两群人搞得接近一点,互相理解。毕竟将来他们是有机会互相接触的。”
现在,《汉字》在意大利的发行由罗马和米兰两个较大型的书店发售纸质版,包括亚马逊在内的网上书店也能买到PDF版,主要的读者来自大学、评论界和出版社。《汉字》是意大利十几所教汉语的大学的选读或必读参考书,不只是用来阅读,老师和学生们也用来做一些翻译。李莎介绍,他们每年会举行一个翻译比赛,鼓励学中文的学生们参加,从《汉字》选择作品,获奖的翻译作品将在《汉字》上推介。这样做的初衷是因为中文和意大利文的区别太大,翻译有可能把一本不太好的书变成一部杰作,或者把一部杰作变成垃圾——“我不一定翻译得对,你可能有一个方法比我做的好;或者我的翻译是一种选择,还有其他五六种选择也很好;我们也可以讨论为什么会这样翻译。”
早些时候,大部分意大利读者熟悉和喜欢的中国作家包括莫言、阿城、苏童、余华等,“一方面的原因是影视带文学进来的”,“《红高粱》出来了,人家说这个是莫言写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出来了,人家说这苏童写得不错;《活着》的时候,就开始看余华”。这是好事,但近几年,李莎更希望意大利出版社和读者能更直接关注到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家和作品。杂志是一种媒介。除了学中文的学生或者对中国感兴趣的普通人,李莎希望能够通过《汉字》向意大利的出版社推介更多新的作家和好的作品。所以在选择作品时,她们会有意识选择以前很少或没有作品被翻译成意大利语的作家。现在已经有更多中国作家进入了意大利读者的视野,冯骥才、刘震云、李敬泽、李洱、麦家、徐则臣、张悦然……李莎的策略是,“我们拿短篇吸引出版社的兴趣”,将这些重要作家介绍过去。
当年看了英文版而喜欢上王安忆的作品,而现在,李莎希望意大利学习中文的学生能够通过意大利文来了解中文、了解中国文学。刘慈欣《三体》的意大利文版是从英文翻译的,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是通过法文转译为意大利文,李莎觉得这种通过第三种语言转译“是上个世纪的做法”,“当然,英文是很重要的语言,但我们的语言不是英语,我们的语言是意大利语。”对于重要的作家作品,李莎认为必须要由中文直接翻译成意大利语,她对翻译力量比较乐观,大学里有老师和学生对于中意文学翻译抱有热情,意大利也有很多优秀的中文翻译,“当然你不能认为这个事儿一做就能成功,你得投资,精神上的投资,你必须付出时间才能有所收获”。
接受采访时,李莎说:“把中国文学介绍到国外,这是我们愿意做的,不是义务,而是好玩、有意思,愿意这么做。”今年是中国与意大利建交50周年,在筹备使馆文化处的各种纪念活动之外,李莎正在翻译李洱的小说《花腔》。或许李莎口中的“好玩”“有意思”,正在于她通过当代文学,克服了初到中国的“沉默症”,觉得“有话可说”,从而打开了解读中国的一扇门。 (王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