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我愿把有限的生命凝固在作品之中
来源:中国文化报 | 舒晋瑜 2020年07月07日07:02

叶永烈先生因病于2020年5月15日在上海长海医院逝世,享年80岁。
叶永烈,1940年生,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知名小说家、历史学家、报告文学作家。从11岁发表第一首诗,到80岁去世,叶永烈创作了超过3500万字的作品,平均每年50万字。知名媒体人舒晋瑜曾问他,不停歇地采访写作60多年,有没有感到厌倦过?他笑了:“写作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如果哪一天没写,就会觉得空落落的。”如今,我们还有太多的“为什么”希望得到先生的解答,让我们一起跟随舒晋瑜,在这场最后的访谈中再一次走近叶永烈——
1 19岁写了《碳的一家》一书之后,叶永烈开始与科幻作品结缘
舒:小时候读的书,都是来自哪里?哪些书对您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叶:上中学时,我也很爱读科普书籍。伊林写的《十万个为什么》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本书像一位忠实的向导,领着我进行了一次“室内旅行”,使我明白了自来水、衬衫、镜子之类也有许多科学奥秘呢。
有一次,我借到一本被翻得很旧的《科学家奋斗史话》,一口气把它看完,接着又看了一遍。我懂得了科学家不是天生的,而是“奋斗”出来的。我还读过《趣味物理学》《趣味几何学》。我特别喜欢这些用文艺笔调写成的富有趣味的科普读物。
后来,在上大学的时候,20岁的我成为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便得益于中学时代的这些阅读。常常有人问我,你怎么会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你小时候读什么科幻小说?我小时候读的科幻小说,跟你们现在读的科幻小说全然不同。我在21岁写作《小灵通漫游未来》之前,既没有读过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硬科幻小说”,也没有读过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软科幻小说”,更没有读过美国作家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科幻小说”。
使我对科幻小说发生兴趣的是两篇苏联科幻小说,尽管这两篇科幻小说都没有“名气”。
其中的一篇叫《射击场的秘密》,是惊险样式的科幻小说。故事很有趣,事隔几十年,我仍能复述:间谍拍摄的微缩胶卷被查获了,所拍摄的是军事禁地射击场。奇怪的是,拍摄者的视角都很低。据此推理,破案的焦点集中在一只可以随意进入射击场的狗。最后查明,是间谍在狗的一只眼睛里安装了微型照相机。
接着,我又读苏联科幻小说《奇异的“透明胶”》,写的是一天清早,有人正在刷牙,忽然见到从空中飞过一个人,他大为惊讶:这“空中飞人”是怎么回事?经过侦查得知,原来是一个发明家,发明了奇异的“透明胶”,充进氢气,就飞上了天空。这种“透明胶”有着奇异的用途。
舒:写《碳的一家》时您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学化学是因为喜欢吗?
叶:我喜欢写作,高考本来准备考北京大学中文专业,我的理想是当记者,可是当时只招50名,其中一半是调干生。我担心考不上,报了化学系。
大三时我参与编写《十万个为什么》,是当时最年轻,也是写得最多的作者。1960年暑假,我把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书稿寄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个月后收到了出版社的回复,这本书在我大三时出版。
当时北京大学化学系是六年制,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研究所,但我还是惦记着写作,就主动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去当编导,完全改行了。
舒:您是较早从事科幻小说写作的,是否了解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
叶:我写过一部不算厚的《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被翻译到英、美、德等国家。写这本书的缘由跟当时的日本研究生武田雅哉(现在是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有关。1980年,他到上海复旦大学,专门研究我国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由于复旦大学没有合适的人选担任他的导师,便请我给予指导。当时上海图书馆有规定,外国人不能查阅新中国成立前的资料。这样,我被迫泡在上海图书馆里查阅,追寻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
我查到中国科幻小说最早出现在1904年,是署名为“荒江钓叟”的作者写的《月球殖民地小说》。这个考证得到普遍公认。
中国的科幻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20世纪50年代,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那个时候的科幻小说多是写给青少年看的;第二个高峰在1980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科学的春天来临,催生了中国科幻小说的繁荣,出现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批报告文学,但是后来中国科幻小说受到打击,几乎一蹶不振,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慢慢复苏。
舒:那时您的小说创作如何?1983年,您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遭到密集性的批判,带给您怎样的影响?
叶:我不到20岁成名,在当时很轰动,但《十万个为什么》只是一些短的文章。我有点小野心,想写长篇,就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个书稿寄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因为和时代不合拍被退稿,一直到16年之后的1978年才出版。1976年初,我写的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发表在《少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
“文革”结束之后,我的科幻小说已经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法国出版了我的科幻小说选集,意大利也出版了单行本,世界科幻三巨头之一的美国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来上海,我陪了他4天。美国的科幻小说作家卡恩为美国大学主编教科书,推出一套“世界科幻小说丛书”,收录了我的《腐蚀》。
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科幻小说《黑影》最早在《羊城晚报》连载,影响很大,珠江电影制片厂打算将其改编成电影。后来,《黑影》成为批判目标,批判文章连续发表。我决心不再写科幻小说,此后“胜利大逃亡”。
舒:怎么“逃”的?结果如何?
叶:中国文学界对科幻小说冷淡,认为其不是主流作品。科幻小说在中国文坛没有地位。为了争取地位,我尽量写纯文学作品,希望进入主流文学的阵营。1981年,我的小说《腐蚀》发表在《人民文学》头题,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中,以几票之差落选。
同时我也写报告文学,写一篇红一篇,经常被十几家报纸转载。我最初写文化名人,而且多是敏感的文化名人。后来又转到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中,在这条路上一走多年。
舒:您是最早从事科幻创作的作家,起步的时候,大概没有预料到有一天,中国的科幻小说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吧?
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还有中国民众科学素养的普遍提高,高科技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种种因素促成了科幻小说时代的繁荣。我已经彻底离开科幻小说。很多科幻小说的活动再三邀请我,我一概不去。我反感被称呼为“科幻作家”。
2 20世纪80年代,叶永烈转向传记文学创作
舒:什么动力让您一直那么精力充沛地写作?您根据什么确定传主?
叶: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作品是“凝固的时间”“凝固的生命”。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我愿把我有限的生命凝固在作品之中,奉献给时代,奉献给广大读者。
作家写作,要有一定的金钱作为物质上的保障,但是如果仅仅为金钱而写作,这样的写作是不会持久的。
对于我来说,已经经历过两次“金钱”的考验:一是在十年“文革”中,出书没有一分钱稿费,我出了10本书,而且还有好多本书在当时写成了,在“文革”之后出版;二是现在,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我即使不写一个字,也可以过着不错的生活,但我仍天天写作。
我选择传主,有三个原则:一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二是能够折射一段中国当代重要的历史;三是没人写过(或者即使有人写过,写得浅或者写得不好)。
还有一个条件是能够采访传主本人。如果传主去世或者传主无法采访,但是能够采访深知传主的人。我不写那种根据资料拼拼凑凑的作品。
我强调作者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不写“复述”式的作品,强调作品的原创性——尽管这么一来就得四处奔走、四处采访。
舒:您的报告文学中的人物,有的是科普名人,也有篮球名将、文化名人,更多的则是政治人物,您的采访是否难度很大?您本人的身份给您的采访是否带来一些便利?
叶:采访科学名人、体育明星、文化名人,一般都不难。政治人物的采访,尤其是政治敏感人物的采访,相当艰难。正因为艰难,我才以为更值得采访。我主要以作家的诚信、充分的尊重,获得对方的认可。当然,我的“品牌”也起一定作用。其实这“品牌”也是多年以自己的诚信建立起来的。
舒:2005年,中国首次举办的“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评选,您名列其中。能评价一下当代传记文学作品吗,它们普遍存在什么特点或者问题?
叶: “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的青铜奖杯,不仅使我意识到传记文学作家使命的沉重感,同时也表明,冰雕艺术虽然璀璨哗众却只华丽于一时,朴实严肃的青铜艺术将留传于千秋,而青铜艺术正是传记文学的象征。传记文学用文学记录人生,折射历史。
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我的传记文学作品,用事实说话。众多生动、形象的细节,是传记文学的“细胞”。我注重第一手材料。我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往往“七分跑、三分写”。我把广泛、深入而艰难的采访,视为确保真实性以及捕捉丰富细节的不可或缺的创作途径。传记文学写的是人。名人是人类的精英。一部又一部名人传记,把一个又一个“人”汇聚成“众”。“众”就是历史,所以传记文学是历史与文学的联姻。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相当活跃,出了许多好作品。不过,在我看来,组织专门的传记组、花费大量人力写出的一些厚厚的传记,往往过于刻板,缺乏可读性。另外,为尊者讳仍是中国传记文学常见的通病。
舒:由于很多作品都属重大政治题材,为此您特别严谨,力求“史料准确,立论正确”,那么,您是如何保障这一点的?
叶: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文件,尤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知读过多少遍。我知道怎么把握历史和政治分寸。作品要符合党的相关政策,这一条非常重要。所以,我的作品做到了一是史观正确,二是史实准确。
大量采访和搜集档案,保证了我叙述的事实准确。我是上海的“北京作家”。北京是政治人物云集的地方,每写一部作品我都要去北京。我多次到中南海等地进行密集性的采访,人脉也越来越广。另外,我是“旧闻记者”,我非常重视对当事人的采访,很早就不自觉地做着口述历史的工作。写一部长篇,至少采访二三十位甚至五六十位当事人,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采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当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入挖掘。我发现这个领域有无数的宝藏,尽管有一些采访不能在当时发表。
我是“理工男”,思维习惯于追根究底,反复推敲。争议和传说多的,我把相关的事情一二三四全部罗列出来。比如周恩来的右臂为什么一直弯在那里?我把听到的六七种说法全部罗列出来,让读者自己判断;所有的引用,我都会加注解,比如几月几日在某地采访过某人。
所有的毛泽东讲话、邓小平讲话都注明来自《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第几卷第几页。我的录音记录都保留着,我将1135盘采访录音磁带捐给上海图书馆,每盘是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还只是录音的一部分。
3 有人认为叶永烈是“双肩挑人物”,一头挑纪实文学,一头挑科普作品,其实远远不止
舒:您是“双肩挑人物”,一头挑纪实文学,一头挑科普作品,在您的创作经历中,纪实文学和科普作品分别占多大的比例?
叶:人们以为中国有同名同姓的两个叶永烈,一个是写纪实文学的叶永烈,一个是写科普作品的叶永烈。
过去,我并不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纪实文学和科普作品分别占多大的比例。在1999年时,我要整理出版我的文集,这才弄清了大概的数字:纪实文学约7/10,科普作品约3/10。
我的文学作品中有小说(中短篇小说选以及长篇小说)、散文、诗、杂文(多篇杂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童话(根据我的长篇童话《哭鼻子大王》改编的六集动画电影曾获1995年中国电影华表奖)、寓言、剧本、传记、相声……当然,主打作品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
我的科普作品主要有科幻小说、科学小品、科普读物。我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至今,《十万个为什么》总印数超过一亿册,而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用户也将近一亿,这两个“亿”是我丰富的精神财富。
舒:您是一个多产的畅销书作家,但是能做到这两者兼顾很难。尤其是那么多纪实文学,都要经过大量的采访。您的时间是怎么支配的?
叶:我把外出采访与案头写作,看作是不同工作状态的交替。
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和星期日,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从不在长假外出旅游。这样,我能安安稳稳写作,相对而言,我的创作时间就多一些。
我的体质好。除了1990年因写作过度导致视网膜剥落而住院动手术之外,至今没有住过医院,也无慢性病。
另外,我在长期的写作中,往往是思路通畅,一气呵成。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一次性写成,很少有写了一半重新再来。即便是为《人民文学》杂志写的小说,也是一次性写完。
我从1992年起就改用电脑写作,是第一批换笔的中国作家之一。电脑写作,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同时也减轻了写作的劳动强度。
舒:您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纪实文学,每一本都特别厚重。
叶:我是做“砖头”的工人。新华文轩出版了我5部纪实长篇,除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45万字,其他每部都是70万字。每一部都像砖头一样,但是很多读者说,看了几页就被吸引住了。我已经用了尽量浓缩凝练的笔调写作。
舒:您的很多科普作品被收入国内教科书,同时也被翻译到国外。您认为怎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科普?
叶:语文课本应当选一定比例的科普作品,使中小学生从小就对科学产生兴趣。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们从小对科学产生兴趣,会使他们一辈子热爱科学。
当然,大家在为语文课本在选科普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科学知识的准确。比如,那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悲壮的两小时》,多处存在明显的科学错误,我曾经就此事发表过谈话,希望语文课本编好之后,那些科普作品最好请科学家看一下,以免贻误下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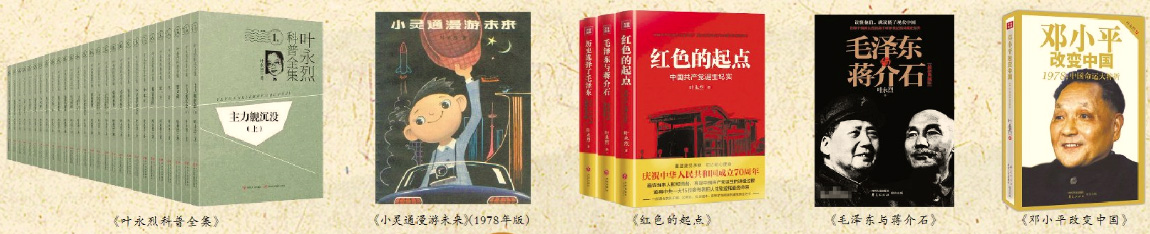
左起:《叶永烈科普全集》;《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版);《红色的起点》;《毛泽东与蒋介石》;《邓小平改变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