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葫芦引》:要在葫芦里装宇宙
来源:中国作家网 | 何英 2020年10月21日08:05

宗璞(1928~),原名冯锺璞,原籍河南唐河。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曾任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委会主席团委员等。著有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系列四部,其中《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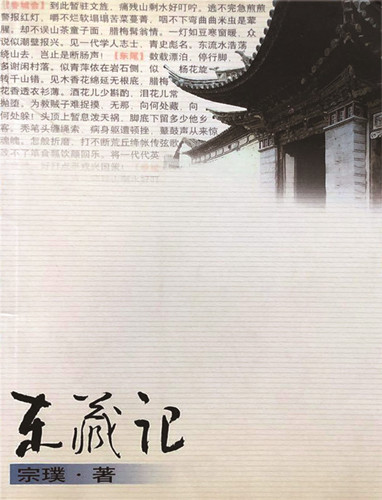
《东藏记》
宗璞先生从1985年57岁开始创作《南渡记》,到2019年91岁出版《北归记》, 历经33年完成了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四记”的创作。其间,作家经历了父丧、夫丧,以及其他一些亲人的亡故。自己的健康状况亦不佳,只在创作《南渡记》时身体稍好一些。创作《东藏记》时大病一场,眼疾加重,视网膜几度脱落。从《东藏记》后半部分起到《西征记》直至《北归记》的写作都是口授。《北归记》写作将近一半时,宗璞先生差一点脑中风,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又是多么顽强的毅力,令作家坚持完成了《野葫芦引》“四记”的创作?
“其实也简单,就是要留下生命中值得记忆的、可珍贵的,而且不是属于我个人的一段历史、一段生活。”“我写这部长篇小说,很希望通过对几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记载,起到一点历史的借鉴作用”,“我很想真实地写出当时的精神是什么精神”,“我也想写出那特定时代的人生遭遇”。
小说所叙的抗日战争年代正是危机四伏、民族到了存亡关头的“至暗时刻”。《野葫芦引》“四记”以孟家为中心,讲述三代知识分子和十几个家庭经历大学南迁、在日寇的空袭下坚持办学,西南联大学生深入前线作战,以及胜利之后返回北平的历史故事。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历史的舞台上经受着是非功过、道德良心的考验,承受着各自命运的艰难选择。
有话要说的作家将生命的真火化为了文学的灿烂光华。《野葫芦引》“四记”亦成为当代小说中的煌煌巨制。而此时,作家的人生经验、智慧襟抱,也达到了人生的顶峰阶段。文学的积累与修养、小说的理念与技巧,都令“四记”成为当代文学中值得期待的文本,亦是作家本人集大成式的写作。由于作家的笔触主要胶着、盘桓于校园和知识分子群体,“四记”还堪称百年知识分子的镜像之作。无论是从当代文学史角度,还是对宗璞个人来说,“四记”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这样一部心血写就的巨著,读者需要保持与之相配的阅读与研究的态度。事实上,《野葫芦引》并不是一部容易看懂的小说。这是一个充满复杂与矛盾、极富暗示性和悲剧性的文本。叙事的表层时间是1937年至1949年。深层时间,也就是叙事的话语时间则是从1985年至2017年。如此一来,总的时空跨越了80年。在这80年里,国家、社会自抗战以来的沧桑巨变,三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风雨考验,作者个人的人生遭际等因素都将纳入小说考量的范围。小说里叙事的时间长度不过是12年,只是嵋从童年到青年的时期,但背后的话语时间,实际上贯穿至作者写下《北归记》最后一个句点的时刻。
宗璞先生曾先后多次在访谈及文章中表达过自己的创作动机与目的:“向历史诉说”。通过细读小说,读者亦能体味到作家意欲记史、传史的心意。而由宗璞先生来记录或诉说这一段历史,则又有了历史选择了她的意味。作为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她差不多见证了中国近百年的近现代历史。宗璞先生出生于鸿儒硕学之家,父亲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冯友兰。她自小生活在水清木华的清华园,家中来往的都是高层知识分子,家族里更不乏中国当代史中的传奇人物。而宗璞先生自己,甫出文坛也以《红豆》一鸣惊人。之后的《紫藤萝瀑布》《三生石》《弦上的梦》《鲁鲁》《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名篇,亦是几代文学人的经典记忆。在当代,不能说没有比宗璞更有资格写“历史”的作家,但无疑,她确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书写者。
除了意欲记史、传史,另一个更为直接的创作动力,也许就是其父冯友兰先生的言传身教。冯友兰80岁才开始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父女俩晚年写作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同一间书房、同样的失明,父亲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女儿完成了她的《野葫芦引》前二记。最终,宗璞先生在师法父亲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早年的夙愿。当然,对任何一位作家来说,创作的“当下此时”都会成为文本中一种隐在的生命痕迹。对宗璞先生而言,对老年、生命之谜的质询与象征性解决,也是小说创作的一个潜在动机。这从整个文本笼罩的晚期风格中可见一斑。
《野葫芦引》“四记”追求一种史书风格,是带有自传色彩的编年体叙事,叙述体现出记、诉的修辞特点。“纳须弥于芥子”,既是宗璞先生的创作宗旨,是一种关于小说的宏观意义上的内容安排的想象,更是某种对小说境界的哲学追求。所谓“芥子纳须弥”“和光与物同”的境界,正是一位惯看历史风云、曾经沧海的老作家的自我期许。“纳须弥于芥子”还对应着小说的空间布局与素材选择,对读者而言,这也正是“四记”所达到的修辞效果。宗璞将“野葫芦”自谦为“芥子”,里面的内容则为“须弥”。暗含着“器”虽小,包容的却是芸芸大千世界、渺渺宇宙之道。而这一切,都需要读者去仔细辨认、揣摩。须弥山一般庞大丰富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也对应着百科全书式写作。在阿恩海姆看来,这其实也是某种“晚期风格”的表现。
一般的作家总被指摘没有细节,或者细节不真实;对宗璞而言,“四记”则充满了细节。由于作家对自己严苛的创作态度,每一个细节作家都务使其尽善尽美,显示出精神贵族式的奢华。作者又极擅描写知识分子的某种情调与氛围,使人物镶嵌在其中,令读者体味到大众文化狂欢中高雅文化的精神飞地,“四记”也因此蕴含着文化史的意味。而中国文人小说传统深厚博大的内涵与技巧,更是在“四记”中有着精心的表现。冯至曾如此评价《南渡记》:“总之你的文笔细致,字斟句酌,可以想见你是通过多么缜密的思考在写这本书。如果读者认真、通读细读了四记的话,会惊叹于作者叙事的严谨。”作品令人一睹什么叫“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如嵋与无因的爱情,在《南渡记》中就埋下伏笔,两人最终无缘无果;玹子由早期的骄傲公主变成阿难的继母,也是在卫葑与雪妍的婚礼上就暗示了两人的姻缘。整个文本得益于这种传统叙事的经验,可见出叙述在这一方面的精心和细腻。
整个文本在思想规范方面是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统辖着叙事,甚至主宰了人物命运的。孟弗之对人对己都强调要“尽职尽伦”。以孟弗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大节上他们爱国,是“先觉者”,坚决主张抗日,为国培育人才,个人则著书立说、淡薄物质;在日常生活中,在知识分子看重的“名”上,虽也不免文人相轻抵牾攻讦。当然,由于宗璞先生本人的家学渊源与教养修为,除了对极个别人物,一切写来总体都还是温柔敦厚的。事实上,“四记”就是现当代知识分子思想体系的形象表现。《野葫芦引》的历史叙事,无疑还包括作为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精神史的形象描述。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投机狂潮”“黄金梦”的腐蚀中,一群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坚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人格操守;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不管是新人还是旧人,新道德还是旧道德,在民族大义的关口,这群知识分子彰显出中国士人、君子的传统道德: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君子忧道不忧贫……
除了在战时道德操守上的坚持,伴随这一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更是作为民族、国家“寻路者”的痛苦追寻。作为“寻路者”的直系后裔,作者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聚焦和复原,同样也是知识分子自我认识的需求。作家在几个主要人物身上寄寓了自己的主题,在整部小说中也灌注了作家自己的思想规范、道德伦理,并使其隐在地成为塑造人物、影响人物命运的主旨。
《野葫芦引》“四记”的人物谱系主要是一种“范型人”。比如孟樾、萧澂、庄卣辰、江昉、秦巽衡、李涟、梁明时、刘仰泽、钱明经、晏不来等,都是知识分子的类型形象。如卫葑、李宇明等,则是现代文学以来的形象类型:青年知识分子革命者谱系。他们与老革命家吕非清构成一种革命的接续与比照关系。除了“范型人”,还有处在“何事”中的人,严格说来,书中所有的人物都处在抗日战争这个大事件中。直接参战的人物有国民党军长严亮祖;作为大学生走向滇西战场的詹台玮、冷若安、孟嵋、李子薇等,更有民间抗日英雄、传奇人物彭田立和苦留、福留等;与之相对的汉奸缪东惠、凌京尧(这个人物作者倾注了同情);还有几位师母、太太,作为传统“女主内”型的形象,最典型的如碧初,贤惠、识大体,国难当头以自己柔韧的力量维持家庭的存续。另一些人物在爱情中,如嵋、庄无因、雪妍、玹子、殷大士等,峨则很快因单恋受伤变成一个执著于事业的女强人。这些在爱情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爱情故事,都体现出宗璞创作史中的互文性。卫葑与雪妍、嵋与无因的爱情,似乎与《红豆》也有着话语时间中的互文性。
孟樾这个人物承担着小说有关“知识分子主题”的大部分的主题成分,是作家笔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高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像一个先知,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智者、仁者。一些形象是围绕着孟樾而设置的。钱明经的浮浪衬托出孟樾的端方;萧澂、李涟的右倾跟孟樾的“左倾”形成对比;在更加激进的江昉那里,孟樾又代表学校的官方正统立场;《北归记》出现了社会学家刘仰泽,是继江昉之后新的政治激进派。他在屠刀前下跪,是孟弗之被抓的衬写与情节循环;白礼文浇漓无行却一再受到孟樾的提携赏识,写出了孟樾的爱才与宽厚。跟庄卣辰、李涟等在1949年的“走” 对比,孟樾是“留”的一方。这大关节的选择最后昭示出他的爱国情怀。
当然,历来好人难写。有缺点的人几乎能立刻让读者认同他的真实性,一个古怪的人则常常是有趣的。如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性格怪僻偏执的人物。连《白痴》中的梅什金伯爵也向来被认为不如他的邪恶的对手刻画得好。与孟弗之(孟夫子)的完美形象相比,一些有缺点的人物,比如钱明经、白礼文等则显得更加生动可感。
人物塑造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文学史自身。卫葑是自现代文学以来的重要形象类型,即青年知识分子革命者。这个形象与现代文学史及宗璞自己的小说史形成极明显的互文性。作为小说思想体系之一部分的表现,卫葑的形象意味深长。与雪妍、玹子的婚恋则又续写了后革命时代“革命加恋爱”的主题。卫葑的婚恋情节以及卫葑这个形象,透露出时代的、历史的、文学史的多方面信息和意蕴。
因大部分的叙述倾向于记史实录的写法,致使虚构成分较少。情节曲折、传奇跌宕之类的美学风格不是它的主旨,但读者却因此收获了对当代知识分子文化史深刻内涵的认识。作家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们还原为日常生活中有着衣食住行需要的“凡人”。这些大师、巨匠们的风采素来是被仰视的,大多数时候是象牙塔中神秘的存在。而《野葫芦引》“四记”却使得中国高层知识精英的日常、心灵与精神生活在作家笔下次第生动铺开,因此也可以说,这同样是一部祛魅之书。矛盾与张力也即在此。
作者的古典文学修养以及对西方经典文学的熟稔,都使人物形象体现出这两方面的影响。如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古典诗词、西方文学经典内容等,这些或已成为某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作家的行文,不自觉地灌注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或成为一种隐喻手段来刻画人物;至于哈代、伍尔夫等的叙事手法,则成为一种丰厚的技巧底蕴。当然,“四记”最突出的叙事特点仍然是中国传统小说、文人小说作为一种知识背景和思维图式的精深呈现。比如形象迭用。最为人所熟知的如“晴为黛影”“袭为钗副”的描写法,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中也可见其惊鸿之影;作者的主要人物大多形成平行或相反的结构设定,并且反复或重新形成这类平行或相反的人物来产生效果。这种模式的用意显然是为了突出人物的个性以及创造一种结构上对称的形式美,使小说的多层次质感得以展现。如孟弗之与钱明经、吕碧初与金士珍、雪妍与玹子、吕非清与凌京尧、詹台玮与庄无因等。
在叙述爱情时,文本亦表现出一种晚期风格,即那种对悲剧性情感的偏爱。有时,青春爱情的炽烈激情往往被忧伤怀旧的回忆所取代。比如,叙述大士和玮玮的爱情时有这样一个细节:他们隔着煤油箱默然相对。两颗本应激动跳跃的心变得平静安宁了,使炽烈的青春爱情染上了暮色。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叙述者在这里暗示玮玮将为国捐躯,而两人的爱情最终是伤痛而无果的。某种意义上,这既是晚期风格的一种年龄和心境的体现,也是作者的伦理道德观的自然反映。又如,当有记者问宗璞先生,“您写的爱情一直是只牵手的,最多亲一下脸颊,有没有想过突破一下?”宗璞一听也笑了,差一点笑掉了助听器,顿了顿,才认真回答:“我觉得《西厢记》《牡丹亭》写得很美,但是主人公的大胆举止我是不赞成的,发乎情止乎礼是我们的传统。我喜欢这样的爱情。”看完“四记”中的爱情、婚姻描写,确如作者所说,这便是作家的原则和尺度了。孟樾和碧初这一对和谐恩爱的夫妇之间最亲密的举动也只是“抚抚肩、拍拍手”。即便是钱明经和郑惠枌的离婚,也是风平浪静,不起波澜。郑惠枌亲见钱明经跟女土司的亲密举动,还能笑着对答。令读者见识了上世纪40年代读书女性的涵养和风度。
《野葫芦引》“四记”提供了一部个人的历史, 也是一部特殊群体的历史。其中有着对于过去的大量洞见,从智性升华到人生的高点,合成一种成熟的世界观,更获得了某种言说的自由度,不再想要讨好读者或其他什么人。这种熟练的、惊人的流畅宛转,也昭示出晚期风格的复杂。既有创新,也有某种体能上的力有不逮;辉煌中掺杂着可能存在的风险;精雕细镂中潜伏着拖沓冗慢。深刻的矛盾情绪、奢华却平静的文字,处处深藏暗示与玄机。而这一切都在最后向读者证明,表现历史的可能性却在奇迹般地增大。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