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把人心点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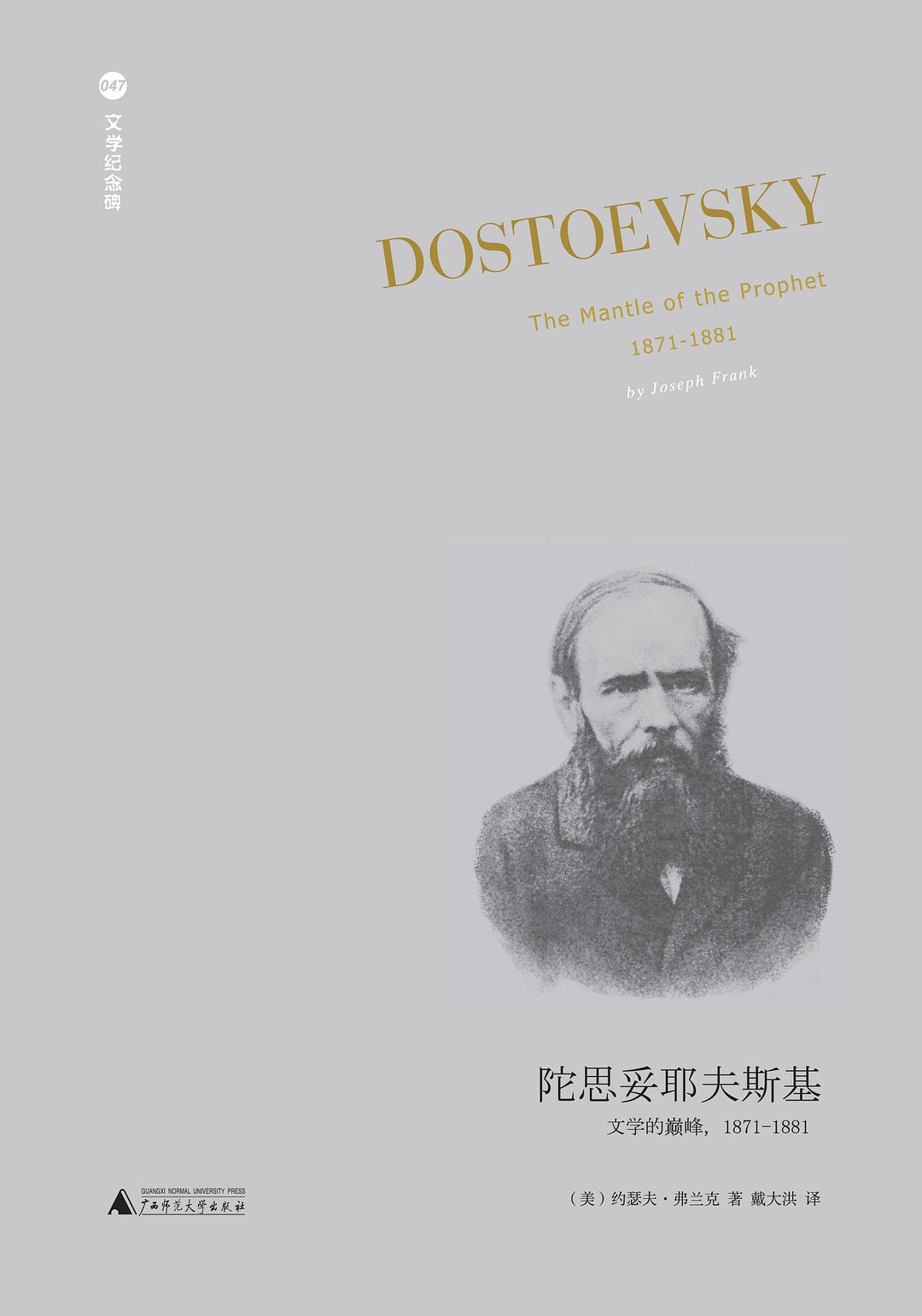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5卷):文学的巅峰,1871-1881》,[美]约瑟夫·弗兰克著,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2年3月版,1160页,198.00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文学纪念碑”丛书(魏东主持)于2014年推出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最后一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原书名Dostoevsky: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1871 -1881,2002;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煌煌五大卷、总共近四千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文学纪念碑”中那座最宏伟的碑,是文学与思想、理想与信仰之间最深邃的幽谷,其意义远超出一般的文学翻译出版项目。
想起来这是我为这套陀传写的第四篇书评了,读一部人物传记而写了四篇书评,在我是从未有过的。在连续追着阅读与写作的过程中,也经常与夫人和儿子讨论。印象很深的是夫人谈起以前读《卡拉马佐兄弟》,特别感动的是在结尾阿辽沙对一群孩子讲的那番话;儿子则和我讨论弗兰克的这套陀氏传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终结者”,他自己也把弗兰克这五大卷的英文原版买齐了。他说弗兰克掌握资料的丰富与论述的深入,更重要的是从传主生活所切入的文学分析、俄国社会史及思想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恐怕都难以被超越。我谈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我是从车尔尼雪夫斯基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从政治和文学的角度经历了对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六十年代人的认识与思考的过程,但是对于其间的思想争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认识还是很简单。虽然自九十年代以来阅读了不少关于苏俄革命、思想和文学的论著,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伟大作品也早已确立了他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但是对他的文学创作与生活经历及思想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仍然是不甚了然,现在读到弗兰克这套堪称博大精深的陀氏传记算是迟来的补课。更重要的是,我在每一次阅读这套陀氏传记和写书评的时候,我都要重复谈到一个问题:曼德施塔姆夫人把俄国“知识分子”“全都在‘胜利者的统一意识形态’前缴械投降”的罪孽看作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弃绝”。(《曼德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9月,28页)这或许是我们必须继续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由吧——或者说,不需要任何理由,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七天里四次排队做核酸的间隙中写完一篇“书记”、修订完一篇五万字论文,然后看完这部一千两百多页的陀传第五卷,还要不时翻看手机上的战争、疫情和所有牵动人心的信息,而且是在南方4月的广场上排队,有时真的会出现幻觉。似乎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在我们的核酸队伍中激烈争论起来,好像是关于对普希金的评价问题,还有工作人员不时走过来善意地提醒他们要保持一米距离。
由于写到了最后一卷了,弗兰克在“前言”中的一些论述颇有概括性。比如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人物,如果不懂得他们如何深受当时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各种问题的困扰,不懂得这些人物的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就不可能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还要懂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把那些问题提升到道德与哲学的高度,并且是以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俄罗斯方式呈现出来;在那些伟大的长篇小说集中表现了俄罗斯文化的各种问题,而且是以他的末世论观点和救世主眼光改变了问题的形式。因此弗兰克说实际上他是在写一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中心的经过浓缩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化史,并非虚言。他认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远见和卓识在当时引起的那些反应,我们要澄清其意义,而且这变得更加重要。
同时,第一章“引言”也带有回顾性。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偶尔发言时“总是怀着强烈的义愤严厉谴责构成俄国社会秩序基础的这种制度令人无法容忍的不公”,以后他终生不忘自己的这段经历:聚会、被捕、监禁、假枪毙、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苦役营,通过痛苦的个人经历,他发现了阶级之间巨大的文化和精神鸿沟,发现具有个人自由意识的人性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以及发现认为可以依靠理性的力量控制并且支配人类生活的想法是多么愚蠢。(9-10页)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从流放地归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相信俄国没有必要为本国的社会问题向欧洲寻求解决方案,他担心的是以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H.A.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六十年代激进主义对民众的煽动会延缓甚至阻碍解放者沙皇正在进行的不仅涉及农奴而且涉及军队、司法系统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改革。1871年7月8日,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国外回到俄国首都那一天,对涅恰耶夫小组成员的公开审判正在进行,由米哈伊尔·巴枯宁或谢尔盖·涅恰耶夫撰写的充满冷酷无情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革命者教义问答》和一些重要文件向社会公布了。事件的起因是涅恰耶夫领导的一个秘密小组谋杀了该小组的一名成员,据说是担心告密。对政治犯的审判通常都是秘密进行的,政府决定公开审理和公布这些文件,目的是让公众看到激进分子为达到目的如何不择手段和残忍。结果是一方面辩护律师和一些被告在法庭上以自由和正义的名义发表的激动人心的演说,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影响,另一方面涅恰耶夫的手段中各种阴险邪恶的细节也使人们产生极度的反感,就连那些赞同其目标的人也不例外。这事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创作了《群魔》。
作者回顾这些是为了说明在1872年《群魔》完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与艺术生涯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他发现俄国激进主义发生变化,愿意承认基督教道德价值观念的正当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七十年代的作品明显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使他与左派民粹主义者的短暂结盟,在他们的杂志《祖国纪事》上发表他的作品,并且将使他获得了先知的地位。“以此我们开始了本卷的叙述,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令人吃惊的最后十年,不仅通过个人的成功,而且通过《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他的天才以艺术形式对使其一生备受折磨的所有焦虑的回应——他的人生达到了顶峰。”(16页)
从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上看,此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矛盾,他对俄国君王制一直持维护的态度,支持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认为无论在实行过程中有什么缺陷,这些改革对于维持俄国内部的稳定至关重要。(49页)“他被认为是一个尽管忠于沙皇但却成功地超越了狭隘的派别争斗的人;在七十年代,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一度冷静温和、远离政治的民粹派人士由于绝望转向恐怖活动时,他试图利用这种地位防止逐渐迫近他的国家的灾难发生。”(111页)他在担任《公民》周刊主编的时候发表的专栏文章《作家日记》受到读者欢迎,在这些专栏文章中他广泛地讨论过各种社会问题,从农村、城市的贫困问题到家庭与儿童问题,从教会到司法机关的体制,从西欧到俄国的未来,使他成为引导公共舆论的意见分子。其中有些看法相当独特,是他此期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来源。比如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陪审制度改革,使农民陪审员对许多即使被明确认定有罪的罪犯也会做出从轻处理甚至免于刑事处罚的裁定,有一种观点认为这说明俄国民众耻于运用他们获得的权力,并且对这种作为礼物恩赐给他们的权力感到恐惧,而且认为“如果我们碰巧陷入同样的处境,我们甚至可能做出更糟糕的事情”,因此他们总是宽大为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感到这些看法令人感到“安慰”,但是他认为这种“环境论”违背了基督教的教义,而且会降低民众的道德水准,因此坚持认为对犯罪行为予以惩罚。(122-125页)这些思想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体现出来。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决反对陪审团尽可能宣判案犯无罪的倾向,而要求实行“严厉的惩罚、监禁和苦役”;而作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基础的法理思想,则是“犯罪的思想也应当与犯罪的行为一样受到惩罚”。(954页)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严惩思想,这很值得研究。
在此期,不能不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皇室的关系。当他听说亚历山大皇太子对他的《作家日记》感兴趣的时候就非常高兴,马上写信给皇太子解释没有从一开始就呈送刊物的原因,信中的一些话也很难听:“俄国历史所蕴含的巨大的时代能量已经焕发出难以想象的活力,把俄国人的精神和内心世界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使他们可以理解以前无法理解的许多事情,并且使神圣的俄罗斯思想在我们的意识中比以前更加清晰鲜明。我对在我国的大地上和我国正直、非凡的人民中发生、出现的一切事情不能不全神贯注地做出反应……我[也]早就考虑和梦想有幸把我卑微的作品呈献给殿下。”弗兰克说他有充分的理由对罗曼诺夫王朝的皇室感恩戴德:尼古拉一世为他减刑并且恩准他保留公民权;亚历山大二世批准晋升他为军官的要求;三年前皇太子馈赠了钱帮他度过了一个困难时期。(317页)1878年2月的某一天,亚历山大二世的两个小儿子的家庭教师以沙皇的名义来访,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学生见面认识。弗兰克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慨万千完全是可以想象的——曾经被判决犯有反叛国家罪的罪犯和苦役犯人,现在以贵宾的身份受邀进入最高贵、最排外的宫廷,担任俄国的未来最终将被托付给他们的那些人的导师和顾问!“他发现自己具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身份,不仅年轻一代激进分子,而且还有统治家族的年轻成员,都把他当作值得重视的顾问。因此,如果他感到命运(或上帝)在俄国历史的这一决定性时刻赋予他一项使命的话,那么,他肯定也有充分客观的理由相信,这一重大使命就应当落在他身上。的确,快速回顾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清晰明确地发现,自从一八六〇年从西伯利亚归来以后,他一直努力扮演的正是他现在所充当的角色——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与整个俄国社会之间的仲裁人和调解人。”(522-523页)但是,秘密警察仍然把他当作一名前政治犯进行监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利用他现在结识的权势人物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努力得到回应,保证不会再有问题,只需要由他本人正式提出申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申请材料中写道:“我通过成百上千页的文章作品已经表明而且还在继续表明我的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我希望,这些信念和信仰不至于提供怀疑我的政治道德的理由。”他的名字终于从第三厅的被监视者名单上划掉了,但是留给他的自由的时间只剩下两年了。(567页)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俄国的政治斗争越趋激烈,激进派的道德理想与牺牲精神越来越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1877年,政府三次把民粹派人士送上法庭,其中第二场审判被称为“五十人”审判,它给激进派知识分子留下了特别深刻因而难以磨灭的印象。“保持着尊严的被告有力地证明他们不得不忍受难以忍受的拘押条件,这使越来越多具有人性并且受过教育的公民直接面对专制统治的残酷现实。这场审判使公众感到震惊的是,这些年轻人在接受审判之前被极其不公正地长期监禁,而使他们被判重刑的那些‘罪行’完全是温和的合法行为,甚至经常是慈善行为。”(343页)更为感人的是,所谓“五十人审判”把那些年轻的女士为传播社会主义的“福音”而甘愿自我牺牲的行为公之于世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绝没有任何激进思想的诗人雅科夫·波隆斯基写了一首题为《女囚徒》的诗,开头是:“她是我的什么人?——不是妻子,不是情人 / 她也不是我的女儿,/ 可是,她那该死的命运为什么 / 让我日夜牵挂?”(344-345页)对于这些斗争于牺牲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大的愿望是影响那些经常被人们比作基督教早期殉道者的民粹派青年,使他们沿着阿辽沙的道路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道路前行”。(345页)
在政治与阶级压迫的恐怖社会中,“打人”常常成为一种奴役与反抗的象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一月号的《作家日记》生动地回忆了一件往事:当年他与父兄一起前往彼得堡,在途中一个驿站目睹了一名政府信使像例行公事一般挥拳猛击他的农民马车夫的后脑勺,而马车夫则马上挥鞭抽打他的马匹。“这一令人憎恶的情景终生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它成为习惯性残忍野蛮的俄国社会秩序的象征”。后来他想,如果有朝一日要创办一个政治团体的话,一定要把这辆马车刻在团体的徽章上,“作为一种象征和警示”。(365页)
另外一件“打人”事件是激进女青年薇拉·扎苏利奇听说圣彼得堡市市长费奥多尔·特列波夫将军竟然下令鞭笞一名拒绝在他面前脱帽的民粹派政治犯,于是她以正式求见为借口冷静地走进将军的办公室并向他开枪,但是将军只受了一点轻伤。在对她的公开审判中,由于辩方提出详细的证据证明鞭笞囚犯的残酷无情,结果她被判无罪释放,“挤满了政府高官和彼得堡上流社会显贵的法庭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512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鞭笞囚犯深恶痛绝,因此对以牙还牙的扎苏利奇抱有某种同情。但是他认为无论判决她有罪还是无罪,都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判决她有罪,她将成为殉道者;如果判决她无罪,她的行为将被赋予某种合法性,俄国的国家权威将因此受到损害。”后来的局势也证实了他的担心。她走出法庭后,欢庆的人群把她高高举过肩头,激进分子的欢庆引发了一场示威,以警察开枪打死一人而告终。“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许多俄国人突然发现自己身陷忍受一个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权与诉诸暴力进行反抗之间左右为难。”(513页)“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指责那些愿意做出自我牺牲的血统纯正的俄罗斯青年,他希望引导他们走上别的道路。”(515页)顺带要说的是,所谓血统纯正,也暴露了他的反犹思想和立场。
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同时也把这些关注与思考与他的文学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也极力警惕和反对政治观念对文艺创作的支配。在发表美术评论的文章中,他反对一些画家呈现出的按照某种“思想倾向”创作绘画作品的趋势,反对“他们允许自己的灵感被激进的功利主义观念所支配,把艺术首先当作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一种武器。……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坚持认为,尽管文学和艺术无疑扮演着某种重要的社会-文化角色,但是,使文学和艺术产生影响的最好办法只能是允许艺术家根据他们的才能完全自主地进行创作。否则的话,艺术家最终将穿上‘制服’……”他谈到涅克拉索夫最近一首诗的某个细节:一个来到西伯利亚陪伴服刑的丈夫的妻子在他们相见时首先亲吻丈夫戴着的镣铐,在完成了这个表示公民抗议的姿态后才去拥抱他;这表明“我们这位公民诗人现在肯定正在把制服穿在身上”。(144页)我觉得这个细节例子还可以讨论,但是他对于文艺“制服”的警惕和反对仍然不过时。他对青年作家提出的忠告是:“永远不要出卖灵魂。……永远不要因为稿费……而被迫写作。”(565页)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绝笔之作,他的“天鹅之歌”,是弗兰克用作书名的“文学的巅峰”,这也是这部第五卷的核心主题。由于篇幅关系,在此无法继续谈这部小说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全书的末尾,阿辽沙对孩子们说的那番话可以看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什么是爱与善良的思想的最感人的表述,我甚至觉得是他的在天之灵看到今天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恶人、那么多底层互害的冷漠与暴行而对我们说的。阿辽沙的心灵里仿佛被什么东西强烈地震动着,面对一群孩子——他亲切地叫他们“小鸽子们”,他严肃而庄重地说了一番话:“我们以后也许会成为恶人,甚至无力克制自己去做坏事,嘲笑人们所流的眼泪,取笑那些像柯里亚刚才那样喊出:‘我要为全人类受苦’的话的人们——也许我们要恶毒地嘲弄这些人。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我们怎样坏,只要一想到我们怎样殡葬伊留莎,在他一生最后的几天里我们怎样爱他,我们怎样一块儿亲密地在这块石头旁边谈话,那么就是我们中间最残酷,最好嘲笑的人——假使我们将来会成为这样的人的话,也总不敢在内心里对于他在此刻曾经是那么善良这一点加以嘲笑!不但如此,也许正是这一个回忆,会阻止他做出最大的坏事,使他沉思一下,说道:‘是的,当时我是善良的,勇敢的,诚实的。’即使他要嘲笑自己,这也不要紧,人是时常取笑善良和美好的东西的;这只是因为轻浮浅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诸位,他刚一嘲笑,心里就立刻会说:‘不,我这样嘲笑是很坏的,因为这是不能嘲笑的呀!’”孩子们听到这里都很激动,也想说点什么,但是忍住了,继续听阿辽沙说:“我说这话,是害怕我们将来会成为坏人,”阿辽沙继续说,“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会成为坏人呢,诸位?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互相遗忘。这话我还要重复一下。诸位,我要对你们发誓……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孩子们全部激动地用响亮的嗓子喊着“是的,是的,永远的、永远的!”阿辽沙继续说:“孩子们,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不要惧怕生活!在你做了一点好事、正直的事的时候,生活是多么美好啊!”“是的,是的”,孩子们欢欣地附和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14卷,《卡拉马佐夫兄弟》(下),耿济之译,秦水、吴钧燮校,人们文学出版社,2018年,916-918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诫世人:即便是作恶的时候,也要在内心保持一点最后的良知,面对苦难中的妇孺下手不要那么狠;不要以为时代的灰尘永远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即便不为自己打算,也要想到家人可能会受到的报应——在陀氏的小说中,个人与家庭、此生与彼世总是连接在一起。过去在一些文学评论中陀氏的这些思想会被看作“连篇累牍地向读者进行他关于爱与善的说教”,但是在时代的灰尘蔽日的时候,这不是说教,而是最高的祈祷。当年俄国画家伊·尼·克拉姆斯科伊在1881年2月14日写给帕·米·特列季亚科夫的信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起过巨大的作用,只要生活对于这人不是欢乐、而是深刻的悲剧的话。”他还说自己在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好几次恐惧地环顾四周,感到奇怪,一切居然还是老样子,而且世界也没有在自己的轴心上翻个过儿。似乎觉得:卡拉马佐夫父子在佐西马长老的修道室开过家庭会议之后,在‘宗教大法官’之后,人们还在照样地掠夺他人,政界还在照样地公开宣传伪善,高级僧侣们还安之若素地照样认为,基督的事业在自行其道,实际的生活也在自行其道——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是预言性的、烫手的和启示录性的,它使人觉得再不能待在我们昨天待过的老地方了,再不能抱着我们的老感情,再不能除了可怕的末日审判以外净是胡思乱想了。我说这话只是想对您说,大概,像您我这样的人绝不是个别现象。肯定有许多灵魂和心灵感到惶遽不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是我们的社会良心”。(同上,956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欢的诗歌之一是普希金的《先知》,他经常大声朗诵这首诗:“把海洋和大地统统走遍,/ 用我的语言把人心点燃。”他的确就是这样。
- 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的作品中,预言了俄罗斯的命运[2022-0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