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它是对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命名”
今年四月,许多人在社交平台引用了艾略特经典长诗《荒原》的开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2022这一年,正好是《荒原》问世一百周年。
《荒原》是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代表作,其出版被誉为“西方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1922年10月,《荒原》首发于艾略特自己主编的季刊《标准》创刊号,同年底在美国出版单行本,艾略特还在单行本中加入了五十多条注释。
在四月,澎湃新闻记者特就《荒原》在中国的接受史、它对中国诗人的影响、它与当下的关联等话题专访了几位中国诗人,他们之中很多人还是批评家、作家、学者、译者、文学期刊编辑。
此文为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就《荒原》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对话】
澎湃新闻:今年是《荒原》问世百年,想请你先和我们谈谈这部经典长诗在中国有着怎样的传播与接受历程?
王家新:在中国,第一个大力介绍艾略特并对中国新诗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是叶公超。叶公超曾留学美英,出版过英文诗集,1930年代中后期,他在清华任教期间先后写出《爱略特的诗》(注:当时叶公超把“艾略特”译为“爱略特”)、《再论爱略特的诗》,并让他那时的学生卞之琳译出了艾略特的重要诗论《传统与个人才能》。后来,他的《再论爱略特的诗》又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荒原》译本,即赵萝蕤译本的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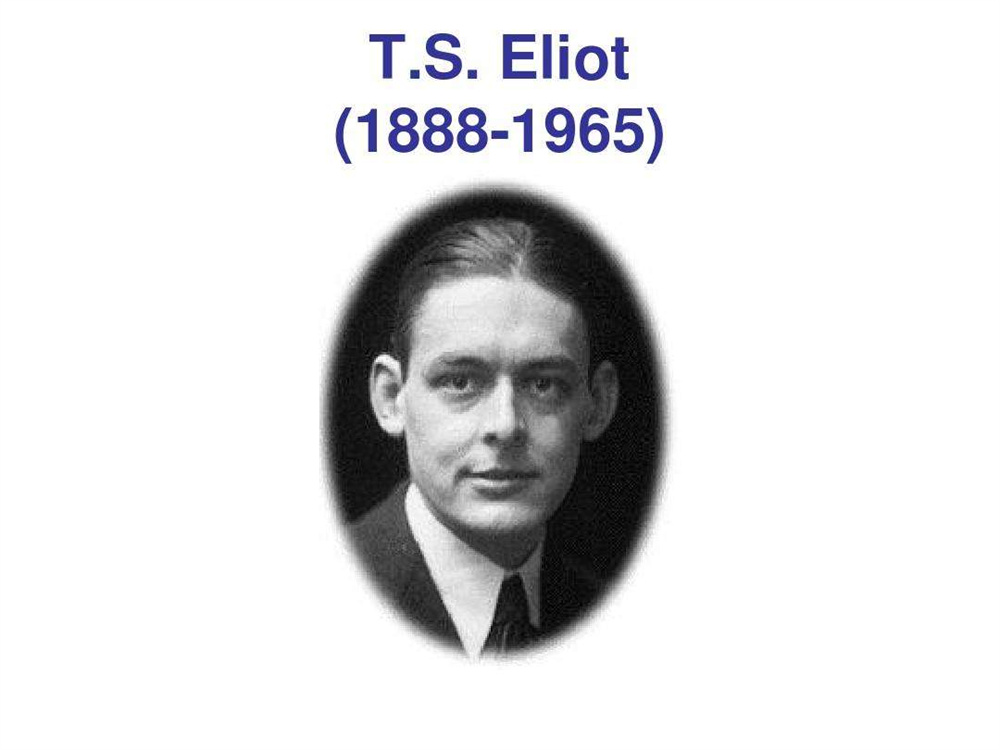
艾略特
正因为叶公超等人的大力译介,在当时中国新诗界促成了一轮“《荒原》冲击波”(孙玉石语)。现在看来,叶公超对艾略特的评论仍具有相当的敏锐性和穿透力。他认为,“《荒原》是他成熟的伟作,这时他已彻底地看穿了自己,同时也领悟到人类的痛苦,简单地说,他已得着相当的题目了,这题目就是‘死’与‘复活’”。他还指出“等候着雨”就是《荒原》的“最serious(严肃)的主题”。
而在诗艺方面,叶公超称《荒原》为“诗中最伟大的实验”,因为它“是综合以前所有的形式和方法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叶公超并没有就技术谈技术,而是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爱略特的诗所以令人注意者,不在他的宗教信仰,而在他有进一步的深刻表现法,有扩大错综的意识,有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爱略特的方法,是要造成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要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
“要造成一个古今错综的意识”,“要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叶公超深刻把握了艾略特诗艺的性质。所以他这样的译介能够扩展和深化一个时代的诗学意识。1930年代中国新诗坛上卞之琳等人受到艾略特影响的诗作,可以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荒原上的丁香”(张洁宇语)。
到了1940年代,艾略特、奥登对中国新诗诗人尤其是对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影响就更大了。正是这种影响,有力推进着穆旦等一批新锐诗人对现代性的艺术追求。比如穆旦的《五月》一诗,就明显采用了《荒原》式的不同文体的拼贴方式,全诗由一种别出心裁的“正文”与“副歌”组接而成:“副歌”为五首才子佳人、风花雪月式的旧体诗的戏仿,“正文”则是一种穆旦式的诗,语言富有现代肌理和内在张力,高度浓缩到要爆开的程度,甚至有意识地用了一些充满暴力的军事用语和工业性比喻,极尽现实痛感和战争期间的残酷荒谬。这样,在“正文”与“副歌”之间,正好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对照,并产生了强烈的思想艺术的张力。可以说,正是由于艾略特、奥登的激发和启示,穆旦他们找到了进入到他们自己的现实的方式。
澎湃新闻:你什么时候第一次读到了《荒原》,当时有着怎样的感受?
王家新:我是在1980年代初,从袁可嘉等人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卷)中第一次读到赵萝蕤的《荒原》译本的。它和那时我读到的里尔克、叶芝、奥登、瓦雷里、洛尔迦的诗一起,对我构成了对我的一生都至关重要的“现代性的洗礼”。至于《荒原》那时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幅时代的巨型壁画或交响乐,我难以一一描述,作为一个年轻诗人,在当时我也很难一窥其全貌。我记得我在诗中划满了标记,那些片段和句子可能是最刺激我的地方。但即使在那时我也意识到了:这是一部需要我反复阅读的启示录式的作品。我们到现在也很难说我们可以穷尽它。
澎湃新闻:在此后反复阅读的岁月里,你对《荒原》的感受发生过变化吗?
王家新:的确,对《荒原》的阅读和领悟会伴随我们一生。1993年我在伦敦时,曾写下这样的句子:“乌云在街头大口吞吐、呼吸,这就是伦教。而当它变得更阴暗时,艾略特诗中的路灯就亮了。”后来我还曾写下《〈荒原〉的第八行》《“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讲话”——艾略特的〈荒原〉及其反响》等文,再后来我研究过赵萝蕤和穆旦对的《荒原》的翻译。就翻译而论,赵萝蕤的翻译不仅为首译,而且在很多方面都难以为后人超越,穆旦的翻译,他自己不太满意,他曾建议友人还是读赵萝蕤译本,但他却能赋予他的译文以特有的语言力量,这是一般的译者做不到的,如穆旦译《荒原·死者的葬仪》的一节——
可是当我们从风信子园走回,天晚了,
你的两臂抱满,你的头发是湿的,
我说不出话来,两眼看不见,我
不生也不死,什么都不知道,
看进光的中心,那一片沉寂。
荒凉而空虚是那大海。
这样的译文,不仅精确地再现了一种现代诗的质地、难度和异质性,而且十分深刻感人,好像读到这样的译文,我才真正进入了《荒原》的内核。我在那里也“说不出话来”“不生也不死,什么都不知道”,但却可以“看进光的中心”了。
多少年过去了,《荒原》并没有“过时”,和历史上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性作品一样,它已成为一种要求我们不断去“重读”的东西。而每次重读,我仍有一种新鲜感和钦佩感,都会惊讶于艾略特那种无比成熟而又诡异的心智,那种深邃而又广阔的历史洞察力,以及《荒原》本身那种在今天看来仍很奇妙的在对照、反讽和拼贴中不断产生诗歌含义的结构及叙述方式。
澎湃新闻:近几年你对《荒原》也有了更丰富的理解?
王家新:《荒原》不仅没有过时,从多种意义上,我们仍生活在“荒原”中,就像艾略特本人从伦敦城里走过时感到仍生活在但丁的地狱中一样。
《荒原》是对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命名”。什么是“荒原”?有人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的写照,有人说“荒原”就是神性消失后的人类生活本身。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生活出发对它的阅读,比如说,《荒原》十分阴郁,仿佛是但丁《地狱》的现代版,只是在诗的最后一章“雷霆的话”里,有一点希望的迹象:“刷地来了一柱闪电。然后是一阵湿风 / 带来了雨”(赵萝蕤译),大雨将临这片干涸的荒原,而雷霆却说着一般西方读者所不懂的梵文:“datta,dayadhavam,damyata”,这多少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全诗以这三个梵文词结束,它引自佛教典籍《吠陀经》,意思是:“舍予,慈悲,克制”。
我注意到这个耐人寻味的结尾,并体会到它在巨大悲悯中的克制和一丝反讽,也是近些年来的事情。这说明对《荒原》的阅读,如同对一切伟大作品的阅读,都需要伴随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体验,需要某种如叶芝所说的“随时间而来的智慧”。
澎湃新闻:回过头看,你认为《荒原》对你,以及你这一代中国诗人是在何种意义上产生了影响?
王家新:《荒原》是在经过了长时间禁锢之后,重现在中国诗人和读者面前的。它在1980年代初的“重现”也正是时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我们自己的“荒原”上醒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看清并走出我们自己的精神废墟。这就是说,《荒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
当然,对于《荒原》的巨大影响力,也有不同的看法。美国诗人威廉斯就曾说“《荒原》的出现是美国诗的一场灾难” 。但问题是,这场“灾难”却是现代诗歌必须经历的。没有这场“灾难”,威廉斯本人也不可能在诗艺上另辟蹊径。
就我个人而言,在艾略特的作品中我更看重《荒原》。诗人的另一部著名长诗《四个四重奏》,在诗艺上更加精湛,也具有个人精神史上的总结意义,但我觉得还是《荒原》更具有“原创性”意义和冲击力,它更丰富、也更具有不断到来的生成性和启示性。我喜欢它那种“破碎的完整性”。
至于《荒原》对中国诗人的影响,还要结合到艾略特的其他作品和文论,它们是一个相互呼应的整体。如艾略特在其影响深远的文论《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的“历史意识”(The historical sense,又译为“历史感”):“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的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卞之琳译)
这一段话,很多中国诗人和评论者都一再引用。我们现在也会更清楚地看到,正是这种“历史意识”使艾略特本人对个人与传统、诗与时代和文明的关系有了更开阔和透彻的把握,使他有可能在《荒原》中“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说话”,而不是仅仅发出一些个人的不连贯的梦呓。正是这种贯通古今的“历史意识”,使他发明了一种别具匠心的“引文写作”,以让所有的年代都“并存”于现在,从而使他的“荒原”成为整个西方文明和心灵的艺术写照。
与这种“历史意识”相关的,是所谓“非个性化”诗学。艾略特是以反浪漫派诗风的姿态走上诗坛的,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他指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他甚至声称“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对这种“非个性化”诗学,尤其是对“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这种“高论”,在早年我并不是特别理解,现在则完全理解了:他为我们昭示了一种艺术精神的至境。
“历史意识”及“非个性化”构成了艾略特诗学思想的核心。耐人寻味的是,艾略特还声称这种“历史意识”对一个“过了25岁还想继续作诗的人”,是“最不可缺少的”。可以说,我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许多诗人“过了25岁”还在继续作诗,并且一直写到了今天,其原因也在于我们听从了这样的教导。最起码,它帮助我们跨越了青春抒情阶段,开始试着“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讲话”,并进入到愈来愈成熟、愈来愈开阔的文学的成年。
澎湃新闻:每年四月,不少人都会引用“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你怎么看待《荒原》与当下的关系?
王家新:毫无疑问,《荒原》正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次上演,全球性疫情、战争、日益加深的生命困境,都会使人们对《荒原》有了更切身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我理解人们爱引用“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句名句。
《荒原》这部长诗创作于百年前,但它又是“指向未来”的,它又在不断引领我们“进入当下”,这就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只不过它与当下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接和简单。比如《荒原》那个插入了梵文引文的结尾,现在看来,诗人让结尾时的隆隆雷声说着充满奥义的“外语”即梵文真是再恰当不过。这充分体现了艾略特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反讽性认识,或许还透出了以另一种文化参照来反观自身文明危机的意图。此外,这样做也出于对诗歌本身的尊重,诗人面对的,是整个时代和文明的问题,但他不愿提供明确结论,他要使他的《荒原》自始至终保持一种“多声部”的、充满暧昧和悖论的性质。正如瑞恰慈所说,《荒原》提供的不是说教,而是“思想的音乐”。愿我们也能这样来倾听《荒原》,或者说,倾听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时隔百年的《荒原》何以依然鲜活?当我们纪念艾略特,纪念《荒原》,我们是在纪念什么?
王家新:是啊,时隔百年,我们在纪念什么?要回答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想起的仍是《四个四重奏》中的那两句名诗:“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这两句诗已成为艾略特先生的墓志铭,而我们仍在“荒原”中跋涉。或者说我们仍处在某种文学精神、生命和命运的循环往复中。我们所要做的,是在万般艰难中,在《荒原》这样的伟大范例之后,能够继续打开文学和生命的新的一页。
- 中国文学在加拿大的翻译与传播[2022-04-22]
- 汉语语境中的西语诗歌翻译实践[2022-03-29]
- 王家新:诗无论古今,“崇高”依然是一个很高的标准[2022-03-14]
- 川合康三谈李商隐与诗歌[2022-02-17]
- 解说叶芝:瞄准作者本意[2022-02-14]
- 用翻译点亮海海人生[2022-02-14]
- 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创作与接受的对谈[2022-02-11]
- 高峰枫谈维吉尔与《埃涅阿斯纪》[2022-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