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祥龙:哲人远行
2022年6月8日晚上10点50分,张祥龙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3岁。张祥龙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以现象学、儒家哲学和东西比较哲学研究闻名于世,他对中国文明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对中华文化复兴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其著述文章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亦多有启迪。
张祥龙先生治学严谨,学贯中西,会通古今,在东西方哲学比较、现象学和儒家哲学等领域造诣深厚,成就斐然,他的学术思想气象恢弘,自成一家。在现象学研究方面,张祥龙先生以海德格尔哲学为起点,融入中国传统体道方法,别开生面,推动了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思想的结缘,促进了海德格尔的中国化。他对现象学的研究极富新见,在汉语学界乃至国际现象学界都卓然自立。长年来张祥龙先生在比较哲学研究领域进行了卓越的探索,为深化哲学的理解和各文明哲学之间的对话,带来了诸多启发,开创了包括印度哲学在内的东西方哲学比较的新思路。张祥龙先生积极探索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范式。他早先以现象学方法研究先秦诸子,后逐渐转向并集中于儒家哲学研究,旁参印度古学,参酌现代西方哲学,体大思深,发人未发,成为儒学思想当代建构的重要代表人物。
《中西印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一书是张祥龙先生最后出版的著述之一,该书源于张祥龙先生在北大同名课程的讲稿,是一本带有普及性的哲学导论,在比照和互文中呈现不同文明的哲学特质。经出版方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其中《先秦真知观》一章部分文字发布,谨表纪念。
——编者按

张祥龙先生(1949.08.14-2022.06.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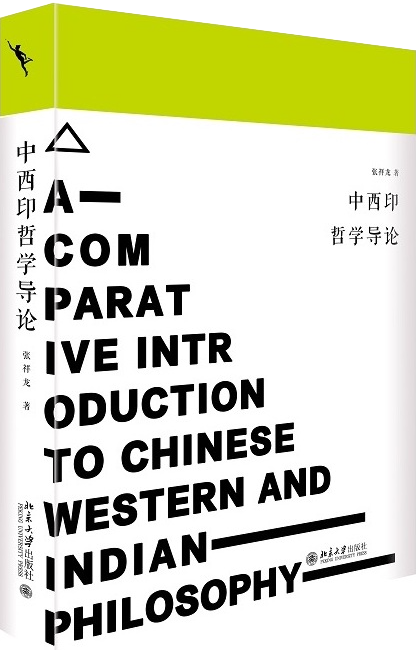
《中西印哲学导论》,张祥龙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设想一下,如果持另一种终极实在观,即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观点(主张终极实在是不变的存在本身),而是认为终极实在是处在变易之中的,那么整个知识论的格局会有什么改变呢?当然会有巨大的转变!而我们以前也看到了,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观点。如果终极实在处于变易之中,那么主客之间的所谓异质性就不那么硬性了。正因为整个存在的根基处是正在变化着的,于是就可以设想,所谓主体和客体是这存在的不同变体,它们正在参与同一个生成过程(比如阴阳大化过程),因而可以达到相互融合,或者说它们只是一个既行且知的过程的不同表现而已。这恰恰就是中国古人对真知识的看法。
所以这个主客异质导致的无公度性问题,在中国古代很不突出,因为终极实在本身就是一个发生的和相互理解的过程。我们可以先看一个例子。《庄子·秋水》(《资料》,第213页左)讲了一个寓言(这本书里充满了寓言),它是这么说的:“庄子与惠子[惠施]游于濠梁之上”,濠就是濠水,在今天安徽凤阳县附近,梁就是桥。他们两位,即庄子跟惠施,是好朋友、诤友,碰到就一直辩论。这二人站在桥上,庄子看见水里有鱼儿在游,就说:“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你看这鱼在水里游得多么快乐呀!惠施马上反驳:“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你怎么知道[‘安知’]……?”这就是认知的问题,而惠施特别强调主体跟客体的异质性对认知的阻障作用。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以彼之矛反过来攻击他。惠施马上反驳:“我非子,固不知子矣”,我不是你,当然我就不能知道你;但是“子固非鱼也”,也就是:有一点我是不会搞错的,即你肯定不是鱼;“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因此,你不知道鱼之乐是毫无疑问的了。这里惠施的论辩好像占了上风,逻辑上更进了一层。看庄子怎么说,他现在已经被逼到绝境了。“庄子曰:请循其本。”让我们回到原本处吧。你向我发问道:“‘汝安知鱼乐’云者”,你问我“你是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等,那么就表明,你“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你本来就已经知道我知道鱼之乐了,只是在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里好像有点儿诡辩,但其中的道理见后边分析)。那么我就告诉你,“我知之濠上也”,我站在这濠水桥上就知道水中鱼是快乐的了。
这里庄子论辩的要点在哪里呢?就在这“请循其本”,即让我们追踪到我们辩论的根本处。那什么是此辩论的根本处呢?当然是思想语言的交替使用和相互理解。你问我怎么知道鱼之乐的,我回答;你懂了我的回答,于是再问;我懂了你的问题,于是再答。你既然能问我,我也能答你,说明我们有一种非常根本的语言上的和意义上的交流,也就是某种相互认知。你以为:我不是你(我非子),你也不是我(子非我),我们就相互“不知子”或不知晓对方的意愿或意思了吗?不是的呀!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你的客体,你也是我的客体,我是主体,你也是个主体,但是我们居然可以通过语言乃至其他途径(比如表情和手势)而发生有效畅快的交流和相互理解。那么,即便我不是鱼,鱼也不是我,你怎么能断定我和鱼之间没有一种根本的、在主客分离之前的交流呢?我与你可沟通,那么我也可以在这桥上与水中的鱼儿沟通啊!这是庄子更深的含义和论证。表面上庄子是在抓话语间的“你怎么知道”这个话头,但是里边有深意。也就是说在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分离之前,我们已经处在了某种相互纠缠、交融的状态中,所以我们才能够进行语言和意义的交流。那谁能断定在我们跟鱼之间、我们跟万物之间没有一种根本的纠缠和交流呢?这是一个反映中国古代认知观特点的很犀利的论辩例子。于对话当场层层深入,丝丝入扣,首尾回荡,颇有些禅宗对话的味道,只是理路更清晰细密。
所以,中国古代关于真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主客的静态相符。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哲人来讲,认识真理主要不是克服主客异质而达到普遍必然性的问题,而是一些动态的问题。也就是要在有无相交缠的生成之处,来理解、对付、预知生成变化的结构、趋向、节奏和样式。
中国人确实很实际,一切哲理都源自实际生活经验,可是中国人的实际不是说不要理论,关键是其理论走向与西方不一样。就此而言,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突破“时障”。我们生活在现在,怎么突破现在与过去,尤其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那个屏障,让我们的认知和思想能够穿透过去,尤其是能够走向未来,预知事态发展,这才叫真知。中国古人最看重的恰恰是这种知识。
这种突破时障、朝向将来的时几(机)化特点,在《周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而无论是孙子、老子还是孔子,概莫能外。传统西方这一面,我们已经看到,那些知识形态、认识论形态想找到的是普遍必然的规律,用它们来规范人生和世界。这种知识就不是预知活生生的未来,而是要制造未来。人为自然立法,科学改造了整个世界,把我们的未来全部重新塑造。中国古代的哲理不是这样的。它认为自然的变化、整个人生态势的变化本身就有合理性,我们不但要跟着它走,还要知道它本身是怎么回事。这与西方的认识论是大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知识中,时几(机)、事态、记忆或者说是变化的样式,比如往返等,都是最受关注的。时几是时机之源,而“几”恰恰是《周易》特别强调的。“知几其神乎!”(《周易·系辞下》)认知的要害和神髓就是要“知几”。“几”是“动之微,吉之先见[现]者也”(同上)。这里“吉”指预兆,已经出现了这个势头,已经出现了存在的势态,但是还没有见诸明显的形式,也就是还没有被实现为可把握的存在者。有无正在交织着。“动之微”,指非常微妙的变动,但是这个“动”已经出现了,一个趋向已经出现了。很多人都看不到它,只有真智者,也就是中国古人认为的那些得到了真知识的人,才能够看到此“几”。这是中国古代知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即感知和追随那朝向未来的趋向,具有很强的时间性、时几(机)性。但是为了朝向未来,就须特别重视过去,能够回溯以前的、古代的事情,在一圈圈的回旋中获得冲向未来的动势,而且,只有找到这种回旋的内在结构,你对历史的回顾才能帮你知道未来。因为历史有重复之处,但更有出新之处,必须领会了时几的微妙结构,才能真正突破时障。
除了这突破时障、朝向将来的时几化特色,中国古代知识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用势。“势”和“几(机)”基本上是相通的。“势”往往是无形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山上的一个堰塞湖,或一块大石头处于悬崖边上,它们就有一种向下之势,但它还未被实现出来。如果你认识到了,并善于运用它,例如你有本事把敌人引到它下面,而你自己处于上面,再加上山道相当狭窄而无法躲避的话,那几乎就赢定了。或者说,时值冬日,但过几天将有反常的东南风,谁要事先知道了,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那么现在还完全无形的风势到那天就会以时机化的方式实现出来,凭之而摧毁敌方几十万大军,改变历史走向。《孙子兵法》就是探讨怎么能把自己放到那个优势位置,而把敌人放到那个劣势位置,则我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到那种情况,敌人只能投降,不然的话,巨大的石头从上面滚落下来,人的求生本能就使之要躲开,也就相当于投降了,于是当即拿下。
所以我刚才问那个同学:战争之术是不是有不战而胜的境界?很多西方的战略家,比如克劳塞维兹,就不承认有这样一个境界,认为战争永远是打出来的。当然,事先谁谋划得好、安排得好,就可以创造得胜的机会,但是不战而胜这个境界怎么可能呢?敌人来就是跟你打的,怎么会不打就投降呢?我看我国军事科学院写的《孙子兵法》评论,有的就认为此境界无法理解,是《孙子兵法》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当然也不是完全否认,但是从道理上无法理解。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认知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通过“势”来认识真相,因为这真相处于变化之中。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生活在“势”里边。你想想你的24小时是怎么度过的?几乎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不用反思,顺势而行。你们在听我讲话,我根本不会注意到我发音的时候这个喉头是怎么震动的,话就讲出来了;你们也不去分辨我语音中的音素,囫囵个儿地就明白了我的意思。走路,抬腿就走;骑自行车,蹬上乘势就骑。势态根本不用反思,如果你还要去思考、细察,说明出了问题,比如你的车的车胎没气了,或者车链子掉了,或者你的身体哪儿不舒服了,以至无法用势。
第三个认知特点就是技艺化。中国古代认识论中更看重的是“技”和“艺”,而不是逻辑分析、形式推理和抽象理论的建构。当然也有理论,阴阳五行就是很高深的理论,某种意义上也很抽象,但它是活的,一定要体现在活生生的生发和维持的过程之中。所以孔子要以六艺来教学生,同样可以想见,老子和庄子教学生,也是凭借技艺而活泼多姿的。你去看《庄子》,其中“庖丁解牛”“梓庆造”等,讲的都是手艺人,通过精绝的手艺而得道,此外还有或显或隐的气功修炼的技艺。佛家则重打坐参禅。这是印度传来的技艺,即瑜伽的变式。关于瑜伽,以后我们会专讲。但是中国的禅宗对参禅的技艺加以变化,不一定非要坐禅了。坐禅修行当然也可以,但只是开悟法门之一。嬉笑怒骂,搬柴担水,机锋对谈,棒打刀削,只要能够开启智慧、摆脱执着,让你进入人生思想的生动过程中的,皆是禅机。
由于这个缘故,在中国古代知识论的视野中,对变化的发生结构、时机生熟和实现样式的关注几乎是高于一切的。比如其中的一个变化样式就是往来或循环。我们以前讲到《周易》中至简至易的结构——阴阳结构,凭借这么简单的区别性特征来实现它的具体含义时,要通过大量的往来、循环来表现,所以中国古人对于循环结构非常敏感。如果它只限于形式上的循环,那就没什么意趣了。中国人觉得《易》讲的天地四时的循环,或过去未来之间的某种循环,比如按阴阳五行结构进行的循环,越循环越能出新意。《周易》说:“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周易·系辞上》,《资料》,第128页右)又说:“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周易·系辞下》)日月、阴阳往来的时间构成中,隐藏着往来循环的微妙结构,因而含有无穷的“神以知来”的可能。
因此,中国古代知识论的要害,就是要知变化之道。“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周易·系辞上》)什么是“真知识”?就是知晓变化的道理和样式。“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周易·系辞上》,《资料》,第127页左)一位君子要想有所作为,要采取行动,就要去询问《易》以知变易的趋向。“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同上)《易》回应此君子的蓍问,如响应声,不管何种非对象化的隐幽事态,都可曲折透入而知将来之物。所以“往来”的根子在时几,往指过去,来即将来。“知来物”正是要害。“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同上书,第128页右)《周易》的神妙就在于可凭之明了天下之至变。于是在这儿摆弄摆弄那五十根蓍草,算将起来,实际上是算入了时几的微动处,就能够预测未来。现在的网络小说,不少是“穿越”式的,也就是当代的一个人,比如一名特种兵、一位工程师、一个大学生,凭借某种机缘回到了过去,在三国、宋朝、明朝、清朝乃至抗日战争时期大显身手。而这些主角儿之所以能干出一番改变历史的大事业,就是因为他预知了未来。但这只是文学的虚构,不仅从技术上做不到,而且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如果他改变了历史,那么他本人还能不能存在呢?很危险呀。未来影响了过去,而改变了的过去也会影响未来呀。但《周易》却是真真实实地“彰往而察来”,靠的不是取巧,而是进入非定域的感通之几。“《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干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同上)。《易》的思维与观念化思维很不同,它在后者的意义上是“无思”“无为”,但又完全时机化,被情境触动后,就“感而遂通”天下之事。因为它进入了阴阳不测的神妙处,即可深入幽深事理而探究对象事物的几微征兆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