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力斌 周明全 喻向午:有关文学基本问题的时代申辩
编者按
2009年,李敬泽出版了一本书叫《为文学申辩》。他有感于文学作为一种弱的事物“备遭猜疑蔑视”,也为部分文学维护者们渐趋僵硬的思维模式而痛心疾首。13年过去了,当我们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凝视文学时,有关“文学的价值和可能”的问题收获了新的视域,也遇到了新的经验疑难,这一切都等待辨明和澄清。本期“对话”,师力斌、周明全和喻向午三人均是长期耕耘于文学第一现场的写作者和期刊编辑,他们将在文学生活内外,为我们小心求证它的基本价值和时代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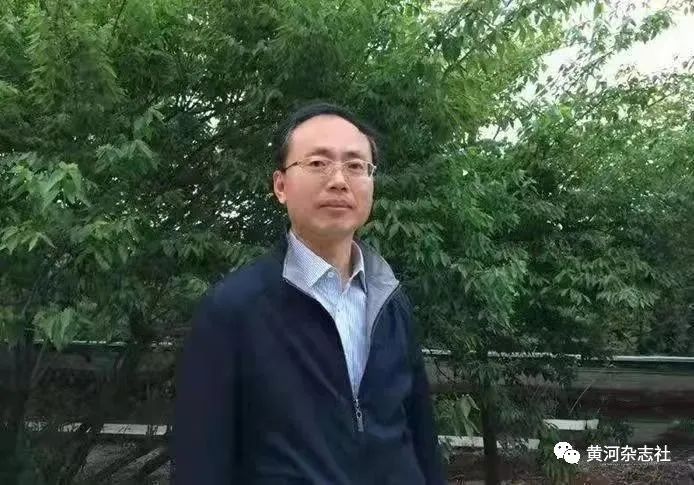
师力斌,笔名晋力,山西长子人。诗人,评论家,文学博士。199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政治学系,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获全国首届新田园诗大赛、巨龙杯首届高校诗歌大赛、第三届名广杯诗歌大奖等奖项。自印诗集《心灵散步》《筒子楼静坐》,著有《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杜甫与新诗》,编有《北漂诗篇》四卷(与安琪合编)。

周明全,1980年10月生于云南沾益。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约研究员。在《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等发表文学评论文章多篇。著有《隐藏的锋芒》《“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70后”批评家的声音》《中国小说的文与脉》等;主编《“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与陈思和共同主编)、《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等。曾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文学报•新批评》2015年度优秀评论新人奖特别奖,2020年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批评家等。

喻向午,1972年生,湖北大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文化译著一部,在《文艺报》《文学报》《小说评论》等报刊发表文学理论、评论文章若干。另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若干。曾任湖北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江西省文化艺术基金等奖项和项目评委。
1、现实比虚构更精彩?
师力斌(北京文学期刊中心副主任,以下简称“师”):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牵涉到文学创作理论中一个常见的关系,生活与艺术、现实与虚构的关系。从理论上讲,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虚构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个公式可以轻松地套用到所有写作当中,简单粗暴,左右逢源,一劳永逸。但是,经常难以在感受上说服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遭遇无数莫明其妙、神秘莫测、匪夷所思的事情,冲击三观,炸开脑洞,惊爆眼球。且不必讲历史上那些宫廷秘事和英雄传奇,仅就当下感受而言,全球疫情中出现的无数奇葩故事,俄乌冲突的突然爆发及其过程中的稀奇古怪,足以让人瞠目结舌。所有这些现实传奇,超乎我们的想象和认知,闻所未闻。在这种感受下,任何人都会认同:现实比虚构更精彩。然而,问题是,这些精彩都归于新闻,归于现代传播,并没有在文学中呈现。文学似乎落后于新闻,捉襟见肘。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就轮到虚构登场了。回想一下那些文学经典,《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传》《哈姆雷特》《哈利波特》《指环王》,它们又远比现实精彩。有些经典,精彩了一代又一代,久盛不衰。是现实精彩还是虚构精彩?作为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
周明全(《大家》杂志主编,以下简称“周”):现实比小说更精彩,现实比小说更荒诞,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阎连科甚至说,现实比想象还要荒诞。那是不是说,就可以不要小说了?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文学创作将现实生活的原材料作为创作的基石,通过艺术加工,生发出既来源于现实生活又别于现实生活的具有超越性的“建筑品”,这个超然于现实之上的“建筑品”,才是文学和艺术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没有超越,简单地白描、记录现实,或者和现实的虚构、荒诞竞争,那还要文学作品干什么。作为作家,必须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绝非狗皮膏药与皮肤式的那种粘贴,文学是一种艺术行为。
在我看来,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把历史和现实完美地安放在文本中的,或者说,但凡伟大的艺术,一定既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它们最终都指向人性。
最近再次看了周绍良批校的《敦煌变文集》中的《孟姜女变文》,也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这本是一个爱情故事,范喜良和孟姜女相亲相爱,但范喜良却被抓去修长城。孟姜女千里寻夫,结果,自己的丈夫死了。孟姜女悲痛交加,手拍长城,失声痛哭起来。成千上万的民夫也跟着孟姜女哭得天昏地暗。忽然“哗啦啦”一声巨响,长城天崩地裂似的倒塌了。孟姜女哭倒长城,这是文学的想象力,现实是不可能的。哭倒长城,这是文学化的历史,这同时也是历史的意愿,是民心所向,它高度概括了历史发展中的倾向,同时它却穿透了人性,成为数千年来影响至深的一个民间传说。其实,孟姜女哭倒的不是长城,而是暴政本身,这是对秦始皇暴政最大的、最有力的批判。
我个人认为,当代作家对历史、现实和文学这三者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没有文学责任。作家没有文学责任,如何去书写历史和现实?文学是要有责任心的,对历史和现实负责,这是作家无法逃避的。我们现在只讲对文学负责,这是不全面的,作家的第一责任是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第二责任才是对文学本身负责。只对文学负责,就变成了为搞文学而搞文学。
喻向午(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编审,以下简称“喻”):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话题,谈论它需要相应的语境,否则就会造成歧义,因此,还真不好用几句话来做是非判断。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搜索了一遍我所积累的哲学知识。想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在内容上是同构的。主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是对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反映和升华。但并不是客观世界的所有内容都能构成主观世界的内容,只有纳入到人的实践以及认知活动范围中的那部分客观世界,才能转化为主观世界的内容。实践从根本上制约着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接触范围,以及主观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可以强调现实的重要性。深入生活、扎根基层,从广阔的客观世界吸取营养,获得新的认知,不断丰富我们的主观世界,对作家的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同时,文学界还有一个最常见的认知:文学创作就是虚构。托尔斯泰曾说,没有虚构,就不能写作,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人类的精神世界需要虚构,而且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虚构,许愿,赞美、祷告,或者对邪恶的诅咒等等,都是虚构。现实不能完全取代虚构。消解了虚构的价值,也就消解了文学创作的意义。
还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行万里路,经历丰富的人,就能成为优秀的作家。文学终究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在文学创作中,虚构是无法绕开的途径和方法。现实生活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它发生的时间也许特别漫长,特别无序,可能我们就看不到结局,即使能看到结局,我们也可能看不清过程中的意义。所以,客观世界无法提供现成的艺术,也很难提供发展的、完整的故事;提供的更多的是碎片式的情节,或者不完整的故事。王安忆说,虚构就是在这样漫长的、无秩序的时间里,要攫取一段,这一段正好是完整的。一个作家,一个生活在局部里的人,他可以狂妄地要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周期。王安忆谈《史记》时还说,在特别漫长的时间里,规模特别大的空间,确实有一个全局的产生,但这个全局太辽阔了,我们的眼睛太局限了,我们只可能看到只鳞片爪,而司马迁将这一个浩大的全局从历史推进文本,成为目力所及的戏剧。这就是虚构。
我们生活在当下,当下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也终将会成为宏大的历史。成为历史的现实如何“复活”?作家无法再进入过去的现场体验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被记载下来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物,也许就只有几句话。那些永远消失的细节和情节,只会在作家的虚构中,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了。虚构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作家的重构成为可能,这也是我们需要虚构的理由。回顾历史,时代和社会的具体风貌如何,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由作家呈现的结果。
当然,虚构也需受到现实的约束,虚构的文本要能得到现实生活的印证,经得起生活常识和逻辑、情感、伦理等等范畴的检验,否则,凌空蹈虚,不切实际,也将无法获得读者的信任,更无法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
在文学世界里,现实与虚构,从来不是非此即彼,或者厚此薄彼的关系,而是一对镜像关系,一起建构了人类丰富的精神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它们形影不离。
2、中短篇小说一直是各大文学期刊发表的主要门类之一,请略谈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前景。
周:我做编辑,每期看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发现一个让我很惊奇的现象,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域的小说家,题材的重复度非常高,而且更让我吃惊的是,故事的推进、结局几乎大同小异。很多小说,只要看开头,就几乎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不会给阅读带来兴奋感和神秘感。同时,很多小说没有为我们提供必要的信息量和知识量,批判太多,以新、奇、怪吸引眼球,但知识量小,审美不够。我想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我们当下的写作陷入了概念化,理念先行所导致的。理念多,口号多,但就是没老老实实地遵循小说创作的基本理念。文学是要有责任心的,对历史和现实负责,这是作家无法逃避的。
小说创作,无论是中短篇还是长篇,我现在还是觉得60年代这批作家整体写得好。至于前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也不必悲观,我还是相信,会有一批优秀的年轻作家能在小说艺术上有所作为的。
喻:相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短篇小说的读者群在不断萎缩,社会关注度在不断降低,这是不争的事实。记得20世纪90年代,很多报纸副刊还在刊登短篇小说(主要为小小说),现在已很难见到。当下的一些出版热榜上,还可以见到不少长篇小说作品,但已经难觅中短篇小说或者中短篇小说集了。何以发展到这样的局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包括但不仅限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等等深层次原因。
中短篇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逐渐成了小说大家族中的弱势群体。长篇小说在出版社的市场化经营下,美学风格越来越世俗化和通俗化,同时也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市场化显然不是中短篇小说的强项。如贺绍俊所说,短篇小说就像是一块磨刀石,作家们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中不断磨砺着自己的文学性。因此我们也不必为短篇小说成了弱势群体而伤感,相反,我们要为短篇小说而感到骄傲。它具有强大的韧劲,它坚守着文学的理想。
中短篇小说的阵地今后仍旧会在文学期刊上。它的前景是越来越小众化,读者也将越来越专业化。
师:这同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果断回答的话,创作旺盛,前景可观。目前,中短篇小说是国内主要文学期刊的主打内容,绝大部分刊物都开设了相关栏目。作品发表以后,评论,推介,结集出版,参加评奖,整个领域的活力相当旺盛。在这个领域深耕收获的作家人数相当可观,成果也相当丰硕。每年的文学排行榜都会冒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年轻新锐小说作家。如此,中短篇小说便事业兴旺了吗?这样的回答绝不能让人满意。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问,中短篇小说现在是否能有举国谈论的轰动效果,正如当年人们谈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爱,是不能忘记的》一样,人们在弱弱地问,排长队购买《红岩》《青春之歌》的奇观是否还会再现?或者什么时候中短篇小说能再像《红高粱》一样转换成家喻户晓的电影,为文学从影视抢回风头?稍对这个行当有点期待,便会进前一步,追问它在整个文艺中的位置和作用。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当下中短篇小说产生了哪些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在何种层面上,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文本和叙事经验?一旦我们的参照标准发生位移,我们的判断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的态度就会由坚定向犹豫游移。老问题重现:有高原,是否有高峰?
3、在碎屏化的视听时代,长篇小说还有生命力吗?为什么?
喻:前面我们提到了长篇小说。相对于中短篇小说而言,长篇小说还有一定的阅读市场。像贾平凹、余华、刘震云等等作家,凭借自身影响力,他们的长篇小说出版,还能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比起网络上各种类型小说蔚为大观的读者群,传统的长篇小说也只能归于小众市场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严肃文学一再边缘化,文学界也逐渐默认了这个事实。长篇小说作为严肃文学大家庭中的“种子选手”,肯定依然保持着生命力,虽然它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阅读市场的显要位置退居到了边缘,但只要在读者市场上,还有一些人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长篇小说就会有生命力。
师:我的看法相当肯定,有。长篇不仅是一个文字写作的问题,更是一个人生阅历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境界的问题。我相信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会有那种令人惊叹的人生阅历,也会有那种非同寻常的思想境界,是蒲松龄、罗贯中们没有的。我经常在想,马云是否会写长篇小说?省委书记或政治局委员是否会写长篇小说?即使现在不写,将来是否会写,悄悄地写?文学史并非总是发表出来的样子,很可能将来会改变。
周:这不是第一次人们感到视觉媒体对文艺、文学创作的冲击。摄影、电影出现的时候,人们也这么担心过绘画、小说创作。然而事实上,前者逼迫后者发展出了更丰富的表现手法,而并没有取而代之。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多诺等人对此都有过独特深入的论述。阿尔多诺认为电影是文化工业的产物,迎合抚慰了人们的需要,而不是像文学作品那样挑战了它们。就拿电影和小说来说,电影往往告诉我们确定的主题和情感,一个明晰的故事;小说却是道德悬置的场所,它的哲学是复杂与含混。因此这么多年来,电影和小说各行其是,电影从没有替代过小说。
我倒觉得碎屏化的视听时代不会是写作者要面对的难题,更不是长篇小说有无生命力的一个证明因素。恰恰相反,新媒介给文学插上了翅膀,让文学飞了起来。新媒介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让写作者和读者都受益其中。新媒介还是要靠语音(或者声音,而声音也是语言)传播,并没有改变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新媒介的扩大,打破了过去单一纸质媒体,有利于新人、真正写得好的人出来。
但不可否认的是,传播媒介的改变还是会多少改变小说的写作。这一点晚清民初的“传播革命”具有借镜意义。当时报纸杂志兴起,小说“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创作不再称许“闭门造车”,小说家不再追求不朽的意义,小说不再是对抗时间的艺术品;小说创作成了生活的平面移植,追求读者的震惊效应,而不像《红楼梦》那样,费十年之力,增删五次,成为一个全景式的、具有深度的意义世界。同时,小说创作也不再是静态的、个人的表达,而成了与读者互动的过程。总之,正如梁启超所说,“自报章兴,吾国之小说,为之一变”。但是尽管如此,小说的艺术标准却始终没有改变,今天看来,当时完全迎合“传播革命”的众多小说鲜有好的作品,大多人物肤浅、结构松散,而只有那些一面坚持小说艺术的标准,一面满足传播需要的作品,才能获得蓬勃而持久的生命力。
4、记得王尔德曾说过,在文学创作中,什么都重要,唯有题材不重要。您是如何理解题材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的?它们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尺度上能取得平衡?
师: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早就得到了解决,但在实践中,始终困扰着我们。对于有些作家来讲,题材并无决定作用,像博尔赫斯、汪曾祺。但是,对于另一些作家来讲,特别是那些偏于现实性的作家来讲,比如茅盾,陈忠实,题材可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写什么题材,取决于作家的阅历、秉性和技艺,不可一概而论。雄鹰喜爱辽阔的天空,而荷花偏爱静谧的湖面。
喻:这个话题本质上还是“怎么写”与“写什么”的问题。对于现实主义作家来说,把故事讲好是小说最重要的叙事伦理,但先锋作家可不这么认为,他们将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小说技艺的创新上,试图做到从形式到内容全方位的陌生化,以期让读者得到前所未有的审美惊诧。但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的先锋文学,到90年代就逐渐式微了,那是有其内在原因的。那个时期的先锋作家对于形式和内容创新的突飞猛进,让普通读者短时间内难以适应,毕竟中国文学的根基是现实主义。同时我们也看到,先锋文学以殉道者的姿态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些先锋文学的创作技巧,正被当下现实主义作家广泛采用,读者也已经习以为常。这正是当年先锋文学的历史功绩。在当下,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读者的文学素养普遍提高,特别是一些比较专业的读者,他们不仅需要读到一个好的故事,有题材的倾向性,也同样看重小说的叙事能否提供新的审美。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中,成为一个优秀作家的难度显著加大了,他不仅需要考虑“写什么”,还同样需要考虑“怎么写”,这很可能就是今后中国文学的大方向。
5、就小说来讲,什么样的稿件是您或贵刊所青睐的?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周:我本人是一个深受传统小说影响的人。所以,我个人觉得,好小说第一是故事好。小说“说”什么?就是讲好故事。这是中国小说的传统。离奇曲折的故事是打动读者的重型武器,也是小说成败的关键。一句话,小说不能没有令人满意的故事。中国小说特别是几部古典名著,故事个个都是非常精彩的。生动的人物和好的故事,几乎是中国小说最最重要的特征。第二是人物典型,个性突出。有了好的故事,还要有好的人物来承载这个故事。有血有肉,说起来就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但要真正做到却不简单。近十年来,每年创作出几千部小说,但其中少有让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人物成了浅薄作家们的传声筒和提线木偶,和创造他们的作家一样灵魂模糊且没有人味儿。如此乏味糟糕的小说,用来垫头小憩会让人做噩梦,盖鲊罐分分钟漏气,真不如一片方方正正的厚木板。第三是语言优美有力。再好的大师,面对真正要写的一部小说时,如同女人生孩子——你无法掌控你生的孩子是否如你想象的完美,连是否健康都无法掌控,这就是小说的魅力。大师同样也有很多败笔,甚至失败的小说,因为创造一部小说如同创造一个人。人是有血肉、灵魂、思想的,你无法控制的就是这些。一部小说是否写得生动,作家真的非常难控制,这就要求作家的语言要有激情,要有力量感,而且感性。语言就是鲜花的外表,语言必须像一朵花一样美。古人言,妙笔生花,就是此理。第四,要有思想深度。没有思想深度,是当代绝大数中国文学作品的一个致命硬伤。李敬泽认为,思想性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指标。在他看来,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之所以在当时广受读者热爱,除全面缺吃少穿的时代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作家们那时站在思想的最前沿,部分地解决了思想贫乏问题。
当然,不是说这四点是好小说的唯一标准,只是最基本的要素。只有具备了这些最基本的要素,谈小说艺术才有可能性。
喻:近些年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那就是AI会不会取代作家的写作。普遍一致的观点是,人工智能可以在技术方面有所突破,不断模拟人类进行创作,但它无法拥有人类的创新能力和来自生活的情感体验,因此很难完全取代人类进行艺术创作。文学创作是一个处于精神领域非常靠前的对人的审美、思想、智慧存在巨大考验的“手艺活”,它无法标准化。一百个优秀作家,有一百条通往成功的道路。辛弃疾的词非常棒,流传近千年,在当代仍受欢迎;而同为南宋的“婉约派”词人李清照一样有无数“粉丝”,他们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而是相互印证的关系,印证了在中国文学史层面,丰富性和多元化格局是源远流长的。所以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是很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我们的办刊宗旨就是“开放、包容、坚持、尊重”。但真正做到很难,这对编辑的要求非常高。
师:好小说。我和《北京文学》的同仁们期盼好小说,特别是关注现实、技艺精湛、有思想力的好小说。可能我们在个人审美上会有不同,但在好小说的问题上,大家有基本的共识。依据就是小说作品本身。那些获过我们奖项、进入过我们年度排行榜的作品可为参照。
6、近几年,您都发现了哪些新锐小说家?请介绍一下他们的写作特质。
喻:近些年来,90后新锐小说家层出不穷,像王占黑、杨知寒、丁颜、渡澜、梁豪、庞羽、王苏辛等等,都已经引起文坛和读者的关注。
渡澜是一个很特别的蒙古族女作家,她的语言和叙述风格有比较明显的辨识度,这与她的民族背景和美学观念有很强的相关性,初读她的作品,比如《昧火》《三丹姐姐的羽毛》等等短篇小说,共同特征就是营造了一个如同超现实主义梦境一般的叙事环境,读者可能会有一些“膈应”,但走进文本,走进人物内心,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民族文化和审美方式;王占黑面向都市,方寸之间,小小天地,作品中的人物,哪怕是面临困境,也经常在寻找世间动人的温情;丁颜的叙事不疾不徐,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能从她的小说中看到宁静和朴素,稍显陌生化的题材和视角,加上老到、熟练的叙述,让她的作品有了滋味;杨知寒的视野和思考的深度,以及对于世界的理解超越了她的年龄,她的叙事总能直抵人心。这些从同龄人中走出来的新锐作家,不论是在审美层面,还是思考问题的深度和方式,都有过人之处。
我们还曾转载过一个出生于2005年、名叫王宁婧的高中二年级学生的小说,如果不说年龄,你绝不会相信小说出自一个16岁少年的手笔。所以我坚信,在当下,文学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当代文学的处境一再边缘化。
周:面上的我就不谈了,大家心理都清楚。我想说的是一个小说“新人”,她叫于昊燕,大理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她博士是做老舍研究的,到大理大学工作后,除了持续对老舍和现当代重要作家研究外,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也做得非常出色。一个熟读经典,深入研究过老舍,整理、研究过少数民族神话和创世史诗,并且熟悉古典小说的学者型小说家(本质上她还是一个学者,小说只是研究之外的副产品),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作为职业编辑,我们会发现,不少小说家,是依靠才情创作的,自身的知识积累不够,导致他们很难在小说艺术上有更大的突破。格非、韩少功、李洱等应该属于学者型作家,所以,他们在小说艺术上的探索是做得非常棒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于昊燕在小说创作上,一定会取得非常大的成绩。
于昊燕近年开始创作小说,虽然创作量不大,但每篇都非常精致。首先,于昊燕的小说语言感觉非常好,在前不久我和她的一个对话中,她说:“语言一定要过关,我是对语言有洁癖的人,毕竟文学是审美的艺术。”我想,一个对语言有洁癖的小说家,在面对作为语言的艺术的小说时,她是该有多虔诚。在叙事上,她非常绵密,逻辑性非常强。若说,这只是技术层面的话,那么于昊燕的小说的意义指向是非常明晰的。各位有兴趣,可以找她小说《狗奴》《掀起你的盖头来》《丢失金鱼骨的女孩》《带着杜蕾斯出行》《红叶与狐狸》看看。
师:很开心谈这个问题。《北京文学》有多个平台渠道发现新锐小说家。我们的选刊版《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每月发表六七篇中篇小说,是从全国近百家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中海选出来的,几乎每月我们都能第一时间发现新锐小说家。原创版《北京文学》(精彩阅读)设有“新人自荐”栏目,每月推荐发表一位小说新人的处女作。另外,我们每年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都能从全国年度文学作品中精选一批优秀作家,其中不乏新锐小说家。这些年轻的作家,虽然风格迥异,各具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较好的文学技艺,有切入当下生活的能力,并充分显现自己的创作特质。
- 4年时间写出20多万字小说 南充耄耋法官编织文学梦[2022-05-09]
- 央视驻拉美记者眼中的古巴[2022-04-02]
- 赵德发:作家要葆有敏感和钝感[2022-0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