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反思”与精神史的多元图景 ——关于《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李静:洪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的新著《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集合了近年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十六篇文章,首先让我好奇的是,您持续开掘这一领域的动力是什么呢?
洪子诚:一方面是对一些问题感兴趣。比如没有收入这本书里的,讨论伏尔科夫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的真伪问题,还有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的经历,她的诗和悲剧性格等,有一些难解、神秘、有价值的问题吸引我。另一方面是觉得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开展得不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阶段。这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是个缺失。“当代文学”是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来设计自身的,文学史研究如果缺乏这个视野,很多问题将得不到深入的解释。因此,我尽管不大具备做这个课题的条件,这些年还是勉力为之,想引起有条件的学者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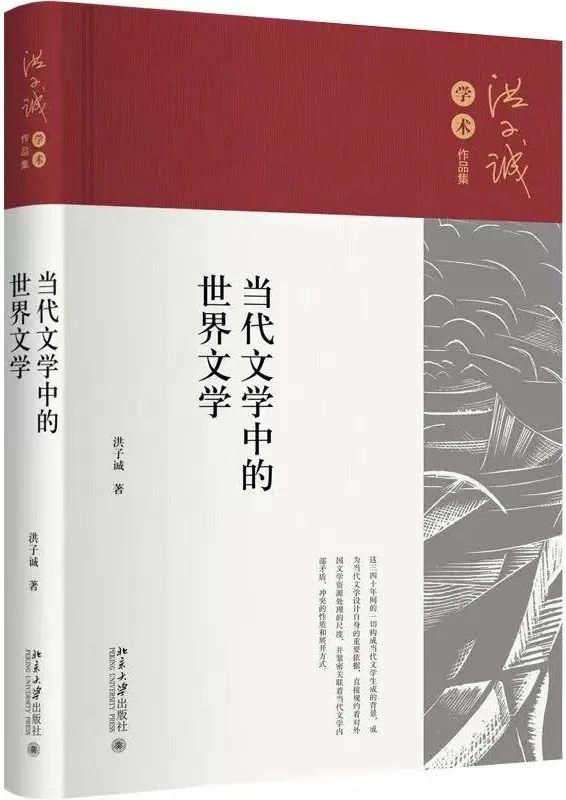
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李静:收入这本书里的文章,大多是个案研究,很少概括式的整体描述。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认为“法从例出”,还是有其他的考虑?
洪子诚:其实这是我的薄弱环节。除了编写文学史,我写作的最大问题是事先没有总体规划,缺乏设计“体系”的意识和能力。就是从读书、读材料中获得感想、经验,然后努力形成文字,有点想到哪就写到哪。有的看法,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明确,或突然发现的。这种偶然性经常发生,有时比事先确立的观点更有吸引力。理论写作有时候也和文学写作一样,会有“灵感”突然发生。只是这种情况在我这里是很偶然的,这是学识和想象力的问题。我的一些书的名字,看起来“主题”明确,其实常是将要成书的时候才有的朦胧意识,像《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我的阅读史》《材料与注释》都是这样。《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同样出现这个问题。因此,各篇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分量也大小不均,也没有整体性的论述。不过,这些个案文章,在写作的时候也潜藏着对文学史上“更大的单位”的注意。这种讨论模式,是试图从具体文本、事件里发掘与当代文学的重要问题的关联;反过来说,也就是在选择具体文本和事件的时候,会从文学史“更大的单位”来作出判断。“更大的单位”,是指文类、时期、主题、思潮等。
李静:您虽然总是谦称自己的研究方式缺乏“体系性”,但我们从集结成书的效果来看,这些文章的问题指向是清晰有力的。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如何内化俄苏、西欧的文化资源,构成贯穿全书的鲜明主线。其实您早在2015年便提出研究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的“相关性”,本书所践行的“内部反思”是否是对“相关性”议题的延续和深化?通过探索这些形形色色的个案,您认为最需反思的“内部问题”包括哪些?
洪子诚:前些年我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做过一次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关系的讲座,结束后有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找到我,说我的讨论方法不是比较文学严格的方法。她说得对,我没有受过比较文学的学科训练。我的这些文章有的也可以归入影响、接受研究的范围,不过也不完全是。我主要想解决遇到的问题,“相关性”说法的提出,与这个时期中国文学和苏联、欧洲左翼文学具有特殊关系的状况有关。因此,它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方法论概念。佛克马在《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这本书的前言(1965)中说,要把“影响”和“相似性”区分开来。他说,中国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在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有某种“相似性”,因此他的研究选择有严格文献依据的实证方法。我提出的“相关性”,既有“相似”的成分,但比“相似”要进一步;也就是说在研究当代文学建构时,要有与作为参照的对象的那种自觉关联,包括借鉴、融入、拒斥、辩论、屏蔽等,这用“相似”或“影响”都难以准确概括。这是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在方法上的设定。至于你说的“内部反思”,和“相关性”有关系,但它是另一层面的问题。
李静:是的,我们接下来再专门谈您在本书中所作出的“内部反思”。在此之前可以稍微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关于社会主义文学文化的整体反思一直在进行。其中大概有几种代表性的路径,一是借助历史档案溯源真相,以实证化的姿态解构之前的“意识形态神话”;二是通过阐释文艺与政治、社会、主体彼此塑造的过程,将社会主义文艺视为具备能动性的崭新创制,试图从中汲取正面经验;三是以更加合乎学术规范的方式,钩沉梳理大量史料,但对史料的主题式归纳往往通向既定结论,与您上面所说的兴趣使然的内驱力不同,更接近于制式化的学术生产。不知您如何看待这些面对历史经验的不同方式,又是如何生成自己的视角的?
洪子诚: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在20世纪是重要现象,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目前,余波和影响仍在延续。不管是作为历史还是现实问题,都需要认真清理、研究。你说的几种“反思”的类型,由于精力关系,阅读量少,我不大清楚,也很难抽象讨论它们各自的合理性和成效,还是要看具体的研究论著吧。社会主义文学、文化自然有它的质的同一性,但是在内部构成和演化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地域的文化传统,由于参与者不同的“文化性格”,也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的国际、国内的问题,因而存在许多并非可以忽略的差异和矛盾,存在着多样性。我在书中收入的讨论1950年代现实主义“大辩论”,讨论1960年代东欧和左翼西方文学界如何开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边界的文章中,都关注到这一点。中国文艺界1960年代批判苏联电影“新浪潮”,也显示了彼此的差异。
这种差异、冲突,确实与历史、地理、文化传统有关。举例来说,在如何对待卡夫卡、颓废、现代派等问题上,出生于1905年的萨特说:“我在象征主义文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统治的世界生活过,后来,在自我的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西方哲学”;我“慢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同时又保有以前获得的一切”;“除了其他事物以外,是由于阅读弗洛伊德、卡夫卡和乔哀斯(现在通译为乔伊斯)……我才被引向马克思主义的”。萨特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之间存在争议,加洛蒂就不承认。他的这段话表现了不同立场、观点的文化来源。过去,我们都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看作统一的,不存在内部裂痕的整体,周扬在延安编纂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是这样。这本书在“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等专题下面,分别摘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毛泽东、高尔基、鲁迅等的论述,这种编选方法,显示了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的见解似乎完全一致。但其实他们有一致的地方,却也有不同,有的不同还是“重大”的,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不可还原地是多种多样的,好争议的;这历史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简单地归为‘过去’”(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因此,观点相异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信仰者在论争的时候,往往会引述不同经典作家(如恩格斯),或是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论述(如早期的马克思)作为依据。面对这种复杂性、多样性,以前的处理办法是将有争议、有冲突的方面划分为正统与异端(修正主义)、革命与反动,来解决、压制分歧。现在重提这些议题,我想还是要将分歧充分释放,特别是释放那些被压抑的部分,重获多个角度、路径探寻对象的复杂性的条件。
李静:可以看到,您在书中确实非常充分地释放了那些被压抑的部分与多元化的思考路径。在您的清理之下,那些认同社会主义理念,却又遭遇主体性精神困境的作家、思想家成为主角,比如马雅可夫斯基、阿拉贡、加洛蒂、爱伦堡、秦兆阳等。您将他们的历史命运与公共形象戏剧般地剪接串联,将他们思想观念的复杂性、暧昧性与变化过程充分展现,其中蕴藏着必须直视的“我们的问题”。在观察这些问题的时候,您采用了“内部反思”的方法。我想问的是,我们如何避免陷入某种“感伤”式共情与廉价的“正义感”,进而把“内部反思”简化为“为异端翻案”?或者说,您认为“内部反思”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希望读者借此能收获什么?
洪子诚:所谓内部反思,或内部清理,是观察当代文学历史的一种角度。我的许多文章、书(如《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等)都是这个思路。采取这个方法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我把当代文学(特别是前三十年)看作具有时期特征的整体,并认为对它的深入考察具有历史和现实的价值。而且我不主张笼统地从外部加以全部肯定或否定,也不主张立刻将它删除的简单处理方式。一方面承认它的主导观念和具体实践有某种合理性,但也存在严重问题。这些问题部分存在于它的观念、纲领中,更重要地表现在某些时期的具体实践、策略里。因此需要对其“内部”做具体清理。第二,这种内部分析,却必须有“外部”的观念和历史实践作为参照,避免将讨论封闭在“内循环”的洞穴里空转。没有这种差异性的参照,许多问题将无法得到照亮。《红与黑》中的于连在临死前有一个著名的独白:“在长长的夏日中,一只早上九点出生的蜉蝣,到傍晚五点就死去了,它又怎能理解黑夜是怎么回事呢?”不理解黑夜的蜉蝣,也不可能真正懂得所经历的白天。这种参照,也包括承认“内部”存在的差异,既不把“社会主义文化”看成坚硬的“铁板一块”,也避免把差异简单划分为“正统”与“异端”。第三,这一角度、方法的采取,与个人的切身经验,与人的情感结构、生命体验相关。
其实,内部反思的工作,从社会主义文化诞生之日起,特别是在演进到某一关键阶段的时候就存在,一直存在着“内部质疑者”。他们看到这一理念和实践存在的问题,这种发现,又和他们遭遇主体性精神困境有关。这本书里谈及的苏联的爱伦堡、丘赫莱依、西蒙诺夫、叶夫图申科,法国的阿拉贡、加洛蒂,奥地利的费歇尔,南斯拉夫的维德马尔,中国的秦兆阳、黄秋耘……也还包括没有谈到的胡风,一个时期的卢卡契、周扬等,都曾程度不同地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在某个时间面临一个重新检查政治、文学信仰的问题。但是他们并非全部否定自己原先的选择,只是试图在内部进行纠正。曾是法共领导层成员的加洛蒂在自传性的《时代的见证》里讲到,“我们曾自豪地把自己关闭在里面的水晶球破裂了。神奇的戒指断裂了”,“在这种焦虑中它被从内部解体了,他在自身的深渊里战栗,固定不变的一切都在它内部动摇了”。不过,加洛蒂在后来改宗伊斯兰教——这是另外的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文学史研究上的“内部反思”的性质和他们是不一样的。这是现实政治与学术(尽管与政治问题有关)的区别,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是“深渊里战栗”的生命内在性与有点游离、旁观的历史叙述者的区别。他们是要解决现实政治、文学的紧迫问题,我们有时候倒像是在偿还某种“债务”。看到那些热忱信仰者为着所信仰的事物遭受的苦难,就觉得要把努力放在为历史的留痕上,而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应夸夸其谈。
李静:阅读您这本书时,最触动我的正是这些在“深渊里战栗”的内部叩问,以及您“为历史留痕”的责任感——不是“夸夸其谈”,而是尽可能“走进”。您在书中谈到,对加洛蒂、丁玲、胡风、冯雪峰、周扬等人来说,“战争、革命、社会主义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种‘内在性’”。艺术与人相互统一,“人对现实的把握,不是凝视的,而是被经历和支配的现实”,他们是作为生产者的、行动的作家。(《内部的反思:“完整的人”的问题》)而这部分内在性往往是一般学术研究处理不了的,比如您书中提到的“大众”“现实”“深入生活”“人民性”,连篇累牍的概念辨析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那么,您是否觉得“生命史”“精神史”的探寻,更有助于我们重回“20世纪语境”?一些私人视角的材料,比如日记、回忆录或其他个人创作,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和限度是什么?
洪子诚:“内在性”是阿拉贡、加洛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思文章中提出的,他们都从自身的经历、体验,谈到信仰、道路选择的问题。在他们那里,“革命”“人民”等不是抽象的,不是观念性的符号,而是联系着自己、家人和广大民众的经历处境,也就是“人对现实的把握,不是凝视的,而是被经历和支配的现实”。这样的话,文学史研究在关注共同性主题的同时,也特别要探索不同人(物)的各自情形,他们各自是如何进入“想象的共同体”(有点不恰当地借用这个概念)的,他们在这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位置,遭遇诸种问题时的不同情感反应和采取的不同行动方式。深入这种个别、差异,有助于我们把握历史的多样和复杂,也有助于我们发现与历史主导潮流中或支持,或游离,或逃逸的不同事实。而经验告诉我们,异见、逃逸、游离也值得重视,它们在某种条件下是制衡、纠正的积极力量。从经历说,有时候可以让深陷悲观、宿命的我们暂时获得拯救。
这就提醒不要忽视个案的研究方式。整体、体系性的研究方式自然很重要,在我们这里无须提倡也很流行。相反,个案研究往往被认为缺乏整体覆盖性,被认为不全面因而受到忽视。史景迁在《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木山英雄在《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里面,都讨论了这一方法问题。它们都是讨论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的著作,但是都没有、也不试图构建全面、严密的体系。史景迁的书就是讲述几个个案:康有为、鲁迅、丁玲。他说:“书中叙及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各自的内容和形式,并不表现时下颇为流行的‘集体传记’的风格。或者说,我欲揭示的是,他们每一个人在不得不做出日常决定时所面临的困难,他们身处共同的混乱环境,他们本想置身事外却免不了的外来干扰,以及他们偶尔做了出格的决定后外界的反应等。”木山英雄的书大体上也是这样。当然,他谈到的人比较多,杨宪益、黄苗子、郑超麟、李锐、杨帆、潘汉年、聂绀弩、舒芜,等等,但是他的“取景框”却很小,仅限于他们在当代的旧体诗写作,借助他们的这部分写作,讨论他们“与革命建国以来种种运动和事件相关的……一直关注却无从看清楚的,涉及具体个人的细微部分,以重新思考其中的意义”(《人歌人哭大旗前·致中国读者》)。我在一篇谈论这本书的短文中写到,这里显示了木山英雄的历史观和文学研究方法的特点。他肯定没有,也不会认同计较、厮守于细枝末节,热衷奇闻轶事的癖好,但也警惕沉湎于总体论述,而忽略细部、忽略个体细微表现的偏向。他的研究,体现了他对差异的高度注意力,以及敏锐的分辨力。对于耽于空洞议论的危害,木山英雄有这样的话:“在权力支配下空洞的议论越多,人们的本性便越发暴露出来”。权力与空洞议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乐于结盟?这里的人的“本性”指的是什么?这句话值得深味。从个性和学术基点而言,这体现了木山先生作为一个“后撤”者柔性中的坚韧。
说到日记、回忆录、书信等,在历史研究中自然是重要材料。它们和档案、公开文献等一样,如何有效辨别、使用,检验着研究者的能力。最近我们讨论谢冕先生写于“文革”期间表达他的精神挫折的痛苦的诗,它们从未公开发表过。人民大学的孙民乐教授有很好的见解。他说,即使某些细微的私人材料,有时候也有向精神史和大历史掘发的进路;其实,“整体性的历史场景一去难再,精神史的图景大概只能通过情感的考古,隐私的考古来构建了”。
李静:上面谈了很多“内在性”的问题,我对您这本书的另一关键词,也就是“世界”,同样很感兴趣。依旧是在《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一文中,您借用20世纪80年代激动人心的口号“走向世界文学”,以此强调中俄同处落后境地,都试图克服时间差,努力在“世界历史时间”中确立自身主体性。而在《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中,您不再直接沿用洋溢着80年代气息的修辞(“走向世界文学”),而是更加清晰地阐述研究思路:“如何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来想象、定义自身,以及在此基础上,为世界文学提供何种普遍性的‘中国经验’。”在您的描述中,双向互动的视角十分突出,并明确提出所谓“普遍性的‘中国经验’”,这算是您这几年的一个变化吗,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调整?在经历了80年代“走向世界”的激情、90年代融入全球体系与建立文化认同的艰辛、21世纪初逐步确立大国叙事的自信之后,如今是否有必要、是否有可能更加综合地谈论“中国经验”的相关问题?
洪子诚:变化是有的,但也不是那么大。就是说不是那种翻转的变化。实际上“80年代气息”在我这里并没有、大概也不会完全清除,甚至也可以说它是无法去除的“底色”。不过我在自省中做了许多修正,这种修正确实不彻底。许多年前,李杨老师写有讨论我的文学史研究的文章,在肯定的同时也有批评,批评的一个方面就是我身上的“80年代气息”。这种“80年代气息”,通常的理解是指启蒙的历史观,纯文学想象,处理问题的本质化、非历史化的态度。他说,在“与洪子诚的学术对话中我曾经对他的文学观念中的80年代思想残留物进行了批评。……(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与我们这一代人并不相同。譬如说,他始终怀疑50—70年代的‘文学’价值,对我提出的所谓50—70年代文学的‘文学性’的观点不以为然。虽然一直以50—70年代文学为研究对象,在他内心深处,他仍然认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40年代的文学成就要比50—70年代文学高得多,并因此常常被我讥评为有‘小资情调’。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福柯、德里达等人对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他也始终心存疑虑。……洪子诚显然还不愿像我一再提议的那样,通过詹姆逊提示的‘永远历史化’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历史’与‘叙述’之间的永恒难题”。这是二十年前讨论我的《问题与方法》的文章里的一段话。他敏锐、准确地看到我“内心深处”的问题的症结:这确实是我的问题。我也试图能够改变,但是很难。要略作纠正的是,我其实并不特别喜欢张爱玲,尽管她感觉细腻犀利,语言技巧高超,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萧红有些粗糙的《呼兰河传》,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读起来也颇有趣。而且我也并不认为“永远历史化”自身就不必“历史化”,正如伊格尔顿说过的,如果“永远历史化”是一种真理性的表达的话,那么,这一命题自身也不能自动在“历史化”上获得豁免。
我们的自信心很好,令人鼓舞。但是我的“普遍性经验”的说法跟它没有关系。在我这里它只是在说明一个事实,就是在说明社会主义文化缔造者的期待。这是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建构的动机和实践方案,当然也包括曾经做出的对成效的评估。苏联1934年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进步文化的世界性的纲领、1966年中国激进派“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的提出,都明确表达了这一愿望。至于是否提供了“普遍经验”,提供了什么,达到何种效果,对“世界文学”作出什么贡献,那是需要另做具体分析。譬如说“作为生产者作家”的命题的提出,还有文艺与大众的关系等。在有关经验、成效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不仅是现在,过程中就有激烈争议。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说,争议不仅发生在外部,更发生在内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是否存在问题,对表现“远景”的绝对化强调是否妥当,是否开放它的“边界”,朝什么方向开放……其中,焦点问题是这一“主义”是否产生足够的被认可的作品。巴人1957年在《人民文学》的短论《“拿出货色来”》就是回应这个质疑。卢卡契1956年则有这样的抱怨:“现在形成了那末一种公开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那么一些平常的、机械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正是为我们的批评家所捧上了天的……我们没有以我们在自身中存在的力量登上世界舞台。”(《近代文化中进步与反动的斗争》)这样的看法当时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捍卫者的批判理所当然。但是他的提问仍然没有失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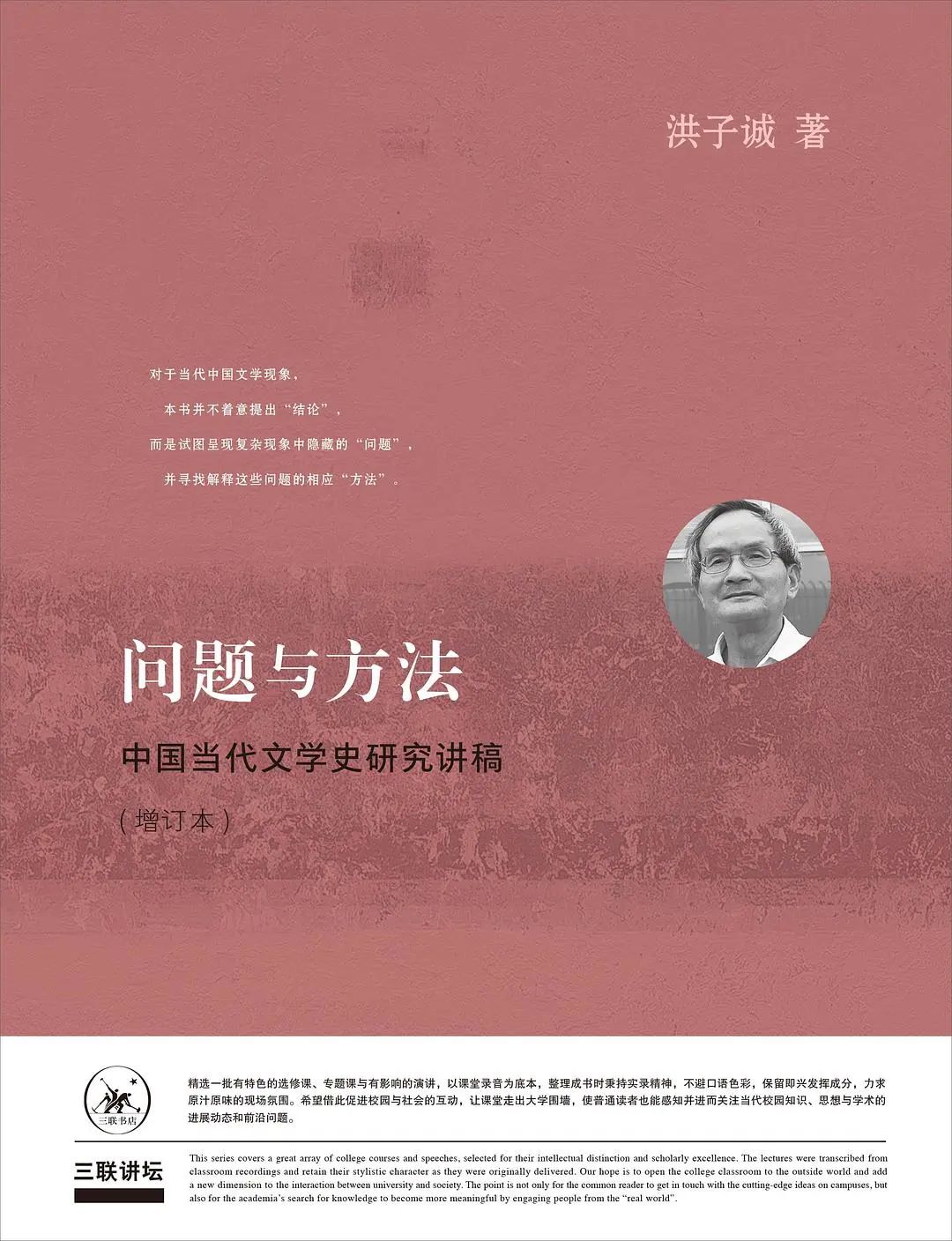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李静:这里想进一步请教您,我在阅读过程中感到您书中讨论的“世界文学”似乎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视野下的“世界”,而另一层是“文化”的“世界”,前者不断处于博弈、斗争与变化之中,而后者则是永恒、连续与超越的。在您的笔下,那些曾经的主流与异端,穿越时势沧桑,最终又回到文化价值秩序的某种“常态”之中。您在写作中是否隐含着这样的二元论,而文化正是您所说的“仍有稳定和值得信赖的事物”?这些值得信赖的事物,即便只能旁观或流浪,即便非常小众,仍然是人保持尊严的方式?
洪子诚:两个世界的说法,有点像是文学、政治二元论的味道。我大概不是政治/文学的“二元论者”,不过从80年代开始,确实在文章中有这样的想法,即文艺应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建立自身的“传统”,不能和政治完全捆绑在一起。这不是说文学要脱离政治,也不是说文学不应处理现实政治问题。相反,对关系到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切,是它的重要责任之一。所谓“独立性”,是指文学在处理包括政治等问题上一定的“自治”权力——想象、虚构和形式选择的权力。我们需要文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超越性。这本书的多篇文章谈到,社会主义文学的内部论辩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强调社会主义文学特质的同时也要重视它的开放性;不同历史时间、不同“阶级属性”的文艺是否可以相遇、相通,是争辩的要点。比如,秦兆阳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论述,钱谷融关于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爱伦堡认为读19世纪的《红与黑》比读一些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感觉更亲近。奥地利共产党人费歇尔认为,在50年代中期离世的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虽然“极不相同”,一个是“人道主义与讽刺的最后一个伟大的资产者”,一个代表“正在诞生的世界”,但他们有重要的共同点:“竭力保卫人,反对混沌、谬误、虚无的威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冷战的地缘政治格局,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政治意识形态的“通道”是狭窄、无法调头的单行道,文化界、文学界仍不断出现拓展边界的呼声。加洛蒂1959年出版的《人的远景》一书,就是试图对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指出这些流派在掌握“完整的人”的共同努力中可能存在的不谋而合之点。他的这个主张,在当年的“地缘政治”情境下,自然被批判为向资产阶级谋求调和的修正主义。我想,这种自觉站立在路口,开放地试图接纳看起来“敌对”思潮、流派的人,正是因为如《契诃夫手记》中说的,意识到在“有神”和“无神”之间还有广阔的空间;这一空间的不同事物,有着“稳定和值得信赖的”“本源性”的存在。
李静:说到这里,我回想起2017年您的《材料与注释》出版时,李浴洋与我曾以《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为题采访了您。如今看来,“制度与人”依然是理解您这本新著的重要切入点,并对人道主义给出了更深的理解——并未简单地回归19世纪人道主义,而是在深入反思“20世纪”经验之后继续“寻路”。在对文学与政治、文艺生产制度与文艺生态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在乌托邦的极限之外,您再次追问“人”的价值与意义。那么,您是否认为“人道主义”作为中国语境中的超级话语,被一定程度上误解,而对个体的重视是否是激活思想主体性与历史潜能的必要条件?而这与重视结构、制度、阶级的社会科学方法又是何种关系,互斥、互补或是对话?
洪子诚:人性、人道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争论的焦点问题,在政治、哲学、文学领域都是这样。我这本书的不少文章,如对苏联电影新浪潮批判,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边界的讨论,都或隐或显地牵涉这一主题。这并不是纯理论的探讨,而是现实紧迫情境的驱动,也就是对现实问题所作的回应。80年代初中国的人道主义讨论也是这样:如果离开“文革”这一背景就无法真正认识这个现象。1965年,阿尔都塞出版了《保卫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口号,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他认为,对于对斯大林的错误的批判,应该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种种历史条件,而不应该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意识形态火焰”,这并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阿尔都塞的批评是对的,从“新时期”的文学状况看,也可以认识到只把人道主义当作情感火焰,而未能深入探索产生灾难的历史条件的缺陷。他认为,马克思只是在还信奉费尔巴哈时才是人道主义者,而在“认识论断裂”后,已与人道主义决裂。他认为人道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口号可以起一定作用,但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不过,这种讨论不应降低人道主义(即使作为一个“口号”)的巨大意义,它的价值(即使只是“意识形态火焰”),不应导致对历史上发生的灾难的无视,在文学上仍应充分肯定它的伦理、价值。
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上,我确实在一个时期内很重视制度、体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的研究相当忽略这个方面,没有认识到“制度”在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活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目前,对这个方面的研究已经不限于政治、社会制度方面,一个重要的现实是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对人的生活,也对文学“生态”产生的那种强大的制约力量。但是,这也不能取代对人、个体的关注。一方面,制度需要人来实施,并且要落实到人的感性生活,人的社会活动,以至情感状态,否则制度自身就是失效的。另一方面,相似的境遇中,在相同的制度下,不同个体的应对、表现有很大甚至相反对的差异。这也就是文学史研究不应以关于“制度”的一般性描述作为终点的原因,也是前面说到的,史景迁、木山英雄他们为什么会把差异的个体作为辨析的关注点。
李静:您上面所说的这些研究方式、研究关怀最终是由本书的写作来承载和体现的。您是公认的有自身语体与文体的当代文学史家,这本新著便展现了您强烈的学术风格、深厚的审美积淀与真挚的人文关怀,这些要素共同凝结出这部作品的生命力。这力量既来自您选取的历史本身,也离不开您对语言本身的珍视、斟酌与“编织”。最直观的体现,便是您对诗歌的青睐。您在《〈《娘子谷》及其它〉:当代政治诗的命运》一文中信手拈来,关于诗歌的阅读经验(也包括对音乐的欣赏,事实上对于不同材料的统筹交响,也如同指挥家一般)流动、串联。此文最后,您也直接附上汪剑钊的《娘子谷》译本,与王家新所忆起的、收入同本诗集的《戈雅》。文学文本大量、直接地进入,与精准文学史研究交相辉映,对读者产生冲击。您是否可以谈谈自己理想中的文学研究写作样貌?
洪子诚:这其实这是我的向往,但是难以实现。我读过许多出色的文学理论批评文字,观点主张不说,它们也很讲究语言,讲究文体章法,也融入作者个人的体验、情感,可以当文学作品来读。我的一些文章,或文章的个别段落或许还可以,总体而言问题不少。这次将它们集合成书,毛病就暴露得很清楚。譬如语言、章法、论述方式无意中形成的公式、套路。举个例子说,如多次使用“……图像”的描述方式:司汤达在当代中国的图像,马雅可夫斯基的图像等。思维、语言惯性形成的公式化,是很恼人的事情。公式化概念化是五六十年代文学写作一个饱受争议的,却难以克服的“痼疾”。当时指的是文学创作(诗、小说,特别是戏剧),其实,理论批评这方面情况也很严重。不过理论批评文章的文体问题好像不大引起注意。这本书中讨论纪念莎士比亚的一篇,就谈到批评的僵化的“语法”现象。记得1956年樊骏先生在《人民文学》上有一篇短论《既然……那末……》,也是针对当代批评的公式化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最主要当然是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的制约,但也与批评家的修养——学识、想象力、才情、语言敏感相关。想象力、沟通由各个渠道获得的体验的灵感,也是批评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我在什么地方说过,20世纪50年代同样是批判南斯拉夫维德马尔“修正主义”的《日记片断》,里夫希茨(苏联美学家)和刘白羽的文章,它们之间在学理、修辞的差别真的不可以道里计。对比着读,有一种沮丧感,体会到“权力”下激昂空洞的言辞的苍白。
写出有生命温度的、有较强可读性的文字,总是我们的梦想。我也有过努力,但这不是下决心就可以实现的。岁数一大把,各方面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定型,现在再努力也无济于事了。
李静:那在您看来本书写作中是否还存在什么遗憾,还有哪些意犹未尽的话题或研究对象呢?
洪子诚:每本书最后留下的都是遗憾;所以我不大回过头重读自己写的东西。这本书选择的个案带有很大随意性,也太局限原先积累的材料而难以向更大方面拓展。书里有些部分谈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个有着多种可能性的时间。但由于知识条件的极大限制,虽然想能有深入一点的讨论而没能实现。这样的年龄和精力,“意犹未尽”也就只能留在心里了。
李静:总体来看,我认为《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价值已超出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更像是一部社会主义文化史,如同您书中数次引用的《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那样,当然后者的时段与容量要更广。您作为时代的同行者,所撰的这些文章不仅抢救了历史记忆,而且同样以“艺术打破了沉默”,唤醒了一种面对历史的伦理态度。您书中提及的对象,依旧时时浮现。比如疫情时代青年人对卡夫卡的仿写,比如《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继续推出新的中译本,并化身为自然主义文学杰作,再比如《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苏联歌曲仍是许多当代电影的关键元素……历史并未远去,而也只有在“当代性”的视野中,您的论题“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也才成立。在我的阅读观感里,您在每篇文章的末尾,似乎都将笔调隐隐指向未来。那么,就让我们顺着“时间的漂流”结束这次访谈:您是如何理解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历史研究的关联的?您身处的当下语境对本书的写作发挥什么具体作用了吗?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洪子诚:有在文章结尾“隐隐指向未来吗”?好像没有。“未来”是什么样子,我真的不知道,我有点接近现在大家批评的“虚无”的消极态度。因此我只谈历史,从不敢预告“未来”。但是我谈的历史问题,多多少少和现实有直接、间接关联。譬如对社会主义文艺的评价、文学制度、人性、苦难记忆、文学性、历史叙述的性质……譬如说,在后现代绝对主体幻觉打破之后,“自我”的存在与责任。而对于一个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者来说,他的主体性是否就必须消失于社会主义文化要求之中?孤独、追求自由的个体是否也可以成为这一责任的承担者?
文学批评、研究一方面受制于批评的对象,也受制于历史形成的模式、成规,但也为个人生活经验,为每个人都有的、不同的乌托邦幻梦所制约与推动。在我的当代经历中,目睹许多悲剧性的失误,这些失误有的今天仍在重复、重演——这无法不在研究中得到体现。好的,先谈到这里,也谢谢你的提问。
- 视差之见: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描述与理论反思[2022-11-16]
- 加快推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对外传播[2022-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