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长书 | 《沿途》:在新旧交替中踏浪而行,与时代交汇的心灵景观
2024年,中国作家网特别开设“短长书”专栏,邀请读者以书信体的方式对话文学新作。“短长书”愿从作品本身出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愿从对话中触及当下的文学症候,既可寻美、也可求疵。纸短情长,我们希望以此形式就文学现场做出细读,以具体可感的真诚探讨文学的真问题。
陆天明是志在为一代人立传的作家。在“中国三部曲”之一《幸存者》中,他写下青年一代在上世纪60年代投身边疆建设的故事,他们经历的磨砺与伤痛让人难忘。第二部《沿途》则将时间延续到大历史变动之后,青年人返乡重归京沪,从新的环境中寻找自我。正如小说扉页的文字,“我们这代人一切的幸与不幸都缘于我们总是处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替的漩涡中。”“短长书”第4期,评论家王雪瑛、杨毅从《沿途》出发,探索无尽沿途里的历史内涵与时代命题。
——栏目主持人:陈泽宇
本期讨论:《沿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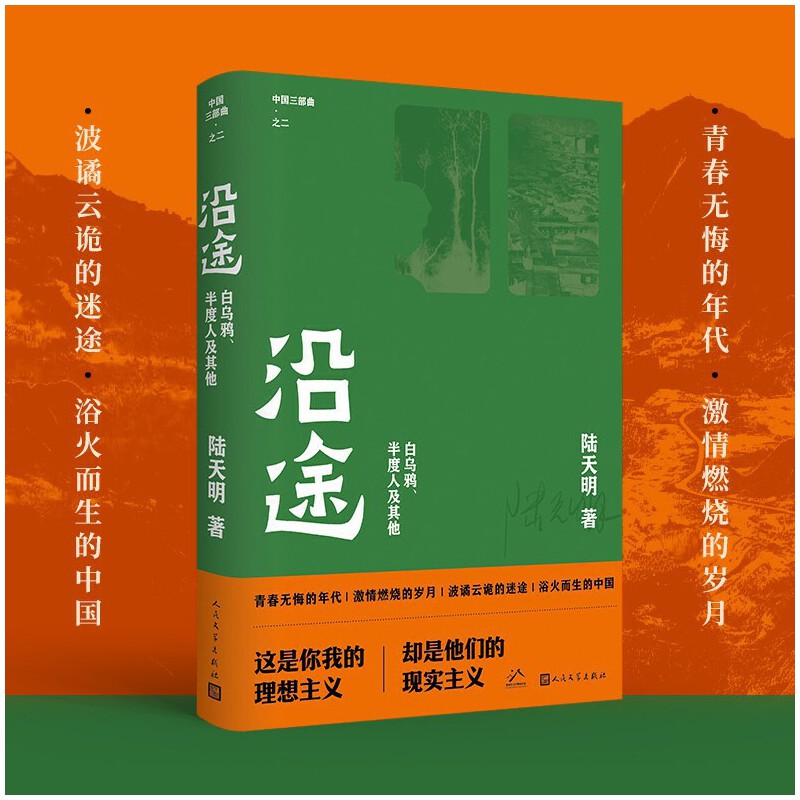
《沿途》,陆天明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入选作品。
作为“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沿途》承续了《幸存者》的脉络,谢平、向少文、李爽在大西北的卡拉库里荒原经历的种种磨砺与伤痛在陆天明笔下依次展开。
十几年的知青岁月之后,他们返乡重归京沪,崭新的时代已然铺展在他们面前。然而,在新旧交替的漩涡中,反腐斗争、思想异化、阴谋罪孽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如一叶扁舟,裹挟其中,破浪而行。面对风云翻覆的重大变局,他们恰似时代的骄阳,坚守信仰之光不灭;又似一块块拼图,际遇交错咬合,演绎出一首生生不息的人间史诗,让我们得以看清当代中国的来路与前程。
作者重返历史现场躬身勘察,以饱满情感和泣血之思描绘出这群共和国同龄人的思索、追求和奋斗,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备忘录。
作者简介

陆天明,作家,编剧。祖籍江苏,生在昆明,长在上海,两次上山下乡,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度过难忘的青春年华。后长期供职于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长、名誉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黑雀群》《木凸》《高纬度战栗》《命运》《幸存者》等长篇小说和多部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影视剧。曾多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飞天奖、金鹰奖,以及国家图书奖。
短长书

杨毅,文学博士,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讲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小说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发表论文及评论多篇,主持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
雪瑛老师:
您好!很高兴和您以通信的形式谈谈我阅读陆天明长篇小说《沿途》的感受。说来惭愧,最早知道这个作品还是听您说起,然后很快看到了您在《文汇报》上和陆天明、陆川的对话。就像您说的,《沿途》“以现实主义的有力笔触勾勒出谢平、李爽、向少文为代表的人物形象,回溯他们在大西北农场经历了磨砺与伤痛的青春岁月,追踪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相遇崭新的时代,新旧交替中的观念碰撞,自我反思中的踏浪而行”,给我最大感受不是叙事上的,而是作家投入情感来塑造人物及其诸多事件。“这是你我的理想主义,却是他们的现实主义。”虽然《沿途》的叙事手法大体上是现实主义的,但小说中的人物不完全受到事件本身的控制,主人公内心的想法和触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灵历程和人生轨迹,才是这部作品的核心所在。
这些几乎和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同龄人,亲历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用陆天明的话说,“这一代人最典型的生存特征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变。我们经历了人生的巨变,可以说当年中国之巨变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在我们这代人的生命历程中。”小说中人物也有类似的话。但要意识到这种心灵和生命历程中的“变”,既是个体的更是历史的,而且根本上是历史的。
《沿途》从扎根大西北农场的上海知青结束插队生涯,面临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何去何从写起,但在叙事时间上不断跨越新旧两个时期,更多展现上述三个人物在时代转型中的心灵激荡。《沿途》不是直接描写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生活,而是先从谢平等人在大西北的经历出发,进而从历史记忆中,把握新时期后个体的精神状况。
尽管主人公的经历让人联想到知青文学,但《沿途》既不是知青文学中的“青春无悔”,也不是对历史简单地否定或批判,反而悬置了价值和道德判断。不过,不时插入作家的议论,又表明叙事者的在场,意味着叙事者既置身其中也能跳脱事外地看待人物所处的历史境遇。
谢平等人从大西北农场回到大城市后,没有享受安逸的生活,而是在激变中思考自身的处境。无论是谢平的思想转变,还是李爽的婚姻风波和向少文的仕途生涯,作家没有猎奇式的写法,而是在写实的基础上,不断逼近和追问着他们内心的想法,展现他们在时代转型中的心理。正如您访谈提到的,谢平的笔名,“白乌鸦”和“半度人”,无论能否上升到哲学意蕴的高度,都是主人公人格处于不断摇摆和未臻完善的“中间状态”,也是作家对人物精神状况的概括。这甚至也影响到了小说的叙事方式,即无法对这代人的精神状况作出明晰判断的“中间态”,似乎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进行时,以至于我们今天仍处于这种“半度人”的状态中。
我认为《沿途》的价值不在于叙事本身,而是带有记录中国社会思想史和心灵史的意味。如果说作家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来窥探处在新旧两个时期的人的精神状况而带有心灵史的话,那么,小说还隐含着关于转型社会内的知识界和思想界的状况,构成小说作为思想史的路径。比如小说开篇多次提到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新思想和新思潮对知识界带来的影响等等。这也使小说更多聚焦精英阶层的思想和生活,而对更普遍意义上的,基层社会生活关注不多(比如对向少文仕途历程和心理的把握相当精彩,窥见出作家以往涉猎的官场或反腐小说)。但精英阶层的思想状况和基层的社会生活,构成何种关系,似乎在小说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我感兴趣的是,和年轻读者通过史料文献把握作品不同,您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是否感触更深?
如果说有不满足的话,《沿途》聚焦转型期个体的精神状况,但又没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始终在历史与个体之间摇摆。虽然从历史记忆中走来,但又没能反思历史之于个体意味着什么。因为我觉得对历史的书写不应放弃反思立场,更何况是对关系到无数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另外,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沿途》整体上的叙述比较流畅,但故事的叙事时间过于跳跃,又没有明显的逻辑线索或指示语,只用泛指代词(比如“那天”)表示,读来显得有些错乱。这些只是我的粗浅看法,非常期待学习王老师的高见,《沿途》带给您哪些惊喜又或者遗憾。
期待您的回信!
杨毅
2024年3月18日于天津

王雪瑛,《文汇报》高级编辑,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曾获2014年全国第六届冰心散文优秀作品奖。著有《千万个美妙之声——作家的个体创作与文学史的建构》《倾听思想的花开》《访问迷宫》《淑女的光芒》等作品集。
杨毅您好!
我仔细地阅读了您的来信,很高兴我们交流关于陆天明的长篇小说《沿途》的读后感。去年8月初,我和陆老师做过关于这部长篇的对话,上海书展期间,我又和何向阳老师、吴俊老师一起做了新书分享,您的来信,让我再次回味《沿途》,作为不同代际的读者,我们的阅读体验会丰富《沿途》的“年代感”。
意大利作家埃科曾说:“我们终身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何而生,为何而活。”《沿途》就是陆天明要书写的属于自己的故事,当然这个自己是作家的自我,更是同代人,他以《沿途》书写同代人的心灵史,为历史留下一代人探寻前行的身影。
这代人亲历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用陆天明的话说,“这一代人最典型的生存特征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变。我们经历了人生的巨变,可以说当年中国之巨变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在我们这代人的生命历程中。”您的来信不长,对这部长篇的核心内容抓得很准:“这代人心灵和生命历程中的‘变’,既是个体的更是历史的,而且根本上是历史的。谢平等人从大西北农场回到大城市后,没有享受安逸的生活,而是在激变中思考自身的处境。无论是谢平的思想转变,还是李爽的婚姻风波,和向少文的仕途生涯,作家在写实的基础上,没有猎奇式的写法,而是不断逼近和追问着他们内心的想法,展现他们在时代转型中的心理。这代人的心灵历程和人生轨迹,才是这部作品的核心所在。”
我也想从这部长篇的人物塑造谈起。因为如何呈现时代转折时激起的大潮奔涌,文学作品擅长的是塑造经历转折大潮冲击之后的人物。作家对自我和同代人的反思,对时代和历史的审视,往往是融汇在人物的塑造、叙述的细节中,这代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值得我们深思。
《沿途》起笔不久,叙写了三个主要人物的出场,主人公谢平带着妻儿小满和小别根离开卡拉库里直奔北京。他们是在某报驻京记者站的“代理副站长”李爽、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向少文这两位好友不断的电话和信件的催促中来到北京:“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到了必须沉下心来做前半程总结,认真规划自己后半生的时刻”。而谢平带着妻子来北京治病也是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这两个原因互为隐喻:时代转折后的人生选择犹如人生的重新出发,与治病救人一样重要。
谢平有多个笔名,“半度人”、“白乌鸦 ”、“麦田”、“吐瓦克”等,用于歌词、杂文、随笔和时局短评写作,已在坊间引发热议……他们三人曾经日夜相处,同住地窝子,同吃苞谷馍,一起在大漠胡杨红柳窝里出生入死……但是他们分别几年,经历着时代转折的关键时期,李爽和少文已经难以认识谢平内心世界里的思潮涌动,无法想象昔日最熟知的谢平写出了如此“陌生”的文章。时代激烈的变化就这样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
谢平是一个思想者、一个精神探索者,他曾经遭遇过误判、改判和平反,他在坎坷的人生路上前行,感到自己像风暴潮中的破帆船,又像云雾山中的小木屋。远在上海的应奋姐成为他的心灵对话者,精神上的“橡树”。他每次见到应奋都会莫名地激动,感受她谈吐中的思想,笑容中的暖意。还有对“半度人”颇感兴趣的孙涛,是他发现了这许多笔名的主人就是谢平。他有着非同一般的家庭背景,对解冻后的时代潮涌非常敏感,他研习中国经济,他思考改革态势、环球动向,他是“向涛头立”的时代弄潮儿。陆天明折返历史现场,以自身参与和见证的经历,围绕着谢平、李爽、向少文这三个主要人物,构建小说的人物群像,回溯时代变迁的激流中同代人的重新寻找自我定位,深入梳理同代人的精神历程。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情感和生活、欲望和动机,有着不得不面对的抉择和焦虑,没有“好人”与“坏人”的简单化标签,而有着各自的成长曲线。人物之间常常展开辩论,关于理想与现实、名利与人格、异化与人性等,小说通过辩论来揭示人物在直面现实时,对自我的反思,对理想的考量。人物之间的辩论,其实也是作家内在自我的对话,从而提升整部小说的思想深度。
我简要梳理小说人物随着社会转型、时代发展、人生境遇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审视的过程,是为了回应你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沿途》聚焦转型期个体的精神状况,但又没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作家的思索和态度是借助人物塑造来完成的,小说中人物的选择和态度很明确,他们将时代变革中的大浪淘沙当成又一所“我的大学”,在这所新的“大学”里,学会“不必疾风暴雨,也无须电闪雷鸣”,“从心灵伤口里长出的应该是什么?必须是翅膀。”谢平貌似与世无争,却坚定地去守望、润泽麦田的未来。小说中的人物还多次引用罗曼·罗兰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以后,仍然热爱生活。”在陆天明的笔下,人们在面对理想主义时,不是只有非此即彼的两种结果,而是挖掘时代转型中人物面临现实考验时的复杂人性,他提出值得深思的概念“半度人”,小说人物之间推心置腹的对话中,也提到:“你我都还处在不完善不完美的‘半度人’阶段……”回望历史现场,描摹同代人的心路历程,并不是轻松的事情,陆天明坦言,“认识和获取真理的过程并不像许多青年朋友想象的那么愉悦,认识自己和获得自我真相的过程也许更漫长,更痛苦”。可见“半度人”不是一种修辞“翻新”,而是一种对自我状态的辨析与自省。陆天明不掩饰生活的骨感,不回避人性的复杂,不丧失理想的坚守。《沿途》呈现出时代大变迁下错综复杂的人生际遇、命运转折与人性变化,而不是获得一个简明易懂的结论。雅斯柏斯曾说:“人不完整,但他永远向着未来敞开大门。”小说的魅力在于提出有深度的问题,提出引人关注和思索的问题,“半度人”就是一个有深意的、值得咀嚼的“问题”:我们无法获取终极真理,但总在接近真理的“沿途”中。
你在来信中还提到,对历史的书写不应放弃反思立场,我很认同。小说开始就描写了沉重的一幕:枪声响起,白乌鸦惊飞,钟绍灵倒下……这写实的悲剧性的一幕,同时也蕴含着象征性。这个人物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但是陆天明对他的处理极为精要,从小说开头布下的悬念,一直延伸到结尾,谢平是带着一颗沾着血迹的小石子离开卡拉库里的,蕴含着作家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您提出的问题有深度有力度,体现了青年评论家的敏锐和阅读生活、分析作品的能力,让我又一次“开卷而思”这部厚重长篇承载的历史内涵与时代命题,这也关乎有历史跨度的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命题。我想优秀的作家往往将思想和态度隐没在叙述的峰峦、人物的塑造、小说的结构中。记得张炜曾经说过:“小说中思想的深邃力量往往藏在浑茫的文字深处,当读者合卷离开时,它们会不声不响地一直追随着他们。”
我的大学岁月相遇了风起云涌的“改开时代”,相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浩荡奔流。从本科到读研阶段,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品、“走向未来”丛书、西方现代派作品选等成为我的枕边书。当年的我年少青涩,16岁就读中文系本科,从校园走向校园,缺乏社会生活的经验和历练,常常思考的是自我与时代、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如何突破自我的有限,认识广阔复杂的社会。我曾经很羡慕比我年长许多,有着丰富社会阅历的那代人。通过阅读《沿途》,让人到中年的我更深入地理解那代人的心路历程,他们在风雨中的艰难跋涉与时代交汇的心灵景观。感谢陆天明老师的创作,为历史留下珍贵的备忘录。如果三个主人公的职业、身份等“人设”的反差更大,会延伸出更丰富的社会生活层面,关注到如你所说的“更普遍意义上的基层社会生活”,“沿途”的时空中将展开更为广阔的时代风貌,生生不息的人间史诗。我们期待着陆天明老师“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
王雪瑛
5月15日
“短长书”专栏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