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家洪子诚
来源:《中华文化画报》 | 贺桂梅 2018年09月13日09:04
一
在我心目中,洪先生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学者。他1961年本科毕业后就留在了北大中文系任教,是资格很老的“老教师”。人们很难意识到,80年代风头很健的“青年学者”如钱理群、赵园、黄子平、曹文轩、戴锦华等先生,其实是洪先生的学生辈。虽然,当代历史的错乱之处也在,洪先生和钱理群先生事实上同龄,都是1939年生人。洪先生1999年出版36万字的代表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已是花甲之年。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他是90年代才开始活跃起来的学者。我甚至有一两次听人开玩笑:原来洪子诚是个老先生啊,我以为是年轻学者呢!其实《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之前,洪先生已经完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等重要著作,只是名声和影响还在比较专业的学术圈内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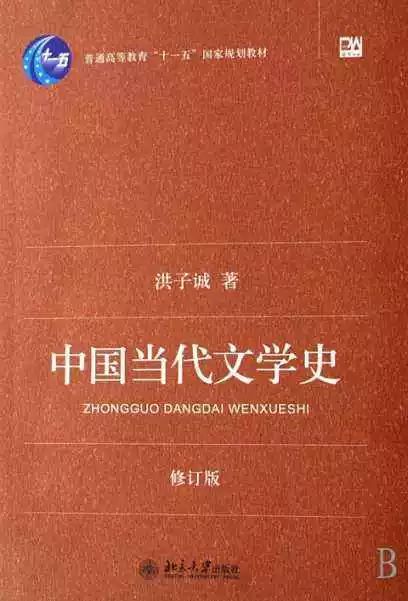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94年我决定师从洪先生的时候,他刚刚结束日本东京大学的两年教学任务归国。他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我是因为听了吴晓东、韩毓海等年轻老师的鼓动,选择洪先生做导师。不过,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坚定了我的选择。1993年,北大出版社在校园内有一个很小的门市部。因为书太多,一些折价书摆在院子里。我从中挑选了一本绛红色的精装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因为那些作家和流派与我喜欢的当代文学相关,虽然读不太懂,但是打折书,决定买回去慢慢看。我那时完全没留意过“洪子诚”这个名字。奇怪的一幕是,我走到门市部的柜台交钱时,一位书店工作人员对售货员大发雷霆:洪先生的书怎么可以折扣这么低!把他的书全部搬到室内来!我没弄懂事情的原委就赶紧离开了,当然,还庆幸用很低的价钱买了一本很好的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用如此尊敬的态度谈到另一个不在场的人,而且,也是第一次在校园里听到有人用“先生”称呼一个老师。因此印象深刻。
第一次见到洪先生真人,是在他北大蔚秀园的家里。我不请自到,拿着几篇自以为得意的论文未打招呼就去拜访他,并且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要求做他的研究生。洪先生坐在堆满书的房间里接待我,温和地和我谈话,谈些什么都忘记了。我的印象里,一点都没有紧张的感觉,反而觉得洪先生有点局促似的。后来在洪先生面前,我一直都很自如甚至张狂,虽然我常觉得自己生性拘谨。他总是很平等地交谈某些问题和某些书,还会反过来问我的态度和看法。
1996-1997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史》最后收尾的那段时间,因为洪先生生病,所以我帮他做一些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并模拟他已有的样稿、思路和笔法改写了最后三章的初稿。在新书研讨会上,这三章受到了最多质疑,让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那只背后站着老虎的狐狸一般。幸好这三章洪先生后来全部重写了,我以后看到也不再脸红。但我因为这本书得到了很多殊荣。好多次,有不认识的学生或朋友过来打招呼,说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他(她)们知道了我的名字。洪先生后来在访谈文章中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史》完稿的时候,自己惴惴不安,便问我觉得怎么样,我的回答居然是“还可以吧”。这件事我没有印象。不过想想以洪先生的宽容,我这么张狂的回答也不是不可能的。
洪先生年轻时的腼腆和低调被很多人提及。最近出版的《两忆集》、《回顾一次写作》中“曝光”了他年轻时的几张照片。年轻的洪子诚那种腼腆和青涩,让我们学生大开眼界,同时也想到那时他一定是那种内心丰富、感觉细腻而又极度敏感和羞涩的人。戴锦华老师讲过的一个著名“段子”:洪先生给她们78级文学班监考,他坐在讲台上埋头看书,抬头无意间看到有学生偷偷传抄考卷,他像自己干了坏事一样脸红了。我没有见过这种充满喜剧感的场面,因此总有些怀疑这个段子的真实性。
在我读书的90年代,谢冕、洪先生牵头组织“批评家周末”,会后聚餐时,孟繁华、徐文海、孙民乐等老资格学生,在谢先生面前略有拘谨,在洪先生面前就完全称兄道弟,亦师亦友。他们敢趁着酒兴拍洪先生的肩膀,但即便醉了,见到谢先生也还是毕恭毕敬的。他们对洪先生的学问其实是极为佩服的。孟繁华后来写道:“我的一个朋友说:‘洪老师的研究真正把当代文学纳入了学术的范畴,使当代文学成为了一门学问’。其评说如何自当别论,但这样的评价足以说明子诚先生在青年学人心中的位置”。所以也有人说,他们很“怕”洪先生。我想洪先生谈学问时大概是让人害怕的,但是聊天时却很风趣。我常常见识到他的种种“冷幽默”,不时在课堂和会场引发一片笑声,也为朋友们平添许多乐趣。前几天,华南师大的滕威老师来京召集我们一起聚聚,电话打到洪先生家,他说:“太好了!每天在家吃糠咽菜,暗示贺桂梅、李杨他们好多次请我出去吃饭,他们就是假装听不懂!”让我大呼冤枉。
洪先生的这种平和,我常以为是人生阅历和智慧的表现。年轻时的敏感羞涩、中年时期的严肃深沉,到了老年,都化作有幽默感的包容。90年代后的洪先生,与他年轻时比起来,别有一种潇洒而睿智的风采,仿佛许多沉重的东西,这时都得到了舒解和释放,并转化为特有的人生智慧。
二
我常想,洪先生或许是最适合做“文学史家”的人。在对当代文学做学术的梳理和研究,与通过文学而感受、体认生命之间,他做到了一个学者可能达到的化境。
洪先生常常慨叹,他不如钱理群、戴锦华先生那样具有“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能力,但他也不是学院和书斋中职业化的“读书人”。他的位置介乎两者之间。也可以说,他把握到了一种关于学术、学者的独特位置。赵园先生曾这样评价:“校园对于其间人物的影响,是我感兴趣的题目。洪先生的特别之处,在我看来,也在学人而有文人气习”,又说:“洪先生常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
洪先生是学院中人,且是典型的“北大人”。1956年他17岁,从南方一个小县城揭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他的求学、就职、生活、学术研究等,就都与这个叫燕园的校园联系在一起。校园的生活是平静的,但人的精神却并不平静,应该说更丰富更复杂;从50年代到新世纪,这个校园也并非总是安宁,当代中国历史中那些曲折的事件和变动,在这里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了;而在这个号称全国最高等学府中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实践,也常常处在前沿位置。这些都对洪先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经历或历史经验对许多人都是相同的,每个人则会有自己不同的应对方式。

50年代大学时期的洪子诚
称洪先生为“文学史家”,不仅是指他在学术专业上以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著称,同时也指他内在的精神气质:他是有能力将繁复、断裂甚至悖论性的当代历史经验和文学经验,进行理性的学术处理的人。他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是他能包容历史的丰富与厚重。这是文学史家的最重要品质。
洪先生常常自嘲,自己缺少把握新时代的敏感。关于50-70年代,他说:“我没有出过风头,也没有被打倒在地:这是幸运,也是悲哀”。但那段历史中的复杂经历和记忆,却成为他长久反思、咀嚼的对象。关于80年代,他常讲的一个故事,是1980年春天去南宁参加“全国诗歌讨论会”。当时诗人、诗评家都在为“朦胧诗”激动不已,谢冕、孙绍振先生的两个“崛起”就酝酿于那次会议。洪先生内心也是支持“朦胧诗”的,但他谈论的却是早已“淡出历史”的诗人田间。对自己“判断力”、“前瞻视野”的怀疑,使洪先生选择了在80年代相对冷落的文学史研究。不过,虽然不是“弄潮儿”,但洪先生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视角,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新时代。
日本学者竹内好曾这样评价鲁迅:“他不是先觉者。他一次也没明示过新时代的方向。……他不退让,也不追从。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之后,再把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我觉得这段话用来说洪先生也是合适的。他是以“挣扎”、“怀疑”的方式,将自己置身时代前沿,并在与新潮的紧张角力过程中,形成独特的自我和作为文学史家的主体意识。
洪先生受到最多赞誉的著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在北京大学的研讨会上,钱理群先生说,这部书“标志着当代文学有‘史’了”;谢冕先生则说,这本书标志着洪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的成熟”,也标志着“‘当代文学’学科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当代文学史》此后成为各高校的教材和参考书,多次再版(2007年修订重版),印刷总量达60余万册。译成英文、日文,也即将译成俄文和韩文出版,是国际学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可以说,这本书使洪先生跻身于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列,也使一个学科——当代文学——获得了相应的学术地位。
这本书是洪先生多年教学工作和参与文学史写作的结晶之作。洪先生常说:我主要是个“教书匠”。他的学术研究常和他的教学直接联系在一起。但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使他的每一次授课都成为一次思考和锤炼观点的过程。在80年代,洪先生承担了10多次当代文学史的基础课教学,每讲一次都会重写讲稿。这些讲稿的一部分,后来出版为《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是最早反思新时期文学的限度,并从作家意识的内部做出批评和探讨的著作。1991-1993年间,洪先生在东京大学的教养学部讲了三个学期的文学史,其讲稿历经曲折出版,即香港青文书屋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在此基础上扩充、展开和推进,洪先生完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2002年退休以后,洪先生曾三次受邀到台湾的大学讲课。一位台湾老师写道:“目前在台湾专攻中国现当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大概很少没旁听过洪先生的课的。”
洪先生的另一特别之处是,历史的机遇和偶然,使他在50-70年代、80年代,都参与了文学史写作。还在学生时代的1958年,洪先生和其他当年的六位学子,在高校学术大跃进的集体写作文学史热潮中,编写了第一本现代新诗史《新诗发展概况》。尽管对这部年轻时的“造反”之作普遍评价不高,但参与写作的先生们都承认,这事实上也成了他们学术研究的起点。洪先生与刘登翰先生后来在80年代再度合作,在此基础上全盘重写了当代部分。这就是影响很大的第一部当代诗歌史著作《中国当代新诗史》。

刘登翰、谢冕、洪子诚
1977年,洪先生参与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的组建工作。为给恢复高考的学生编写教材、也为适应新时期的变化,教研室的五位老师编写了《当代文学概观》。这是文革结束后出版的当代文学教材中最早的一部。1986年修订重版后,很长时间还被一些高校用作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史》超越了此前的写作范式,将当代文学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本书的另一意义,被认为是第一部个人独立完成的文学史著作。但此前的写作和研究经验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而是在批判性的反思中,被重新理解。在洪先生看来,学术研究不同于道德化评价,它首先应该深入某种政治(历史)逻辑的内部,去探索其被构造的发展轨迹。80-90年代当代文学史的许多研究,要么重复50年代构造出来的那套框架,要么推翻另建一套说法,而洪先生的做法,是“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勾勒这套框架被建构的过程,及其中互相冲突、矛盾的力量关系演变,从而客观地描画出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图景。
三
在洪先生的精神世界中,“历史”与“个人”构成了充满张力而具有能动性的两条轴线。这里的“个人”即研究者的主体结构。如赵园先生所说,洪先生是有“文人气习”的人。他对学术问题的处理不仅是职业化的,而是与文学、思想等一起构成了他的“整体人格”。
2002年从北大教职上退休以后,洪先生有意识地选择的一种写作文体,是从个人经验角度切入,重新思考当代的历史、学术、文学问题。这包括《我的阅读史》《两忆集》以及他牵头组织的《回顾一次写作》。应该说,洪先生的历史记忆和反思能力是超常的,他极大地凸显了“个人经验”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同时,洪先生性格与精神中那些“坚硬”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些反思中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
洪先生第一次在《语文课外的书》一文中,提及出生基督教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我的外祖母和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高小上的是教会学校,所以,读(和听别人读)得最多的,是《圣经》”。《圣经》对洪先生的影响,其一是对“界限”的意识,“一个人要时刻保持对善恶、美丑、经验和超验区分的信心”,所以他认为自己在最基本的方面,仍是个“二元”的信仰者;其二是对词语的感觉,“文字能创造一个世界,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奇妙、甚至神秘的事情。”后者使他从初中时代开始,变成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觉得书本为我提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起我见到的,每日所过的日子来,要有趣得多”。这种对于文学的爱好一直持续下来。可以说,没有文学爱好者的洪子诚,就不会有文学史家的洪子诚。
2012年,洪先生出版《我的阅读史》,提及自己不同时期阅读的、影响甚深的著作(和人),也勾连起不同时期的阅读记忆。其中最精彩的是关于契诃夫、《日瓦戈医生》和《鼠疫》的写作。从这些文章里,我们可以窥见洪先生精神世界的深邃之处。一个时期的阅读心态、当时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感受,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结合起来,同时也包含了对这些理解和感悟的反思性思考。学术观点因此不仅仅是理念,经过丰富人生阅历的咀嚼与思考,而成为了某种“智慧”。比如从契诃夫那里理解的“怀疑”,比如从《日瓦戈医生》那里理解的“生活”和“大自然”,比如从《鼠疫》那里理解的“艺术”与“道德”的张力……
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先生在为洪先生台湾版的《阅读经验》所写的序言中,提及两人的有趣交往:在如何看待文学的本质上,两人分属两派,洪先生是“文学自主派”,而吕先生是“灵魂工程师派”。两人因此常常开玩笑地互相争吵,“彼此嘲讽”,但“交情却越来越深厚”,“这让我的学生颇感奇怪”。吕先生认为原因在于,“我们两人都是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每个人如果真心实意的寻找自我生命的价值,常常就需要某些特定的文学作品来作为这种价值的依托”。在这一点上,文学关联的不仅仅是某些作品,而是“人生态度和美学态度”,是某种“信仰”一样的东西。
洪先生的文学趣味,正如他的音乐爱好,都偏于俄国、东欧作家。这与50年代读书期间的经典资源相关,也与洪先生的个人性格相关。在某一处,他提及伯林谈论的“法国作家”与“俄国作家”的差别:前者是专业的小说家,而后者则总是要求将他的“整个人格”都与文学关联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洪先生的学术、文学趣味和精神诉求,毋宁都是更“俄国式”的。
在洪先生那里,与“文学”的位置相当的,还有“诗歌”和“音乐”。洪先生不善写诗,但他一直热爱诗歌和研究诗歌。2012年八卷《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出版研讨会的答谢词中,洪先生引用赵园先生的话说道:“一生钟情于诗,是一件美好的事,经由诗而保持了审美的敏感,对文字的细腻感觉与鉴赏力”,“这确实‘润泽’了我本来枯燥、灰色的人生”。洪先生的弟子大多是诗人,同时也研究诗。比如大名鼎鼎的臧力、周瓒、冷霜、胡续冬,他们在北大校园简直可以说呼风唤雨,在粉丝群面前总是“大师”气派,唯独见了洪先生,都变成了谦逊局促的学生。洪先生曾主编过一套《北大诗选》,序言提及他和北大诗人们的交往,写到诗人们千奇百怪的笔名、王清平的字、骆一禾的毕业论文、麦芒的长发……2001年北京大学成立新诗研究所,出版“新诗研究论丛”和《新诗评论》刊物,洪先生都是主要组织者和运作者。我是洪先生弟子中少数两三个不写诗也不研究诗的学生之一。以前觉得无所谓,后来慢慢感到,不懂诗而要进入洪先生的精神世界,便欠缺了不少。
洪先生的一大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在蓝旗营他那间不大的书房里,最显眼的就是一套音响。传说北大中文系的两大音乐发烧友,一是洪先生,另一是语言专业的王福堂先生。不过洪先生一直否认他是“发烧友”,只是听听音乐而已。他和吕正惠先生的交情,除了不打不相识的文学观,可能还因为两人都是CD爱好者吧。洪先生有过两三篇文章写到他与音乐及对音乐的理解。童年时期的唱诗班经历,可能是最早的源头,但是真正变成爱好的,却是50年代北大学生校园生活中的一种社团活动:哲学楼101是固定的音乐欣赏的地点,大一的洪先生会把几乎每个周末晚上都消磨在那里。那时他还是十足的音乐外行,“有时候不过是想安静地坐在那里,抛开为生计的处心积虑,听那些仿佛来自心底,但又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我常常想象,在枯燥的学术工作之余,心仪的文学作品如果提供给洪先生的是某种“生命的支点”,那么音乐可能就是他遐想神游的另一个美妙世界了。
当然,除了这些“高雅”的爱好,洪先生还是球赛爱好者和汽车鉴赏家,虽然他既不会踢球也不会开车。戴锦华先生开玩笑:洪老师这些都是“大男孩的爱好”。
写到这些洪先生的个人情趣,忽然会意识到他是多么的“文青”。现在这个词已经十足贬义了,但用在洪先生及他们那代人身上还是合适的。谢冕先生就毫不愧疚地宣扬“文学是一种信仰”。洪先生也一样,只是他不张扬出来而已。但这里的“文学”其实并非所谓“纯文学”,而是可以给人不断提供精神滋养的“经典”。在这一意义上,文学、诗歌、音乐,甚至《圣经》都是一样的。马修·阿诺德说:文学是宗教消失时代的替代品。只要我们还需要内在精神的滋养,需要构建别一世界的精神想象和依托,广义上的文学就不会消失。也许,这是一项高尚者的事业,它与政治相关,但永远比某一时期的政治更广博,因为它创造的是无比广阔和无限可能的心灵。



